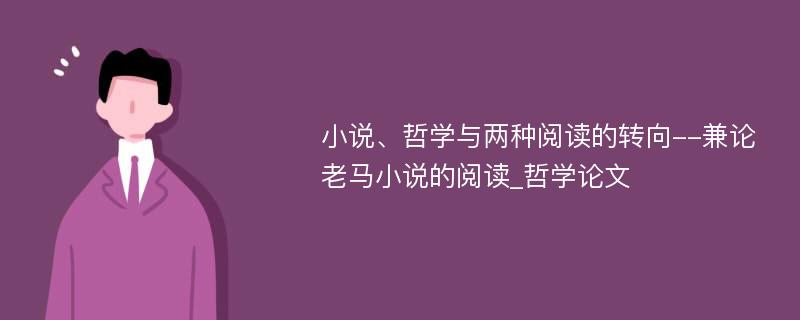
小说、哲学与二人转——劳马小说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人论文,小说论文,札记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能够证明:嬉皮笑脸、大大咧咧的东北二人转,它的最初原型,极有可能是一种古老的“二神转”。它跟原始先民祈求旺盛生殖力的圣婚仪式密切相关。圣婚仪式的核心,则被认为落实于祭祀场上神圣的淫荡,或淫荡的神圣性。它是原始先民围绕生殖活动,组建起来的舞蹈仪式,既如痴如醉、酣畅淋漓,又充满了露骨的色情意味。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的加拉阿什岩画,将淫荡的神圣性和神圣的淫荡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激烈、大尺度的舞姿,大母神肥硕的阴部与臀部在四下摇晃,男性粗壮、夸张的生殖器,则在寻找可以用于施力和冲刺的对象。它们相互激励,阴部与阳物共舞,在共同祈求生殖力的旺盛与绵延。有足够强劲的证据可以表明:圣婚仪式经过漫长的演化,终于下替为程式较为固定的舞蹈,演变为世俗性的二人转——丑角(男)或蹲下或弯腰,奉旦角(女)为轴心,以“眼睛不能离开旦”①为底线,一边转动,一边相互调情(但多以丑角撩拨旦角为主),并说出或者唱出一个个故事,以取悦观众,以对付东北平原漫长、寂寞难耐的冬季。②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民间艺术十分相似,色情也是二人转的宪法,是让观众开怀大笑的不二法宝(但又不能简单地称作远古神圣淫荡的遗迹)。③在寒冷和二人转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需要的亲密关系:寒冷渴望二人转给予温暖和笑声——事实上,除苦笑、冷笑、奸笑和淫笑等不良之笑外,开怀大笑本身就是温暖和热度的一部分,是冬季里的阳光;二人转则期待寒冷充当自己被倾听、被观看的前提——没有酷寒带来的被幽闭的漫长闲暇,二人转将丧失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或许,正是漫长、寂寞的冬季与寒冷,才培育了作为民间艺术的二人转,还有东北人特有的、深入骨髓的幽默感。④
二人转叙事的基本要点是:丑角以夸张、幽默,甚至猥亵的言辞调戏旦角(即圣婚仪式上大母神的蜕变形象);旦角则以假装的羞涩感,积极回应丑角的撩拨与挑逗。就是在这种戏谑性的一来一往中,讲述着一个个令人开怀、捧腹的故事。这种一唱一和、你来我往、朴素善意的叙述方式,充满了狂欢效应,狂欢效应则构成了二人转叙事的根本原则。和民间笑话中总是最后时刻才拍马赶至的高潮句本身不含笑意十分相似,⑤二人转中的丑角和旦角也几乎不含笑意,他(她)们的目的与功能和高潮句完全一致:仅仅是负责挑逗观者发笑,以便解除他们的寂寞与寒冷。即使丑角、旦角在表演时发出了笑声,那也是假装的,具有强烈的虚拟特征,它像伴音,但更像过门,为的是更加主动、有效地挑逗热情的观者。
“小说为动作编码,哲学为动作下结论;小说直接面对动作并以动作体现小说的目的,哲学则直接赋予动作以意义并将动作掩盖起来。”⑥小说渴望通过对生活细节的叙事性锤炼、打磨,达到认识生活的目的;哲学则寄希望于对生活进行抽象性、概念性的总结,达到知道生活之本质的目的。在古老的希伯来语中,“认识”(yada)的词源学意思是“做爱”;撒加利亚·西琴(Zechria Sitchin)对吃了智慧果之后才开窍、才赤身裸体翻滚于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有一个很大胆、也很惊人的阐释:做爱意味着“知道”(to know)。⑦看起来,在小说与生活之间,在哲学与生活的边境线上,只有存在着一种水乳交融的肉体关系,才配称“认识”生活,才能宣称自己“知道”生活之本质,因为“只有经过肉体首肯的事实,才能叫认识或认识的结果”;⑧因为“如果我们在认识任何一种事物时没有投入足够的热情,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这种事物”。⑨哲学与生活以及小说与生活,彼此间,必须构成一种二人转的关系。惟其如此,小说才可能及物,哲学才有可能把握世界。
相较于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生活,与二人转中的角色分配很相似,小说和哲学顶多只拥有丑角(即男性)的身位;惟有生活本身,才配接管旦角(即母性)的名分。生活永远是土壤,永远都是生殖的发源地和策源地:“土:吐也,能生万物也。”⑩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来源于生活(即“土”或“吐”),但不一定非得高于生活。在更多的时刻,它们有必要蹲下或弯腰,作礼贤下士状,做鞠躬致敬科;它们必须以生活本身为轴心,挑逗、撩拨以及抚摸旦角,为生活做前戏(re-play),为的是旦角能够尽快达致湿润的境地,以便配合小说进驻自己的“认识”状态,催促哲学迈向它的“知道”境界。生活就是远古圣婚仪式上的大母神,她“丰乳、肥臀、鼓腹、大阴”,(11)拥有近乎于无穷的生殖力,但这还得看哲学与小说对它采取何种态度。能否零距离进入、进入的急切或疲软,才是决定大母神或土地繁殖能力的关键。就像寒冷和二人转彼此需要,在哲学、小说与生活之间,也拥有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哲学、小说渴望激活生活的关键部位,触摸生活的敏感地带,以便达到成就自身的目的;生活则寄希望于哲学与小说的射精作用,以便让自己得到总结、表达,最终能让自己开口说话,并产下作为生殖后果的小说或哲学。作为丑角的小说和哲学,必须以生活为根基或大母神,必须“‘刮掉’理论的表面,以寻回‘人’的本质”。(12)否则,它们将处于无根状态,其毁灭必将指日可待。
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东北籍小说家,劳马想必十分熟悉二人转叙事的基本套路,深谙它的程式与习性——在他的小说中,就充满了二人转的喜剧味道和幽默气息。作为一个曾经以研习哲学为主业的作家,劳马的小说碰巧(?)有一个很隐蔽的底色,用以充任他全部小说写作的基础,如同布面坦培拉(Tempera)对涂抹其上的色块所能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基础必将培植或哺育基础之上的一切事物。劳马仿佛中国东北版的哈谢克(或哈谢克附体于中国东北的劳马),在以狂欢化的小说风格为工具,反思或考察何为哲学、何为哲学家;他在抿着嘴偷乐的当口,轻而易举就揭示出哲学和哲学家在以何种方式与生活——这个大母神——调情或舞蹈。当他轻描淡写地给出答案,并让答案成为小说写作的隐蔽基础(或称基本逻辑)后,老谋深算的劳马才在嘻嘻哈哈之中,展开自己的小说叙事——只是这个“隐蔽”的基础“隐蔽”得比较深,以至于粗心的读者往往将它忽略了。
在标题直白、干脆利落的微型小说《哲学》中,劳马令人捧腹但又以抿着嘴偷乐的神态,回答了“何为哲学”这个过于深奥的难题:“只有傻瓜和笨蛋才学哲学,因为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聪明人本来就很聪明了,不需要再学它。笨蛋想变得聪明,所以才需要学习哲学。”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即哲学教授杜某——直接为他的宠物狗取名“哲学”,遛弯时,还“死死地抓住拴在狗脖子上的绳子,不停地喊它的名字并诅咒它”。看起来,哲学就是段位不高、爬行跳跃的哺乳动物,或仅属于动物以及动物级别的智商;它是笨蛋和傻瓜用于纵横、驰骋的专有领地。这与常人心目中哲学乃“科学之母”的形象大相径庭。曾经光鲜、神圣的哲学,何以潦倒、落魄以至于此呢?而在令人拍案、击节的长篇小说《哎嗨哟》中,小说家劳马借叶老师指导高考生伊百填志愿,戏谑性地说到过哲学乃科学之母的神圣性。那一年,高考录取线创纪录地仅有一百多分,因此,叶老师很严肃地规劝伊百:“你考了四百多分,不能只学一个专业,得多学,哲学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又在它们之上。你好好想想,同样的价钱,你是买粒瓜子儿,还是买个西瓜呢?当然要买西瓜啦!西瓜不仅比瓜子大,里面还装着瓜子呢。”高考成绩近乎于录取线的四倍,在笃信哲学乃科学之母的叶老师看来,这跟做买卖一样,也得讲究个一分钱一分货,必须要购买更多的东西,否则,就对不起那四百分。哲学于是很严肃地成为伊百的首席选择——因为它是科学中的科学,而且,还绕道从周边包抄了科学,并直赴科学的老巢或洞穴。“它吓唬了人,却坚强了他的心。”(13)听从叶老师的教诲选修哲学,并荣升哲学教授后,伊百果然成为一个不懂任何实务的人,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家的门牌号,尽管他已经住在那里好几年了。但他又是一个能总结任何实务的人:“伊百习惯了‘整体把握’”,而“这是一种哲学态度”(劳马《伯婆魔佛》)。(14)整体意味着不屑于细节,不待见局部或部分。但事情的吊诡之处刚好在于,“部分是最多的,比全体还多出一个”。(15)哲学没能让研习它的人变聪明,反倒变得更笨了;研习者没能弄懂部分和全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才是生活这个大母神真正的实质。叶老师当年的严肃性和伊百多年后获取的滑稽性,在东北人劳马的小说中,构成了性质奇异的对比。这情形,似乎正合巴赫金的妙论:“一切神圣和崇高的事物都从物质-肉体下部角度重新理解,或者都与其下部形象相结合,相混淆了。”(16)
而在劳马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烦》中,伊百的同类或影子,哲学教授沙胡回老家——兔子窝镇——搭出租车时,为解乏,主动与黑车司机聊天。无论他怎样解释何为哲学,司机都搞不明白。最后,反倒是司机为哲学下的定义,“折服”了“折服”于海德格尔的沙胡教授:“哲学就是你的出租车,而我的出租车也就相当于你的哲学,都差不多!”哲学就是乡下的出租车,而且还是来路不明的黑车;教哲学和开黑车都是饭碗,相较于讨生活本身(而不是作为大母神的生活本身),确实谈不上差别。但什么又是哲学家呢?沙教授的学生普遍认为,以说怪话为专长和专利的人,大体上就算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有胡言乱语的特权。而听不懂哲学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观点:“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这个用汉语表述起来显得特别拗口的观点,正好隐隐约约、掐头去尾、嬉皮笑脸地出没于劳马的多部小说(比如《伯婆魔佛》、《抹布》、《哎嗨哟》、《烦》等)中。他是在有意讽刺海德格尔吗?从劳马制造出的普遍的小说语境推测起来,他还不至于有这种企图,似乎也不会那么傲慢,毕竟海德格尔的哲学成就举世皆知,“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更是业内人士耳熟能详的哲学表达。或许,他仅仅是想借用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大名鼎鼎的观点,来反思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注定只能作为丑角的哲学,如何与作为旦角的生活构成真正的二人转;如何从真正的二人转关系出发,去拯救哲学,为哲学输入鲜活的生命力。正是它,构成了劳马迄今为止全部小说的隐蔽基础。它是劳马小说的背景,是底色;在它之上,方能让劳马抿着嘴偷乐着,组建五颜六色的小说叙事。惟其如此,读者才能理解:为什么谙熟海德格尔全部“洋气”教义的劳马,会将自己的小说冲动,主要寄放在“土得掉渣”的东北乡村生活之上。
赵汀阳有一个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哲学的困难不在于我们缺乏知识能力,而在于生活和思想的意义是活的,它的问题不断变化,它不是认识对象,而是创造对象。”(17)所谓创造,急需要哲学以“眼睛不能离开旦”作为最低要求,死死抓住旦角的要领,紧紧盯住生活的关键部位,然后,才需要一种动词性思维做保障和保证:“它的思想问题都围绕着‘做’(to be or to make)。”(18)真正的哲学是“做”,不是“想”和“说”;哲学必须要成为可以用于做事的学问:这也是生活这个旦角的希求与渴望。但《哎嗨哟》中的哲学教授伊百先生却认为,“对于思想家而言闲着发呆就是工作。手忙脚乱时没法思考,没有思考也就没有哲学,所以,闲就是忙,忙就是闲,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正是如此这般理解自己的丑角身份,在搞笑佛学强调的辩证统一中(即“闲就是忙,忙就是闲”),才导致了哲学的阳痿与早泄;它不再以旦角(大母神或生活)为轴心,而是在看似围绕旦角,边转、边说、边挑逗旦角时,不断把自己抛向了越来越远离旦角的不归路。哲学似乎老有一种从生活中仓皇逃窜的念头和行为。或许,正是感慨于哲学和生活之间拥有一种越转越远的二人转关系,修习哲学出身的劳马,才故意拿海德格尔的著名观点开涮,以便向哲学远离人间烟火味的不良习气做鬼脸。
哲学只有与生活构成标准的二人转关系,才能在与生活的交尾中,生产出鲜活的经验。不用说,一切人类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但哲学却乐于从经验中提取纯粹的概念,由此,哲学很早就走上了概念自慰的险途(19)——自己玩弄自己的那话儿,在性质上,直接等同于越转越远的二人转关系。劳马在幽默、狂欢化的叙事中,为自己的小说写作贡献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无疑是:如果哲学不与生活发生肉体关系,或者,在哲学同生活组成二人转时,找不到旦角的敏感地带,触碰不到旦角的关键部位,就休想有零距离的、让哲学销魂的“进入”,哲学休想“知道”生活之本质,生活也就不可能同哲学一道生儿育女,产下哲学。这情形,和圣婚仪式的象征含义大有区别:男人与女人交配,父精母血,产下的是他们的后代;哲学与生活交媾,产下的是却哲学自身,尽管它也带有生活的一半血脉——哲学得依靠这一半血脉,才既能让哲学自己产下自己,又能免于单性生殖与自我抚摸。而越转越远的二人转关系意味着:哲学已经高度阳痿,它不敢靠近生活或旦角,它的“本钱”已经由二两锐减为十克;阳痿的哲学或仅剩十克的“本钱”没能力挑逗旦角,更没办法与大母神发生肉体关系,因而无法与生活生儿育女——它连旦角的一般血脉都没能继承。以概念自慰的哲学倾向于单性生殖;在自慰中产下怪胎,才是它的专利和专长。而没有后代的境况,最终让生活变作了哑巴:它既不能指望自己得到哲学的总结和提升,也没有能力发出声来,更不能讲述自己的欲望。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越转越远的二人转关系,面对巨大的生活之流,研习号称能让人聪明起来的哲学的那些人,反倒成了傻子。中篇小说《抹布》的结尾称得上意味深长。考进大学就决定再不返乡的哲学教授伊百认为,对他来说,老家葫芦镇“只是一个‘在’,而且‘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伊百知道,这句著名的怪话,只有他货真价实的傻瓜哥哥伊十才能听懂(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劳马的小说《伯婆魔佛》中)。和生理-智力型傻瓜不一样(据劳马叙述,伊百生活的那个村子家家户户至少有一个傻瓜),哲学型傻瓜是因为修炼哲学才把自己弄傻的;生理-智力型傻瓜渴望聪明,哲学型傻瓜则巴望着愚蠢。在劳马小说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中,愚蠢就是聪明,聪明就是愚蠢,这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也是一种搞笑佛学。
哲学已经阳痿、早泄和哲学型傻瓜形象的出现,构成了劳马全部小说隐蔽起来的基础或基本逻辑。从这个表面上看有些搞笑的基础或逻辑出发,劳马有权力、有能力为自己的小说叙事提出两个任务:小说如何治疗哲学的阳痿与早泄,如何善意地让哲学型傻瓜痊愈,或者,小说如何面对哲学留下的烂摊子;小说如何深度消化生活,如何与旦角共舞,以便成就小说自身。不用说,第一个任务基本上是无解的,但似乎更应该说成无所谓解不解的:既然哲学热衷于远离旦角(或大母神),乐于自我抚摸(俗称“打飞机”),自甘于阳痿、早泄的状态,那就让哲学一边去玩它的“语义空转游戏”(20)得了,小说还真的拿它毫无办法,因为哲学总是倾向于将“最伟大的爱情也缩减为一个枯瘦的回忆的骨架”。(21)小说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种情形、这哲学留下的烂摊子揭示出来;何况在米兰·昆德拉眼中,在我们时代,小说反倒比哲学更有望“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22)假如这是真的或可能的,小说又何必去诊治哲学的隐疾,去幻想拯救哲学型傻瓜呢?但哲学的隐疾和傻瓜型哲学家却有义务充任劳马小说的叙事动力,并为小说的被出生,贡献绵薄的力量——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废物都可以得到利用。或许,这就是劳马修习哲学却成为小说家的原因,何况从小耳濡目染的二人转及其叙事方式,为他成为小说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二人转不仅不能造就哲学,反倒是哲学不屑于顾及、不愿意待见的东西。
劳马小说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无时不在暗示:哲学和哲学家无法完成的任务,只得让小说和小说家去承担。但这得采取一种同哲学完全相反的态度或姿势:注定只能作为丑角的小说,不能像哲学那样在概念丛林中自我抚摸,不能寄希望于单性生殖来完成自己和达致自身。它必须同生活保持正常(最好是标准)的二人转关系,必须遵循二人转的叙事原则,必须效法远古时期的圣婚仪式。它得冲动,得有激情;它得面色潮红,必须对旦角充满欲望——称“欲火”可能更恰当。它既不能离旦角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会显得唐突、鲁莽,会惊诧了羞涩的旦角,以至于贸然间求欢未遂;太远,则又会看不见含情脉脉的大母神,也就解除了二人转及其叙事原则。总之,只有在圣婚仪式暗示的那种中间状态——即距离的中庸主义——才令小说拥有让生活(或旦角)怀孕、分娩的能力。劳马的小说及其叙事方式,跟生活保持着非常恰当的距离,在试着向“精神的最高综合”迈进:在同生活保持真正的二人转关系中,劳马的小说不仅触及了生活的皮肤(瓦莱里:“最深的是皮肤”),也从皮肤中,提炼了本该由哲学去提炼的内容——如果哲学不阳痿、早泄,哲学家没有变傻的话。
在劳马的几部重要小说(比如《伯婆魔佛》、《抹布》、《哎嗨哟》、《烦》、《傻笑》、《抓周》等)中,对历史的关怀、考量与算计,来得十分热切和浓烈。通常情况下,确实有一种叫历史哲学的东西存在,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历史哲学往往既不历史,又过于哲学:历史哲学把握不了历史,仅仅是无限靠近处于阳痿状态下的哲学。最终,是性无能的哲学居然成功地猥亵了历史。而所谓历史,就是事情的集合,但又大于事情的总量;还可以说成:所谓历史,就是生活的和合,但又大于生活的全体。劳马的小说在“知会”有“会心”的读者:所谓真正的历史或历史哲学,最终是事情的总量和生活的全体多出来的那个部分。这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小说对生活的提炼,正好对称于“精神的最高综合”,也才配称真正的历史哲学。而在所有可能被关注的历史中,劳马的小说对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最为劳心费神——事实上,这很可能是劳马迄今为止唯一感兴趣的历史段落。
历史既没有它自身的目的——历史目的论是个超级大谎言,也不具备起码的理性——历史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仅仅出于虚构和杜撰;(23)它倒是更乐于走错房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是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24)大体上,历史更愿意遵循一种非理性的摇头丸规律。(25)而在“另一个房间”里,是不是住着更漂亮、更性感的女人?她到底“在”哪个“在者的在中存在着”呢?对于这个难缠的问题,似乎有必要询问历史自身;但劳马更愿意尝试着给出答案。在他的中篇小说《抹布》里,有一个如假包换的生理-智力型傻瓜,大名叫伊十。此人喊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并于“十八岁从小学二年级主动退学”;而退学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在那个荒唐的历史时期,傻瓜伊十居然差点当上镇里的造反派头目。他之所以没能如愿以偿,是因为“生活作风”出了问题。事情的经过和由来是这样的:同一个镇子上的万瘫子无法让老婆怀孕,决定让老婆接种于伊十。万瘫子夫妇一相情愿地认为,此人至少不会把这丑事给说出去,因为他实在太傻了,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宛若上了十字架的圣子对门徒们说,原谅那些刽子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知道。等接种计划成功实施、万瘫子老婆怀孕后,傻瓜也懂得了办这事带来的快乐,伊十于是继续上门纠缠,想继续求欢,最后居然发展到“由敲(万家)的门变成了砸门和砸窗”。当镇上派人前去制止时,傻瓜伊十说出了一句很傻,但也很诚实的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毛主席也干这事。”就因为这句大实话,伊十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很不幸,傻瓜伊十不可能“懂得在游船上的忧郁”,(26)所以他翻船了。但镇上的革命群众并不认为伊十是冤枉的,他们反倒很纳闷:“毛主席根本就不认识万瘫子的老婆”,怎么能同葫芦镇上的瘫子婆娘“也干这事”呢?无独有偶,在劳马皮笑肉不笑的中篇小说《傻笑》里,又出现了一个大号为东方优的生理-智力型傻瓜:
东方优最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面前,以及在“毛主席万万岁”的时髦口号的后面加上数个、数十个甚至是成千上万个“最”和“万”字。他像背圆周率似的,一个人摇头晃脑没完没了地“最最最最最……”或“万万万万万……”说下去……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下来,东方优成了个地地道道的结巴。
自称语义与合法性都无可争议的革命,却让一个热衷于革命的傻瓜成为现行反革命,让另一个热衷于革命的傻瓜成为结巴——“结巴是那场革命运动留给东方优的纪念,也是他无限忠诚的记录”。这是革命的奇迹,也是小说同大母神结成真正的二人转关系之后,为小说带来的美好结局,但更是丑角挑逗、撩拨、调戏旦角,才得以从旦角身体内部提取出来的内容。“他们的奥秘即埋藏在生活的奥秘之中……生活杀死他们,但他们咕哝一声便唤醒了未来……”(27)遵从小说写作的隐蔽基础和基本逻辑,劳马仰仗小说从生活中提取的内容,只是小说能够提取的表层内容,更深、更根本、更核心的,还处于被提取的状态之中。而生活的全体与事情的总量中多出来的那部分,能否被小说把捉,就看丑角能否对旦角燃起更为猛烈、更为劲道十足的欲火。幸运的是,劳马就丑角和旦角如何才能构成真资格的二人转关系,有着十分精当的意识。他知道圣婚仪式比附于小说写作的实质是什么。对此,抿着嘴偷乐的小说家有一个十分会心的描写:当东方优及其父亲为如何矫正他的结巴劳神费心时,一条狗挽救了东方优的言说能力——“他去一个姓汪的家里喊人,走进人家的院子里‘汪、汪、汪、汪’地喊了半天,结果冲出一条狗,把东方优的小腿肚子撕开了一条大口子……从此,他的结巴毛病基本治好了。”革命运动给予革命者的“纪念”和“记录”,终结于一条本地土狗的冒失举动。这意味着貌似处于历史腹心地带的革命,根本不是狗的对手;历史的非理性、历史的不可测度性以及历史的走错房间性,由狗的冒失举动,被作家劳马鲜活地呈现了出来。
“如果历史的暴力能以加括号的方式来涵盖和压抑,那么人们不禁要怀疑,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不也就一同销声匿迹了吗?”(28)劳马的小说在轻描淡写之间,就否决了这种局面的来临。但由狗及其行动呈现出的历史吊诡特性,依然算不上更深、更根本和更核心的提取。真正的提取,反倒被劳马看似不经意地浓缩于《抹布》中的一句话:“在全镇上下热火朝天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日子里,没有人觉得伊十傻,”以至于处于接种计划而消失于革命和革命群众之视野的伊十,没有引起群众和革命的足够注意。有真资格的二人转关系撑腰,被浓缩的那句话的真实意思只能是:“捍卫”直接等价于“傻”。历史的非理性和历史的摇头丸规律,修改了“捍卫”和“傻”千年不变的词义。但更实质的含义或许是:历史从不具备目的性、理性和必然性,它的本质就是傻。这就是生活的全体、事情的总量中多出来的那部分。阳痿、早泄的哲学,曾经给过历史太多胡言乱语式的解说(比如,黑格尔就认为历史在绝对理性的推演中所能获得的最高形式,就是他的普鲁士王国);但小说通过与生活调情、交尾,丑角与旦角构成真资格的二人转,却让劳马越过小说写作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给出了历史更为恰切的语义:所谓历史,就是傻。傻是历史的本质。这是小说和生活组成标准的二人转关系时,彼此为对方送上的令人震惊的礼物。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礼物,只因为在丑角和旦角之间,凡是被送出去的礼物,都“仍有灵魂,它们仍为其原来的主人所关注,同时,亦追随它们原来的主人”。(29)而历史的傻瓜特性(简称傻性),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傻,是历史无所皈依和历史流浪的象征或证据,它意味着处于历史之中的所有人,都得承担历史的傻性,哪怕是以最聪明的方式去承担(比如《哎嗨哟》中的亿万富翁、聪明人吴超然以及市长伊万)。劳马小说的隐蔽基础已经暗示了:哲学型傻瓜是承担历史傻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生理-智力型傻瓜在还没来得及承担历史傻性的时候,就已经先在地傻了:他“在”他自己的“在中存在着”,无论那只冒失的狗是否“存在着”。
劳马小说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以及由此才得以展开的狂欢化写作,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前提:将二人转叙事转化为小说叙事,但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践的平均主义”(30)——二人转叙事须得内化(internalizing)于而不仅仅是均衡于小说叙事。作为一个地道而纯种的东北籍小说家,劳马有这样的小说冲动和艺术抉择,或许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二人转为培育东北人的幽默感,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劳马将二人转叙事具有的狂欢效应,创造性地转化为自己的小说叙事;他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建立在二人转叙事的基础之上,或多多少少都跟这种叙事方式具有一种亲缘关系。大母神在渴望更猛烈的撞击,小说则急需要这种撞击能力,以便为自己壮胆、鼓劲,直到最后成就自身。在《抹布》中,劳马写道:“镇子为什么取名‘葫芦’一直是个谜。老人们说古时候后山(又名泰山,海拔不足四十米)的老虎洞藏了把金葫芦。谁藏的?神仙呗!哪路神仙?说不好。”会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将这段简短的叙事语言改写如下:
过门:镇子为什么取名“葫芦”一直是个谜。老人们说古时候后山(又名泰山,海拔不足四十米)的老虎洞藏了把金葫芦。
丑:谁藏的?
旦:神仙呗!
丑:哪路神仙?
旦:说不好。
这似乎可以被看作劳马小说叙事的结构性模式。它具有一种隐蔽得快要胀破自身外衣的狂欢效应,一种抿着嘴偷乐的搞怪神情。作为基础的结构性模式不仅潜伏于劳马小说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也暗藏于小说叙事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小的旮旯。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劳马小说一个非常打眼的特征:以二人转叙事去催促小说与生活尽快、尽好地构成一种恰切的二人转关系。或许,劳马小说写作的大部分秘密就在这里:惟有二人转叙事(或结构性模式),才能更好地帮助作为丑角的小说围绕作为旦角的生活旋转;由此,才让小说有别于阳痿、早泄的哲学,拥有让生活(或旦角)怀孕、分娩的能力,拥有强劲的生精和射精功能。惟其如此,劳马的小说才能从旦角身体的最深处(敏感部位仅仅是通往最深处的开关或闸门),抽取本该由哲学抽取的核心内容:只有傻性,才是历史真正的实质。
和二人转演出中的丑角和旦角不含笑意完全相同,小说家劳马的二人转叙事也不含任何笑意;就像不含笑意的丑角和旦角逗笑了观众,劳马不含笑意的结构性模式也搔到了读者的痒处或笑神经,让他们哈哈大笑,乐不可支,甚至还迸出了眼泪。二人转叙事(或结构性模式)让劳马有能力将任何看似悲剧、悲苦的东西,全部予以喜剧化、狂欢化处理。这不仅对应于二人转本身所具有的狂欢特性,也对应于小说从历史中提取出的核心内容——历史的傻性本来就不值得皱着眉头的正剧或悲剧去表达,只能以结构性模式的狂化效应去对待。和一本正经的“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比起来,或许,以二人转叙事为原型的结构性模式,才更有资格宣称自己拥有更强劲的解释力度,只因为通过它,劳马为小说找到了零距离进入旦角的方式与方法。
与阳痿、早泄的哲学和哲学型傻瓜完全相反,结构性模式扩展了劳马小说的生殖能力,它让小说和生活在恰切的二人转关系中,忘情地抚慰、调情、交尾,最终,产下了它们的爱情结晶。和哲学以单性生殖完成自身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小说是双性的产物,它和旦角一道生下了自身。这就是劳马的小说《哎嗨哟》、《抹布》、《傻笑》、《烦》、《抓周》、《伯婆魔佛》……但更是它们提取出来的历史哲学,历史的傻性特征。这是“精神的最高综合”,远不是越转越远的二人转能够完成或可以企及的。恰如劳马在《伯婆魔佛》结尾之所说:“抹布擦掉了肮脏,也擦掉了已有。它在擦抹的过程中变黑、变馊,成了那个时代的写照。”但是,劳马的主人公马上又代表劳马宣布:“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抹布。”或许,这句不是怪话的怪话的恰切意思正好是:尽管历史很傻,但我们需要这种傻,因为除了傻性,历史什么也没有。我们宁愿傻,也不能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傻,连吴超然和伊万(《哎嗨哟》中的主人公)的聪明也没有一点用处。
历史就是一块鸡肋样的破抹布。
小说代替了哲学,也战胜了哲学。
二○一三年二月十一-十四日,北京魏公村
注释:
①杨朴:《二人转的文化阐释》,第11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②见杨朴《二人转的文化阐释》,第165-216页。
③其实,所有的下层文化、民间文化(比如民歌、民间笑话),都有色情的成分。见敬文东《用文字抵抗现实》,第185-192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
④见佚名《东北人都幽默》,《郑州日报》2009年12月24日,第16版。
⑤见王杰文《民间笑话三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⑥敬文东:《灵魂在下边》,第4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⑦见撒加利亚·西琴《通往天国的阶梯》,第97页,李良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⑧敬文东:《网上别墅》,第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⑨敬文东:《写在学术边上》,第9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⑩《释名·释天》。
(11)杨朴:《二人转的文化阐释》,第179页。
(12)郁白(Nicolas Chapuis):《悲秋:古诗论情》,第5页,叶潇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名哲言行录》,第257页,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4)伊百以及兄长伊十的名字出现在劳马好几部小说中,比如中篇《伯婆魔佛》、《抹布》,以及长篇《哎嗨哟》。
(15)欧阳江河:《谁去谁留》,第13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16)《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430页,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7)(18)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第1、67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19)见韩少功《暗示》,第300-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0)见敬文东《灵魂在下边》,第40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1)(2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6、15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3)见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第144-15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4)《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5)见敬文东《一部历史应该少到可以拿在手中》,《新文学》第7辑,第18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26)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艺术》,第155页,朱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7)詹姆斯·米勒(James E.Miller):《福柯的生死爱欲》,第7页,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8)刘禾:《跨语际实践》,第12页,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9)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礼物》,第187页,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0)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读〈资本论〉》,第46页,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