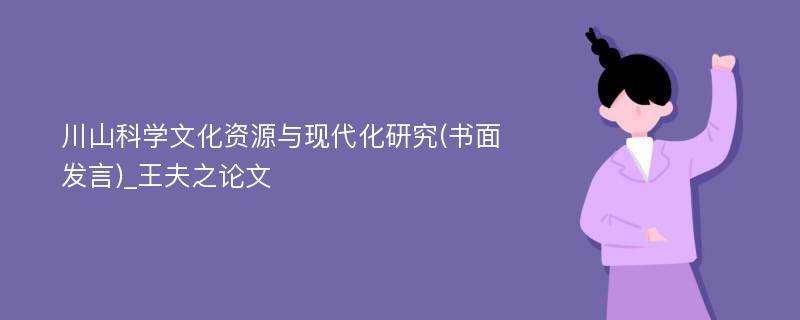
船山学文化资源与现代化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船山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6)01—0001—09
完成两个转变,推进船山学研究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船山学的研究在海内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在文本上出版了《船山全书》十六册,为研究者提供了最系统、最权威的珍贵资料,而且在理论上发表了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在海内外举办了多次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会议。王船山的名字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船山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正在走向世界。
当步入21世纪后,我们所考虑的不只是对过去辉煌成果的赞美,而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船山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让它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要推进船山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完成两个转变:一是从旧的研究范式转变成新的研究范式,二是船山学研究如何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把船山学中富有生命的哲学智慧,转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完成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转变。
在过去船山学的研究中,通常采取的研究范式:一是理学研究范式,二是“两军对垒”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虽然对船山学研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从现代学术眼光看,在总体上已不再适用,应当及时地代之以新的研究范式。
所谓理学研究范式,是指一百多年来,学者多根据程朱理学的理论架构,依据他的文本依傍和学术渊源,将船山学理学化。至今,仍有学者认为船山与程朱之异,“是理学内部之异,即理学内部的批判者,而不是反理学者”,王船山“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根本不承认王船山所创立的气学思想体系在宋明学术史上的独立地位。在20多年的中国实学研究中,我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学术发展并不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足并行”的格局,即是程朱与陆王互相辩难、互相消长、并行发展的格局,而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载)王(船山)气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它们之间既相互对立、辩难,又相互依存、转化,描绘着丰富多彩的学术画卷。他们在形而上方面,虽引进了佛、老的“本体”范畴,但都不同意佛、老把宇宙本体说成是虚无之体,肯定宇宙本体是“实体”而非“虚体”。在批判佛、老的“空寂寡实之学”上,儒家各派的观点是相同的。而当进一步探讨与回答宇宙“实体”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一“核心话语”上发生了分歧。程朱“以理为本”,陆、王“以心为本”,张、王“以气为本”,他们按照各自的致思心路完成了时代“核心话语”的转换,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这就是我近年提出的“一源(儒学)、三流(理学、心学、气学)”说。只有按照“一源三流”的理论架构,才能把船山学从理学研究范式中解脱出来,正确地把握与评价船山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王船山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庞大而复杂,学术渊源也是来自多方面的。他在批评程朱、陆王的同时,也改造、吸取了他们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成分。但是,从王船山的“核心话语”来看,他继承和发挥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张载的“气学”。王船山公开声称自己“以横渠为宗”。在自撰的墓志铭上写道:“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对“张子正学”倍加赞扬:“张子正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张载的气学说成是“立天、立地、立人”的“往圣之传”,可谓“功之正也”。在张载与程朱发生分歧的地方,王船山往往认为“横渠之说”比“程子之说”“尤为著名”(《读四书大全说》卷10)。在本体论上,王船山发挥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提出了“天地之蕴,一气而已”(《读四书大全说》卷10)的命题,认为“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篇》)。既反对程朱的“以理为本”,也不同意陆王的“以心为本”。在道器观上,王夫之针对程朱的“道体器用”、“道本器末”论,提出了“形而上而不离乎形,道与器不相离”(《周易内传》卷5)的观点,肯定“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在理气关系上,王船山依据“气上见理”,“理依于气”的气本论思想,批评朱熹的“理本气末”、“理先气后”之说。在人性论上,王船山根据“气日生故性亦日生”(《读四书大全说》卷7)的观点,极力批驳程朱的性二元论,指出“气质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则有一气质之性也”(《读四书大全说》卷7),肯定本然之性即在气质之性中。在天理人欲关系上,王船山针对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提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的论点,并且肯定天理与人欲皆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王船山在同程朱、陆王的辩论中,完成了“核心话语”的转换,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气学思想体系,形成与程朱、陆王相对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所谓“两军对垒”研究范式,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按照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把一部中国哲学史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史,并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不加区别地分成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四大块。这就是“二条线四大块”的研究范式。按照这种苏式研究范式,中国多数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予以充分肯定。这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从总体说,它亦不再适用了。依照西方某种哲学研究范式去诠释船山学,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船山学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明清实学思潮影响下,而逐步建构起来的,属于与西方哲学研究范式不同的哲学体系。它的“核心话语”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根本不同于西方哲学。所以,依照“两军对垒”的范式,解读船山学,只能把船山学变成西方哲学的附庸,完全失去了它的独立品格。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因此,只有将船山学研究范式,从理学范式和“两军对垒”范式转换成“以气为本”的实学的研究范式,方可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加深与拓宽船山学的研究,恢复王船山作为实学大家的本来面貌,从而正确地评价船山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所以提出转换船山学研究范式,恢复他在中国实学发展史上的巨匠地位,目的是为了通过学者将他的实学思想精华转化成民众的智慧,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建设。而要完成这一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工作,采用“经典现代诠释法”是必不可少的。
探讨船山学的现代价值,使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就必须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现代化需要出发,去重新审视、检验船山学,并在实践中判定船山学中何者是精华,何者是糟粕,以便过滤出它的合理价值。中国现代社会实践,既是检验船山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客观标准,又是推动船山学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船山学的历史命运,主要是依它满足于中国现代社会需要程度如何而定,并不是由少数学者所决定的。我们必须直面时代的呼唤和挑战,如生态环保、道德滑坡、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从船山学中选择与此有关的、有生命的东西,放在突出的地位加以研究和阐述,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与教益。离开社会需要和时代精神,是无从使船山学走向社会、走向民众的。
揭示船山学的社会价值,还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发掘和弘扬它的积极因素上。在王船山的实学思想体系中,固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应把着眼点放在它的积极因素上。即使船山学中的积极因素,我们也不能直接地拿来使用。既不能将它庸俗化和商业化,把船山学变成商业广告和赚钱“明星”,更不能将船山学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发掘和弘扬船山学中的珍贵文化资源,绝不是简单地从《船山全书》中寻章摘句,而是以研究者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船山之书,体悟和验证它的真理性,并进一步根据社会需要,加以现代诠释,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努力寻求船山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启现代人的智慧之海,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我近年来提倡的“经典现代诠释法”。
将船山学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仅以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为例,加以说明之。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王船山在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王充的“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张载的“天与人,有交胜之理”的观点,提出了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天人和谐”的著名论点。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对“天”与“人”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界说。他认为“天”既不是“意志之天”,也不是“义理之天”,而是无意志、无道德意识的“自然之天”。他指出:太和之气“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即是天,阴阳五行“合着便叫做天”。天是太和之气和阴阳五行的总名。他认为“势”与“理”二者“合而名之曰天”。“天”是用以标志客观事物发展趋势(“势”)及其规律性(“理”)的概念。在王船山的心目中,人不是“任天”之人,而是“相天”之人,即人不是消极地听任自然安排的动物,而是具有智慧和爱心的人。这样,王船山就把“天”与“人”的关系归结为客观事物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二是在对“天”与“人”界定的基础上,他辩证地回答了天人关系。他在《周易外传·系辞上》篇指出:“以天治人而知者不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有功于天地之事毕矣。”在这里,王船山把“以天治人”与“以人造天”结合起来,既肯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又承认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动作用,“以天治人”与“以人造天”虽是矛盾的,但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协调下,又是可以构建天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当“天”按照客观规律运行时,往往会给人类造成各种灾害(如水旱灾、地震、风灾等等),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者,可以“以天之理为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可与天相争胜。比如,人为了御寒可以“缉裘以代毛”,人为了自卫可以“销兵以代角”(《尚书引义·洪范一》)。不但“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夫也可以“造命”(《读通鉴论》卷24)。命运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并非是一切听任自然摆布。正因为人是具有智慧的高级动物,所以“知者不忧”。但是,在“以人造命”过程中,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膨胀了的私欲,只顾眼前利益,无限制地向大自然争权,无节制地乱伐森林,过度地使用地力和牧场,过度地捕捞水产,过度开采矿藏和地下水体,过度施放工业、生活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废渣等),以及人类自身的过度生育等,都是造成现代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根源。不管是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命题,张载提倡的“民胞物与”思想,还是王阳明主张的“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以及王船山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仁者能爱”生态伦理思想,都是试图通过扩展人的爱心,去遏止人的私欲,以便建构天人和谐的境界。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的最高理论形态。如果我们根据时代精神,将这一天人模式注入现代科学精神和法制观念,克服其时代局限性,它也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天人和谐”关系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层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和揭示船山学的现代价值,虽然是一件不易之事,但它对于拓宽船山学研究领域,将它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把它变成具有现代生命活力的哲学,铸造中华民族之魂,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在崎岖的道路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弘扬船山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
王兴国
(湖南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1)
船山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十分注重经世致用。其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说他“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船山全书》第16册)。这里讲的“实学”即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它与空谈义理不切实际的“虚妙之说”是完全对立的。
船山重经世致用,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湖湘文化的历史承传。就时代的原因来说,主要是明代后期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流弊。所以船山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对这种空谈的流弊痛斥不遗余力。就湖湘文化的历史承传来说,则是南宋时期形成的湖湘学派的重经世致用的传统。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均特别重视经世致用。胡安国发扬“春秋经世”的传统,一生以治《春秋》名家;其子胡宏则从体用统一的高度,为经世致用奠定了哲学基础。胡宏尝言:“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胡宏集》)这既从体用关系的理论上说明了读经与致用的关系,而且说明了“致用”所应包括的一些大体范围。
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正是湖湘文化优良传统和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船山的哲学思想,是在精研《易》理,反刍儒经,熔铸老庄,吸纳佛道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他对《周易》特别重视,尝言:“体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吉失凶之故,而《易》作焉。”(《船山全书》第1册《周易内传》)船山治史,则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船山虽然强调不论是治经还是治史,都必须以“致用”为目的,但他又不是那种浅薄的功利主义者,即简单地将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文字或历史上一些史实与现实相比附。恰恰相反,他认为要真正做到经世致用,就必须深入到经典或历史中去,把握其“微言大义”或“枢机”,即实质或规律。他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义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显义也。非事无义,非义无显,斯以文成数万而无余辞。若夫言可立义,而义非事有,则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船山全书》第5册《春秋家说》)这里讲的“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就是人们将自己主观臆想的一些东西塞进客观对象之中。这样做,当然无法真正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所以船山讲的经世致用,是要在深层次上揭示和把握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在船山的各种著作中,虽然其经世致用的倾向十分明显,但是其理论分析也是十分深刻的,不论是其治经还是治史,都能开出新的生面。
船山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对于清代以来的湖湘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就是在清代汉学占主导地位时,湖南许多学者在治学时仍然不忘经世致用。例如岳麓书院的许多山长在教学过程中,就反复强调要注重经世致用。而到了近代,经世致用更是成了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近代湖南所以人才辈出,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因为近代湖南的一些人物都特别重视经世致用。在近代湖南学界,有以陶澍、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也有以魏源、王闿运、皮锡瑞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经世学派,还有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世学派。须知,清代的汉学家是不重视经世致用的,近代的汉学大家章太炎甚至尖锐地批判魏源的经世致用主张。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使湖湘士人特别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的火热斗争之中,因而造就了近代湖南的一批又一批人才。
在近年有关湖湘文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讨论中,人们在分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构成时,发现政治和军事人才比较多,因而认为经世致用只注重政治和军事,所以不适用于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就经世致用的本义来说,其“用”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船山之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中说:“府君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船山全书》第16册)这就说明,船山的经世致用是既包括“江山险要”的地理、军事方面的事物,也包括“士马食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事物,还包括“典制沿革”的礼仪、政治等方面的事物。总之,它要求人们“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吉失凶之故”,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事物,而且要研究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事物。况且,近代湖南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人才也不少。例如,以丁取忠为代表的长沙数学学派,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范旭东则是近代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又如,朱昌琳、聂缉规、聂其杰、梁焕奎、李烛尘等则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有的甚至是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只是由于湖南近代的政治、军事人才太多,从而掩盖了他们的名声;加之近年的湖湘文化研究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力度不大,所以不为人们所知罢了。
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人们关注人生社会一切实际需要的领域,不分学科,不分冷门、热门,只要有用就应当研究;而作为一种学风,则与我们经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有相通之处,它要求人们不要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这种价值取向和学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是迫切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震动心弦的雷电
——王夫之道器论的哲学精神
赵馥洁
(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西北政法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3)
谭嗣同曾称颂王夫之哲学是“昭苏万物”的“雷声”,梁启超曾赞誉王夫之哲学是震动“青年心弦”的“电气”。这是对王夫之哲学力量的形象描绘和热烈赞美!王夫之的哲学之所以具有这惊雷闪电般的震撼力量,完全渊源于他的哲学的内在精神。对于船山哲学的精神蕴涵,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视角进行探索,这里仅从道器论的角度观之。
“道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含义十分丰富的重要范畴,道器关系蕴含着规律与事物、原理与事实、普遍与特殊、观念与实际、抽象与具体等诸多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关于道器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维历程。最早提出“道”、“器”范畴的是《周易·系辞》,它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命题虽然看到了普遍规律和特殊事物、抽象原理和具体事实有形上、形下的区别,但未深入说明两者的关系。直到隋代,人们对道器关系的理解仍然未能超出这个水平。唐代李鼎祚所著《周易集解》一书,援引了唐人崔憬(年代不详)的“道器观”。崔憬以“妙理之用”为“道”、“形质之体”为“器”,以“体用”释“器道”,颇有新义,但很简略。宋明理学各派都重视“道器”问题,观念纷呈,各有所见。程朱强调道器的形上、形下相分说,陆九渊倡导道器一体说,前者有重对立之偏,后者有重统一之弊。王夫之总结、反思、批判了宋儒关于道器的诸多论说,提出了自己的道器论,其核心观点是:天下惟器,道在器中;道器统一,道随器变。围绕这一核心论点,王夫之对道器关系的诸多层面,都进行了深刻、精辟的阐述,在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器观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思维水平。那么,王夫之道器论的基本观点及其所蕴含的哲学精神是什么呢?
1.“天下惟器”的崇实精神。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意思是说,充塞天下的只有实际存在的具体器物,“道”是从属实际器物的,而器物不是从属于道的。这是王夫之道器论的根本出发点。它明确表示实际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本原的,而作为道理、规律的“道”足派生的、从属的。从这一“器决定道”、“道依于器”的唯物主义观念出发,他提出了“有其器则有其道”、“无其器则无其道”、“能治器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同上)。他特别指出,“有器则有道”的道理。即使“君子”、“圣人”不懂,参加生产实践的普通老百姓(“匹夫匹妇”)却会懂得,因为这是普通常识。有时人们由于不掌握某种事物的规律,因而做事未能成功,但做事不成功并不是事物本身不存在;没有办成的事情也是事情,没有制成的器物也是器物,所谓“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同上)。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唯物主义观点集中体现了王夫之尊重实际(“惟器”)、不蹈虚空,崇尚实践(“治器”)、不尚空谈,赞赏劳动者、不迷信圣人的崇实精神。
2.“古今异道”的革新精神。从“有其器则有其道”、“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出发,王夫之深入阐发了道随器变、古今异道的观点。他说:“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又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同上)。这足以说明,历史是进化的,而进化的动力则是器物的革新。随着器物的革新,“道”就发生变化。既然“道”是随着历史上器物的革新而发展变化的,那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根本不存在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今一贯的“道”。这种变革更新精神,是他的“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张子正蒙注·大易》)、“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的发展变化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和展开。
3.“圣人治器”的创造精神。既然历史的发展、社会的革新是“道随器变”的过程,那么“器变”是如何实现的呢?王夫之认为是“圣人治器”促使了“器变”,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王夫之所谓的“治器”,就是治理、改革和创造具体的器物。在他看来,器物是“实体”而规律不是“实体”,因此具体的器物可以治理,可以创造,而规律不能治理,不能创造。所以他说“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然而,他又认为“道不离器”,“道在器中”,规律又依于器物,器物是规律的载体,因此在变革事物、创造器物的过程中就会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所以他又说:“治器者则谓之道。”(同上)他指出,《易》的“象”、“爻”、“辞”中所蕴含的道理,都是由“像器”、“效器”、“辨器”而形成的。因此,“圣人”之所以高明,并非由于他能“治道”,能践“形而上”,而是因为他善践“形而下”,即“善治器而已矣”。圣人通过“治器”而“得道”,因而具有了高尚的品德;圣人努力“治器”而“器成”,因而具有了卓越的行为;圣人不断“治器”而使“器用之广”,因而使天下变通;圣人由于治器而产生了显著的“器效”,因而成就了伟大的事业。王夫之通过对“治器”与“得道”关系的精辟阐发,通过对“圣人治器”之深远意义的赞誉,深刻阐明了历史的进步是从物质改造活动开始的,物质的创造活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由此而高度弘扬了人的主体创造精神。
4.“君子尽器”的实行精神。王夫之不但高度颂扬了“治器”的圣人,而且认为普通君子的人生之道就是“尽器”。他说:“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同上)“尽器”就是发扬一种面向实际的、勇于实行的精神去穷尽具体事物。“尽器”包括认识事物的品种(“识其品式”)、辨析事物的条理(“辨其条理”)、熟知事物的功用(“善其用”)、明确事物的本性(“定其体”)以及用文字说明事物(“显器”)、鼓励人们改造事物(“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等等。而且还要把深入认识器、真实掌握“器”作为自己的品德(“成器在心而据之以为德”)(同上)。他认为儒家经典的根本精神就是教导人们“作器”、“述器”、“明器”、“显器”、“治器”。船山指出,君子若能把“尽器”精神贯彻于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和钦佩;若能把促成器物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就会具有高尚的道德。不难看出,船山通过阐发“尽器”之道,赞赏的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行精神。
5.“鉴愚)恶妄”的批判精神。王夫之根据“天下惟器”、“道不离器”的观点,深入地批判了道器观上的种种谬论,包括道家的“道虚”论,佛教的“道寂”论,理学的“离器言道”论等等。他指出这些道器观的共同错误是“标离器之名以自神”,即“离器言道”,从而把道虚空化、寂灭化、神秘化。他说,那种离开器的“道”,无形的“形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也。”正由于“无器则无道”、“无形则无形而上”是“显然易见之理”,因此,对于种种“离器言道”的“邪说”和“欺骗”,“君子之所深鉴其愚而恶其妄也”(同上)。“鉴其愚”、“恶其妄”正是王夫之所倡导和所奉行的反思批判精神。
王夫之道器论所深刻蕴涵和鲜明体现的崇实际、尚革新、贵创造、主实行、倡批判的哲学精神,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精华,它的形成自有其特定的原因。正如萧萐父师在分析王夫之理想人格美形成原因时所说的“时代的风涛,个人的经历,传统文化的教养,学术道路的选择”都促使并激励着他的理想人格美追求一样(《吹沙二集》),船山哲学精神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历史变革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哲理升华,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反抗的人生实践的理性凝结,也是他“希张横渠之正学”的学术承传的理论感发。王夫之哲学的精神,对近代以来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曾经发生过深刻的思想影响。戊戌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说:“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又说:“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思纬壹·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王夫之道器论直接成了他的变法主张的理论依据。因此,他诗赞船山哲学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嶽一声雷。”(《论艺绝句》,《谭嗣同全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今时代,王夫之哲学的实践精神和创造精神,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雷电般的船山哲学精神将继续闪耀其不灭的光辉。
船山“日新”观的启迪
朱义禄
(同济大学 文法学院,上海 200003)
记得20多年前,读船山的著作,最敬佩是他的“日新”观。那时还把“新故相资而新其故”这句话抄于本子上,反复思索。如此意味隽永的话,似我等之人是绝对写不出的。近来空余时再作些咀嚼,觉得对当今的社会还是有很大启迪意义的。
船山的“日新”观是从宇宙论着眼的。船山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自然界的日月风雷,大地上流淌着的江河,照亮人间的灯烛之火,人身上的肌肉爪发,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与更新。以人来说,人的形体看似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实际上却天天进行着实质性的更新。这是完全符合生物学的新陈代谢规律的。人的毛发、细胞天天在更新着,这已为现代生物学所证实。“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者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周易外传·震卦》)。天下的事物,在未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的条件下都是保持着原先的形态,这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天下事物的内容从无停止过更新。“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思问录外篇》)。船山从“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事物一旦出现了无法更新的现象,就必定会走向死亡。在船山看来,这是一个永恒的规律,任何事物要“相延相代”地存续下去,贯串其中的无非是一个“变”。这种不停顿变化就是船山“日新”观的宗旨所在。
从逻辑推演上来说,对任何一个构建了体系的哲学家来说,都会把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推及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上,否则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船山也不例外。“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其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五章》)这样的隽语,完全是从认识论上讲的。船山把人的学习与思维看作是相互推动的辩证过程。学习与认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变化的行程,新旧知识互相作用不断地推陈出新。人的思想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发展的,这样明显的现象与隐蔽的本质相继为人们所洞察,“微”的本质是从“显”的现象那里得到了说明。就人的认识而言,要不断地变化自己,才能获得永不枯萎的生命力。“才以用而日继,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积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洼,九夏之方熯而已涸也”(《周易外传·震卦》)。人的才能只有在运用中方能发展,人的思维如同江河之水,在不停的流动中才会永不穷竭。那些微小的水洼,经不起夏天的太阳的日晒,很快就枯竭了。理由非常简单,水洼中的水是不流动的。诚如汉人所言,“牛蹄之涔,无尺之鲤”。《淮南子》作者是从常识角度来说的,而船山将其提升到哲理的高度,把人的学习、认识、思维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人的认识在不断的变化中才能显现出活力来。
王夫之的“日新”观与现今举国上下都在谈论“自主创新”,还有着一些差别,但从精神实质来说是相通的。其共同点都是认同趋时而更新,强调出新才是活水源头的所在。只不过船山是从新陈代谢的规律来说,而“自主创新”侧重于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所在,是从国家是否有竞争力的制高点着眼的。另外一点是,船山把人的认识活动视为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永远不会固守在某一个层面上的,这对“自主创新”来说,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已经年产3000万台dvd的中国,厂家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亿美元的专利费(向欧洲),这是因为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以往国家提倡加工贸易,现在觉得效益太低下。据统计,国内企业对一个国际著名品牌的加工,最多只能赚取内中利润的8%。这是由于没有“自主创新”的品牌。创新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创新才是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硬道理。由此我们再细细品味船山的“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更觉其中内涵深刻得很。
中华民族应该挺起自主创新的脊梁骨,这包括激活人们创新的心理、气质、精神与价值观念。“自主创新”观念要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必须形成有利于这一概念的文化环境。现在重温船山的“天地之化日新”、“新故相资而新其故”这些主张,对促进这一文化环境的形成,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就此而言,船山的“日新”观,实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
王船山与质测之学
李明友
(浙江大学 哲学系,江苏 杭州 310028)
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科学的每一个进步,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理论的发展,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总是尽可能关注并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王船山之所以在总结古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不少新的哲学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关注并吸收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成果。
以王船山哲学的认识论为例,王船山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心性之学的影响,但他强调即事以穷理的质测以明理,以客观外界事物为认识对象,以认识外物之理为目的,其认识论表现出一种开始摆脱心性之学局限的倾向。王船山认识论中的这一新因素,是他吸取质测之学的方法的结果。
质测之学的兴起,是明清之际在自然科学研究上出现的新动向。方以智是质测之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说:“物有故,实考究之,大而元合,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可见,所谓“质测”,就是对事物进行实际考察,这门学问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际考察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质测之学的主要代表还有宋应星和徐光启。宋应星强调通过实验的方法求得对物理的正确认识。他认为对某一科技方面的知识是肯定或否定,都应经过实验、试验之后方可确定。例如,他曾对当时一些士大夫关于兵器弹药的制造的空谈,表示不可信,说:“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实验。”(《天工开物·佳兵》)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例如,当他对一些榨油原料作了些实际研究但尚不充分时说:“此其大端,其他未穷究试验,与夫一方已试而他方未知者,尚有待云。”(《天工开物·膏液》)这是相当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大科学家徐光启也主张在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探求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他指出,事物的变化,“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义,推究颇能,法立数著,遵循甚易”(阮元《畴人传》卷32)。因此,他主张建立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即所谓“度数之学”,即在通过反复实验所得出的数据的基础上掌握物体变化的数量规律的学问。这种科学的方法,使徐光启在天文历算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每一进步,都给同时代的哲学家以深刻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哲学思维的进步。王船山是一个亲身参加社会斗争,关注社会现实的哲学家,他同样也关注着时代的科学成果。尽管他在抗清斗争失败后独居湘西僻壤近四十年,然而他并没有与世隔绝,更没有与科学隔绝。我们从他的哲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受到科学空气熏陶的。就连当时西学东渐的情况,他也同样予以关注。他在《思问录外篇》中曾多次评论西方传教士。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及狭隘的民族偏见作怪,船山拒绝利玛窦等人关于地球形状如弹丸的说法,但他对西方科学中利用仪器进行实验的方法却表示赞赏。船山说:“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并指出西洋历家用“远镜质测之法”所测知的七曜远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参看《思问录外篇》)。方以智是王船山交往密切的朋友,船山对质测之学有较多的了解。船山曾赞赏道:“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
“即物而究其理”,本是朱熹在《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中对“格物”的解释,但朱熹所谓“即物,”其真正的含义是:“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而其所穷究的理,除物理之外,主要指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而言,且最后导致“本心以穷理,而顺理以应物”(《观心说》)。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虽然有些合理的因素(如“考之事为之著”),但就其全部来看,则是一种通过物理以明性理的心性论。王船山的“即物以穷理”,是建立在实际观察的基础上的,“惟质测得之”,即只有通过实际观察才能“即物以穷理”,这显然排斥了朱熹所说的“察之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这些非属“即物”的内容,而以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为认识之对象,以了解天地万物之理为认识之任务。船山说:“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故所恶于异端者,非恶其无能为理也;冏然仅有得于此,因立之以概天下也。”(《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就是说,人们要认识事物之理,只能从客观事物本身中去探求它,而不能凭主观臆造的所谓“理”或凭某一现成的“理”去限制具体事物,那些鼓吹异端邪说的人,也许有时会说一番“道理”,但他们把自己一闪念间所得到的所谓“理”确立为事物的法则,并用它概括天下万事万物,那就大错特错了。坚持“即事以穷理”,反对“立理以限事”,是王船山在认识论上的杰出贡献。
关注自然科学的进步,了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还要善于吸取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改造旧哲学,如果不善于吸取,其哲学的创新就必然受到影响,譬如明清之际另一位大哲学家黄宗羲,黄宗羲与王船山同样重视自然科学,也有丰富的科学思想,但他的认识论仍以性理为对象,而不以天地万物为对象,他以为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认识了人心之理便同样认识天地万物之理,并没有摆脱王阳明的心性论。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摒弃对于天地万物之理的认识问题。当他在谈论对自然之物的认识问题时,又主张“即物穷理”。他说:“穷理者必原其始,在物者必有其因。”(《获麟赋》,《黄梨洲文集》第308页)即探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对于那些迷信邪说,他认为只有以“推物理之自然”的方法还自然物的本来面目才能破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质测之学”的科学方法。但是,黄宗羲没有像王船山那样,用“质测”来改造“格物”,没有用这种宝贵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去改造阳明哲学的格物致知,而是保留了阳明哲学的“心物一体”、“心即理”说,沿着由内向外的路线,将穷理解释为穷心,将格物解释为格心上之物。这就与王船山走的是不同的路子。
哲学理论要创新、发展,哲学家除了密切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吸取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之外,还要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变化,吸取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否则,哲学理论的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当今,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问题,已引起哲学界的高度重视,我想,重温一下三百余年前王船山哲学理论的创新与质测之学的关系,不无启迪。
标签:王夫之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读四书大全说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船山全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