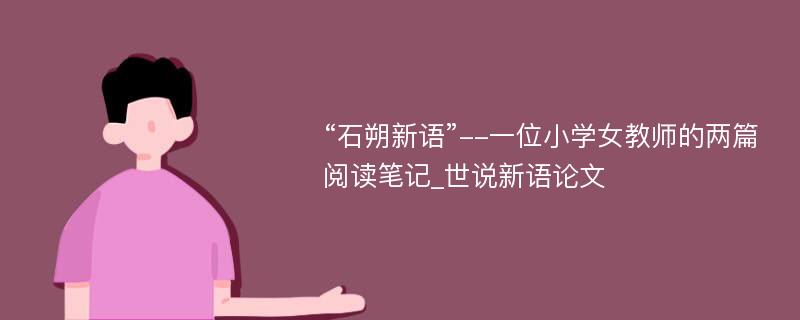
《世说新语》新得———个小学女教师的两则读书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教师论文,两则论文,读书笔记论文,小学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之一:老人国里的好孩子
近读《世说新语》,若干“模范儿童”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小心重、少年老成。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德行第一·范宣受绢》十指连心,怎能不痛?但范宣“大啼”却是因为自己的“不孝”——一时不慎,竟让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遭到了损伤!这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吗?这个典型的“有德少年”,终因“洁行廉约”而名播四海。其实,至少从八岁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己,没有了童年。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言语第二·小儿偷酒》)“孔融让梨”是中国式的美德佳话。在那个故事里,孔融全然失去了儿童天性。他的儿子则青胜于蓝:连偷酒喝都忘不了“礼”。在这里,我们看到童心裹着礼教的茧子;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将看到这茧子是如何变成金属模具的。
孔融被受,内外惶怖。时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免乎?”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言语第二·覆巢之下》)
早就知道“覆巢无完卵”的出处。然而,当我再度读到它时,作为母亲和教师的心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和悲哀:“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轻轻一语,道尽人情冷暖世情残酷。相比之下,孩子的父亲反而显得幼稚。这正是传统中国教育所期待的成果——小小年纪,便有了一颗饱经沧桑的心。
孔融肯定会因为殃及小儿而伤心,但是他是否会为孩子夭亡的童心而内疚?不会的,不仅是他,从刘义庆到《世说新语》历代的读者,大家都着意于欣赏孩子的深沉和懂事——这真是一个扼杀童心,催人老去的国度。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卿面何以汗?”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第二·汗不敢出》)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儿俱行。庚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七八岁。庚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言语第二·猎场应对》)
德也好,礼也罢,将圣人之教钻透,无非就是为了沽名钓誉或在帝王脚下讨一杯残羹。而要达到后一个目的,溜须拍马的功夫是少不了的——上文对答堪称典范:既挠在了痒处又儒雅得不露声色。如此高档奉承的享受者,要想把持住自己而不飘飘欲仙,简直很困难!面对几位少年俊杰,同道的成人也当深愧不如。
一个问题:这是否有违于圣人之教呢?读读《论语·乡党》你就知道啦。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聚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夙惠第十二·不见长安》直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小皇子的机智和能言,而对于“长安何如日远?”这个问题的本身,千年以来却少有人去认真思考。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比起嚼烂儒教就足以沽名取惠而言,研究这样的问题太苦太累太傻了,简直是对自己的虐待。
魏晋之人尚清谈,长于无聊的巧舌之辩。“不见长安”所记载的,正是这种变态的小聪明。语言成了巫术般令人迷醉的游戏,它一旦与礼教合围,求索的火花必遭窒息,而企图冲出“鬼打墙”的勇气早晚被扼杀——一个民族的大脑和筋骨就是这样萎缩软化了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天人三策》)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魏晋,已经过去三百年,从表面上看,当时儒玄佛道捣腾得很热闹,但是儒家的主流地位已经毫不含糊地显现出来。从那时到清末又是一千六百多年,定于一尊的文明怎能不变得烂熟、封闭、有毒?越来越厚,越来越重,铁屋一样让人透不过气的,是暮气妖气腐尸气——这是一个典型的老人国,老人国里的好孩子就该是深沉早熟的小大人。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至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其实,“老大帝国”之衰老,早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之二:俯仰无愧谢安石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永王东巡歌》
少年读此,便觉豪气冲天,同时也牢牢记住了一个重量级历史人物的名字:谢安。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第六·儿辈破贼》)淮上即淝水,所谓的“淮上利害”,其实决定着东晋的生死存亡。历史上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是东晋史上的转折点。使谢安名垂青史的,正是此战。
当谢安游栖东山,屡招不仕时,东晋人士异口同声地叹道: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排调第二十五·新亭送别》)隐居的谢安是否真的心如止水呢?“捉鼻而语”实在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夫妻对白: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排调第二十五·捉鼻而语》)
显然,他并不想老死林泉。在谢安看来,获得荣华富贵直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然而仅有富贵是不能让他感到满足的,谢安对自己的才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在等待机会,伺时而出。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有人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排调第二十五·一物二名》)郝隆的话,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典型的迂腐之见。殊不知谢安四十余岁的东山再起,使清谈流弊的东晋少了一个吟啸自足的隐士,赢得了绝处逢生的机会;也使谢安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至,最大限度的实现了人生价值。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以自己的胆识和才略为历史写下壮阔动人的画卷——谢安,你又何必有愧。
相比之下,还是简文帝比较了解谢安。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识鉴第七·与人同忧》)审时度势,进退有节。既善享受,又能尽己所能地服务社会,成就一代伟业——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谢安当然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但是比起那些贪婪鄙佞,一味损人利己的硕鼠蛀虫来,又不知道要高尚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