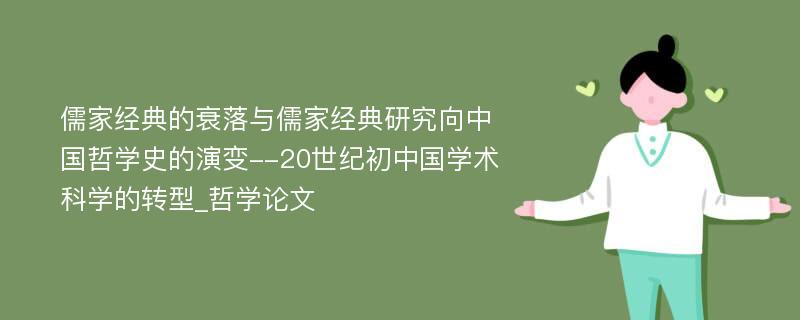
经学的衰落与诸子学向中哲史的嬗变——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诸子论文,国学论文,初中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戊戌”到“五四”,中国学术界以风起云涌的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的冲撞对峙和会通融合为契机、为动力,哲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历来以经、史、子、集为标帜的古典学术形态中析离化合,脱颖而出,逐渐生枝长叶,展现于世。这是中国学术沿着古老的生命轨道、历经数千年缓慢演化之后,终于从根底上生发的一次新陈代谢。尽管来得很迟,但它终于出现在20世纪初的学术史页。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由于学术域面的急骤扩大,原先的古典学术的躯壳已无法容涵所致。其实问题决不仅仅如此。从深处看,哲学从旧学的脱颖与分化,正是中国学术在其本身发展的诸多规律支配下,出现于特定阶段的历史必然。这里既清晰地印有传统经学从中衰走向终结、诸子学从复苏走向繁盛等等一系列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内部自身的遗传嬗变轨迹,亦有备受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刺激,尤其是西方哲学潮流迅猛冲击、激发示范等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催发,内外呼应、经纬相织、纵横交错,蔚成一幅中国数千年学术史上罕见的转型景观,集中展现了学术史发展的诸多规律的幅合交映。本文着重从经学之衰落与子学向中哲史嬗化这一脉络加以追寻与勾勒。
一
学术的历史是由社会的历史规定的,这已是学界的不刊之论。中国20世纪学术史正是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活生生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从古典学术形态向现代学科的转型,以其恢宏的整体场景,再一次印证了学术史发展的这条规律:每一时代的学术无不是与时代感应的产物,无不随时代的变革而因时嬗化或革故鼎新。时代是催动学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发展的外在气候和供它滋养吮吸的活水源泉。在学术史流变上,时代缘素的考察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正处于自春秋以来数千年未曾有的历史巨大变局中。历经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俄战争、中日战争的迭起世变,特别是甲午之战败于蕞尔日本,达到了世变之亟,带来割台湾、赔款二百兆的奇耻大辱,终于真正地惊醒了中华民族“四千年之大梦”〔1〕。中国临“数十国之觊觎”〔2〕,站在了豆剖瓜分、危如累卵的民族存亡关头,受到了“精神上的强击”〔3〕。
空前的民族危机不仅使社会诸种新旧矛盾激化,同时也直接引发了旧学术整体的、根本的、剧烈的危机。其重要表现之一,是以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戌士人,终于走到了漫漫数千年科举取仕旧路的尽头,开始了向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向。这些举子士人对甲午之役的反应,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其余各阶层,他们感受到的是如“受巨创”的震动、如“负深痛”的刺激。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标志着国门被撞开,引起的是致力于“轮船火车、水雷枪炮”的三十余年洋务运动,那么甲午战事使这些士人清楚地认识到,洋务仅是强国之策的枝叶,“非其根本”〔4〕,前此言变, 不知本原,只是“补苴罅隙,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灭亡”〔5〕; 因此,强国之本原在于要像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改弦更张——“讨论学业,讲求官制”〔6〕,在道的层面上吸纳西学。 他们再也无法将自己局限于八股八韵、词章帖括、训诂考证,纷纷把目光转向新学——西方学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早就痛感“学问饥饿”,如饥似渴地“欲求知识于域外”,以已译西学为“枕中鸿秘”,成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不懂外国语的西学家”;但甲午之前,西学输入仅“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7〕, 即多为自然科学领域的格致之学,其给学界的影响表现为诸如谭嗣同、康有为以“以太”、“电”、“元素”等西方近代科学声光电化的科学物质概念,来为构造自己的自然观和理论体系服务。正是甲午之战的深重刺激,才促使严复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世界观上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使中国朝野震聋发聩,并随后接连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学、逻辑学著作。也正是甲午之战,使中国学界看清了日本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的成功榜样,在20世纪伊始之时兴起了大规模留学潮流。伴随着这一潮流,终于出现了迻译西方哲学的热潮,标志着“向西方学习”开始进入了讨论“形上之学”的最高层阶段。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曾写道:
“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8〕
后来他又写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9〕
王国维也是因甲午世变而有志于新学:“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10〕他从故乡海宁来到上海不久,即从日人那里觅得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著作,“心甚喜之”,曾转入“专攻”。也几乎是在同时,章太炎告别了求学八载的杭州诂经精舍,走进了上海:“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1〕
20世纪初出现的留学潮流正是以留日本为最先一路,涌起于学界。一批批学人负笈东渡,人数逐年剧增:1899年仅有200名,1903 年已达千人;1904年增至四千,1906年约8000人〔12〕。与此同时出现的景观是,大量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中间之驿骑,骎骎而入中国。据当时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资料统计,1899年的《东西学书录》中,西方哲学著作仅占西学输入之比重的2.1 %,且仍归在“理学”名类;到1904年,时局一变,风会大开,《译书经眼录》显示的哲学政法等社会科学类译书已归入“哲理”类下,数量急速上升,占西学输入总数的61.5%,成为当时西学东渐的荡荡主流〔13〕。而“哲学”一词, 为中国学术原本所无之词, 是日本学界由英文PHILOSOPHY所造译的一则典型新学语,也正是在当时由日本传入我国学界,并在新旧势力的一番较量后〔14〕,终被接纳。按王国维的说法,这类新学语的输入,本身即是意味着新思想的输入〔15〕。被称为“西学命脉”的西方哲学终于能在本世纪初中国本土的报刊上广为流布,实有赖于这一批留日学人在东土的大量阅读、迻译这一转输之功,其中尤以介绍传播古希腊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最为引人注目(亦已开始有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介绍)。
另一路时间上稍晚些,以胡适、冯友兰等庚款公费生为代表的留美学子,飘洋过海,在大洋彼岸目受耳濡英美哲学。当他们于“五四”前后归来中国后,则以所濡增、所历练之学力与识见,自觉地致力于中国哲学学科的构思与建设。
第三路是辛亥革命前后开始的,最初以朱执信、王缁尘等人为代表、而在“五四”前后以李大钊、李达等人为先锋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
上述这三路人士在20世纪初热情介绍、转输大量西方哲学著作与思想,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继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在世界观上又作了重大而深入的推进之外,其余两路,也都已突破了进化论这一世界观的层面,直接进入到西方哲学更为广阔的学理与方法的视域之中。这不仅是量的激增,更是质的显变;它为中国哲学从旧学术中的独立蜕出,树立着范导,营造着氛围,积蓄着力量,推动着波澜。
1905年,清廷被迫废除已推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由戊戌一代士人转化而来、热衷新学的学者,加上留日、留美等延为辛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共三代学人,整个过渡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已然构成,烘托出从戊戌直到“五四”,正像梁启超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蚕变蛾、蛇蜕壳”的学术大变动时代;而这支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正是营建哲学学科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二
以甲午之战为枢纽,这一激烈变动的时代所催成的,不仅仅是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队伍的形成,不仅仅是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热情投注、迻译研习,更且促动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接受西学的洗礼中从内部发生着根本的裂变与新生。这首先表现为随着西方哲学的滔滔涌入、咄咄逼人,中国学术界绵延二千年的以经学为统领的价值取向开始从根本上逆转,经学独霸已日益走入日暮途穷。可以说,这正是一物之两面,相辅而相成。而这,也正是汉代以降二千年来以儒学独尊为不变基调的中国传统学术终于出现根本转型的重要迹象。
率先对二千年来“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的名教与经学网罗进行冲击的是谭嗣同。他不仅指斥名教:“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更揭露传统经学与之纠缠一气,助纣为虐:“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16〕由此他发出了响亮的声讨檄文:“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17〕
梁启超亦于1902年毅然“我操我矛以伐我”,与乃师康有为分道扬镳,从“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转为“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他纵横议论,矛头直指跋扈学界二千余年的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方式:
“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之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18〕
这位当时舆论界的骄子,对“守一先生之言”、“煽思想界之奴性”的经学思维方式作了嬉笑怒骂的嘲弄和鞭辟入里的批判,他所求所争的,正是为了要开辟一条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之路,树起“唯真理是从”的标尺,作为学界之评判准绳:“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19〕在另一处,他更激情澎湃地宣布:“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20〕其中洋溢着的是一派“求研究之真、求研究之大无畏”的精神,一份只有近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才能持有的感悟。这正昭示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带根本转折意义的时代已经开端。如果没有这一变动时代中追求学术自由精神的涌动,哲学从旧学中挣脱桎梏得以新生独立,将是不可思议之事。
王国维也在1906年宣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21〕,并把这份感悟提升到申求学术独立、挣脱各种羁绊的界面:“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22〕。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透彻的睿识,这位在上一世纪之交即对康德、叔本华哲学“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心怡神释的王国维,早在1903年就发出呼吁:“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23〕1906年,王国维任“学部”参事,正值张之洞等人在其主持制定的《秦定学校章程》中对经学文学这二科,详定教授之细目及其研究法,“肫肫焉不惜数千言”;对哲学则诋为“有害”之学、“无用之学”,悍然砍去。王国维即撰《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力驳张之洞的谬论,针锋相对地申明自己的观点:“缺哲学一科”是“根本之误”;“哲学不可不特置一科;其他科中必不可不讲哲学”。他不仅早就强调过哲学之兴味是“知力之优”的表现,更在此文中声明:哲学是人作为形而上学的动物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需要,是“求真理,求智力之发达”的需要;并清晰地表达了自己“不研究哲学则已,苟研究哲学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是从”的意向。在同一篇文章中,在将哲学尊为“最高之学术”的同时,王国维更直接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批判经学独霸。明确地申论儒家只不过是诸子之一家,其价值有待研究方能明了:“苟儒家之说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耳”。他强调哲学的态度应是“为研究之故而研究”,“是非非由圣贤立”〔24〕;孔孟之学对于哲学只能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而非信仰的对象:“若我孔孟之说,则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25〕。
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冲决经学藩篱、为哲学之崛起张旗击鼓的场景相映衬的是,张之洞等视哲学为“酿乱之麹蘖”,出于“惧邪说之横流、国粹之沦丧”的戒心和维持道统的立场,骇于“哲学”这一名词不敢采纳而以“理学”代用,并在大学章程中特意砍去哲学一科。这恰从反面印证了其感觉与王国维等同样敏锐:哲学之兴与传统经学之衰在中国学术史上正是共时态的同步伴随,正是中国古老学术内在生命新陈代谢的典型征候。
不仅是哲学之兴必定伴随、并且促进经学之衰亡,此时在传统经学的内部也正再度经历着激烈的今古文之争。与汉朝的那场今古文之争不同的是,以康有为、章太炎各为代表的这场清末今古文论战,导致传统经学这座显赫二千年的神圣殿堂,日甚一日地戛戛坼裂,行将彻底崩溃。而这也与学术史发展的另一规律相参证:每一变动时期中学术内在矛盾之演变,是推动其必然地按特定方向、向特定形态嬗化的内部依据所在。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秉袭龚自珍、魏源“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之遗风而作了重大发展。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这一派的重要典籍《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至少有以下两点影响了20世纪的学术流变:第一,《新学伪经考》以考证辩伪法,断定《左传》等十四篇古文经典均系刘歆伪造、是以伪“左”灭“公羊”、以乱孔子“改制之经”,这一断定不仅其“进退古人、去取古籍”的大胆怀疑精神在学海激起余波、延为疑古思潮、一直影响到“五四”后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而且这种将千余年来“举国学士人人习之”、“咸所依据尊尚”的经典之作指为伪说、扫出庙堂、“虽圣人不得不俯首而听吾驱策”之举,本身无疑给了传统经学的威权以极大的震动与冲击;其二,《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专辟《诸子并立创教改制考》一章,把先秦诸子全都论说成是像孔子一样致力于托古创教改制的人物与学派——老子托于黄帝,墨子托于大禹,许行托于神农,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无不托古改制。正像梁启超指出的那样,这一阐发将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均解释为出于“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26〕,实际上已将孔子夷入于诸子之列。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则采取了另一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路径:直接抹去二千年来笼罩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申言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27〕,孔子决非教主,只是“古良史也”〔28〕,先秦诸子之一而已;《春秋》不是什么改制创作之书,其功只在重夏夷之别、为中国“存种姓、远殊类”〔29〕而已。不仅如此,章太炎更对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家思想之弊端作了无情而尖锐的批判:“儒术之害在淆乱人之思想”,“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30〕;“孔子讥乡愿不讥国愿,湛心利禄,矫言伪行”;“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31〕。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策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从此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是非之准、主术之原,作为官方学术定于一尊;中国学术在两千年漫长的经学时代,递次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的演变。而清末这场今古文经学之争在学术史上的结果之一是,两派从不同方向、在一点上两极相通了起来:打破了两千年来禁锢学界这一“别黑白、定一尊”的格局,开辟了以平等眼光看待儒学与其他诸子的视角,导致新的比较研究的浩荡学术潮流。这一学派之争的另一结果是导致了经学的分裂,并由此加速了经学的衰亡。它汇同前述王国维、梁启超等对经学思维方式的批判摧廓,使中国学术史上二千年来“守一先生之说”而“兢兢焉不敢出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的局面终于行将彻底结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底色与学术背景、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千年学术史从根本上生发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哲学这一“以追求真理为天职、以人类形上需要为依托”的新时代的学术之子,才有可能挣脱二千年的羁绊、从旧学中争得新生与独立。
三
和哲学之兴必然伴随着经学之衰、催促着奴视学界的经学终于就要走完它的全程一样,中国学术史本世纪初的根本嬗革同时还表现为,哲学之新兴必然伴随诸子学的从复苏走向繁盛。而子学在世纪初的这一兴盛,其最显著、也是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受了排挞涌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的样板示范、刺激生发。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对中国固有学术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刺激、引导诸子学不断摆脱道统的箝制,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的方向嬗变,而诸子学因此也就成为中西学术最初结合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也清楚地展现了学术史的第三方面的规律:外来之学术最初必得通过与本土学术的内在固有资源的相互寻求共同点的呼应、进而结合化生,才能在异域生根发芽;而本土学术一旦掷弃故步、吸收外来学术的佐养,则将抽绽开新的枝叶花蕾,焕发出一个堂堂的新气象与新局面。
早在清代中叶,乾嘉学派以考据、辨伪之法即所谓朴学之法,已几乎遍治了儒家群经。由于缺少更多的参考比较材料,学者们开始引诸子以证儒家经典,由此启动了对诸子的普遍校勘,带动了学术史上沉寂已久的诸子学开始相应地悄然复苏,日益潜流涌动;并朝着阐发诸子义理的方向发展。然而清中叶开始的诸子学复苏,其内容与方法尚囿于初始阶段的谨慎,未能脱出考证学的藩篱,可以说仍属经学的附庸与余绪:“此仍治经,非治子也”〔32〕。
20世纪伊始,清末民初的诸子学研究日趋繁荣活跃,不仅在量上,更在研究的角度、方法、内容上发生新的质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33〕。
这一阶段研究诸子学最着力、成果与影响甚大的学者,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孙诒让等人为代表。除了孙诒让的研究仍主要表现出考证学特征外,其余几人由于皆受到西方哲学的启示与熏染,治子各有独到的革故鼎新,使诸子学研究焕现出20世纪初中国学术根本转型的鲜明时代性格。
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均重视、并热忱于治子,这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先秦子学具有能动的创作性,不事依傍,因而不仅是中国固有学术的宝藏,而且能与西方学术相化合;由此都将开掘浚发这一宝藏、淬厉增长中国学术这一部分优秀遗产,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章太炎在1906年的《论诸子学》(后改名为《诸子学略说》)一文中这样写道:“所谓诸子学者,非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他十分赞赏先秦诸子“矜己自贵、注重独立”的品格,认为它们寻求义理,自坚其说,持论强盛,义证坚密,绝少依傍:“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34〕,绝不像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强相援引,妄为皮傅,调和附会。他以“上天以国粹付余”自许,以免使“支那宏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自警,将以诸子学说为主的传统文化视为矿藏,“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已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益”,力求以“傃古”“禔以便新”〔35〕。他按刘歆《七略》,把周秦诸子分为十家九流,其《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等篇,逐一对各家考镜源流,辩析剔抉,融会贯通,评观得失,“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给了胡适以颇大启发,胡适更将其中《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推为“空前的著作”〔36〕,并从中细悟出章太炎治子的特点是以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来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37〕。由此,胡适体味到,要治成一部中国哲学史,必须要有比较参考的外来哲学资源:“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8〕。胡适因而表示,他治中国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条理头绪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39〕。
梁启超、王国维也和章太炎一样,十分重视诸子学的地位。梁启超治子,一是有见于西学东渐后一些“沉醉西风者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中国学术有“沦陷澌灭”之虞;二是有见于当时不少学者将中学只是等视为八股、试帖、律赋、楷法,只知“旋贾、马、许、郑之胯下,嚼韩、苏、李、杜之唾余”,传统学术文化出现了深刻断裂的危机。由此他针砭前者“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强调“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予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40〕。针对后者,他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热情赞颂了诸子学的地位:“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在后来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指出:“春秋战国间学派繁茁”、“卓然自树壁垒”,是因为“以思想家的资格创造思想,惟先秦诸哲独擅其能”。他称颂诸子思想是“民族的活精神的尽情发露”,是“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陶铸而成的国民意识”,“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并满怀激情地表示:“在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41〕。王国维则将周秦时代称为中国思想最富创作性的能动时代:“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42〕。他以更为敏锐的学术眼光,将诸子学直接列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夫周秦与宋代,中国哲学最盛之时也”〔43〕,并针对张之洞等人连对诸子学也心怀疑惧、将之归入文学科类之举,特别强调对诸子之书,首先必须从哲学的角度对其思想内容作思考的、求真理的考察与研究:“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44〕。
另一方面,梁启超、特别是王国维,都注意到外来学术进入本土后必须与本土固有学术思想“相化”,才能获得支撑的息壤并生根发芽;而中国固有学术也必须通过找到与外来学术的结合点并与之相化,才能淬厉其本有、采补其本无,得以焕然新生。梁启超将这种结合点称为“遗传共业”、“国民意识”,而诸子学说正是此“遗传共业”、“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新思想建设之大业,……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必须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濬发和合理的箴砭洗炼”;并强调外来的制度、学术“非通过本国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45〕
王国维也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指出:西洋之思想“即令人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与此同时,他更注意到,中国学术因其“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对照“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 步伐严整”〔46〕,必须“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 “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47〕。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学无中西”、中西学术必须两相能动化合的观点:“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48〕,“所异者,广狭疏密耳”〔49〕;中西学术,盛则俱盛,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50〕。尤其是西方哲学已方法精湛、体系朗然、领先一步,中国哲学要获得新生,取镜借鉴,十分必要:“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梁启超和王国维治诸子学,正是更多地表现出受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的样板示范激发,形成了崭新的思路与范式,在清理诸子源流、比较差异、品核得失等学理分析中,引入西方哲学的许多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作为横向的比较参照和纵向的贯通构式。
梁启超早在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授《古今学术源流》时,即已表现出对诸子学的极大兴趣,并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对之著力最多,写了《老子哲学》、《孔子》、《儒家哲学》、《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墨经校释》、《孔老墨以后学派概观》、《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庄子天下篇释义》、《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比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等文或专著。他对先秦儒、道、墨、法四大家议论纵横,观析流变,阐察义理,褒贬得失;对老子的“道”,从本体论、名相论、作用论三方面审察评析;将先秦学派的政治思想概括为无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对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作整体比较以裁定优缺长短,均是贯穿了以西方哲学为浚发、匡正之参照这样一条线索。而他对儒道人生观的崇扬,则可视为对西方哲学不重安身立命的一种救治补弊。梁启超不仅对诸子学兴趣盎然,而且由于受康有为重视古今学术源流及受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近代之演变的启发,使他扩及对整个中国学术史、“道术”史,具有一种明晰的整体考察流变的历史主义眼光。早在1902年写成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即已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这一志意。而这,亦正构成了引发诸子学衍成哲学史的另一酵素,给了胡适以另一启发。胡适对此文表示过极大兴趣,认为:“这是第一次用近代论的历史眼光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第一次给学人一个‘学术史’的见解”;但“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阙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自己忽发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51〕此后胡适愈加留心先秦诸子的研究。其实,后来胡适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现决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革命,激发他写作动机与思路的契机与学术氛围,早已在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处显现出端倪与线索。
至于王国维的诸子学研究,较之梁启超更具一种“哲学专攻者”的素养与气质。有人曾赞叹王国维治学“其心中如具灵光,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52〕。此灵光,实际上正是因他所独具的深湛的西方哲学素养、及其注重中西学术能动化合的心力与眼光所发注而来。以西方哲学为“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诸子学等传统学术文化,使王国维别具法眼,披沙见金,达自如敏锐之境。他在1906年即注意到老子哲学的“道”是一种探究宇宙之根本的形而上学,由此判定其为中国真正之哲学的开始;他以新柏拉图派的分出论来比较列子的实体论及天地开辟论,并将列子的解脱观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的悟道体验相互阐释;他最先从西方心理学角度对孟子的“仁义礼知”作出分析立论,并从这一角度定出其伦理学说的基础,揭示其首开宋儒心性理论先河的脉络;他用西方名学来整理诸子名学遗产,根据墨子的定义论与推理论,论列墨子在名学上之位置与西方芝诺相近;他高度推崇荀子的“心有征知”说所揭示的“直观因悟性而起”的精见,认为这一见解超过了上自希腊哲人直至康德之识见,只有叔本华的充足理由论文第二十一章全文有所涉及,但也只可视为荀子此说的注脚而已。他更以西方哲学的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对中国旧学最普泛的范畴“性”与“理”加以论释:以西方的“理由”、“理性”,与中国的“天理”作比较鉴定,考“理”之语源,察其变迁之迹,辨析其性质只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即仅有心理学上之意义,但在中国却演化成了形而上学及伦理意义上的“天理”;他并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分析架构,对“性”这一古代诸子最具争议的范畴,甄定为“知识之材质”而“非知识之形式”,只能从经验上立论,并由此对上自周秦、下至宋明的历代诸子言性者之所以不得不盘旋于善恶二元论所表现出的种种自相矛盾,从认识论角度作了透彻辨析。
像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一样,胡适也感奋于中国学术由于得了“欧美日本学术界的无数成绩供参考比较,给无数新法门与借鉴之镜而得以明晰昌大。他认为《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无人能解;《易系辞传》的“易者,象也”,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子的“类不悖,虽久同理”,得亚里士多德的“类不变化”的参考更易懂〔53〕。胡适明确地将运用西方哲学的思考方法作为研究诸子学的工具,使中西哲学得以相辅相长引为自己的责任:“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54〕。由此,他直接将诸子学的复兴与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这两者的结合,看成是中国新哲学诞生的必然的、也是最好的契机:“子学复兴,经过清代学术的变迁,有点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再加上西洋学术输入潮流,——两大源头汇合,若不能产生中国的新哲学,则辜负了好机会”〔55〕。而胡适著写哲学史,不但在契机动因上如前所述受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诸子学研究的启发,而且其撰写哲学史的三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可以说也是与上述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利器的诸子学研究路数一脉相承并更为集中推进,还在观点的辨识、角度的匡设上,进而与之相互切磋,相互激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诸子学研究,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个不可分割、连成整体的学术景观;前者是辅垫与酝酿,后者是集成与突破。可以说,这是发生于本世纪初中国学术史的十分重要的现象之一——这是一个学者群,在20世纪初这一学问的过渡时代中,致力于学术转型、开辟新学界的群体耕耘与群体播种。1914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新增了“中国哲学门”; 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时,哲学系已位列显著地位。诸子学向中国哲学史的嬗变这一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的重要转型,如果就其作为经学衰落的产物、作为以西方哲学的思考精神和研究方法与中国诸子学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是中西最高学术相结合的产物而言,无疑可视为对19、20世纪之交沸扬于中国学界的“中西学术体用之争”的一个事实上的总结,即:在中国学术史进程中,中国哲学在本世纪初首先在哲学史领域获得蜕出与独立这一事实本身,正是对“中体西用”论的一个根本的、胜利的、事实上的超越。
注释:
〔1〕〔2〕《康有为上皇帝书》。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4〕〔5〕〔6〕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7〕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
〔8〕《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第81页。
〔9〕《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2、第186页。
〔10〕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
〔11〕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12〕郑登云:《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13〕《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54页。
〔14〕参见王国维:《哲学辨惑》。
〔15〕参见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
〔16〕〔17〕谭嗣同《仁学》。
〔18〕〔19〕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20〕梁启超:《论自由》。
〔21〕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2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23〕王国维:《哲学辨惑》。
〔24〕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25〕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
〔27〕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驳建立孔教议》。
〔28〕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
〔29〕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
〔30〕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31〕章太炎:《论诸子学》,载《国学讲习会略说》。
〔32〕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子之法》。
〔33〕〔36〕〔37〕〔38〕〔3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34〕章太炎:《国学讲习会略说·论诸子学》。
〔35〕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尊荀》。
〔40〕〔4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
〔4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43〕王国维:《哲学辨惑》。
〔44〕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4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
〔46〕王国维:《哲学辨惑》。
〔47〕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48〕〔49〕〔50〕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51〕胡适:《四十自叙》。
〔52〕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载《诗词散论》,台北开明书店1953年版,第68页。
〔5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54〕胡适:《先秦名学史》。
〔5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标签:哲学论文; 梁启超论文; 章太炎论文; 王国维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经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甲午年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