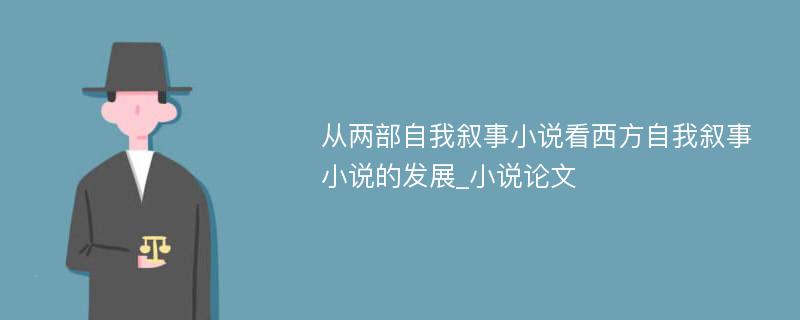
西方自叙体小说发展管窥——从两部自叙体小说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叙论文,小说论文,两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作家塞林格的自叙体小说《麦田的守望者》(1951)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开篇即告诉读者:“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①]像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1850)那样,由主人公从头到尾地叙述自己从小到大的传记式故事,已成为传统自叙体小说的叙述惯例。霍尔顿却对此感到“腻烦”,他不打算“告诉你他妈的我整个自传”,只想说说“我在去年圣诞节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这段话并非信口开河,而是表露出作者对狄更斯式自叙体小说有意识的背离。背离了什么和背离的意义,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对这两部相距百年、在各自时代都颇有反响的作品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西方自叙体小说的一些发展变化。
1
由作品主要人物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小说,便是自叙体小说。西方自叙体小说源远流长,几乎与西方小说发展同步。作为西方小说源头的史诗《奥德修纪》中,主体部分的奥德修斯海上漂流历险经过是由他自己以第一人称倒叙的。现存最早的罗马小说、公元一世纪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由主人公恩柯尔皮乌斯自述到处行窃的经历、见闻。对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以《小癞子》为代表的“流浪汉小说”,也是自叙体小说。自叙体最初为人们所青睐,很大意义上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便的结构方法:“他的经历也许并非显得合乎逻辑地联结在一起,但起码由于所有部分都属于同一个人这种一致性,而使这一部分跟其它部分连结起来。……第一人称将把一个不连贯的、框架的故事聚合在一起,勉强使它成为一个整体。”[②]随着自叙主人公自身重要性的增强,自叙体小说逐渐由见闻录型转向自传型,像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那样被叫作“我自己的传记”或称作“回忆录”。其中“我”不仅是一连串事件的负载者,而且是情节自始至终的完成者,情感强度和参与力度大大增加,情节从“我”所见闻的一系列故事,发展为关于“我”的“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高尔基语)。小说作者不仅要把握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合乎客观真实的逻辑,而且要把握它们与人物性格的密切联系,让性格化的行动构成情节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恰恰与整个西方小说结构意识中心从建构故事转向塑造人物的过程相吻合。
狄更斯的自叙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鲜明地体现了传统小说“性格—事件”或“人物—情节”的模式,它主要从人物外在行动出发进行描叙,记录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具有井然有序、自我完满的线形叙事结构。比起主人公仅起聚合作用的自叙体小说来,狄更斯的小说大大地进了一步,他不仅加强了情节间的有机联系,而且努力把主人公塑造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怀着把握整个人生的自我完满的信心,试图兼容个人故事与社会画卷。但狄更斯更多的是一个成功的讲故事人,而不是人类心灵的探秘者,他“从来不从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发展人的性格,而是着手刻划人物的本性是怎样由其一生的外部生活环境发展而成”[③],他的自叙体小说是属于“社会小说”型的。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发展变化的,他们逐渐意识到社会现实不仅是由人们外在的日常生活及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现实关系构成,还包括人们丰富、微妙的精神生活,人是与世界对等的独立存在的主体。人们从认识外界进而认识自己,从认识自己的外表进而认识自己的内心。西方小说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结构意识出现以人物心理为结构中心的趋势,自叙体小说更是加强了心态特征,而这也正是自叙体小说魅力之所在。与狄更斯一起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夏绿蒂·勃朗特在她的《简·爱》等三部自叙体小说中,在表现主人公个人故事同时,展示出他们细腻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轨迹。作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变格的书信体、日记体成为自叙体小说的新形式,也是叙事心态化的一种表现。可是书信体和日记体的自叙小说,常需要作者以编者或次要人物的身份作一些串连、解释,自传体仍不失为较自由的方式,不过自传体也因加重了心态内容而有了变化。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的奇书《项狄传》(1759—1767)戏拟了从主人公出身讲起、情节性强的自传体小说,打乱了叙述顺序和连贯性,让主人公自传部分只成为微不足道的一丁点,以表明小说结构的基础不是逻辑性的而是情感性的原则这种认识。浪漫主义小说家自觉地把自叙体小说作为表达个人情感的重要形式,加强了封闭性、内向性,文体上自传、回忆录、忏悔录、独白等混合,加重内省色彩,篇幅也趋短,夏多布里昂的《勒内》(1805)、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1836)便显现出如此特征。现代自叙体小说更是“向内转”,从自我出发去认识和表现生活,把自叙体小说的心态特征推向极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1929)、萨特的《恶心》(1938)、加缪的《局外人》(1942)、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7)、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1944)、《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纳博科夫的《洛丽泰》(1958)等自叙体小说虽具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风格,但都从心理角度去探讨人生世界,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便是其中的一部杰作。
这部小说讲的是圣诞前夕,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因为功课不好,第四次被学校开除了。他决定提前离校,在旅馆里住几天再回家。他去夜总会跳舞、喝酒,在旅馆里受到妓女和皮条客的敲诈,与女友去看戏、溜冰,先后与同学、老师和妹妹谈话,最后精神崩溃进了疗养院。不同于《大卫·科波菲尔》为追求对社会作全景性、俯瞰式反映而采用多线结构、完满的故事情节的写法,《麦田的守望者》情节平淡,线索单一,只描写主人公生活的一个片断——在纽约一天两夜的经历。尽管出现了各色人物,作者不对他们作过多的交代,更不让他们构成独立的故事,始终专注于对主人公心理的剖析,展示他在恶俗现实中怀疑、烦闷、寻求、绝望的心路历程,每个场景都通过他的意识显现,人物对话中总夹杂着他的思绪。作者非常注意保持限知视角,视点人物霍尔顿是个孩子,敏感又不失天真,唯其如此,他的痛苦才格外真实,他的追求也格外执拗。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塞林格对狄更斯自叙体小说的背离首先就在于突破传统的、自我完满的故事结构,淡化故事情节,充分利用自叙体小说的心态特征,突出主体意味,对人生、人类的生存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从心理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背离也正折射出西方自叙体小说从社会型向心理型,从世态型向心态型不断转化的进程。
2
《麦田的守望者》中还有一处提到了狄更斯。霍尔顿与女友闹翻后,独自去看了场电影,影片讲的是因战争负伤失去记忆的男主角与一个“可爱、温柔、真挚”的姑娘相遇,他们恰好都带着狄更斯的《奥列弗·退斯特》,“因为彼此都喜欢这个作家”而一见钟情,可是男主角以前的未婚妻突然出现,他也恢复记忆,由于温柔的姑娘“心地十分高尚”,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结局是人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故事对高尚品德、善良本性的信念、自我完满的叙事结构、大团圆的结局与狄更斯小说颇有几分相像。尽管他旁边的观众感动得要命,霍尔顿却十分反感这由两个“热爱查尔斯·狄更斯作品的疯子”而敷演的“假模假式的玩艺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尔顿所厌烦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不仅指对讲完整故事的热衷,也包括建立在传统生活基础上对人生的理解,自我完满的故事结构正是建立在对生活自我完满的信念的基础上。《大卫·科波菲尔》和《麦田的守望者》都是带有一定自传性的自叙体小说,但作者与主人公的联系主要不是事实上而是精神上的,正如狄更斯在大卫身上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霍尔顿的精神历程也是塞林格自身精神世界的写照。两个姓氏相似的自叙主人公Copperfield(科波菲尔)与Caulfield(考尔菲德)精神面貌的不同反映出作家现实感、世界观上的差异,这才是《麦田的守望者》对《大卫·科波菲尔》更深层的背离,也反映也古典和现代自叙体小说在心态内容方面的明显差异。
在他们各自的时代,狄更斯和塞林格都是批判现实的作家。狄更斯出身寒微,童年时全家曾因负债进了监狱,唯一留在外面的他失学去当童工,这段底层生活成为他一生都没摆脱的心中阴影,也使他一直怀着对穷人真挚的同情。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他带着早年经历的切肤之痛去反映了孤儿命运的悲惨,寄宿学校的野蛮,做童工的屈辱,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欺侮践踏,金钱观念对婚姻和家庭关系造成的毒害,鞭挞了贪婪、冷酷、卑劣、自私、虚伪等恶德。尽管揭露是无情的,批判是激烈的,但是“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批判者,同时又深深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④]。狄更斯对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并不怀疑,他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理性的,对人类的进步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认为社会的弊病可以通过努力诸如道德教化加以去除,同情和仁爱的力量能改善社会秩序,当大卫成了落入冷酷世界无依无靠的孤儿时,“有辟果提,有密考伯一家,有贝西姨婆,有特拉德尔——各色好心肠的人的联盟,来共同对付强大黑暗势力”[⑤],“善”终会在现实中或精神上取得胜利。在“善”的信念指引下,个人的不懈努力总能获得回报,大卫终于事业有成,爱情圆满。其他的好人如贝西姨婆财产失而复得,特拉德尔发达有望,博士夫妇和好如初,辟果提家、密考伯家、甚至前面晃过一面的穷教师麦尔先生都在澳洲安居乐业,获得新生。恶总会得到揭露和惩罚,坏人希普、黎提摩进了监狱,纨绔子弟斯提福兹以死救赎了他的罪过,傲慢的斯提福兹夫人永远不能摆脱丧子的痛苦。大卫作为正面理想人物,实现个人价值的标志不超出社会认可的世俗意义的成功:“坐在那里,在四匹马的后面:受有好的教育,穿有好的衣服,衣袋里有许多钱;向外张望我过去在困苦的旅途中睡过的地方”,“我在名利两方面都有了进展,我的家庭之乐是圆满的”,只是个人奋斗过程中的道德自觉使他高于那些为富不仁者。在最个人化的情感生活方面,大卫也始终是道德化的,听凭内心冲动作出错误的婚姻选择后,他扼制懊悔情绪:“她与我的存在既然是那么合而不可分,那种幻想是最无谓的”,“把我必须负起的负在我自己的肩上,而且依然要快活”,让朵拉的病逝体面地结束婚姻的不幸,又让第二次完美的婚姻符合朵拉的遗愿以避免任何负疚感。像他那个时代许多作家一样,狄更斯“在对现实社会作出深刻批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依赖这种现实而存在的一些流行的、对生活作出终极答案的观念和信条”[⑥]。
塞林格出身富商家,生活在战后美国所谓“丰裕社会”,对物质方面的贫穷没有狄更斯的那种深刻体验和敏感,但经历了二次大战对人们心灵的重创、“非人化”社会带来的精神病态,在人们对现存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已产生根本性怀疑的时代进行创作,精神上的空虚、贫瘠、孤独、无归属感却是狄更斯难以体味的,作者通过自叙主人公表现了现代人面临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畸形状态而感受的痛苦。大卫受到的是具体的社会弊病和个别的坏人对好人造成的伤害,对真假、善恶、美丑有着明确的界定,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协调。霍尔顿则失去了与社会协调的可能,因为他对西方中产阶级体面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到处看到的只有西方文明虚伪性的表现——即他最爱说的“假模假式”。这种虚伪远比希普式的“作假”要可怕,希普的虚伪是个别的、易辨认、可抵御的,而价值观念体系的虚伪,就动摇了人类对世界理性把握和自我完满的信心,带给一代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巨大心灵痛苦。霍尔顿是富家子弟,就读于贵族化的名牌中学,可他觉得“这是个最最糟糕的学校,里面全是伪君子”。校长与教师灌输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人生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竞赛成功的标志就是像那个校友、发财的殡仪馆老板一样,坐上“混帐大‘凯迪拉克’,”名利双收。社会给年轻人指引的成功之路是做一个遁规蹈距的学生,“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后“只是挣许许多多的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喝马提尼酒,摆臭架子”,自己都不能把握真实的自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个伪君子”?霍尔顿憎恶和拒绝这种成功之路包含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功课不努力,不想上名牌大学,言语粗俗,要他干的事“没一样是好好照着干的”。但他并不是痞子流氓,他敬佩以生命为代价坚持说真话的同学凯瑟尔,反感思想上的“统一和简化”,厌恶“话不离题”的循规蹈距,把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交流、沟通看作人生“真正的东西”,不过是以不肯进取来避免同流合污,以颓唐放纵来维护内心的价值,在精神上苦苦寻求更真实、真诚、富有人性的生活。但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已经脱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已成奢望,精神上的孤儿霍尔顿得不到大卫所得到的同盟。想帮助他的历史老师与他在思想上“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同学们“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英俊潇洒、遵守校规的室友斯特拉德莱塔不过是“好色的杂种”,亵渎了霍尔顿心中珍藏的对琴的纯真感情;酒吧里遇见的姑娘只知道崇拜电影明星;他的女友萨丽是个“天底下最最假模假式的女子”,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思想;他求教的同学路斯要他去找精神分析医生;他所信赖的老师安多里尼给予他的不过是陈腐、世故的告诫:“你这样骑马瞎跑,将来要是摔下来,可不是玩儿的”,要“发现自己脑子的尺寸”,而且他还极为震惊地发现这位他唯一看重的老师好像是个同性恋者。寂寞孤独、苦闷绝望中的他向自然寻求安慰,想离开都市的人群,遁入乡村的林中小屋,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向人群中最接近自然的部分——孩童——伸出求助之手。尚未受文明污染的儿童不知矫饰和势利,对人和世界有着出自本能、直觉因而更接近真实的理解,保有这个浊世里仅有的纯真和聪慧,所以霍尔顿向能“好好听着”他的小妹妹菲芯倾诉,向心爱的因病死而永远留在童年的弟弟求援:“艾里,别让我失踪”。他认为真正有价值和喜欢做的事是当个麦田的守望者,不让在麦田里游戏的孩子们坠下悬崖,也就是不让纯真坠入恶俗现实的深渊。大卫也曾表达过对大自然和童年的强烈留恋,希望他和小爱弥丽“生活在树中间和田中间,永远不长得更大,永远不变得更聪明,永远是小孩子,手握着手在日光中和开花的草地中游行”,以躲避成人世界的种种不幸。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长大后的世界虽然有丑恶,但真诚战胜了虚伪,善良压倒了邪恶,高尚驱逐了卑劣,基本上还是可以以童心来相处的。霍尔顿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没躲进林中却进了精神医院,出去后还得去另一所“混帐学校”,被逼着回答“是不是打算好好用功了”,他怎么能去麦田里守望?那些站在“那混帐悬崖边”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的孩子们又怎么能不跌落下去?在一个可以用理性理解的世界里,大卫可以做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在一个荒诞虚假的世界里,霍尔顿只能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愤世嫉俗,颓废绝望,又“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⑦]。
3
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逢维多利亚盛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暴露,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仍在向上发展,他一方面怀着艺术家的敏感、人道主义者的真诚,揭露和批判社会阴暗面,另一方面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观,相信理性和进步,认可并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如信仰上帝,乐善好施,追求事业成功,享受家室之乐,等等。大卫是这种思想特征的体现者,这时期其他的自叙体小说主人公如简·爱,总体上也没有脱离这个思想体系。现代社会人们对原来绝对主义的信念如上帝、理性主义等产生了动摇,对传统的绝对不变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怀疑,存在主义思想形成弥漫性的影响。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自叙主人公便成了“迷惘的一代”、“局外人”、“晃来晃去的人”及“看不见的人”。他们精神迷茫、分裂、孤独、悲观,在混乱、荒谬、敌对的世界里寻找立足点、寻找自我。他们不接受传统价值观念,不遵循社会习俗认可的行为模式,是“反英雄”。霍尔顿和他们一起游荡,用反正统文化的语言和行为与社会对抗,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追求真谛,因此引起现代读者极大的共鸣和同情。塞林格以表现人道主义的危机来坚持人道主义立场,通过霍尔顿的心路历程来探讨人类生存境况、人生意义等既现实又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严肃问题,这也是现代自叙体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
西方自叙体小说历史悠久,成绩斐然,悠远、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滋养是它产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乐观的希腊信仰”(罗素语)和商业文化的影响,使西方社会重视个体,强调自我,肯定和张扬个性,基督教文明又培育了西方人的忏悔意识和内省心理,自叙体小说是表现作者自我意识、自身人生经验、感情需求、心路历程的适宜形式(这些或许能为探讨中国自叙体小说的晚生提供一些思路)。《大卫·科波菲尔》和《麦田的守望者》这两部自叙体小说都是反映了各自时代社会心理、美学思想,又触及了基本人性因而深为人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我们从两部小说中看到,塞林格背离了狄更斯式对建构自我完满的故事的热衷,以心理性而非逻辑性的原则来结构自叙体小说,他更背离了完满的故事所依赖的自我完满的传统世界观,从乐观的肯定转向悲观的怀疑,在哲学的层次上探讨现实的人生意义。他的背离不是孤立的,这两点正典型地折射出西方自叙体小说不断加强心态特征的走向,及心态内容上从古典的建构性到现代的消解性的发展变化。
注释:
① 《麦田的守望者》引文均见施咸荣的同名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珀西·卢伯克:《小说技巧》,伦敦,1928年,第13页。
③ 理查·豪恩:《查尔斯·狄更斯》,转引自《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④ ⑤安德烈·莫洛亚:《狄更斯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32页。
⑥ 殷国明:《小说艺术的现在与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⑦ 加缪:《局外人》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