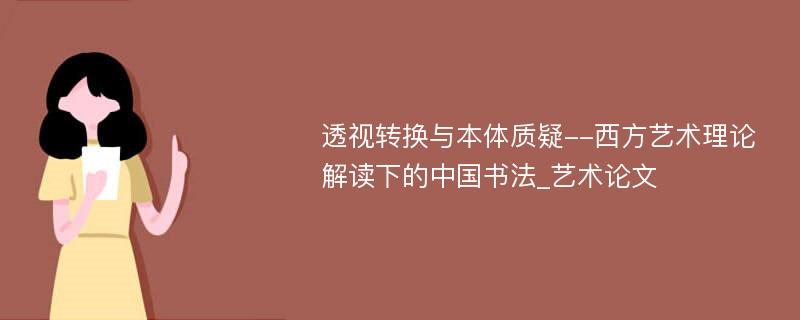
视角转换与本体追问——西方艺术理论阐释下的中国书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书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阐释、分析乃至界定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书法也不例外。对此,学界存在激烈争论。否定者认为,书法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根本就不具备阐释中国书法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已有的阐释也让人觉得有一种生硬感与牵强感。还有人认为,用西学来解释中国书法是一种文化殖民行为,实质上是通过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有意误读和“西化”,来改造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和视觉传统。赞同者则认为,书法与西方艺术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相通性,这为理论上的相互阐发提供了基础。书法的现代转化导致中国古典的哲学和艺术理论很难解释现代书法的一些新现象,除了西方的艺术及其理论外,没有其他值得借鉴的参照系,何况西方艺术理论也的确具备一些中国传统书论没有的优势,用它来阐释中国书法,可以提供新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启示。
以上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第一,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书法已经成为现代书法研究的一个学术传统和事实,对此,学界需要面对的不是“应不应该用”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用”的问题,即如何借鉴西方的理论才恰当、合理、有效;第二,需要思考和总结的是,在已有的阐释行为中,形成了怎样的传统和模式,存在怎样的洞见和偏见?西方的理论对于当代的书法研究、批评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未来书法的发展有何启示?第三,中国书法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与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变迁历史是紧密相连的,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书法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方法论问题,其背后包含着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异常复杂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心理,这些心理对当代书法创作与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何应对这些影响,是书法界需要思考的深层次文化问题。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必须说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书法界和学术界用西方理论来阐发书法的现象和问题,对于西方学术界和艺术界如何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书法基本没有涉及,此当另外撰文分析。
一、身份与归属:书法的学科“定位”与“错位”
晚清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和存在形态开始全面瓦解,不得不在知识谱系、学科划分和概念命名上进行大的调整,即所谓的“废旧学,兴新学”,而调整的依据就是西方现代的知识结构和学科模式。由于书法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现象,在西方学科中找不到对应的形态,最初处境颇为尴尬,几经争议,最后还是勉强被归入到“艺术”和“美术”的范畴,书法于是改变了它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进入到现代文化和教育体系中,被赋予了新的身份。
这种强行把中国文化形式规划到西学结构中去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界强烈的“西潮崇拜”意识和急切的“与西方接轨”愿望。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士人主动学习西方,西方文化的地位不断提高,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20世纪初,国粹派代表邓实已经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①。即便是晚年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强调中国文化具有更高的精神性的梁启超,也在1926年给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讲演(周传儒记录整理而成《书法指导》一文)中,将书法归入美术门下,还提出四点原因:书法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和“个性的表现”。这四点都是和西方的油画相比较而得出的“美术”的共通性②。其实这四个特征不用与西画对比,在中国传统的书论中都几成套话,但梁启超还是选择了新的参照系来旧话新说。书法最直接的参照系不再是传统的中国画,而是西画,这就为后来中国画日趋脱离书法,书法美术化、视觉艺术化埋下了伏笔。由于这种学科归类实际上是把西方艺术确立为基本的判断标准甚至绝对尺度,人们十分自觉地用这些艺术的标准和要求来理解和评判书法,书法的独特性和本体内核常常因“艺术”和“美术”的涵义无法概括而被忽略,只有那些作为“艺术”和“美术”的层面不断得到彰显,书法遂由传统的“道”和“法”变成了现代的“术”。因此,这个现在看来十分自然的归类,却为书法后来的发展趋势、表现形态乃至本质界定确立了基本的向度。把书法归入艺术或美术,就不仅仅是学科规划和视角调整问题,更是本体置换问题。
虽然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把书法归为“艺术”和“美术”,但反对的理由不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强调书法具有西学难以涵盖的独特性,归为美术是对书法的曲解或贬斥,而是用西方艺术或美术的标准来看,书法不够格。30年代初,朱光潜曾一语点破其中的玄机:“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和图画有同等的身份,近来才有人怀疑它是否可以列于艺术,这般人大概是看到西方艺术史中向来不留位置给书法,所以觉得中国人看重书法有些离奇。”③在学界,郑振铎被视为否定书法是艺术的代表人物。1933年,郑振铎、朱自清、冯友兰等人在梁宗岱家聚会,席间郑振铎极力反对把书法算作“艺术”,理由就是中国书法与其他国家的文字书写“追求个性”、“追求美”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西方没有把“写字”归入艺术,中国也不必搞特殊化。郑振铎的观点遭到在场多数人的反对。由于50年代郑振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其否定书法是艺术的言论便成为后来诟病他“阻挡书法发展”的罪证④。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以西方艺术为标准,书法的确不是“艺术”,这个判断不存在抬高或贬斥书法的意思,但由于“艺术”这个概念背后有“西方”和“现代”标准的“权威性”撑腰,说书法不是艺术无异于取缔书法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反过来说,把书法归入艺术,的确在形式上有助于提升书法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书法失去了实用性、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它要么被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作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工具,要么变成古董和拍卖市场上的“商品”、热钱的“炒货”、西方游客带回家的“异国情调”,或者老年大学的“夕阳红养生活动”……视为艺术算是最好的定位了。
尽管书法很早就被划分到艺术和美术的学科下面,但直到1962年才在高校设置书法专业,而实际上真正得到系统的学科化发展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书法界展开了关于“书法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但这次讨论不是把书法的艺术本体从西方艺术标准中分离出来,而是进一步的靠近。由于1985、1986年间西学方法大量涌入,关于书法艺术的本质界定也迅速与新引进的观点相结合,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形式主义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人类学、“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甚至“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几乎都被用来解释过书法,书法被界定为“生命的形式”、“视觉艺术”、“抽象的符号艺术”、“写意的哲学艺术”、“汉字造型艺术”、“线条的艺术”、“空间的艺术”、“表现的艺术”等等。到90年代初,系统的“书法学”被建构出来了,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有了相应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语言论形态和围绕书法史、书法赏评、书法创作、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等的学科分支与知识谱系⑤。书法界开始从艺术社会学、创作美学、接受美学、形式美学、主体论美学、符号论美学等角度来阐释书法艺术的“多质性”⑥。
90年代以后,在各种书法大赛和展览的推动下,书法界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如“流行书风”、“学院派书法”、“广西现象”、“书法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在书法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追求上出现了解构经典、张扬“民间”,拒绝“审美”、崇尚“审丑”,强调“形式刺激”、忽视“心性培养”等各种现象,引起了书法界乃至文化界、大众对中国书法的隐忧、惶惑和质疑。学界围绕书法的创新、形式、制作、评奖机制、审美标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这些现象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当代书法研究和批评在学理上的分歧、价值判断上的混乱和本体论上的迷失。有人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思想解构关于书法的本质形态,强调书法存在的历史主义倾向,认为“书法是什么”应该放到书法史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⑦;有人从后殖民主义思维出发,将西学视为殖民工具,拒绝西化阐释思维,反对80年代关于书法本质的种种“西化”界定;也有人强调书法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软实力价值,书法在东西方文化竞争、中国文化复兴和树立大国形象的伟大进程中被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书法的“艺术性”和“文化性”都被“政治化”⑧。总体上看,就是要从文化的层面来重新审视书法,在“艺术书法”与“文化书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和新的突破口。要把书法的涵义从狭隘的“艺术”领域拓展到更为深广的“文化”视野中去,强调中国书法的“去艺术化”、“去西化”,“还原”其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内涵,祛除附着在书法上的各种“异化”机制和发展歧途,重新思考“什么是书法”。
总之,西方艺术观念的介入为书法的学科归属、发展趋势、表现形态乃至本质界定确立了新的向度,也使整个书法研究不得不在观念和价值系统上进行不断地调整,以应对这种新的转变。书法研究在一个双向的过程中得以展开,“一方面是义无反顾地瓦解着传统书法阐释机制的神圣殿堂,另一方面又不无仓促地铺设着现代书法理论思维的初始构件,前者的破坏性和后者的建设性,构成了20世纪中国书学错综复杂、骚扰多变的历史图景”⑨。
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阐释模式及其误区
在用西方理论来分析、阐释中国书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倾向或模式:科学主义模式和人本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直接承袭了现代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主流形态。
科学主义阐释倾向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已经比较突出。当时,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用西方的心理学来解释书法的艺术规律、创作心理等,重视审美经验的科学分析,甚至照搬自然科学的量化标准和实验检测手段。比如心理学家萧孝嵘的《书法心理问题》,高觉敷的《书法心理》,喜好机械工程、光学的陈公哲的《书法矛盾律》、《科学书法》等。除了科学家之外,也有书法家采用心理学、统计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书法教学规律,比如胡毅的《写字习惯之时间方面(书写实验之一)》,对大中小学生书写时的字形、笔画、习惯与书写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种实验,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些科学结论⑩。这些著述大多是把书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实例,目的不在艺术,而在科学。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主义的分析和阐释模式被大量运用于线条、笔法、空间、节奏、章法结构和视觉心理的研究中,这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的抽象主义美学、分析美学、形式主义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符号学和现象学等理论形态。
书法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与现代中国人的“科学崇拜”有关。科学概念的广泛运用是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晚清以来,科学不仅是解放的象征和召唤,而且也为各类社会文化改革提供了客观根据。它不仅证明了新文化人物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这种变革的目标和模式,并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公理世界观(11)。在强势的“科学”标准下,中国画、中医等都曾被定为“不科学”而差点遭废除。把书法研究纳入科学化的“公理”系统和轨道,也必然成为中国书法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科学主义阐释模式在教学中可以产生明显的效果,通过细致、精确的空间和构成分析,学生可以准确把握法帖的点画细节、用笔方式、运动节奏,迅速捕捉原作的外形,进行“逼真性”临摹。因此,这种阐释模式在当代一些学院教学和书法研究中比较流行(12)。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误区,其阐释的效度主要集中在书法的“技”和“术”的层面,对于书法背后的“道”、“理”、“韵”、“神”、“气”等更深层次的问题难以奏效。书法的动态形式和精神气韵容易被简化为几何与数学的机械构成,书法创作的特殊性、复杂性被描述为一般的心理学反应模式,书法活动的创造性、偶发性和随机性在科学公式和视觉心理学无法辨析、描述、界定的时候被删除。艺术最神圣、最微妙和最迷人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难以言传、无法描述、不可预测和定为一尊的特性。长期运用科学量化和数学思维来分析、理解艺术,会使人的理性能力不断扩张,导致感觉力、想象力和审美性、创造性思维萎缩。从临摹一旦转入创作,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把书法简化为线的几何形态和空间的机械构成,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笔墨观念的曲解和消解,也是把书写者和欣赏者当作机器来对待,更是对中国古代书论的阐释、描述系统的误解。中国古人对于书法形质的描述和阐发被重视逻辑和理性量化的现代科学视为难以实证或验证的玄思、感悟和印象主义,认为这种思维粗浅、混沌、神秘、零散而随意。其实,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这种思维和阐述形式也许更符合审美规律。中国古代书论常常是将抽象化的文字造型通过联想、比喻等诗化手段,转化为丰富的自然物象与心灵节奏,从而激发人们进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诗意境界,赋予有形、有限、有量的文字组合以无名、无限、无极的自由可能。而科学主义的阐述方式恰恰相反,要把书法这无名、无限、无极的自由想象世界分解、切割、“还原”成有形、有限、有量的几何形式和机械运动。在古人那里,书法是人的精神气韵、心性涵养的外化,是自然界一切美与力的展示,高妙的书法作品,有“飞走流注之势,惊悚峭绝之气,滔滔娴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百体千形,巧媚争呈,岂可一概而论哉”(萧衍《草书状》)。现在不同了,视觉张力、装饰效果、抽象符号、图像意识取代了传统书法诗意化的想象神游,拼贴、装置、复制取代了传统书法“心手双畅”的抒情写意,板滞的图案、色彩和“有意味的形式”取代了传统书法那反映生命本源的气韵生动,肤浅、做作、平面而类型化的形式翻新取代了传统书法“入妙通灵”的精神探索。
其实,西方人也承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是感性和审美自由的敌人。早在两百多年前,德国思想家席勒就指出现代人的两大病症:一方面以抽象的科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以粗鄙的情感为代表。“抽象的思想家常常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分析印象,而印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会触动灵魂;务实的人常常有一颗狭隘的心,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被关闭在他职业的单调的圈子里因而不可能扩展到别人的意向方式之中”(13)。关于自由落体,伽利略比亚理士多德“正确”是因为现代物理学不再相信感觉。现代人精于算计,不会感受世界,只会测量世界。美与不美,只能借助“三围数据”和其他种种“科学公式”。在古人眼里,美人“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出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曹植《洛神赋》)。而今人呢,除了喊声“美女”还能想到什么?没有感觉,现代人因此告别了比喻、联想和自由创造。古人在感觉美,现代人在测量美。古人没有关于美的“科学”标准与数据,而他们拥有真正的美;现代人拥有了美的“标准”和“美学”,“美”却离他们远去。因此,当代书法研究与批评应该让大众懂得如何欣赏书法的美,提升大众的审美情趣,而不是为大众制定审美的“标准”和“格式”。
从深层次去思考,这种科学主义向感性世界、诗意表达的全面渗透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古典艺术理论基本以“诗性思维”为主,保持着感性的自由和直觉的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这种诗性思维体现的是自然和精神世界还未完全被科学思维占领之前的状态。要理解古人对诗和艺术的本质看法,首先要求我们从现代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生活经验回到古代人的“神话经验”中去。事实上,在古人的经验中,存在者是某种强有力、难以认识的东西,人类是带着某种敬畏之心把存在物视为神圣事物的,因此,古人的经验可以说是一种神话经验,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一开始就与现代人不同。神话(诗)在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在今天生活中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艺术作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区别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但对古人来说,神话就是真理,也是“法律”(神律)。基于此,古典艺术理论强调“艺术即模仿”就不难理解,在古代世界,日常经验与世界的关系已是如此富有“艺术的”气息,根本无须再“创造”。因此,在古人那里,艺术经验与日常经验常常是重叠的(14)。现代科学把世界的一切都加以“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原来那个令人着迷、难以解释、使人无限遐想的神话世界显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月亮”上没有了嫦娥、吴刚、玉兔和桂花树,只有环形山和无边的寂静,“月亮”变成了“月球”,神话的想象世界变成了科学的征服对象,诗意消失了,只留下科学的知识和天文数据。其实,早在古希腊,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宣称真正值得模仿的是超越现象界的“理念”,或者说是美本身和最高的善时,以模仿可感事物和现实的流动变化的一切的诗就必然遭到“不真实”的谴责。这是古典世界的“诗与哲学(科学)之争”。启蒙运动以前,诗占据着上风,但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哲学)获得了胜利,代表神话思维的荷马被称为“希腊人的老师”,今天,老师的称号属于科学家和技师。
散发着神话气息的古典诗歌和艺术的美,是一种“青春的美”,当人类从神话走向理性时,即当人类不再像发现理性和科学之前那样轻信感觉印象时,那种美就烟消云散了。因此,席勒才会发出感叹,当科学的理性思维取代了丰富的感性思维和鲜活的性灵后,“大自然也许可能还会一再有力地触动我们的器官——但它那千变万化的现象对我们来说却丧失了,因为我们在大自然中不寻找任何别的东西而只寻找我们给它加进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允许大自然向内朝着我们运动,而是相反,我们自己以急切地进行干预的理性向外朝着大自然追逐。假使几个世纪之后,有一个人以宁静的、纯真的、坦白的感官去接近大自然,因而碰到大量我们由于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而视而不见的现象,我们就会感到十分的惊讶,在如此光明的白昼有那么多眼睛为什么竟然什么都没看到”(15)。不辨“古今之变”,必然导致用今人的眼睛去曲解古人,不管其方法多么“科学”,其实质不过是离“真理”越来越远。
与科学主义不同,人本主义阐释模式强调人的感性存在,反对把人变成抽象的理性机器,把人的生命意志、情感表现、感性自由视为艺术的本原,重视艺术鉴赏中的直觉和感悟,主要运用直觉主义美学、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接受美学等来研究、阐释书法和其他艺术。
早在30年代,朱光潜就开始系统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典文艺。与纯粹的心理学家不同,朱光潜虽然也是研究艺术思维和审美心理,但他强调的不是科学的冰冷的分析和量化标准,而是活泼泼的审美直觉、艺术想象、悲剧体悟等。他用德国美学家费肖尔、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兼美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和德国学者谷鲁斯的“内摹仿”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物我同一”(天人合一)观念,特别以书法、绘画、古典文学为例,解释艺术欣赏和创作中的移情作用和内摹仿心理。他认为中国古代书论中关于书法的“骨力”、“姿态”、“神韵”、“气魄”等方面的感受,其实是一种“移情”作用,“都是把墨涂的痕迹看作有生气有性格的东西。这种生气和性格原来存在观赏者的心里,在移情作用中他不知不觉地把字在心中所引起的意象移到字的本身上面去”(16)。相比而言,宗白华很少直接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而是致力于在中西艺术思想的对比中发现、彰显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民族性特质,但是其背后的基本理论框架、阐释角度和审美范畴也有不少源于西方,比如40年代他对中国诗画“空间意识”的考察思路就来自西方。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概括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象征物,比如埃及的“路”、希腊的“立体”、近代欧洲的“无尽的空间”,宗白华认为这三种象征都取之于“空间境界”,体现了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考察中国艺术,发现中国艺术中渗透出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空间意识。他特别指出,中国书法所引起的空间感是“力线律动所构的空间境”,完全不同于西方几何形线的静的透视的秩序,而是由生动线条的节奏趋势以引起空间感觉(17)。这一深刻而独到的看法可惜未被当代书法研究者真正领悟和深入体认。虽然后来也有不少人关注书法中的空间问题,但基本上是走科学主义的道路,用西方的视觉理论和抽象艺术观念来分析中国书法的空间构成,缺乏像宗白华那样的人文涵养、生命体悟和中国文化本位意识,显得机械、肤浅。
8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研究模式大量借鉴西方反理性主义、反现代性思想,比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等。从生命意识和感性存在来解释书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科学主义的刻板和机械,但如果过度张扬这种非理性精神,也可能为当代书坛那些粗野、暴乱、狂躁、荒诞、怪异的书风和创作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合法性论证(18)。把古人诗意精神和本真性灵的书写解释成“本我”的“力比多”释放,把古人苦心孤诣和超逸卓绝的风规神韵简化为“个性张扬”,把徐渭诊断为抑郁症患者,说八大是偏执狂,如此等等,不仅体现了一些研究者学理上的混乱,也表现了他们研究心态上的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同样,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创作,使书法从心性培养和精神提升的艺术蜕化成粗鄙情绪的宣泄艺术、原始本能的放纵艺术。书法的文化品质一旦被抽空,书法就变成了“文盲的狂欢”和“草绳乱舞”。我们的祖先从结绳记事到创造文字,从文字的修饰到精神、人格的修饰,文明得以彰显,书法得以成立。而今,倒行逆施,从文明还原到野蛮,从典雅还原到粗俗,从经典化还原到民间化,从唯美还原到唯丑,从文化精英还原到“文化流氓”……其中荒谬,竟成时尚!这不能不令我们对当代书法创作以及研究和批评背后的价值虚无状态感到担忧。
三、病与药:文化误读与本体追问
用西学来阐释中国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问题,还涉及中西文化之间的选择与认同问题,这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趋势和文化价值取向。
“西方出理论,中国出现象”,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了对西方普适主义的论证,这是用西学来解释中国问题的做法常常被人诟病的地方。的确,晚清以来,中国的各种问题都喜欢到西方去找答案和药方,不可否认,向西方学习是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追求富强文明的必由之路,但过度的现代化崇拜和“与西方接轨意识”逐步养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病态心理,读西方的书,用西方的理论,首先是把中国当作病灶,把西方当作药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对西方和中国的“双重误读”,“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19)。这种病态行为在书法研究中并不少见。比如,因为古人说“书法肇于自然”,就认为书法就是“再现艺术”,这是对古人“自然”观念的误解,也是对西方“再现”观念的误解。这种思维实际上通过把西学确立为普遍主义的标准和尺度,把中国文化他者化,从而强化了西方的权威性、中心性和霸权性。当有人通过“精心研究”,终于“发现”石涛的艺术观念符合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论,中国书画的笔墨意象就是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书法也可以称“主义”,也可以“前卫”,还可以“英文化”……以为这是对书法地位的提升,可以证明书法的伟大,其实这恰恰是在贬低书法和中国文化。
反过来说,这种行为也未必能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当代中国书法的“西化”潮此起彼伏,80年代从日本传来“墨象派”、“少字数书”,而后有所谓的“现代书法”,90年代后有了“书法主义”、“学院派书法”和韩国传来的“物波主义”等等(20),这些实验体现了当代书法的创新勇气和探索精神,但目前在书法界和文化界基本上是批评大于肯定,因为从传统的角度看,这些“书法”好像很难称之为书法,不过是对西方的抽象艺术、装置艺术、包豪斯艺术、行为艺术的拙劣模仿;而从西方现代艺术来看,这些书法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又显得相当的幼稚。
从艺术的中西融合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来看,有必要强调中西距离论。众所周知,潘天寿曾经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反对中国画的西化,也反对油画的中国化,主张中西艺术要拉开距离,保持各自的优点和特长。拉开距离不是自我封闭,更不是文化自恋,而是首先“承认”每种文明、文化的“差异”和“个性”,也就是要还原各种文化的“特殊性”。只有在承认的基础上,深入认识各自的特点,才能避免“文化误读”和“文化利用”。文化误读的原因很多,首恶是无知和偏见。黑格尔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上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普通的民族性,就是模仿的技术极为高明,这种模仿不但行使于日常生活中,而且用在艺术方面。他们还不能够表现出美之为美,因为他们的图画没有远近光影的分别。就算一位中国画家摹拟欧洲绘画(其他一切,中国人都善于摹拟)居然惟妙惟肖,就算他很正确地看到一条鲤鱼有多少鳞纹,满树绿叶有几种形状,以及草木的神态,枝枒的飘垂。——但是那种‘崇高的、理想的和美丽的’却不属于他的艺术和技巧的领域之内。”(21)黑格尔认为凡属“精神性”的东西都离中国人很远。有趣的是,在黑格尔出生前两年去世的一位叫邹一桂的中国画家却这样看西洋画:“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小山画谱》)西洋画在邹一桂的眼中如同中国绘画在黑格尔眼中一样,都只是一种技巧与模写,不是真正的精神性的艺术。黑格尔和邹一桂都表现出一定的无知与偏见,用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性”和“远近光影”的科学眼光来衡量中国艺术无疑是错误的,同样,用中国的阴阳五行和笔墨意识去理解西洋画中的明暗、透视和色彩也极为不当。相比而言,贡布里希对中国艺术的理解要准确得多,他指出中国画“所关注的要点既不是物象的不朽,也不是似乎可信的叙事,而是某种称为‘诗意’(poetic evocation)或许才最为近真的东西。中国艺术家今天仍然作为山峰、树木或花朵的‘制作者’。他能把它们想象出来,因为他知道了关于它们存在的秘密,但是他这样做是要记录并唤起一种心境,而这种心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关于宇宙本质的观念之中”(22)。贡布里希的准确理解来源于他在对比中放弃了用一种观念取代另一种观念的思维,而是还原了各自的特殊性。可见,只有经过准确、深入的认知后,才有文化比较的基础和可能,才能避免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霸权行径和自我中心主义。
“距离论”有文化多元主义倾向,但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平等主义,更不是平均主义,政治、经济领域需要民主、平等,在文化和艺术上更要强调贵族化、经典化,不能因为文化有“特色”或“个性”、“古老”或“先进”就否定文化中基本的善恶、美丑与真假判断,“特色论”、“国情说”有时也是掩盖问题的工具。因此,“距离论”、“文化多元论”都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认识的起点。如果把“距离论”、“文化多元论”当作最后的目的,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泥淖。因为“拉开距离”只是为了“众异并存并成,不要成此蔑彼”(吕凤子),但这尚未解决众异之间的矛盾冲突,应对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在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泛滥的今天,许多人放弃了对本体和终极价值的追问,认为对世界、人性和艺术的理解不会有真正的共识,所有的理解都是因时、因地、因人、因权力、因视角、因趣味、因民族、因性别、因阶级、因信仰、因社群……而异的,世界的本质不过是权力意志的表达,真理是一个“谎言”,“存在先于本质”!也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不需”也“不必”去追问永恒价值和终极关怀,他们需要的是众声喧哗的“狂欢”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自信”。但是,在艺术创造和学术研究中,放弃对高贵精神和终极关怀的追求,学术研究必然失去探求真理的勇气和抱负,沦为稻粱谋,艺术必然失去创造真美善的动力和源泉,成为宣泄本能与放纵欲望的场所,学者、艺术家就有可能变成了柏拉图笔下那“最恶的人”,因为“他们是醒着时能够干出睡梦中的那种事的人”(23)。艺术沉溺于本能,哲学变成了“鸡汤”,文化只剩下娱乐和游戏,思想只为了算计……卑鄙何须通行证,高尚哪来墓志铭?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经常与人争论一些早被今人解构的本体性问题,比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虔敬?等等。争论的结果往往是“没有结果”,但正是这无尽的对话和追问构成了哲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使苏格拉底成为西方理性和探索精神的象征。通过苏格拉底的追问,那些被芸芸众生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成见、传统、习俗、礼法和各种权威意见,都经不起理性的审视和逻各斯的检省,证明了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常常不过是笼罩在幻觉和迷信之中。苏格拉底的本体式追问不是为了得到关于世界和自我的最终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反思关于本体的已有“答案”的可靠性、真理性,敞开认识的自由空间,提出关于本体认知的各种新的可能。所以,本体论追问不是要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用关于事物的“惟一的”、“最后的”、“标准的”答案来遮蔽对事物和人性的开放性理解,而是要推进我们对事物的不懈的探索和认知,使我们的人生拥有持续的高昂感。哲学实际上并不占有,而是寻求真理,因为最终的真理只有“神”知道,但只有进行无尽的本体探索,人才可以向神靠近,人才可能拥有高贵的神性,所以,追问是灵魂上升的过程!其实,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有这种哲学化的终极追问,都有对美与善、高贵与经典的不懈探求与表达。书法是什么?书法为什么?如果没有这种本体思维和高度意识,书法不可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其未来将无从谈起。至今为止,《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帖》依然被视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也许从所谓的技法、形式、视觉构成上看,它们都不是最难、最高甚至最具学习典范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它们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评定艺术和文化的高度的最终标准只在于它体现、熔铸和涵养出了什么样的人格、民族性和生命价值。《断臂的维纳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岸的希腊人对美、和谐和生命的礼赞;《蒙娜丽莎》露出的是西方人经过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带来的青春的微笑;中国书法曾经记录了华夏民族的典雅、冲和、质朴、厚重,也展现了这个民族的雄强、桀骜、昂扬与飞动,透过那些千变万化的笔墨意象,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生命形态的雕饰,对心性情怀的舒展,甚至对人生价值的思考都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达。当今中国书法界如果放弃了这些本体性追求,书法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持久地迷恋呢?
越是观念混乱或多元的时候,越需要这种本体论思维,需要回到原点去追问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当今书法界呈现出来的各种“乱相”其实与学理上的混乱与认识上的“无根”状态有关。好比做人,“关于善的理念我们知道得很少,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24)。同样,关于书法的本体我们知道得太少,也必然陷入无序的争论与盲目的探求之中。“回顾当今书坛,文字聚论,时见蜂拥,各执一词,固守其理:或执冰而咎夏虫,或朝菌而论晦朔;或罔扯西语,购置逻辑;或狂托观念,自圣小我;或指鹿为马,变乱参照;或腹生酸液,口含苦水。视其所争所辨,古人或得其明,今世人文已为其解。而书界执此‘热闹’以为繁荣,直令人啼笑不是皆是,悲哀有时无时”(25)。
笔者并不反对用西学来研究和阐释书法,相反,认为目前学界做得还远远不够,存在太多迷误和偏见。书法研究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西学修养,在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上不断拓展,做到尽可能深入、准确地去理解西方,消除文化误读、误解,只有这样,西学才是真正的“药”,而不是“毒”。
在西学和书法的碰撞中,希望看到的是一种相互的照亮与激发,照亮艺术研究思路,激发出更新、更深、更广的艺术认识和艺术灵感。中国书法中有太多精妙的艺术思想和深邃的民族文化信息等着人们去探索、理解、传承与转化。孔子言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宁可不作(创造、书写),也要保养古传的文化精神。“述”是文化得以传承、光大的基础,问题是如何述,用什么方法来述?用西学来“述”大概是现代中国人难以绕开的方式。但不管是用西学还是中学来阐述中国书法,必须把握“述”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信”与“诚”,应该追求像西方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西方人,也应该像古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古人,这不仅仅是“解释学的回归”,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真正起点。
注释:
①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梁启超《书法指导》,《饮冰室合集》(13),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④韩蕊:《郑振铎与“书法艺术”之争的一段因缘》,载《文津流觞》2009年第1期。
⑤参见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上、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⑥参见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⑦参见李彤《书法艺术的思考与阐释》,江苏出版社2007年版。
⑧参见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岳川编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卢辅圣:《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当代对话篇·序》,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参见陈振濂《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总纲》,陈振濂编著《书法的未来:学院派书法作品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⑩胡毅:《写字习惯之时间方面(书写实验之一)》,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33年5月刊行。
(11)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三联书店2004年版。
(12)邱振中:《现代书法教学中的若干重要环节》,载《书法研究》1990年第3期;参见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3)(15)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第68—69页。
(14)参见克吕格《〈王制〉要义》,刘小枫编,张映伟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1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41—42页。
(17)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熊秉明:《书法领域里的探索》,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19)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见魏因伯格《科学、信仰与政治》,张新樟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20)参见朱培尔编《亚洲当代书法思潮——中日韩书法及其主义》、沈伟编《中国当代书法思潮——从现代书法到书法主义》、洛齐编《书法与当代艺术——世纪末的最后碰撞》,中国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1)黑格尔:《历史哲学》,正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2)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23)(24)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9页,第260页。
(25)周永健:《技道之辨——我的书法观》,《翰墨姻缘》(明轩三集·周永健书法文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标签:艺术论文; 书法论文; 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书法欣赏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书法教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