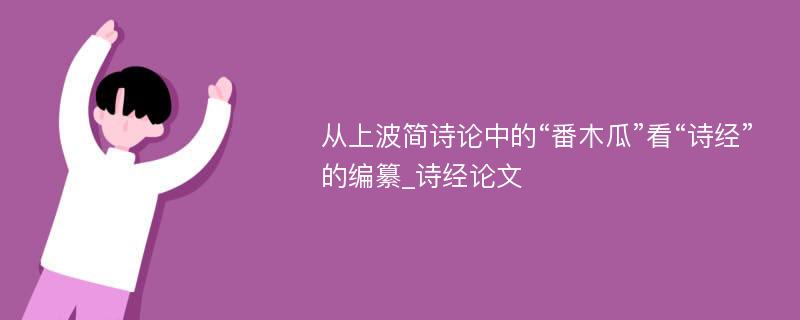
从上博简《诗论》对于《木瓜》篇的评析看《诗经》编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木瓜论文,诗论论文,上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博简《诗论》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于《诗经》的最早评析,它的内容出自孔子。作为《诗》的编定者,孔子对于《诗》中诸篇的理解,应当是我们认识诗旨的标准。《诗论》评诗,惜墨如金,所提到的诗作,其评语用字之少者仅一字,多者一般是两三字或五六字。而关于《木瓜》一诗的评语则有二十字之多(注:上博简《诗论》关于《木瓜》一诗的评论见于第19—18号简,专家或将第20号简补上“吾以木瓜得”五字,则第20号简亦有论此诗的语句,但愚以为第20号简辞语与孔子评《木瓜》诗的思想不类,故不取专家此说。),其对于此诗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孔子何以如此重视《木瓜》一诗呢?通过《诗论》简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理解的线索,并且可以进而分析《诗经》编纂的一些问题。不揣翦陋,试析如下。
一、关于《诗·木瓜》主旨的探寻
《诗·卫风·木瓜》篇共三章,多复叠重沓,应当是民歌风的短诗。此诗各章,词有换而意不移,章相似而意愈深,读后让回味无穷。诗的全文如下: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意本来是明白的,乃得薄施而厚予回报之意。可是,《诗序》却将其联系到春秋时代史事为说,这就引起后世释解的长期纷争。《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注:《诗序》论《卫风》诸篇每每联系卫国史事为说,此将《木瓜》纳入这个模式,不足为怪。)这里所提及者,就是春秋前期齐桓公称霸时援助卫国的为史所艳称的事例。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为狄人攻败,卫国贵族和民众东渡黄河逃至曹地暂住,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馈)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馈)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使得卫国得以复立,后来齐桓公又封卫于楚丘,使卫国民众完全摆脱了狄人威胁,达到了“卫国忘亡”的效果。唐代大儒孔颖达发挥《诗序》之意说:“(《木瓜》)言欲厚报之,则时实不能报也,心所欲耳。经三章皆欲报之辞。”(注:孔颖达:《毛诗正义》卷3,《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儒魏源则推论此诗“正著故卫甫亡之事,则亦邶鄢遗民从徙度(渡)河者所作”(注:魏源:《诗古微·邶鄘卫义例篇》下,《清经解续编》卷1294,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古代研诗者沿用《诗序》此说解释《木瓜》之诗,是为主流。
宋代儒学大师朱熹突破《诗序》束缚,在《诗集传》卷三里提出此诗“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静女》见于《邶风》,是一篇比较典型的爱情诗,朱熹说它“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可见朱熹把这两篇都看成是男女相赠答以结好之诗。朱熹此说实将《木瓜》篇归于他所划定的“淫诗”范围(注:按,朱熹对于《木瓜》诗旨初并不以为是男女相赠答之辞,而只是以为寻常报施的情意表达。《吕氏家塾读诗记》卷6引朱熹的说法是:“投我以木瓜,而报之以琼琚,报之厚矣,而犹曰‘非敢以为报’,姑欲长以为好而不忘尔。盖报人之施而曰如是报之足矣,则报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无物可以报之,则报者之情施者之德两无穷也。”朱熹撰《诗集传》时改变了这个看法而另置新说。)。
清儒对于朱熹的说法多所驳难,对于《诗序》之说亦有批评。其要点如下。第一,史载春秋后期晋卿聘卫时曾赋此诗,依理度之,不当以淫诗示好。毛奇龄说:“《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赋《淇奥》,宣子赋《木瓜》。盖卫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报以为好也。然而此二诗皆卫诗也,向使《木瓜》淫诗,则卫侯方自脉其先公之美诗以为赠,而为之宾者特揭其国之淫诗以答之,可乎不可乎?”(注: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清经解续编》卷21,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毛氏以晋卿在卫侯享宴时赋此诗,断定《木瓜》不当为“淫诗”。第二,若依《诗序》,将《木瓜》作为美桓公之诗,则于史事不合。得到齐桓公颇多恩惠的卫文公在齐桓公辞世以后不仅不帮助齐国,反而趁齐乱而伐之,以怨报德,故而卫风不当有此诗。因此,姚际恒谓“卫人始终毫末未报齐,而遽自拟以重宝为报,徒以空言妄自矜诩,又不应若是丧心。或知其不通,以为诗人追思桓公,以讽卫人之背德,益迂。且诗中皆绸缪和好之音,绝无讽背德意”(注:姚际恒:《诗经通论》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第三,清儒或有另辟蹊径申述《诗序》之说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四认为此诗是讽刺卫君以怨报德,“卫人始终并未报齐,非惟不报,且又乘齐五子之乱而伐其丧,则背德孰甚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明言之不敢,故假小事以讽之,使其自得之于言外意,诗人讽刺往往如此。故不可谓《序》言尽出无因也。”其说思路同于《诗序》只不过是将诗旨由“美”变为“刺”而已。
清儒于传统两说之外提出的新说者,首推王先谦。其说以贾谊《新书·礼》篇为根据,贾谊谓:
礼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则左右亲。苞苴时有,筐篚时至,则群臣附。官无蔚藏,腌陈时发,则戴其上。’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上少投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
王先谦认为“贾子本经学大师,与荀卿渊源相接,其言可信,当其时惟有《鲁诗》,若旧《序》以为美桓,贾子不能指为臣下报上之义,是其原本古训,更无可疑”(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3。)王氏之说,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即古人引诗多断章取义,非为解诗而引,而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言论而找根据。所引的诗句往往已非诗意原貌,此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春秋人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贾谊《新书》引由余之语是在说明君主少施即可得臣下厚报的道理,故而引用《木瓜》之句,并非在于说明《木瓜》一诗即为臣下报君之作。《木瓜》诗中毫无君臣之迹,是可为证。
关于《木瓜》诗旨,清儒多认为是朋友相赠答之诗。如崔述谓:“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于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于说《诗》尤甚。……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注:崔述:《读风偶识》卷2,《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50页。)。
综合古代诸家所论,可以看出,将《木瓜》诗旨定作“美齐桓公”和“男女(或朋友)赠答”是最有影响的两类说法。现代学者的解释则多倾向于“男女赠答”之释,当代学者则多将其定为《诗经》中典型的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从解释《木瓜》诗中的“好”字之义出发,申论和断定此诗非如郑笺所谓“结己国之恩”,他说:
好字从女从子,其本义,动词当为男女相爱,名词当为匹耦,形容词美好,乃其义之引申耳。好本训匹耦,引申为美好,犹丽本训耦俪引申为美丽也。……原始装饰艺术应用对称原则,尤为普遍,故古人言“称”即等于言“好”,而好俪诸字之所以训美,实以其本义皆为匹耦也。上列各诗好字皆用本义。《木瓜》“永以为好也者”,以为偶也。(注:闻一多:《诗经通义甲》,《闻一多全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根据这个解释,可以说“永以为好”之句,意要求偶,犹《关雎》篇之“君子好逑”。依照这种解释而将此诗主旨定为爱情诗者,在《诗经》的现代各种注译本中屡见不鲜。当代研诗大家陈子展先生却不从此说,而断定此篇乃“言一投一报,薄施厚报之诗。徒有概念,羌无故实”(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卷5,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此篇难道仅仅是徒有概念的赠答之诗吗?今得《诗论》简文启发,知道《木瓜》一诗并非如此简单,关于此诗主旨,尚有再研究的余地。
二、释《木瓜》篇的“藏愿”
上博简《诗论》第18号和第19号两简都提到《木瓜》一诗,指明诗中有“藏愿”。关于简序的排列与缀合,李学勤先生提出卓见,将第18简直接缀合于第19简之后(注: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缀合后的简文如下:
《木苽(瓜)》又(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苽(瓜)》之保(报)以俞(喻)其悁者也。
简文“愿”字从为上元下心之字,诸家皆读若“愿”,今迳写作“愿”。所谓“藏愿”即心中埋藏的愿望。简文的“悁”字,原作上冖下悁之形,今从李学勤先生说读若“悁”,今从其说而迳写之。《说文》悁字与忿字互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篇下说:“忿与愤义不同,愤以气盈为义,忿以狷急为义。”《诗·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毛传及后来的解释皆谓“悁悁犹悒悒也”。悒,《说文》训为“不安也”。总之,“悁”意指心中不安而忧忿。简文的意思是说,《木瓜》这首诗的写作是因为心中所埋藏的愿望未能表达出来,所有就借《木瓜》诗里面的“报”来比喻他自己内心的忿懑情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木瓜》一诗之旨并非如《诗序》所言为“美齐桓公”之作,也不是如朱熹所说“男女相赠答之辞”,也不是臣子厚报于君或普通朋友的赠答之诗,而是一首表达心中“藏愿”以排泄忿懑情绪的作品。《诗论》此说,对于我们探寻《木瓜》篇诗旨,直可谓释千古之惑矣!
关于《木瓜》篇所表达的“藏愿”,由简文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愿望是要表达出忿懑(“悁”)。为什么《木瓜》一诗能表达了这种情绪呢?这是我们必须深入体会此篇诗旨方可得到解决的问题。
前人理解《木瓜》之诗多循“温柔敦厚”之旨,认为此诗即为典型之作。如清代大儒戴震说:
诗之意,盖以薄施犹当厚报,欲长以为好而不忘,况齐桓之于卫,有非常之赐乎?卫诗终《木瓜》,可为施者报者劝矣。(注:戴震:《毛诗补传》卷5,《戴震全书》第一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29页。)
他认为《木瓜》一诗充分体现了忠厚之意,无论是施者,抑或是报者皆可从中得到启发。如果依照这个思路,那么此诗作中就只有敦厚而无忿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王夫之曾经揭示出《木瓜》诗的真正含意。他说:
《木瓜》得以为厚乎?以《木瓜》为厚,而人道之薄亟矣!厚施而薄偿之,有余怀焉;薄施而厚偿之,有余矜焉。故以琼琚絜木瓜,而木瓜之薄见矣;以木瓜絜琼琚,而琼琚之厚足以矜矣。见薄于彼,见厚于此,早已挟匪报之心而责其後。故天下之工于用薄者,未有不姑用其厚者也。而又从而矜之,曰“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报之量则已逾矣。……恶仍之而无嫌,聊以塞夫人之口,则琼琚之用,持天下而反操其左契,险矣!(注:王夫之:《诗广传》卷1,《船山全书》第三册,岳麓书杜1992年版,第338页。按,王夫之所提到的“左契”,犹“左券”,指债权人所持的契券。王氏此说意指《木瓜》篇报以琼琚者,非是友好为报,而是图谋取得如债权人般的优越地位而稳操胜券焉。)
此处所提到的“左契”,犹“左券”,指债权人所持的契券。这里意指《木瓜》篇报以琼琚者,非是友好为报,而是图谋取得如债权人般的优越地位而稳操胜券焉。这个说法一反传统的认识,指出《木瓜》所表现的并非忠厚之意,乃是“人道之薄”。别人薄施于我,而我却故意厚报于别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矜”(意即骄傲),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让人看见对方之“薄”(“木瓜之薄见矣”)。诗中所写被“投”以“木瓜”者,是一种将利益名誉算计得特别精明的人。其品格本来是浇薄无比的,但却要摆出一副厚道的模样儿,口中念念有词,标榜自己“永以为好”,实则图谋厚报而构私。这是一种特别工于心计的做法(“工于用薄”“姑用其厚”)。他将天下的事都算计透了,以“琼琚”作为塞别人之口实的工具,目的在于稳操胜券。其如意算盘是,算计遍天下而无敌手(“持天下而反操其左契”)。王夫之揭露了这种人的阴险之至。他对于这种人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我觉得,只有如此理解方可得《木瓜》一诗的深层含意。船山先生的卓见,不禁令人击节赞叹,拍案称奇。对于《木瓜》一诗能够有此睿识而深合诗旨,船山先生可谓千古一人矣。今得上博简《诗论》简文,更可以确证其说之精当。
简文所谓的“藏愿”,即工于心计之人的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心愿。他嘴上高唱“非报也,永以为好也”,心中实隐藏着厚报于己的图谋。他的“报”厚是假,以售其奸则是其真。孔子对于此种人深恶痛绝,于《诗论》中亦多有揭露,如第8号简批判“言不忠志”和“谗人之害”,第27号简赞扬痛斥那些反复无常的为鬼为蜮的谗谮小人的《诗·何人斯》之篇,皆为例证(注:关于《诗论》第8、27两简的考释烦请参阅拙稿《上博简《诗论》之“雀”与《诗·何人斯》探论》(《文史》2003年第3辑)与《上博简(诗论)“小旻多疑”释义》(《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9期)两文。)。《诗论》简所谓的“藏愿”,即心中埋藏某种意愿,这种人可以说是另一类谗谮小人,他们以“厚报”为幌子,一方面贬低了别人(“投我以木瓜”的薄施者),另一方面又借以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把自己扮成忠厚君子。
《诗论》第19号简载“《木苽(瓜)》又(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苽(瓜)》之保(报)以俞(喻)其悁”,简文的意思是,《诗》的《木瓜》篇的主旨是表现一类人心中埋藏的愿望没有得到表达时的情绪。可以从《木瓜》篇所载的“报”看出他(即诗中每每标榜自己“匪报”之人)内心的忿懑。简文正说明了这种人之所以“厚”报的真实目的,其内心深藏的打算之一就是对于别人没有厚施于己的忿懑(“旻”)。这类小人颇好“面子”,为要面子光彩,他便不肯轻易说出自己的内心语言(“有藏愿而未得达”),而以《木瓜》之诗作为表达“藏愿”发泄私愤的绝好机会,以求不露声色地损人利己。然而这种小人再工于心计也逃不掉孔子如炬的目光,上博简《诗论》的这段简文就是明证。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注:《论语·颜渊》。按,朱熹《论语集注》卷6发挥此处经意谓“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内外无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对于敬恕之道做了很精辟的解释。),其意思就是指仁者由于实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所以能够心平气和而无怨无悔。如果相反,则会“多怨”。《论语·卫灵公》篇载孔子语:“躬自厚而薄责於人,则远怨矣。”认为只要严已律己,宽以待人,就是远离怨咎,自己心中亦无怨恨情绪。据《礼记·中庸》篇所论,可以知道儒家主张在处理人、我关系时,其原则应当是“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木瓜》篇所揭露的心中忿懑不平的小人就是孔子所揭露的那种“放于利而行”者,他们厚责于人,而图谋大利,其“多怨”乃势所必然(注:《论语·里仁》篇载孔子语“放於利而行,多怨”,意即逐利而行必多怨,此“多怨”,不仅指别人对于逐利者之怨,而且指逐利者本人之怨气十足。)。
三、《木瓜》与“苞苴之礼”
关于孔子论《木瓜》一诗之事,《孔丛子·记义》篇曾有这样的记载: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於《木瓜》见包(苞)且(苴)之礼行也(注:《孔丛子》一书前人多疑其伪,但其中的许多材料经研究证明还是比较可信的。其中《记义》篇一大段关于孔子论诗的记载与上博简《诗论》颇多相似之处,上引关于《木瓜》的评析语言,毛传曾经引用,证明此段语言绝非伪作。)。
这里表明孔子是将《木瓜》之诗与苞苴之礼联系一起考虑的。什么是“苞苴之礼”呢?(曲礼、少仪郑笺有释)“苞苴”本意为包裹,指馈赠鱼肉瓜果等物品时加以包裹,后来便用它作为送礼结好乃至贿赂的代称。研诗者往往认为孔子是在赞扬《木瓜》篇所表现的馈赠之礼。其实这种理解正与孔子之意背道而驰。
先秦秦汉时期,社会舆论对于苞苴之礼是持否定与批判态度的。《庄子·列御寇》篇谓“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指匹夫之智只限于馈赠礼物和书信致意问候这些细微末节之事。《荀子·大略》篇载:
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之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注:按,此事于古代流传甚广,《说苑》卷1载:“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此载所述与《大略》篇所载者略同,亦将“苞苴之礼”视为恶行之一。)
此载虽然未必为商汤时事,但是传说中的商汤此举却每为后世楷模。《论衡·异虚》篇载:“汤遭七年旱,以身祷於桑林,自责以六过”。商汤将苞苴之事作为六种恶劣品行之一。可见对它是持批判态度的。《后汉纪·灵帝纪》载大臣杨赐奏语谓:“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殷汤以此自诫,即济於旱亢之灾。”这里实认为苞苴馈赠之礼是“谗夫”行谮作恶的行径。《汉书·武帝纪》载荀悦语论风俗之坏,谓“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於门庭,聘问交於道路。书记繁於公文,私务众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论衡·乱龙》篇讲“苞苴”之事,强调这种行为即为收取贿赂:“居功曹之官,皆有奸心,私旧故可以幸;苞苴赂遗,小大皆有。必谓虎应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将收取苞苴贿赂之官视为“野中之虎”。总之,战国秦汉时期,一直将“苞苴”之事视为贿赂恶行。
后世把投桃报李,作为朋友间的问候馈赠,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事情(注:大约从隋唐时代起,投桃报李始作为朋友馈赠之美称,如白居易《岁暮枉衢州张使君书并诗,因以长句报之》谓“贫薄诗家无好物,反投桃李报琼琚”句即已用此意。)。但是在孔子的时代以及战国秦汉时期,却一直将“苞苴”之事作为恶行。孔子说:“吾于《木瓜》见包(苞)且(苴)之礼行也”,并不是赞扬苞苴之礼,而是喟叹贿赂公行使得社会风气败坏。春秋时人虽然并不绝对地反对贿赂,在某些礼仪场合,贿赂还是必要的仪节,但却认为如果它变成了一种收买营私的行为,则必定是败坏国家与社会的恶举,《左传》昭公六年载晋贤臣叔向对于子产之语,说明郑国政治情况,谓“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左传》襄公十年载周臣揭露持政的周卿王叔陈生,说他“政以贿成。而刑放於宠”,可见“贿”已经是在败坏周政。儒家认为就是在普通人的交往中,如果只是重视馈赠礼品,也是不正确的做法。《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谓:
饮食以亲,货贿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誉征利,而依隐於物,曰贪鄙者也。
这里是说,有一种人,靠吃吃喝喝使人亲近,靠馈赠财物(“货贿”)与别人交往,以利益相接以求结合,他求得美誉名声和攫取利益,主要手段就是以财货(“物”)贿赂,这种人可以说就是贪鄙之徒。行苞苴之礼者,就是这种贪鄙之徒,《孔丛子·记义》篇说孔子见到《木瓜》一诗所记载的“苞苴之礼”,“喟然而叹”,其所感慨的就是贪鄙之徒“货贿以交”成为社会风气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这段记载正与《诗论》所载孔子对于《木瓜》一诗的认识相互印证,对于我们理解孔子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这些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孔子礼学思想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孔子并非绝对地肯定所有的“礼”。他对于“礼”进行了具体而微的区分,如《论语·子罕》篇载孔子语谓“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他认为戴麻料的礼帽是冠礼的要求,现在改为戴丝料的礼帽。这样要俭省些,虽然不合冠礼,我也跟大家一样改用丝料的礼帽。细绎其义,可知孔子认为麻冕之冠礼,就是不合适的礼,是应当加以改变的礼。关于丧礼之本,《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朱熹《论语集注》卷2引范氏说谓:“礼失之奢,丧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礼奢而备,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丧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孔子并不拘泥于礼之条文,而是十分重视礼的本质内容。普通的馈赠礼品是合礼的,但像苞苴之礼这样将馈赠作为贿赂收买的手段,那就是“非礼”的行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非礼之礼”。《孟子·离娄》篇载孟子语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所谓“非礼之礼”,赵注云:“若礼非礼,陈质娶妇而长,拜之也”。关于“陈质”,正义引周广业《孟子古注考》“疑是奠贽之义”,意即献上礼品。孟子所说的“非礼之礼”,应当包括了不正当的馈赠礼品之“礼”,如苞苴之礼、奠贽之类。这些“礼”,似礼而非礼,与儒家时常批判的“非礼”实质是相同的。
过去我们多看到孔子对于礼的重视和肯定,我们于《诗论》简关于《木瓜》一诗的评析中明确地看了孔子礼学思想的另一面,即对于礼不要盲目施行,而应当从本质上进行观察分析。判断其是非得失,对于那些属于恶俗之礼则要加以抵制。《荀子·王霸》篇说:“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俗与礼关系十分密切,“恶俗”犹言恶礼。尽管孔子没有提出恶礼的概念,但他在实际上对于礼是有细微区分的。孔子见到《木瓜》一诗所表现的苞苴之礼“喟然而叹”,其所叹息的正是其中所表现的“人道之薄”(王夫之语)。
四、从《木瓜》看《诗经》编纂的若干问题
关于《木瓜》诗旨,古往今来,多肯定其诗中“诗中皆绸缪和好之音”(姚际恒语),而不谓它是对于那些图谋厚报而工于算计的小人的揭露。今得《诗论》可以使我们看到是诗真正的主旨。这其间的差异是巨大的。难道汉唐宋清历代诸儒的解释皆一无是处而毫不可取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启发我们考虑《诗经》中许多诗篇的诗旨应当存在着不同层面。
让我们从《诗》的编纂说起。
《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之官,在先秦两汉时代应当是存在的。《诗》的最初编纂应当出自他们之手。《诗》中有民歌风的诗作最初应当就是民歌谣谚。它们完全出自民间。民间的东西经过文人之手,就难免会渗入文人(亦即那些“采诗”的史官类的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可以推测,编入《诗》的诗篇与民歌谣谚两者的主旨可能是有一定距离的。《诗》中民歌风作品的编纂过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表示:原创(民歌谣谚)——加工(史官采编)——《诗》中的民歌。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诗旨何以变化的问题。鲁迅先生曾经注意到这类情况。他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
《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0页。)
鲁迅先生的这个论析是相当深刻的。他还在《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上)中说:
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檀木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注:《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9页。)
当然,“采诗”的“士大夫”们也有将民歌谣谚编入《诗》中从而使民歌谣谚得以保存的功劳,但也有让民歌谣谚“失去”本来面貌的遗憾。那么,这些作品中“失去”了哪些东西,又增添了些什么东西呢?大体说来,所失去的就是原创民歌的质朴,增添的往往是采编者的意识理念。
就《木瓜》一诗看,其原创应当是民歌。它复叠重沓,琅琅上口,并且,从其所表达的内容还可以看出劳动群众间的企盼和睦友好的真挚感情。劳动群众通过并非名贵之物而是普通瓜果(木瓜、木桃之类)的馈赠,所表达的愿望(“永以为好”)的愿望应当是明确的。《礼记·曲礼》上篇说: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民众间真挚而素朴的馈赠是感情表达的重要方式,其所馈赠之物多为自己所劳动所得的日常所用之物或时鲜果蔬,如瓜果梨桃之类,若以美玉(“琼琚”“琼瑶”“琼玖”)相馈赠,则不似劳动群众的作为。《木瓜》诗中的“琼琚”之类,可能就是采诗、编诗者再工的结果。这种改变,不仅变民间馈赠为贵族礼数,而且在思想意义上也有了重大变化,具体来说,就是由原来对于民众间馈赠结好情感的表达,变为对于工于心计的小人及“人道之薄”(王夫之语)的揭露。
由此说来,将此诗主旨作为馈赠结好,并不是绝对的错误,因为它毕竟说明了《木瓜》在原创民歌阶段的主题。然而,就整体而言,我们所要寻求的是《诗》中的《木瓜》之篇(而不是它的民歌形态)的主旨。所以说就不应当断定《诗·木瓜》的主旨为馈赠结好,而应该如孔子那样指出其对于工于心计的沽名钓誉之徒的揭露。要之,关于《木瓜》一诗主旨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诗经》编纂过程的一些问题,认识到民歌由民间传唱到写入经典正经历着一个随士大夫心态而其主旨略有变化的过程,只不过不同的作品其变化情况亦自有所区别而已。
从上博简《诗论》的语言看,它完全是评诗的吻,而不是述编诗者自己的体会,这可以让我们略微体会到《诗》应当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它的篇幅是比较多的,《史记·孔子世家》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前人对于孔子是否删诗争论颇多。由《史记》的记载看,孔子实际上是进行了选诗的工作。《论衡·正说》篇谓“《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这些记载表明,孔子从古《诗》中选取了三百余篇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本。后世所谓的“逸诗”,应当就是没有为孔子所选中者。孔子选诗的标准依司马迁的看法就是,一,“可施于礼义”,二,可以配乐“弦歌之”。民歌风的作品,复叠重沓的特点决定了它比较容易配乐和演唱。“可施于礼义”,就是指诗篇的思想品格的高下区别。经士大夫“润色”之后的《木瓜》一诗合乎这两个标准,所以入选于孔子编定的作为教本的《诗》。上博简《诗论》的最初形态应当是就是当年孔子授诗时学生的记录。他授诗的内容应当是广泛的,指出诗篇的思想品格可能是孔子所注目的要点之一。孔子特别关注《诗》中那些揭露和讽刺无耻小人的诗作,就是为了发挥《诗》的社会伦理教育功能,《诗论》对于《木瓜》一诗的重视,原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