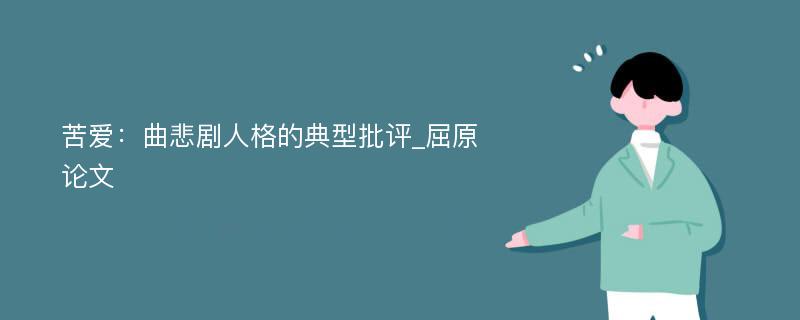
苦涩的恋情——关于屈原型悲剧人格的原型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原型论文,苦涩论文,恋情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原型批评家弗德莱尔在论及原型批评的实际性功能时,曾作过如下阐释:“我说的‘原型’是指由观念和感情交织而成的一种模式,它在下意识中广泛为人们理解,但却很难用一个抽象的词语来表达。同时,它又是那么神秘,不经周密的考察是无法分析辩明的。这种复杂的心理情结需要通过某种模式的故事,既体现它又象是掩盖它的真正含义,待到它原型的意义被分析出来,或者根据表达它的语言找出它的寓言之后,整个奥秘才会昭然若揭”。〔1〕可见, 所谓原型批评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从古代神话原型中提出模式,而在于这种模式不但可以和人类在社会的、历史的、伦理道德方面所凝聚成的有意识心理结构沟通,并且还能从现代流行作品中发现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神话和原型的显现,从而使原型理论观照下的戏剧批评能超越作家本人的无意识,上升为一种具有深刻的理性洞察力的文化批评。
本文试图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对近年来出现的几部颇有影响的剧作(如湘剧《山鬼》、京剧《曹操与杨修》、话剧《李白》)作一番非理性的解析,循着神话原型置换变形的逻辑,透过上述三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的似曾相识、若即若离的叙述模式,力求去触摸隐现其中,并主宰不同表层叙述模式的深层结构。
显而易见,《山鬼》全剧可以梳理出以下两个叙述结构:一是对屈原进入的原始部落作一种背景上的客观呈示与渲染,如田遣与杜若子的恋情、抢亲、哭嫁、祭仪等风俗,砍去小偷的手的野蛮处罚,高阳向屈原学打结等;二是屈原与杜若子的关系以及围绕这一核心关系组成的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与感情纠葛,杜若子似乎很象屈原苦苦思念、寻找的美人,似乎又不是,很有几分若即若离、扑塑迷离的神秘,(此外,她与神话中那位山鬼似乎也有某种隐秘的瓜葛)。她可以割自己的肉为屈原作药引,可以为追求爱情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当她的恋人田遣为她殉情而亡后,她却又投入了高阳的怀抱;她的纯真与愚昧,善良与残酷,柔情与凶悍,她的无拘无束与她最终无法挣脱原始部落对她的羁绊,都可以说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历史与文化的人格化具象。如果说屈原寻找的理想中的美人象征着他对自我的理想人格的追求,那么杜若子的不完美的人格化特征则恰恰形象地展示了屈原所置身的原始部落的现实境遇。这是一种颇含深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规范共时性的呈现与营造:理想与现实,有时那么相似却又相距那么遥远,两者永远并存却永远无法遇合,理想若脱离现实则苍白无力,现实虽然充满生命却又总是残缺的。这第二叙述层次更接近对人生哲理的洞察与感悟,并且其中还隐伏着一个双重意构——屈原先生那充满犹豫、彷徨的寻找与对剧中那位飘渺而隐晦的美人杜若子含愁带怨的恋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向把毕生探索人格完美、虽九死而不悔的屈原先生当作他们人格的楷模,因此,屈原也逐渐变形为一位非历史化的历史人物,他探索人格完美的悲剧底蕴,实际上揭示了人的本性与自身在文明进化过程中确立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既吻合又悖离的这一永恒的悲剧母题。我们若考察一下诗人那缠绵沉郁、深华艳逸的《九歌》、《离骚》、《抽思》、《思美人》等作品,就会发现屈骚中最能表现其崇高人格、“美政”理想和艺术个性的意象,便是“直书其事”体系,“香草美人”体系和神话故事系统,它们或表现为以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婚爱关系为象征:如《思美人》中,称楚王为“美人”,主人公“揽涕而竚眙”,俨然是一位(深情男子期待意中人的痴态,但无奈“媒绝路阻”,他怅然若失“寄言于浮云”,“因归鸟以致辞”,都大失所望。 又“指嶓冢之酉隈兮,曰黄昏以为期”,矢志不渝地追求“美人”以达到爱情的结合;或借山鬼美人意象与其幻化人物“宓妃”、“佚女”、“二姚”相映衬,来倾诉内心缠绵幽怨的相思之苦。这种融政治、人格、情思于一体的抒情意象体系不仅深刻准确地勾勒出了诗人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悲剧人生际遇,而且还无意识地频繁演绎了原始神话中以山鬼为原型的那一类神女、美女“野魅求偶求夫或”自荐招亲,人神嫁娶这样一种原型心理构型,因此,我们要对屈原先生这位由历史生活团抟出的人格神的社会原型作一番人文审视,就不得不从神话原型的角度对诗人在《九歌》中深情眷恋,矢志寻找灵修美人的山鬼作些本源的考察:
屈原在《九歌》中所描写的山鬼,通体流溢出悱恻缠绵的恋慕、相思,“留灵修兮淡忘归”,“灵修”是谁?究竟是人还是神?据萧兵先生的推论,很有可能是当时担任神官、贵爵、祭司长的人,这一点若是依据原始神话中“山鬼”好色、喜与异性交媾结欢的本能来推敲,似乎只有那些作为高级祭司、神官的“公子”、“灵修”才有可能做这些多情的Nymph(山林水泉小女神)的配偶。〔4〕,同时,从神话中山鬼这一原型到屈原笔下的山鬼有一个重要的衍变,就是不仅其神情、肖像变得含情脉脉,娇美可爱,而且基本禀性也由好色的肉欲型本能欲求转换为眷恋、寻找理想中的美人的情欲型精神渴望。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置换变形,它标志着古代知识者精神追求的质的伸拓以及形态上日渐艺术审美化。也就是说,神话中山鬼这一原型从动物本能需求(这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崇拜和交感巫术,在原始人看来,唯有人的这种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和两性交媾才能履行创造生命的仪式)到屈原的笔下升华为一种对美人、神女、香草刻骨铭心的恋情,这是人类以生命意识审视与把握自身与世界的本质关系的艺术写照。
原型批评着意探求的不是一些孤立的文学现象的本身,而是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构建出的一般性的规律。由神话中山鬼这一原型为象征符号的“美人情恋”逐渐演变为揭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悲剧心态的深层叙述结构,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文化人类学资源。但是,人类情感的原型模式并不是先天就存在于个人心理结构中的,而是凭借特殊的语言意象在诗人和读者的心里重建起来的。因此,要追溯其隐秘的宗教仪式背景。描述其发展演变的脉胳,概括和解释其常见的置换模式,就有必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对山鬼这一原型的隐喻与真实做心理发生的解说。
下面,我们先以“山鬼”为焦点对美人情恋作源的追溯:山鬼最初的记载是由夔枭阳、山魈、旱魃变化而来的。据民间传说,山中魈魅会留客求偶。例如[晋]张华《博物志》说蜀中南高山有猕猴者。“妇女有好者,辄盗之而去”。[宋]周密《齐东野语》载,山鬼类之“黄婆”“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辄负去求合。”而当这些山精野魅被当作山神化身或与山的人格化形象相融合时,就更显得其神通广大,变化无穷。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山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复合型神祗,当是以瑶姬、鬼、武罗为主要原型发展而来的。瑶姬之“瑶”,据闻一多先生的诠释:瑶、淫相通,“言以淫行诱人也”。这个名字本身可以说是以性爱内容为隐喻的象征符号,至于瑶姬的变体宓妃,曹植的《洛神赋》中称其为“河洛之神”,据考证系宓羲氏之女,更值得重视的是宓妃的身世,其父宓牺(羲、牺相通)正是与女娲相配繁衍人类的大神伏羲,“伏羲”之“伏”可作“密”解,“羲”可训作“戏”,故当以密戏二字为正。后世所谓秘戏图,是其义也,惟‘密’当训合,非隐密之谓”〔5〕可见,密戏(宓羲)一词有交合的隐喻, 他的女儿宓妃及变体高唐神女、巫山神女之所以在人神交欢的传奇作品中频繁演绎为自荐自招的原型性心理构型是有其坚实的遗传基因的。
从神话思维的特征来看,原型性心理构型具有一种无意识的类化和投射功能,它往往把外在的,客观的物质事实同化为内在的心理现实,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投射到自然物象中去,使之成为可交际的原型。我们若是参照人类学提供的跨地域文化的史料来剖析神话中山鬼这一原型好色、淫泆的禀性,就不能仅仅视其为动物的本能, 从宗教背景上说,应该将这种充满激情的性爱行为升华为创造生命的一种仪式。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考察古希腊维纳斯女神这一原型时,发现其前身为西亚地母爱神易士塔,古代巴比伦人祭祀易士塔及其配偶神阿都尼斯的新春礼仪活动也是以男女交合为重要内容:“人们常常在同一时间内,用同一行为把植物再生的戏剧表演同真实的或戏剧性的两性交媾结合在一起,以便促进农作物的丰产、动物和人类的繁衍。对他们来说,生命和繁殖的原则,不论就动物而言还是就植物而言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原则”〔6〕。与此相对应,在中国古代, 一年一度的春祭礼仪虽然伴随有集体性的男女交媾,但整个仪式表演的核心人物只有两个:即模拟谷神或天父、代表宇宙阳性生命力的国王和模拟地母神、代表宇宙间阴性生命力的女祭司,他们一个是天,阳性、现实世界权力与理性秩序的象征,一个是地、阴性、蕴含、创造着万物荣枯和人类生命兴衰循环,阴阳相济,刚柔互补,以至于人类学家把这种生殖祭仪誉为“圣婚仪式”。显然,这种仪式的本身以及后来嬗变为一种宗教、艺术型的历史文化传统,它包含着祭祀与恋爱的双重变奏的主题,这种双重变奏作为原型性心理的一种仪式历经社会历史生活的沉淀与提纯,在两个层面上无意识地印合了以屈原为范型的古代理想主义者人格悲剧的心理现实:一、对自我纯而又纯的完善人格理想的寻找迷恋。二、对自我的人格理想在现实的挤压下破碎、幻灭的悲悼与祭奠。而且这种寻找与迷恋还由于如容格所说的“阴性灵魂相”〔7〕的原型心理隐现, 使之变形为对灵修、荃、宓妃、瑶姬等美人芳草刻骨铭心的婚恋情结。
历史上的屈原,与他在《九歌·山鬼》中所描写的那位苦苦痴恋与寻找美人、香草的主人公以及湘剧《山鬼》中作为某种历史文化符号的屈原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复杂的血缘脉络?首先,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是以灵修、杜若子、荃、荪、芳草组成象征性意象,借以抒发自己对理想中的美人深情眷恋与寻找。千百年来,屈原作为殉道型人格楷模,所以能扣发其效法者们一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宗教情感,就在于他毕生都在探索洁身自爱的完美人格,不惜以生命的代价去寻求臣直君贤、正道治国的“美政”理想。并且又善于发挥诗人的才情,选择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又能表现乃至升华自己人格境界的神话原型来展示其哀婉凄迷的悲剧心境,正象那位隐身于云雨瞑瞑、幽篁深处的山鬼、“荃不蔡余之中情兮”、“恐美人之迟暮”。而在《离骚》下半篇之“求女”、乃至求“宓妃”、“佚女”,“二姚”,则是把在上半篇中苦苦寻觅、痴恋的灵修、荃、荪等美人意象以神话原型这种象征性思维表述出来。借灵修、美人意象与原型性心理构型交相叠合,将这种缠绵幽怨的美人情恋由一种个人的有意识的借托转换为一种群体的、无意识的心理体验,从而使山鬼型美人情恋在政治、人格及深层的心理能量三个层面上凝聚了更为深广、空灵的文化底蕴。
如上所述,这种美人情恋的原型心理在京剧《曹操与杨修》、话剧《李白》的深层叙述结构中也产生了同样的多重变奏的审美心理效应。
京剧《曹操与杨修》叙述的是封建社会以曹操与杨修为代表的君臣之间招贤不能用贤,爱才却又忌才害才这样一个充满政治寓言色彩的悲剧故事。我们不妨也尝试着把该剧解析为两个叙述层次:一是为揭示曹操与杨修之间互相思慕又互相周旋,互相信任又相互觊觎的矛盾纠葛与悲剧心态而设置的表层情节与性格冲突;第二个叙述层次是作为封建君臣之间在人格上的对象化的相互寻找和相互塑造,他们彼此都希望能以诚相见,相互为用,但实际上却是相互猜忌和耗损,这种周旋、互耗的悲剧底蕴是双方都渴望寻找和构建一种君臣知己型的人格契约和社会权力关系。曹操的寻找是一种“青青子矜,悠悠我心”式的思慕与寻找,其中倾注了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的一腔真诚与深情;杨修期待与寻找的是身处封建政治文化氛围里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既想兼济天下又想“独善其身”的人格构建,这种期待,寻找又是以无意识的心理逻辑呈示出来的。
话剧《李白》也较为成功的刻划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李白在“独善”与“兼济”的艰难选择中顾此失彼,无所适从的尴尬与困惑。李白的人格悲剧的价值的深刻,就在于每每想用“庄子洒脱的胸襟去完成屈原悲壮的事业”。而实际上在自身的性格与命运上表现出古代理想主义者“南辕北辙”式的悲壮与滑稽。剧中促使李白决意出山、跻身仕途的不过是永王的知遇之恩,而永王所谓“知遇”无非是把这位旷世诗才当作他争夺皇位的一个筹码;借重太白先生的生花妙笔替他撰写征讨檄文。如在李白争写“檄文”一场中,宋康祥劝李白将“遇永王东巡‘随行’二字改为“胁行’。李白却据理以斥,然而正是因为这耐人寻味的两字之差使他从永王的座上客一夜之间变成了宋康祥的阶下囚,并为此蒙受了羞辱和谪贬边地的厄运。而当后来郭子仪再度劝说李白为大唐中兴贡献才华时,他却又情不自禁地穿上当年太上皇赐予的宫锦袍请缨从军:“李白虽老迈,不杀尽乱臣贼子,誓不还家!”显然,李白在“独善”与“兼济”这一魔方的作弄下,简直坠入了塞壬女妖布下的迷魂阵:一方面不能不涉足仕途(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把入仕作为兼济天下的唯一途径),一方面又矢志洁身修好,事实上想两者兼顾两者都没顾上,这种两难型人生境遇在剧中被李白与他妻子宗琰的一段对话表述得尤为深刻:
宗琰 这世道容得了一个书呆子去建功立业吗?
李白 请原谅我,我也没想到我又去从军,鬼使神差,我总觉得背后有一根无形的珊瑚鞭在抽打着我,我……可不是为了功名呀!
宗琰 你身在仕途的时候,无法忍受官场的倾轧与龌龊,一旦纵情于江湖,你又念念不忘尽忠报国,你是进又不能,退又不甘哪!
李白 (颓然长叹)入木三分、入木三分!也许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这样来回走着!
请看,李白跌入两难困境并不全是为了功名,既然如此,为何又对仕途的进退表现那般的执着、眷恋?还有那根无形的珊瑚鞭(史实中载,李白确有这样一根珊瑚鞭,系太上皇玄宗所赐)它从一种客观实物嬗变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形式——更多的是李白们这一类人物深层的心理欲求的隐喻与投射。因此,我们不仅可以把这看作全剧表层结构提纲挈领的“关目”,而且还能以此曲径通幽,成为我们破译全剧深层叙述结构的原型密码:象李白这一类人物老是去意彷徨地在社会与人生构成的十字路口来回走着。难道仅仅是来回走着?就没有某种寻觅、眷恋的心态泄露?他们期待着的是什么?最终能够寻觅到些什么?这种以自我身心的憔悴与苦难为代价的寻找,眷恋和祈盼多象情人之间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的苦涩恋情呵!
诚然,象屈原、杨修、李白这一类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在现实中虽不乏“可进可退”人生智慧,或积极入世。或超然物外,或内儒外道、内方外圆、或儒道互补、可进可退;但更多的还是如李白所言“进又不能,退又不甘”,依然希冀能得到圣明君王的赏识与器重,寻求在君臣知己式的社会权力关系中施展自己的才智与抱负,但由于受“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等封建政治文化道统的强行钳制和无意识塑造,君臣之间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都无法建立平等相处的人格契约,而没有平等的人格就难以构成民主政治型的社会权力关系。从本质上说,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思慕、寻找,相互为用,又相互觊觎、耗损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构型。也就是说,用神话中山鬼这一原型以及后来衍变出的美人情恋,来象征封建时代君臣之间双方都刻意寻找的政治理想以及在人格上渴求相互变通,相互塑造的心理现实,这其间有着多么深刻、本质的遇合。
更进一步地说,千百年来,由于神话山鬼这一原型及其美人情恋这一仪式性故事为众多的文学作品所采用、所演绎,因而积累、提纯为一种人文变焦的视角,它不再仅仅是远古人类心灵模式的简单叙述与再现,而且已成为现代人企图再造一种情感,一种充满生命激情的神圣的心理仪典,这种仪典通过动物和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同化与投射功能,颇为高妙地撷取了人类生命意识中对异性的本能欲求及美人情恋这种质朴而永恒的直觉造型,来阐释封建时代由“君”与“臣”组合成的无数精致复杂的政治寓言和人格悲剧,并且还升华出了超越生命本体之上的某种诗意与哲理。就象神话中山鬼与灵修之间的寻找与痴恋,纵然双方都怀有缠绵宛转的哀怨相思,纵然那由夔枭阳、山魈变来的山鬼美人含情顾盼、温柔迷人,但是稍有不慎,美人就可能含怨带恨,随时现出张着血盆大口的狰狞面目,向她的意中人索取性(这在后来引伸为对独立人格的隐喻)与生命的双份牺牲。屈原不是为此付出了人格、生命的惨重代价,直至自沉投江仍未参透这份苦涩的恋情吗?杨修虽恃才傲世,甚至享受了曹操为其牵马坠镫的荣耀,但赏识、重用的同时又孕育着猜忌与杀机,“实实不想杀杨修”的是曹操,最后不得不杀杨修的还是曹操,道理何在?剧中人鹿鸣女道得明白:“我父纵有沧海量,怎容你恃才傲物强出头〔9〕?”而李白更是占尽了圣上的恩宠与殊荣, 但不是也饱尝了仕途上的辛酸与悲凉么?看来,人性的确使人不断地趋于失败,人类最真实的自我或许是人格分裂的自我。
人类,唯有通过这种以祭献与牺牲为代价的苦恋与寻找才可能触摸到人性的奥秘。*
注释:
〔1〕[美]弗德莱尔:《好哈克再回到木筏上来吧》中译本P170页。
〔2〕湘剧《山鬼》见《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剧本集》。
〔3〕《文选〈高唐赋〉序》载:“(先王)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文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笔者以为,这种“愿荐枕席”实际上是神话“山鬼”这一原型“野魅求偶”及后来“自招自荐”式人神嫁娶的变体。
〔4〕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P567页
〔5〕闻一多《为陈梦家〈高楳郊社祖庙通考〉所作的跋》见《清华学报》第十二卷三期P469页。
〔6〕[英]弗雷译《金枝》插图节本第123页。
〔7〕阴性灵魂相:按容格的原型分类, 是指潜伏在男性集体无意识中的美女原型的人格化显现,这种显现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女人的形象,而是一种源于原始、镌刻在男人生命器官上的遗传因素。
〔8〕见话剧《李白》郭启宏《剧本》1991年第十一期。
标签:屈原论文; 原型批评论文; 曹操与杨修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神话论文; 读书论文; 九歌论文; 李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