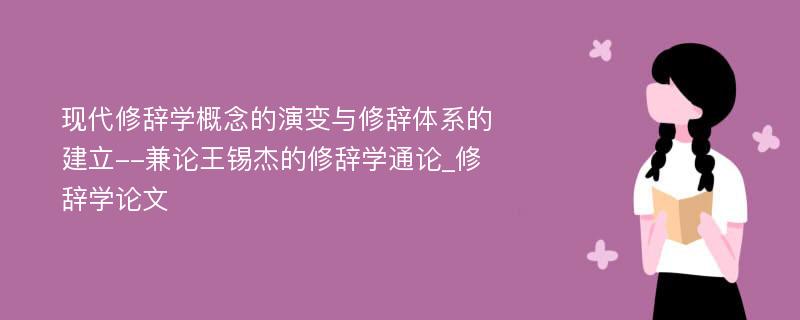
现代修辞观念的嬗变和修辞学体系的建立——兼评王希杰《修辞学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通论论文,修辞论文,观念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现代修辞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在这个过程中,修辞学由萌芽、发展到壮大,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突出地表现在修辞观的不断进步和修辞学体系的不断科学化。在这跨世纪的学术转型期,中国修辞学如何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这是修辞学界深为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希杰先生的新著《修辞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最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46万多字的新著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它的出版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本文拟从现代修辞观念和修辞学体系的历时考察以及《通论》的横向价值对比两个角度,回顾和前瞻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并对《通论》作出一些观念上、体系上的理解和阐释。
二、现代修辞学观念的流变
对于修辞学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在中国却是近现代才有的事情。宗廷虎先生把现代修辞学史的开端定在20世纪初年是有道理的。
1905年问世的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现代修辞学著作。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背影下,有识之士基于爱国的民族热情,主张科学救国。因此,用较科学的方法总结汉语各方面的规律,使人们尽快掌握语言,节省时间学习其他科学技术就成为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鉴于中国传统教学的封闭性,所以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观念和体系多受日本修辞学的影响。龙伯纯认为“修辞学盖集句成段,集段成章诸法也。”汤振常把修辞学定义为“教人能用适当之言语,以表白思想感情之科学”,其性质“属于应用的方面,故为技术而非学问。”这显然是引进了日本岛村泷太郎《美辞学》、《新美辞学》和武岛又次郎《修辞学》的观点。应该说,这在当时起到了引导修辞观念发展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虽然这一时期“文法”与“修辞”这两个观念是混同的,并且把修辞归入了文学的范畴,但是他们的修辞观念对后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王易在1926年的《修辞学》和1930年的《修辞学通诠》中也持类似的修辞观。认为修辞学即美辞学,是美化文辞的学科。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自序》、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傅隶朴《修辞学》、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陈介白《修辞学讲话》、黄庆萱《修辞学》、章衣萍《修辞学讲话》等,还有王力、郑子瑜、陈光磊等先生都持“美辞”说,只是在理解上各有不同。
董鲁安在《修辞学》(1926)中认为,修辞学是运用语文表情达意的技术。并主张将文辞言辞、文言和白话的修辞现象都收在研究范围之内,这一观念,是承袭了汤、龙二人修辞观的另一面,也自然受到日本修辞学的影响。发展下来,就构成了“调整语辞”说,这一流派的集大成之作就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朱星、李维琦、吴士文、李裕德、宗廷虎等先生是这一修辞观的继承者的发展者。
张弓先生在《中国修辞学》(1926)中认为,修辞学既是美化文辞的技术,又是分类说明修辞过程的科学。这可以说是吸收了王易和董鲁安两家之长。对修辞过程的“分类说明”发展到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就衍生了“同义手段”说,认为“修辞学应当负责探讨词句方面的同义手段的选择、运用问题。”这一修辞观到了80年代开始引起重视,王希杰先生撰文《论同义手段》(1981)阐述同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并区分了语言体系中的同义和言语表达中的同义,说明同义和异义(包括反义)、歧义,在词汇学、语法学中是相对静止、相对稳定的,而在修辞学中却是有条件的、相互转化的和复杂多变的。林兴仁先生也就同义形式选择与信息传递的关系进行探讨。张志公先生也明确指出“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一些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也持此说。可以说,整个现代修辞观念的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三条主线发展起来的。其他诸如“准确、鲜明、生动说”、“经济、简炼”说等等只是抓住了修辞现象的某些方面,而非本质,我们认为并非是对修辞本体观的认识。
这三条主线中,我们觉得最富有生机的是“同义手段选择说”,高名凯先生在《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一文中把同义手段作为一种修辞学理论提出来,吕叔湘先生在《我对于“修辞”的看法》一文中也鲜明地表示,修辞学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进行选择。从80年代到90年代修辞学的发展状况看,刘焕辉先生在国际汉藏语学会会议报告中的评价是正确的:是王希杰和张志公的新的修辞观念推动了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一大批修辞论著正是这一新观念的产物。[①]谭永祥先生在《汉语修辞美学》中对“同义手段选择说”持有异议,我们觉得这一方面是对“同义手段”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同义手段选择说”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阐释。王希杰先生《通论》一书的出版,比较科学地解决了“同义手段选择说”的理论问题。王先生把“同义手段”问题放进他的由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潜性和显性构成的体系中,并以得体性作为同义手段选择的规则。这样就使“同义手段选择说”富于更大的解释力和覆盖力,增强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王先生认为,人类的交际活动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而语言交际最为重要。所谓修辞学,就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修辞学是一个学科群,其中的核心是普通修辞学,它包括理论修辞学、实用修辞学、修辞工程等,广义的修辞学还包括修辞哲学、边缘修辞学和修辞学学。这是到目前为止对修辞学蓝图构画最为完整、科学的描绘。在这个学科群中,最重要的是理论修辞学。王先生在现代修辞学研究中,始终坚持在核心理论问题上不断探索、不断超越。1983年《汉语修辞学》就构建了一个新体系,明确区分了“修辞活动”、“修辞”和“修辞学”。提出修辞学就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②]1993年,《修辞学新论》则提出了新的语言观、修辞观和方法论,认为:“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的模式的的一门语言科学。”[③]从这修辞理论研究“三部曲”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修辞观的传承,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不断超越。
胡裕树先生曾说:“他(王希杰)的《修辞的定义及其他》可以看作“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修辞学界的第一声春雷,对于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呼风唤雨的作用”。[④]经过80、90年代修辞学研究的实践证明,这一个修辞学大繁荣时期,王希杰、张志公的修辞观的确起到导向作用,左右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修辞学研究的学术空气。
三、现代修辞学体系的源流和派别
现代修辞学体系的建立,是受修辞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的。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和修辞观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学修辞学体系。现代修辞学体系的源流和派别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最早的现代修辞学体系是受日本影响的。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借鉴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的体例,把“词藻”叫作修辞现象,然后分外形上的“语彩”和内容上的“想彩”两大类,并且又各分了“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所谓消极者,乃“修辞最低之标准,准备上必要者也”。所谓积极者,“乃修辞最高之准备也”。王易在《修辞学》中也把修辞现象分为“消极、积极”两部分。他认为“一切文章必先经过消极修辞过程,然后加以积极修辞,方成为美文”,“缺少消极条件之辞并不能成为文章”。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本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修辞学又引入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说,如英国纳斯菲尔(Nesfield)《高级英文作文法》,美国吉能(Genung)的《实用修辞学》等。受此影响,唐钺建立了第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中国现代修辞学辞格系统。他的《修辞格》(1923)已论及了要与“本题”“贴切”的思想。龚自知《文章学初编》(1926)也比较深刻地论述到“题旨”,认为“题旨,盖一篇文章实际造作之基础观念也。……作者以题旨为其思想活动之中枢,以决定其文章之范围与限制,是故题旨者,全文之胚胎,而全文意义最简最明之总和也……题旨之抉择实为最极重要”。董鲁安也论述题旨是“全篇的中心”,是“文中顶重要的东西”。以上观念对陈望道先生在“适应题旨情境说”基础上建立的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条体系发展之路也是从龙伯纯、汤振常开始的。龙伯纯已论及句、段、篇的修辞,汤振常在《修词学教科书》中更体现了这一框架结构。全书除总论外分两编。第一编“体制”,讲了文章体制的分类、文字、句节、段落、篇章和辞格;第二编“构想”,论及构想和结构的要素以及四种文体(记事、叙事、解释、议论)。到了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1926)融合中外,形成了明确的“字、词、句、段、篇体系”和“文体论的体系”。薛祥绥《修辞学》(1931)采用了上述体例,发展并形成了“字法、句法、章法、篇法、辞格的体系”。后来郑业建的《修辞学提要》(1932)、《修辞学》(1944)也注意吸收中外修辞学理论建立了以“词义、字音、句形及辞格”为纲的修辞学体系,体现出一定的特色。汪震《国语修辞学》(1935)、宋文翰《国语文修辞法》(1935)、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等也基本上都是以词句篇章为纲的。这一流派可以说更多地是从语言文字内部要素和篇章角度考察来建立修辞学体系,是一种微观的研究。发展演变到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可以算是精美阶段。这一体系明确了语言三要素的重要性,强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修辞和汉语各要素的关系,探索了辞格系统并提高了语体在修辞学研究中的地位。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1979)、倪宝元《修辞》(1980)等都明显地受此影响。而陈介白《修辞学》(1931)、徐梗生《修辞学教程》(1933)、章衣萍《修辞学讲话》(1934)、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1956)、倪海曙《初级修辞讲话》(1962)、黄庆萱《修辞学》(1975)、吴士文《修辞讲话》(1982)、宗迁虎、邓明以等《修辞新论》(1988)等著作则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体系的具体化和发展。
1950年,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的出版,开创了语法修辞相结合的新体系。后来的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册)(1979)吴士文、冯凭主编的《修辞语法学》(1985)等著作也都是从不同角度把语法和修辞相结合来谈的。1953年出版的张环一《修辞概要》则把“修辞理论、用词、造句、辞格、篇章、风格”的体系整饬一新,一些中学、大学的修辞教材纷纷效仿。
80年代初,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的出版,给修辞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被同行专家们认为是80年代中国修辞的代表著作之一,它体现了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学术水平。”[⑤]这是一部用辩证法和美学思想统率全书的新体系。90年代初,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则被誉为“观念新、方法新、语料新”的“三新”体系。[⑥]按照王先生自己的说法,《修辞学新论》“只是一个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⑦]《通论》才是“一生中所写得最好的”,最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一部著作,是“到目前为止比较满意的一本”,但并不是“最满意的”。[⑧]那么王先生在《通论》中构建了怎样一个体系呢?
从对现代修辞学体系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修辞格一直是研究的中心,增加了“同词”和“造句”、“语体和风格”以后,也似乎不能完全摆脱开,在辞格研究上,又一味地分化、繁化。但是科学的进步不等于知识在数量上的简单相加。所以王先生认为科学的最高原则就是最简单性原则。80、90年代的修辞学术语虽多,但彼此缺乏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因而修辞学的体系就不够科学。有鉴于此,《通论》就力求按照科学的最简单性原则,把修辞学的体系建立在有限的概念术语之上,准确地说只有三组,就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在这个基础上又派生出二级、三级概念,并以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这是一个简明的全新体系。体系中的每一个概念术语都能贯穿始终,并且明确指出“语体”和“风格”都是与修辞学并列的学科,但是互相联系、彼此有交叉,而修辞学论及语体风格时,只是从表达效果的角度来研究与语体风格有关的问题。这就使得《通论》一气贯通,形成一个比较严整的体系。这个以得体性为最高修辞原则、以三组基本概念有机统一作为基本构架的体系,可以称之为“三一修辞学体系”。
四、修辞学的回归与超越
王希杰先生认为,整个宇宙是既简单又复杂的,修辞学也一样。修辞现象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而修辞学的本质则是简单的,简单和复杂的统一就构成修辞学。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尤其是80、90年代,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失误。比如,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背离了中国修辞学“修辞立其诚”的学术传统。再比如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脱离社会,损害了修辞学、修辞学家的社会形象。一时间大家都普遍感到修辞学的科学品位不高,因此我们提出:
1.修辞学研究要向传统高层次地回归。通常认为,西方修辞学的传统是论辩的,而中国修辞学的传统则是伦理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非绝对。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早就有人反对把修辞术当作辩讼的手段。如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就说:“在这些年代中,我教授着雄辩术,我身为私欲的败将,却在出卖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我一片好心地教他们骗人之道,不是要他们陷害无辜,但要他们有时去救坏蛋。”他认识到,“一件事不能因为说得巧妙,便成为真理,也不能因为言语的朴拙而视为错误;但也不能因言语的粗率而视为真理,因言语典雅而视为错误。”[⑨]美国学者格赖斯1967年提出了交际的“合作原则”,要求交际双方相互信任、配合,以保证交际的顺利。这已很接近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诚”。所以从西方传统来看,修辞学也并不只是唇枪舌剑的争讼,他们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反思,一直在探究“诚”的问题。
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就是“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字,我们今天赋予它“诚信、诚恳、诚心、诚意、诚实”等许多新含义。王先生认为“现代修辞学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抓住这个‘诚’字!把它作为修辞的基本原则,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现代修辞学的发展不能够一味地追求着精密化形式化,也应当带有更多的人情味,伦理色彩。因此我们认为,现代修辞学应当把‘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样现代修辞学才有可能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⑩]所以我们主张修辞学要向传统高层次地回归。回到“修辞立其诚”,回到富于新意的“诚”。这个“诚”对交际者、修辞学研究者和修辞学著作本身都是适用的。
2.注重社会需要。加强实用研究。修辞学最终目的是什么?中国传统修辞讲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得意而忘言”(庄子),“不以辞害志”(孟子)。“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淮南子》)等等,都说明最高的修辞是不修辞,人伦关系最高的和谐才是修辞的目的。所以从本质上说,修辞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1995年10月1日在黄山召开的“跨世纪的语法学修辞学术研讨会”上,李晋荃、王希杰先生提出“把修辞还给社会,还给人民大众!”的口号,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响应。
加强修辞学的实用研究,注重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让修辞学走出象牙之塔,倾听社会的呼唤,解决实际问题,无疑是修辞学走向新世纪的学科生长点。正如王希杰先生所说,一切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服务的。语言科学也不例外。王先生“主张更多的有志者投入到实用修辞学的研究中去,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到千百万使用语言的人们中间去,努力发现和解决他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他们提高语言运用水平。”“在今天的中国,龙其要看到实用修辞学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11)因此,注重社会需要,加强实用研究必然会成为下个世纪修辞研究的热门课题。
3.修辞学研究要不断地超越。胡裕树先生在《修辞学新论·序言》中说:“希杰曾经对我说过:‘一个搞学问的人,要敢于大胆地否定自己。所谓发展,所谓进步,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如果一个人一点儿也愿意否定自我,那么就只好永远地抱残守缺了!’”的确如此,科学的进步与繁荣,就是需要不断地否定和超越,否定自我,超越时代。王希杰先生从《汉语修辞学》到《修辞学新论》到现在这部《通论》连续跨越了三个台阶,而且每一次的自我超越都不是在原来结构体系上的简单修补,而是语文观、修辞观上的更新。《通论》中,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理论,把修辞现象放到了一个“语言——外界——文化——心理”的关系网络中,这四个方面的“合力”制约着修辞效果。这同单纯从心理学,美学等角度观察修辞现象就有了本质的不同。显性和潜性的引入,不但扩大了研究范围,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命,于根元先生曾说:“到了80年代后期,(王希杰)提出了语言有显的一面,同时还有隐的一面,这两方面密切相联又相互转化,加起来才是完整的语言。这就看到了以前一般人不很注意到的几乎占语言一半的新阵地,视野一下子打开了,对语言的认识也就比较全面了,”(12)而且,演绎法被娴熟地运用于潜语言现象潜修辞现象的研究也为修辞学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保证。零度和偏离的引进,使得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提出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两大分野的研究更为科学,进入了一个动态的可以相互转化的结构框架,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在《通论》中王先生还提出:“真正科学的修辞学首先应当具有全人类性。”(13)所以我们考虑王先生这部著作取名“通论”不止是因为它是王先生30多年教学和科研的结晶,也不止是因为它是修辞学研究三部曲中最全面的阐释著作,还应该含有“普通修辞学”或叫“一般修辞学”之意。以往的修辞学研究,视野显得狭窄了一些。修辞学是全人类的,所以修辞的传统不限于中国,在中国也不限于汉民族,只有吸收整个世界民族的修辞学遗产并对此作出系统的科学的总结,才能最后构建起修辞学的理论大厦,《通论》在这方面显然有首创之功。王先生有意识地总结吸收了世界许多民族的修辞学理论和实践,其中所蕴含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其他民族语言的修辞分析,这也是这部新著的价值之一。
五、余论
现代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对近百年来的修辞学进行反思。同时还要以全新的科学的语言观和修辞观对之进行整体观照,这关涉到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方向。
80年代以来,一直有同志在探讨修辞学的科学品位问题。一门学科是否具有较高的品位,一方面取决于学科内部是否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结构,是否构成了一个比较严谨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和互动,看它是否在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同时,也能为其他学科提供成果和方法,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宗廷虎先生在考察了与修辞学有关的中西学科的现状后,前瞻地提出21世纪修辞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其意义恐怕也就在于此。从这个角度上说,《通论》虽然是一部修辞学著作,但其理论也适用于语法、词汇的研究,适用于语言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
总之,本文仅粗线条地描写了现代修辞学观念和体系的嬗变,初步探讨了《通论》的新体系和理论价值,并对世纪之交的修辞学发展作了一些浅近的思考。
说明:本文涉及的对现代修辞学著作的修辞观念和修辞学体系的评介,未能查阅原书的,均依宗廷虎、袁晖、郑子瑜等先生修辞学史的有关评价。
注释:
① ④ ⑤胡裕树《〈修辞·语法·文章〉序言》秦旭卿、王希杰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7。
②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③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⑥胡裕树《修辞学通论·序言》。
⑦ ⑧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后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⑨【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2、77页。
⑩ (11) (1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第118、121、57、60页。
(12)周洪波《于根元先生谈“王希杰语言学研究”》,《池洲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