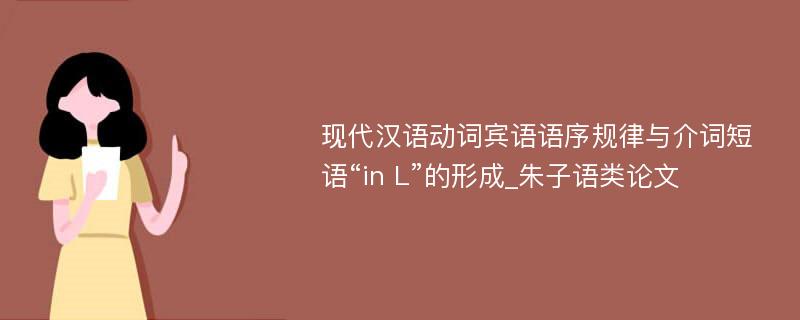
现代汉语介词词组“在L”与动词宾语的词序规律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序论文,宾语论文,介词论文,现代汉语论文,词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汉语中引进与动作有关的场所的介词词组“在L(location )”与它所修饰的中心成分的词序问题是汉语词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学者都有专门研究,我们也曾著文(张赪1997年)讨论过。关于这一词序的一条规律是当动词带有宾语(我们记作“V+O”)时,“在L”不能位于“V+O”之后, 只有当宾语是名词且有数量结构修饰时,才有极少数“在L”可以位于“V+O”之后。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揭示这一规律是如何形成并在何时最终确立的(注:表示与动作有关的场所的介词词组在先秦文献中基本由“於(于)”引导,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在”的使用多起来,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代替了“於(于)”,因此在考察历史文献时我们同时考察了“於(于)L”、“在L”与其所修饰的述宾结构的词序情况。历史上逐步替代“於(于)”的介词还有“从、著”等,“从L ”只位于所修饰的述宾结构前,故没有统计,“著L ”基本位于所修饰的述宾结构后,主要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数量比“於(于)L”、 “在L”少得多, 唐代以后用得更少,而且其情况与我们讨论的情况一致,故也没有讨论。其他的介词使用频率很低也不再考虑。历史文献的考察范围见文末所附的“引用书目”,本文所说的各种统计数字均是在此范围内穷尽考察得出的。)。
1.引进场所的介词词组“於(于)L”、“在L”与其所修饰的述宾结构的词序变化是与处所介词词组的词序从古到今的变化相一致的。在先秦时期,处所介词词组主要位于所修饰的中心成分之后,因此“於(于)L”(注:先秦时期“在”更常见的用法是作动词,是否已是介词,学术界尚有争论,即使有用例也非常少,我们不予考虑。)也基本位于“V+O”后,如“有美玉於斯”(《论语·子罕》)、“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孟子·梁惠王上》)、“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庄子》),这样的例子在先秦文献中俯拾皆是。个别句子中“於(于)L”位于“V+O”的前面都有表示对比、强调的特殊作用, 如“或谓孔子於卫主廱疽,於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万章上》)、“冬日至,於地上之圆丘奏之,……,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於宗庙之中奏之”(《周礼·秋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
2.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引进场所的介词词组与所修饰的中心成分的词序有了变化,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动作的起点介词词组和部分表示滞留的场所的介词词组开始移到中心成分之前,而在动词带宾语的句子中,这种前移的趋势更为明显,“於(于)L”、“在L”都有很多位于“V+O”前的用例。如:
悉将大小於城南待之。(《搜神记》181 (注:本文引用例句时,书名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为页码,中文数字为卷数或回数。))
於其路中,见一婆罗门。(《杂宝藏经》497)
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锺雅、右卫将军刘超。(《世说新语》174)
时剃发师,在门孔中,见其得宝。(《杂宝藏经》494)
在《杂宝藏经》、《贤愚经》两部佛经文献中有“於(于)L+V+O”178例,“V+O+於(于)L”25例,“在L+V+O”19例,“V+O+在L”15例。在《世说新语》、《搜神记》、《洛阳伽蓝记》、 《颜氏家训》四部书中有“於(于)L+V+O”63例,“V+O+於(于)L”92例,“在L+V+O”36例,“V+O+在L”6例。无论是“於(于)L”还是“在L”位于所修饰的“V+O”前都是常见的一般词序, 与先秦时期“於(于)L”基本位于“V+O”后的情况相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进场所的介词词组与其修饰的述宾结构的词序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很多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的“於(于)L”、“在L”移到了其所修饰的述宾结构前,所以位于“V+O”后的“於(于)L”、“在L”以表示动作的归结点的为多,但也有表示其他意义的,如:
食竟弃钵於彼恒河中。(《杂宝藏经》491)
妓儿掷绳在虚空。(《洛阳伽蓝记》126)
帝观戏在楼。(《洛阳伽蓝记》52)
当筑一墙於左右前后。(《颜氏家训》536)
前两例中“於、在”引进的都是动作的归结点,后两例中“於、在”引进的都是动作发生的场所,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於(于)L ”、“在L”位于“V+O”前或后与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有关, 但并不严格。同时“於(于)L”或“在L”位于“V+O”后时对动词后的宾语也没有特殊要求,上述四例中前三例动词宾语是光杆名词,后一例名词前有数词修饰。
3.唐五代时期,“於(于)L”、“在L”的位置继续按照“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的位于‘V+O’之前,表示动作的归结点的位于‘V+O’之后,表示滞留的场所位于‘V+O’前后均可”的规律变化。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的“於(于)L”、“在L”位于“V+O”前的有304例, 位于“V+O”之后的有83例。不符合规律的用例大多是“於(于)L ”,且大多用于特殊的场合,如排比句:
列千军於楚塞,布万阵於黄池。(《敦煌变文集》20)
於是白庄布阵於横岭,排兵於长川。(《敦煌变文集》172)
弹鹤琴於蜀都,饱见文君;吹凤管於奉楼,熟看弄玉。(《唐五代卷》(注:即《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文中简称“唐五代卷”。)2)
习四分於南山,听三年於中道。(《祖堂集》十一)
有些句子虽不是排比句,但是受前面或后面的句子影响为求得句式整齐而将介词词组放在了“V+O”的后面,如:
接臂虚空,承我佛於河滩,达於彼崖。(《敦煌变文集》341)
深惭瞻礼於花台,何幸得逢於居士。(《敦煌变文集》608)
可谓鱼游于水,布网于高山。(《唐五代卷》65)
“承我佛於河滩”、“瞻礼於花台”后面的句子都是“於”引导的介词词组位于所修饰的动词之后,“布网于高山”前面一句的介词词组位于所修饰的动词之后。这些用于特殊场合的“V+O+於(于)L ”共有58例,除去它们,唐五代时期“於(于)L”、“在L”表示动作发生场所而位于“V+O”之后的情况只有25例,同304 例符合规律的用例相比,不合规律的情况是很少的。同时这些不合规律的例子多出现于《敦煌变文集》中,诗歌中,或是散文体作品的一段文言成分较多的叙述中。变文是说唱文学,韵文较多,散文部分为了上口、便于讲唱,也多采用对称的句式,为修辞的需要不合规律的句子要多一些,而像《祖堂集》这样基本是散文句式的文献中,不合规律的“V+O+於(于)L/在L”句就比较少。但是整个唐五代深受骈文文风的影响,在散文体作品中特别是在作品的开始和结尾部分常会出现一段文言成分较多的文字,而骈文讲究句式整齐,介词词组一般要位于句末,因此在以散文句式为主的作品中不合规律的“V+O+於(于)L/在L”句也不时可以看到。这些情况说明,唐五代时期表示动作发生场所的“於(于)L”、“在L”一般不能位于它所修饰的述宾结构之后,只有在特殊的场合,如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或是为了仿古,才能位于述宾结构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时期“於(于)L”位于“V+O ”后占绝对优势,极个别“於(于)L”位于“V+O ”前的例子大多出现于对比句中,这与唐五代的情况正好相反。语言中与基本词序相对的特殊词序常常因有特殊的表达效果而被用在特殊的使用环境中,这是语言使用中常见的现象。唐五代时期“於(于)L”表示发生的场所位于“V+O ”后多见于特殊场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唐五代时期表示发生的场所“於(于)L”一般不能位于“V+O”后。
上面描述了表示动作发生场所的“於(于)L”、“在L”的位置情况,如果“於(于)L”、“在L”表示动作的归结点,则只能位于所修饰的述宾结构之后。如:
纵令无面见天王,亦合留名在史记。(《敦煌变文集》657)
而不住相於彼相中。(《祖堂集》二)
於是大师吐珠於嵩严寺内。(《祖堂集》十七)
遂掷剑於江中。(《敦煌变文集》14)
我乃埋你死尸灵在此。(《敦煌变文集》871)
遂止余於门侧草亭中。(《唐五代卷》1)
这样的用例有21例。动词的宾语可以是光杆名词如前四例,也可以是短语如“埋你死尸灵在此”,也可以是代词如最后一例,没有特殊要求。
4.宋代,“於(于)L”、“在L”与其所修饰的述宾结构的词序延续唐五代时期的情况,表示动作发生场所的“於(于)L”、“在L”主要位于所修饰的述宾结构前,例外只是少数。不过,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个现象是有相当一部分“V+O+在L ”句中的名词宾语前带有数量修饰语,这是以前没有看到的。如:
於是措置几只厨子在厅上,分了头项。(《朱子语类》2647)
有一分不恁地,便夹杂些虚伪在内。(《朱子语类》2486)
岂可帖著一个意思在那上。(《朱子语类》2984)
被我安些汗药在里面了。(《宋代卷》(注:即《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文中简称“宋代卷”。)488)
我新娶一个老婆在家里。(《宋代卷》451)
这类句子共有15例,约占“V+O+在L”句的十分之一。
另一个现象是,当“於(于)L”、“在L”表示动作的归结点必须位于所修饰的动词之后,而这时动词的宾语又要在句中出现时,除了继续使用“V+O+於(于)L/在L”句式外,在宋代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其他句式来表示。
第一种句式是用介词“将、把、以、用、捉”等将宾语提到动词前,形成“介词+O+V於(于)L/在L”式,这实际上就是处置式的一种。共有34例,其中用“将”的用例最多,“把”次之,如:
当时已将上京掠到大辽乐工列於屋外。(《宋代卷》106)
遂将弓箭刀刃之属,尽投於井。(《朱子语类》3293)
只不合将“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里。(《朱子语类》2505)
今官司只得把他儿子顿在一边。(《朱子语类》2645)
待把伊,托在心里。(《宋代卷》544)
将死时,用一剑,一圆药,安於睡处。(《朱子语类》3006)
汉以一国杂见於郡县间,如何?(《朱子语类》2079)
却捉圣贤说话压在里面。(《朱子语类》2892)
第二种是宾语直接位于动词前,即“受事+V+於(于)L/在L ”式,这就是受事主语句,共有34例: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於太虚。(《宋代卷》58)
文字怀於袖间。(《朱子语类》3068)
只是这一个物事,推於爱,则为仁。(《宋代卷》2871)
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朱子语类》3304)
这些愁闷,镇在心里。(《宋代卷》541)
第三种是“於(于)L”、“在L”修饰的动词的宾语已出现在离这个动词最近的前一个动词之后,后一动词的宾语承前省略而直接带上介词词组,形成“V[,1]+O+V[,2]於(于)L/在L”式,有15例:
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间。(《朱子语类》2198)
即寻一事加於王。(《朱子语类》3161)
此事缘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朱子语类》3088)
只是他自有个物事横在心下。(《朱子语类》2931)
买一朵来,与娘插在肩膀上。(《宋代卷》574)
这三种句式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五代时期都出现了。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例子如:
何以卧儿置於坐处。(《贤愚经》429)
若干种种伎乐悬在其枝。(《贤愚经》430)
我捉汝脚,掷於海外。(《杂宝藏经》481)
见于唐五代的例子如:
把舜子头发悬在中庭树地。(《敦煌变文集》131)
千丈之线寄在碧潭。(《祖堂集》七)
则取利刃自断左臂置於师前。(《祖堂集》二)
“介词+O+V+於(于)L/在L”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6例, 在唐五代时期有3例,宋代有34例;“受事+V+於(于)L/在L”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2例,在唐五代时期有20例,宋代有34例;“V[,1] +O+V[,2]+於(于)L/在L”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19例, 唐五代时期有11例,宋代有15例。比较三个时期的情况,“介词+O+V+於(于)L/在L”式的使用明显增多。究其原因,与处置式在唐五代时期产生,到宋代基本成熟并被大量使用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关。
5.元明时期,“在”取代了“於(于)”,成为最常用的引进场所的介词,“於(于)”只出现在受文言文影响较大的环境中。如《老乞大》中“在”出现了55次,“於(于)”只出现了12次,而其中10次出现在书中一段文赋中,可以说在口语中引进与动作有关的场所时只用“在”而不用“於(于)”了,因此,元明时期我们只考察“在L”与“V+O”的位置关系。
这一时期留在“V+O”后的“在L”都是表示动作的归结点的, 几乎没有例外。而且“V+O+在L”句的数量很少。《金瓶梅》中“在L+V+O”有515例,而“V+O+在L”只有86例,其中有41例的动词宾语是带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约占了一半。分别举例如下:
看见月娘摊着些纸包在面前。(《金瓶梅》一)
又放一件镇物在枕头内。(《金瓶梅》十一)
写了二人名字在上。(《金瓶梅》三十五)
他少女嫩妇的,你留他在屋里,有何算计?(《金瓶梅》七)
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金瓶梅》二十)
只怕一时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瓶梅》三十二)
拖翻竹山在地。(《金瓶梅》十九)
“V+O+在L ”句中动词的宾语是带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的用例较前一时期明显增多了,不过就《金瓶梅》的情况看,“在L ”位于所修饰的述宾结构之后时,句子对动词宾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限制。但元明时期其他文献中反映出的情况与此不同。在“元明卷”(注:即《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文中简称“元明卷”。元明时期的文献我们考察了《金瓶梅》和“元明卷”,“元明卷”中文献的性质比较复杂,有当时朝鲜人学汉语的教科书《老乞大》、《朴通事》,有翻译体文献《元典章》、《元朝秘史》、《大学直解》,有戏剧《小孙屠》等,为便于说明,文中举例时均列出作品篇名,篇名后的页码是“元明卷”中的页码数。)中“V+O+在+L”只有6例:
乃分别一个次第在后面。(《大学直解》21)
故铭刻几句言语在盘上。(《大学直解》22)
自家又有个好名儿在天地间。(《皇明诏令》259)
老妻今日却摆些酒食在此。(《团圆梦》342)
他那哥泼皮,又不至诚,又要害我的军,我发他在云南金齿呵。(《遇恩录》79)
却撇他在这里。(《杀狗劝夫》188)
前四例动词的宾语均是名词,宾语前面均带有数量词;后两例是代词作宾语,其中《杀狗劝夫》中的一例出现于唱词中,而就在同一折戏的宾白中同样的事、同样的意思却用“将+O+V+在+场所”的句式来表达:
将你撇在这里。(《杀狗劝夫》180)
将你撇在这塔里。(《杀狗劝夫》188)
曲文中还有两例表达类似意思的句子,也都是与处置式句结合:
把我撇在郊外。(《小孙屠》176)
把我赶在破瓦窑中睚着冻饿。(《杀狗劝夫》183)
据此,我们认为“却撇他在这里”这句只是唱词中的一个特殊用例,不是普通用例。这样,“元明卷”中“在L”位于“V+O ”后时宾语前一般带有数量词,只有一例例外,这说明在这些文献中“在L ”一般不能位于“V+O”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元明时期“V+O+在L ”句式在文献中的分布很不平均。在《金瓶梅》中出现较多,而且对动词宾语也没有限制。但其他文献中这种句式很少出现,即便出现,对动词宾语也有特殊的要求,动词宾语是名词且带有数量修饰语。而在一些文献如《老乞大》、《朴通事》两书中根本没有“V+O+在L”的用例。《老乞大》、 《朴通事》是当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应当是反映了当时标准语的情况,《金瓶梅》的情况可能反映了当时某一方言中的情况。
实际上,元明时期如果“在+L ”只能位于动词后而宾语又要在句中出现时,最常见的是用“把/将”把宾语提到动词前,在各种文献中均有大量用例。
把蒋聪戳死在地。(《金瓶梅》十)
把磕的瓜子皮都吐落在人身上。(《金瓶梅》十五)
将那草稍儿放在脚内踝尖骨头上。(《朴通事》303)
有弟合撒儿将他妻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秃忽撇在王罕处。(《元典章》219)
把神灵丢在九霄云外。(《小孙屠》131)
“元明卷”中这样的用例有22例,而“V+O+在L”仅6例,《金瓶梅》中这样的用例有105例,而“V+O+在L”为86例,用处置式将动词宾语提前的用例远多于“V+O+在+L”式。
这一时期,让宾语位于动词前的“受事+V+在L”式和让宾语出现在前一个动词后的“V[,1]+O+V[,2]在L”式也有,但使用频率并没有上升。在《金瓶梅》中前一句式有27例,后一句式有29例。可见,动词带有宾语又带有表示动作归结点的“在L ”的句子最终选择了“把/将+O+V+在L”格式来表达。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表示动作发生场所的介词词组“於(于)L”、“在L”开始移到所修饰的中心成分前,位于“V+O”后的“於(于)L”、“在L”减少;唐宋时期,表示动作发生场所的“於(于)L”、“在L”基本移到了所修饰的中心成分前,位于“V+O”之后的基本是表示动作的归结点的,而从宋代开始这部分“V+O+在L ”句也有了变化,一些句子中动词的名词宾语带上了数量修饰语,一些句子用介词如“将、把”等将动词的宾语提前;元明时期,“在L ”一般不能位于“V+O”后,只有动词宾语是带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宾语时才有少量的“V+O+在L”句,在“在L”后置的句子里如果动词要带宾语一般是用介词“把/将”将宾语提到动词前,在元明时期的标准语里这一规律非常严格,但在某些方言里还不太严格。现代汉语中引进与动作有关的场所的介词词组“在L ”和动词的宾语一般不能同时位于动词之后的词序规律在元明时期最终确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