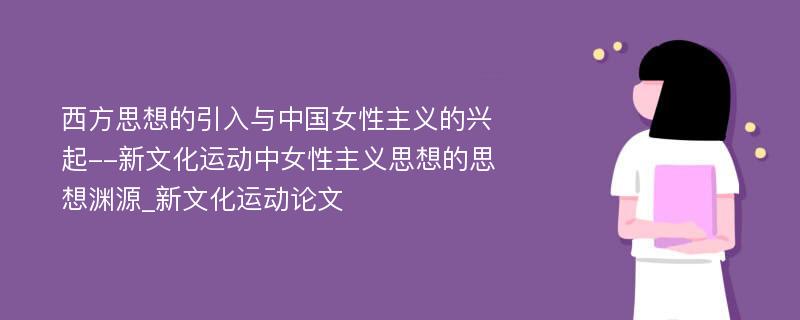
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崛起——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思想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思想论文,女性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4)04-0482-06
女性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指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兴起了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思潮。它的产生,直接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启迪和影响。
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播到中国。1902年,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本女性主义著作。1903年,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也被译介进来。1904年柳亚子所作《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中即称述:“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1906年孙雄在《论女学宜注重教育》一文中,描述了女学东来的盛状:“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关注女性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以各种方式翻译或介绍西方女性主义著作。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人Max Orell的《Thoughts on Women》;孟明翻译了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著的《女性与科学》,震瀛翻译了美国高曼女士著的《结婚与恋爱》,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与谢野晶子著的《贞操论》,哲父转译了英国Edward Capenter著的《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李达翻译了日本堺利彦著的《女性中心说》。在当时东方杂志社编纂的《妇女运动》一书中,收录的10篇论文几乎全是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不仅有罗罗翻译英国爱理斯著的《妇女地位之将来》,及君实译述《一九一八年与世界之妇女》,陈霆锐译述《世界女子参政之动机》,而且有佩韦著《世界两大系的妇人运动和中国的妇人运动》,心瞑著《一九一九年妇女运动之进步》,健孟著《女权运动的根本要素》,……总之,中国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热潮,通过这些宣传和介绍,为中国女性主义者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开阔了视野。而西方女性主义取得的成就,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作出自己的努力,正如沈雁冰所说:“我们不可不知西洋女子主义的起源、分派、趋势、现在和将来,我们不可不知他们发生这问题的背景”,“或介绍他们的学说,或参考他们的学说,印证自己的环境,研究创作”[1](第62页)。
由于此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者意识到,要建构起中国的女性主义,必须借鉴和吸收西方女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凡是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领域,如婚姻自主权、教育权、人格独立和产儿制限等,也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探讨的范畴。
长期以来,旧式婚姻制度是套在女性颈脖上的一条绳索,它不仅贱踏了女性的人格和自由,而且牺牲了女性的幸福。西方的婚姻自主观是中国女性主义者拿来的第一件武器,并把它作为开展女性主义的起点。炳文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美国的高德曼女士(Miss Goldman)在他的《结婚与恋爱》(《Marriage and Love》)中,竭力诋毁婚姻制度,劝导自由恋爱,倍孛儿(August Bebel)在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一文中,也极端攻击契约婚姻,提倡自由恋爱”[1](第233页)。他还引用了社会党员白克斯的一段话:“一切强迫婚姻,及卖淫制度,应要根本铲除。以后婚姻须根基于自由选择、自由意旨,丝毫不受外力的牵引”[1](第234页)。西方女性在婚姻自由制度下获得的人格尊重和个人幸福也为中国女性所景仰。在此影响下,新文化运动深化了对婚姻自由的认识,恽代英认为“结婚为男女自身之事,故当以男女自主之为正也”,“结婚主权,仍应属于结婚之男女自身”[1](第197页);《妇女杂志》还开展了“婚姻自由是什么”的专题讨论;一批宣传婚姻自由的文学作品被编成戏剧上演;一些接受新知识的女青年以实际行动向封建婚姻制度挑战,如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自刎于花轿中,以消极的行为抵制旧婚姻制度,不久长沙另一女青年李欣淑以离家出走的积极方式拒绝了包办婚姻,这两件事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关于婚姻的讨论更加深刻,婚姻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一般知识分子心中。
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是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争取女性教育权是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提出的响亮口号。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争,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欧美各国女性相继取得了中小学男女同校、女子入大学的权利。对此,罗家伦介绍说:“西洋的男女,在初等小学即男女同校起,一直至大学,也是男女受共同的教育。即以美国的高等教育而论,除了少数的几处女子大学而外,其余邦立的大学,全是男女同校的”[2](第10页)。而在此时的中国,男女教育仍分开进行,且仅有极少数贵族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教育体制极不完备。因此,他认为,介绍西方女子受教育的状况,“并不是无的放矢,实在觉得中国要妇女解放,则非实行男女的共同教育不可”[2](第10页)。可见,在西方的激励下,女子教育权的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1919年5月,甘肃女青年邓春兰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要求大学开女禁。此信被称为“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1](第265页),引起了一场关于大学开女禁的激烈辩论。《少年中国》特设《妇女号》专刊,辟出专栏讨论这一问题,第一篇就是特约胡适写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表达了主张大学开女禁的观点。康白情写了《绝对的男女同校》,周炳琳写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呼吁给予女子同等的教育权。1920年1月,蔡元培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发表演讲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3](第256页),巧妙地宣布了大学开女禁的决定。在理论界的强烈呼吁下,1920年春有9名女生到北大旁听,部分省市开始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女子教育权的斗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除了提出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外,特别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这是更高起点上的要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要求建立的新道德,是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为前提的。所谓“人格”,即“个人在大群里头应具的一种精神”,“人格完全的人,……他总要做社会上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女子被人把‘母’、‘妻’两字笼罩住,就轻轻把人格取消了”[1](第124-127页)。人格的丧失就是“人”的丧失,女性从人类历史中被“删除”,成为男性之外的“第二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格缺失了。所以,重唤起女性的人格意识是女性主义的关键。为了引起国人的关注,1918年罗家伦和胡适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译介到中国,剧中的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中并无任何独立地位,不过充当了丈夫的玩物后,毅然弃家出走。对此胡适评价说:“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此剧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指导了一代女青年选择自己的人生。不久后,胡适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美国的女人》,赞美了美国女性“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和“自立”的精神,并与中国女性“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和“倚赖”的特性作了比较,认为“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生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4](第501页)。通过多种形式的理论宣传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女性应具有人格成为大家的共识,一时中国也出现了很多“不当玩偶”、“争取独立人格”、“自立”的娜拉式的女性,揭开了新女性时代的序幕。
西方的产儿制限论也传到中国,李达翻译了日人安部矶雄著的《产儿制限论》一书。瑟庐在《产儿制限与中国》一文中说:“就生产率而言,在西洋如英法诸国大约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下;而在我国据美国洛斯教授(E.A.Ross)在《变动的中国》(《The Changing Chinese》)里所说,则在千分之五十以上。至于婴儿死亡率,在西洋普遍约为十分之三,我国却到十分之八”。可见,我国是一个高生产率和高死亡率的社会,而“低生产率和低死亡率,不但是文明进化的特征,而且也是文明进化的要素”[1](第340页)。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主张人为地抑制人口,新马尔萨斯主义主张通过避孕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美国的桑格夫人称之为“产儿制限”,即用科学的方法,使女性有选择做母亲的权利,从无限制地生儿育儿中摆脱出来,然而这一理论传到素有早婚习俗和多子多福观念的中国,遭到多方攻击,如认为产儿制限会破坏女子贞操,导致种族减少以至灭亡,违背了人类的自然本能等。对此,瑟庐进行了一一还击。1922年4月,桑格夫人来华,演讲《产儿制限的什么与怎样》,由胡适担任翻译,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从此,“产儿制限”理论在中国兴起,从思想上动摇了女人纯粹是生育传种的生物体的观念,实践上也使女性有了选择生活方式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为她们走向社会提供了精力和时间上的保障。
此外,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众多领域,如建立新的家庭观、男女社交公开、发展女子职业、儿童公育、家务劳动社会化等主张,都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讨论的重要内容。
可见,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话语系统,开辟的理论领域,展开的实践运动,都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者所借鉴和吸取,并用来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女性主义直接启迪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是中国女性主义产生的理论资源。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传入
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以传播西方近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使新文化运动分化出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也随之而传入中国。正是这样,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在前期主要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而在后期则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作指导。
“五四”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他们大量翻译反映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著作,如李汉俊转译了德国倍倍尔著《Women under Socialism》中的第三篇《Women is the Future》,李达翻译了《列宁的妇女解放论》,震瀛翻译了《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女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较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著作,为了加快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了解,恽代英摘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章,蔡和森在深刻领会此书的基础上,用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复述了它的思想,并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写成了《社会进化史》一书。通过翻译和介绍,使中国人能越过语言的障碍,直接接触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为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除了直接汲取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外,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来思考中国的女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深刻理解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认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在女子耕作、男子狩猎时代,因耕作的收入稳定而狞猎不可靠,“当时妇女的地位比男子高,势力比男子大”;在畜牧与耕作均归男子去作,女子专事家务的时代,“妇女的地位就渐渐低下”;到工业时代,男子无力养恤女子,生产技术的进步添出了适于女子的职业,女性参加了社会生产,“妇女的地位又渐渐地提高了”[5](第107-111页)。在这里,他揭示了两点:(1)女性受压迫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女性参与物质生产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她的社会地位。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自由有两种意义,一为精神的自由,一为物质的自由。女子所以屈从男子的,因为精神上的自由被束缚的缘故。精神上的自由所以被束缚的,因为物质上的自由先被束缚的缘故[6](第23页)。正如恩格斯在考察女性问题时说:“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7](第71页)。也就是说,两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平等只是表象,女性在物质上对男性的依附才是导致两性在社会关系上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如今要将女子解放,须先使他恢复物质上的自由,女子物质的自由的欲望,到达了最高点的时候,那精神的自由的欲望,自然而然地勃发起来。那时真正的自由,方可完全实现。这样的,才可算作真正的女子解放”[6](第23页)。在这种认识下,新文化运动时期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纷纷提出女子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主张发展女子职业,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创造社会价值,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恩格斯在考察家庭的起源时,认为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促使个体婚制取代了对偶婚制,而个体婚制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的“宣言而出现的”,因此,“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7](第61页)。也就是说,女性的被奴役不仅是一个性别问题,也是一个阶级问题;阶级关系的调整,是解决女性问题的关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阶级问题在女性解放中的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出发,李大钊认为,“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他分析道:英国的女性争得了选举权后的要求,不过“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8](第280页)。陈望道也说:“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9](第29页)。可见“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既然“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那么,“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8](第281页)。他们将女性主义运动区分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女性主义运动,发现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运动有着阶级的局限性,它主张在不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通过一项一项女性权利的获得来实现女性的解放,并不能解决女性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应与阶级解放同时并进,方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强调了阶级斗争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女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大钊说:“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10](第115页),《民国日报》从1919年4月12日到4月28日,刊载长篇文章《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介绍苏俄情况,其中不少篇幅涉及女性问题,文中指出:“他们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前提,……是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女子可以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天经地义的”,“劳农政府对于妇女教育,也很注意,他们在工女农妇中间,传布他们的主义,尤费心血”,“男女平权是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有列宁而后才能够解放女子”。向警予也指出,“异军特起的俄罗斯妇女,于欧美女权运动的程式之外,另辟一条革命的途径,一旦劳农政府成功了,伊们居然不动声色地骤然跻身于‘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地位”[11](第157页)。
苏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越过了女性主义运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男女平等,从而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解决女性问题的模式。这于正在探索之中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一个新的启示。既然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有局限性,而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女性解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在苏俄的实践中被检验和证实,他们通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女性的解放。
西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区别,首先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反映出来。胡适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认同西方女性主义的立场,认为女性主义的目标只有通过“卖淫问题”、“女性解放问题”等具体问题的解决方能实现,空谈“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实际上,他是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胡适的这一观点,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进行了反驳,认为“问题”固然需要重视,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却离不开“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是“根本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需的,一旦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胡适所说的这些具体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因此,在女性观方面,他不赞成西方女性主义争取同男性平等权利的做法,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指导下“根本解决”女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有了新的起点。沈雁冰在《家庭改制的研究》一文中说:“我先声明一句话,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家庭的话,远之如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中所论;近之如伯伯尔的《社会主义与妇女》所论,我觉得他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多是极不错的(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张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1](第255页)。陈独秀也认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先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我以为不论男女,都要研究社会主义,而女子比男子更要奋斗才好。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需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12](第270页)。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已明确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女性解放的道路,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也逐步取代了西方女性主义。
三、结语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从思想来源上看,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两大外来思想资源为其活水源头的。
作为一种先起的思潮,西方女性主义激活了中国长久沉睡的女性意识,它将在西方开辟的广泛的女性主义话题移植到中国,为中国新生的女性主义建立了话语系统,使中国女性主义得以独立健康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但是,西方女性主义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特别忽略了阶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联系;同时,作为一种异域理论,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后还需要经过中国化过程才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但中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却没有看到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加分析地把西方女性主义迎进并在中国原封不动地推行。这决定了它日后必然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认为,阶级解放是女性解放的根本出路,主张用社会革命来完成女性解放的任务,弥补了西方女性主义的致命缺陷。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取代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成为其后中国女性主义主要的思想来源。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政权史无前例地解放了中国女性,赋予了她们与男性同等的尊严和权利,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彻底消灭了娼妓制度。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正确性。
但是,女性的受压迫不仅是一个阶级问题,还是一个性别问题,它需要被当成一个独立的问题加以系统地关注和探讨。阶级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但它不能掩盖和取代性别问题,反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我认为,如果说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是明智之举,而拒斥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却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巨大缺失。这也为今天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汲取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和西方女性主义这两种思想资源,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
收稿日期:2003-11-25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胡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