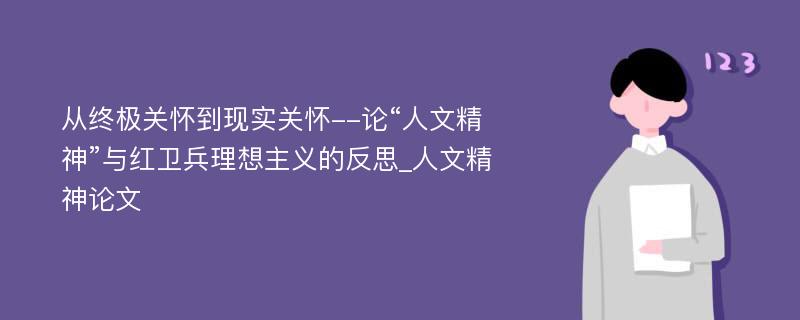
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人文精神”讨论与红卫兵理想主义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卫兵论文,理想主义论文,人文精神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两年,但凡读读书报的人都对诸如“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终极关怀”,以及“失落”、“精神家园”等词耳熟能详。这些话题大致覆盖了近一两年来知识界的热点,而最近几期《读书》(1995年第6、7期,未完待续)上,王蒙、陈建功、李辉以《精神家园何妨共建》开篇展开的一系列反思历史、评价当下文化精神状态的三人谈,无疑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又一朵花絮。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场三人谈开门见山,从理性地质疑和反省红卫兵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入手,不仅为另一场同样旷日持久、社会影响层面更为宽泛的“老三届文化”讨论提示了新的分析角度,而且随着对“大家共同建设一个精神家园的宽容”的呼唤,将这场“人文精神”的讨论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完成了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的过渡,从而和上了社会的脉搏。这两场文化讨论在几度峰回路转后的殊途同归般的藉合是意味深长的。将两场讨论的脉络放置到同一框架中进行一番梳理,无疑会帮助理解这种藉合的内在必然性及其深远的社会启示意义。
“在真正需要勇气的地方,为什么秀才们纷纷沉默了呢?——是“人文精神”失落了,还是旧的文人传统在复活?
“人文精神失落”一说的提出, 大概首先要追溯《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引出的“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 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为世纪末情怀中,面对社会转型期动荡的社会经济文化景观而焦虑、而苦有所思的知识阶层提供了对话的起点。不久,《读书》杂志开辟了“人文精神寻思录”一题,连续开展广泛的探讨。与此同时,《东方》杂志以1994年年初登载的王力雄的《渴望堕落》一文,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坚守怎样的价值体系的争论,《文汇报》也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这些讨论一下子激活了80年代末期启蒙热潮过后曾一度“疲软”的知识界,持“人文精神失落”论的声音先声夺人,评击“近年来浸淫日深的价值失范”,指出过分的急功近利是导致人文精神在近代失落的原因:“人们要富国强兵,要救亡,要现代化,但却忘了这一切本身不能成为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第4期), 将人文精神的低迷上溯到明末清初,描出了一幅“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梁启超)的众生相。在此种氛围中,《废都》的出现似乎正应景般地渲染了某种没落文人的世纪末颓废情怀,象是一声无奈的叹息。而张承志的《心灵史》则大音希声般地传达出一种英雄末路、拔剑茫然回顾的忧愤之情。更有文章将“人文精神”的追思放置到“漫延全球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落感”当中,预言:“在这片干涸的由拜金主义统治的沙漠上,任何人类价值与文化传统都将逐渐消亡”,甚至悲观地发问:“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神思想的代言人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亡?”(《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世界性困境》,《东方》1994年第2期)
这种措辞激烈、异常情绪化的论调立刻如一石激水,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反响。一部分以终极关怀为至上者起而呼应,表示要在社会转型期的商潮涌动、“物欲成为新的人伦关系的宰制”之时洁身自好,做文化的守望者,执著于一个“知识分子话语”的世界。这个世界被解释为“一个与当权者无关甚至在目前也可能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存在”(见《读书》1994年第6期)。 这便多多少少宣告了当前经济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与文化状态之间的断裂,从而引起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异见和民众的不满。有读者尖锐地发问:“中国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危机果真是知识分子的危机吗?……这里我看不到重建人文精神的必要,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内的清谈不可能是代表社会核心力量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10期读者来信)1994 年第3期《文艺争鸣》发表蔡翔文章,指出当代知识分子中的闲适文人倾向正得到意外的鼓励,成为人们逃避今天、把玩当下的借口。文中一方面承认有关社会和人的乌托邦的想像受到现实实践的致命打击,一方面对这种文化的失望情绪刺激下的文人传统的复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不再关心社会,作出应当怎样的价值允诺,并失去了所有的关怀激情。他重新躲进传统,在那些所谓的闲适小品的写作和阅读中,重新获取一份‘内在的欢乐’。然而,这种欢乐已经不再成为一种内在的超越的努力,而只是作为一种逃避今天的文人借口。”一时间,“话语”的子弹满天飞,“动辄七、八个象征,五、六个隐喻,十几个话语系统”,人们随之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但是这些东西真的能遮蔽我们头顶上的风风雨雨吗?我们和脚下的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真正需要勇气的地方,为什么秀才们纷纷沉默了呢?”(张卫民《无法对话的文人“话语”》,《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
“人文精神需要的是在价值和历史进程之间寻求更具实践性的依托”
当这场知识界的讨论沸沸扬扬之时,另一场文化现象的讨论正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同时展开着,这就是80年代末以来“老三届”文化的勃兴而引起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文革”传统的再认识。
80年代末以来,悄然兴起的“老三届”文化热不同于“文革”刚结束时的“知青文学”现象。它在文学上的表达与先前的具有强烈控拆和批判倾向的“伤痕文学”有了明显的不同,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旧伤情般的失落和苦难崇拜的悲壮情怀。同时,“老三届”文化热更为显明的特征是它已不再局限于逝者往矣般的文字表述,而是迅速地以当前状态化解到社会活动中去,以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诠释现在和未来,在社会上以种种经济、政治、文化实体的形式施放着影响,成为近年来大众文化中的一股潮流。1995年第2期《东方》上, 陈小雅载文对“老三届”文化热进行了较全面的透视,指出作为“毛泽东热”的后续文化浪潮,“老三届”文化不仅是当今商业文化情境下,价值失范喧嚣中一代特定历史背景的人们怀旧情感的载体,同时它在社会转型期的结构调整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陈小雅同时认为:“老三届”文化在道德观念取向上有重义轻利的倾向,是对目前“物欲横流”的商业文化局面的反拨。
但与此同时,一些“老三届”人对历史表示的“不忏悔”心态和对“老三届”精神,乃至对“红卫兵理想”的一味颂扬肯定也逐渐招来质疑。尤其是“老三届”中的部分成功人士愤世嫉俗地以“社会道德批判力量的主体”自居,割断“文革”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内在连贯性,割断自身角色与所置身的社会现状的联系的作法,引起“老三届”群体中持清醒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士以及青年人的争议。《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和《北京青年报》都曾就“老三届”文化开展连续的专题讨论,旨在挖掘“老三届”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要反映的精神内涵。然而一个时间内也曾出现过对话的双方守在各自的“话语工事”中放空枪的僵持局面(“青春无悔”的一方怎么看历史怎么“辉煌”,怎么看现实怎么不顺眼;持批判态度的一方则对急于“伦理重建”的呼吁持谨慎态度,提出要首先对这“伦理”包含的内容作一考察),使得讨论处于山重水复的状态。
这两场不同社会层面、不同内容的文化讨论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了社会文化转型期人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细究起来,这两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讨论在大致结构和走向上有着一一对应的性质。
首先,这两场讨论所涉及的对象,知识分子和红卫兵理想主义教育下的一代人,虽然背负着各自不同的特定的历史传统,但在转型中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均经历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乌托邦理想(虽然内涵各不相同)的破灭,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找寻的欲望。其次,他们各自代表的精神内涵均受到来自现实的不同意义上的挑战,在几番内省之后拉近了自身与现实的距离,从“失落”后的“寻找”走向“转化”后的“重建”。这便为两场文化讨论的遥相呼应提供了契机。
具体在知识界,王蒙等人对“人文精神失落”一说率先发出了质疑,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几个不同的人文参照系统的交叉点上,一些朋友们关注的人文精神是特指一种文化精神,而寻找或建立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人的存在的承认。谈及“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王蒙说:“失落了四十余年,没有谁说过失落,就是说失落也不许说,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失落了,是不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回归呢?”“失落的时候不说失落,回归了一点反而大喊失落。这是中国特色的现象,甚至是某些悲剧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人文精神的建设重要的是道德或文化品味的建设。余英时认为,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社会不被摧毁,文化就摧毁不了。李泽厚、王德胜在关于文化现状和道德重建的对话中提出了人文导向问题,人文精神的建设同当代中国人最现实的生存处境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李泽厚批评了从儒家的“内圣外王”到毛泽东的“文革”所表现的泛道德主义,比如当年红卫兵就是非常纯洁地、高尚地、禁欲主义地进行大破坏的,而目标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新世界”;不先把这些问题解构、搞清,就阻碍了真正道德的建立。李泽厚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文化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三者间的关系,认为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因为大众文化具有雄厚的基础,从“策略”上讲,也应从这方面入手。它们之所以可以构成联盟,在于它们都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所提出的要求,只是层次不同而已(《东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期《读书》载文《要记住,你是一个人》(贾植芳),批评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商业大潮的冲击的论点,而认为“畸形精神状态在生活激流中大面积的出现,追本溯源的话。其根源则在于50年代以后的‘左祸’的灾害”。
随着知识界的人文精神讨论从终极关怀逐渐靠近现实关怀,对“文革”文化影响的再反思和对红卫兵理想主义的批判开始成为一个热点。在社会上,“老三届”群体中一度被遮蔽的另一种声音,即主张历史忏悔意识的声音也开始高扬起来,一批新崛起的作家开始认真地思考知青文学的走向。知青作家郭小东在继他的《中国知青部落》的创作后说:“应该向一个怎样的层面掘进?那就是彻底抛弃粉饰和以成功者的反思去看中国知青运动”。在后来完成的著作《青年流放者》的序言中,郭小东表示要“以十二分的理性去面对许多作为平民的知青,而且把这种理性的努力实践于他们的心理分析中”。他因此把视角转向知青一代“在创造新生活时,那种由于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磨难和心灵创伤,那种不可铲灭的追忆,是如何成为他们灵魂的十字架,是如何阻碍着他们的精神健康的。我希望能够透过这种现象而启悟我们对知青运动的历史问题的深层思考。它不仅仅是造成中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诸多社会难题:诸如人才缺乏、文化传统断裂、信仰危机等等的原因,它同时使新中国整整一代人中绝大多数优秀分子在现实中沉论了,消遁了。这是尤其令人痛心的。”
来自“知青部落”内部的深层历史反思所具备的感召力是不言自明的,这种力量对当下社会精神状态所作出的调试的努力也引起了思想评论界的关注。李辉曾在《读书》1995年第4 期上载文评点另一部知青作品《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一书,赞扬其中的历史忏悔意识,说:“红卫兵性格决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当年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处世哲学,才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同时,更应该看到,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后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民族身上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遮掩住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启蒙过后经历了一番上天然后落地的过程,他们在十几年前的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异口同声中,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有着预先设定的历史地位和明确的身份。然而90年代的经济、文化的多元走向,以及泥沙俱下的转型浪潮冲散了这原本组成单一的队伍,在与市民文化的撞击中,有一些浪花高扬起来,一时蔚为壮观,波涛起伏。在拐过几个波回之后,其流向已逾见明晰,正顾望着现实的港湾,期待着在那里与市民的大众文化重逢后的共识。在那里,多元文化正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寻找着劫波度尽后的家园意识,知识分子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老三届”人的所谓“青春”回忆无非是这样的一段前奏曲。当“家园”这个议题终于诉诸直接的表述之际,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了对自身的清醒审视,而“文革”中走出的人们开始了对过去的理性反省,这便有了王蒙等人“共建精神家园”的呼吁。而在多元文化氛围中共建一个家园,宽容精神无疑是首先要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