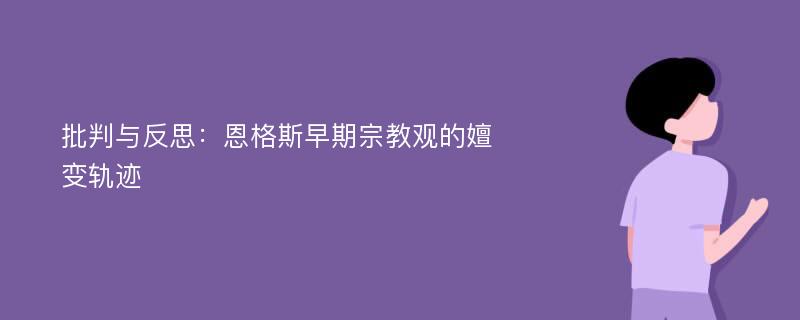
摘要:恩格斯早期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演进逻辑和嬗变轨迹予以分疏与厘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文本考察来看,恩格斯早期在批判与反思中不断克服与扬弃旧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嬗变过程,从最初的虔诚主义到超自然主义,从超自然主义到成为施特劳斯主义者,从施特劳斯主义者导向黑格尔式泛神论,最终进入费尔巴哈为其营建的无神论归宿。
关键词:恩格斯;早期;宗教哲学;人本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
尽管恩格斯一生关于宗教的论述和研究比马克思多很多,但是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对其研究兴趣并不浓厚、研究成果也不多,而对其早期宗教观的研究则相对更少。无疑,恩格斯早期宗教观的研究是有价值且重要的,诚如学者楼凡所言:“宗教观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逻辑起点。”[1](p6-11)笔者通过回顾和检视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发现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对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处于附属的第二位。大多数学者习惯性地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叙事模式,在论证或引用的时候往往没有加以区别和归属,使二者的思想杂糅在一起,遮蔽了二者思想的各自特色与演进逻辑;二是多从“时间—地域”维度对恩格斯早期宗教观进行划界。比如有学者以恩格斯早期生活的乌培河谷、不来梅、柏林、曼彻斯特为分期来研究,此方法固然能演展恩格斯早期在宗教观上的变化,不过并未突显其变化的关键节点。[2](p58-63)三是对恩格斯早期宗教观的嬗变轨迹存在分歧。比如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早期宗教观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虔诚主义、唯理论、泛神论、无神论,[3](p125)有学者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虔诚主义、超自然主义、无神论,[4](p9)也有学者认为经历了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形成之后,[5](p14-21)等等。拙文吸收并采用了前人的某些观点,但却增加了笔者自己的省思与憬悟,特别是突出了恩格斯早期宗教观嬗变的重要节点,并析述了相关人物的宗教思想对恩格斯早期宗教观的影响。需要界定与说明的是,拙文的“早期”主要是指1820年至1845之间。拙文无意用“早期”来割裂与肢解恩格斯宗教观的完整性,反之,却是为了厘清他的思想进程中对象与内涵的摆置侧重,强调恩格斯宗教观的思想连贯与逻辑统一。
一、从虔诚主义到超自然主义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普鲁士乌培河谷的巴门市——一个“虔诚派”的中心。他的父亲是一个资产阶级纺织工厂主和保守的虔诚派教徒,并且在当地的教会中担任公职。恩格斯的父亲以虔诚主义为教育方法,严格用基督教教义教育和规范恩格斯及其兄弟姐妹的言行,要求他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都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圣经和尊奉宗教教义。这里所说的虔诚主义是一种基督教性质的宗教流派,诞生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它的源头可追溯到新教加尔文宗。虔诚主义是一种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相适应的基督教教义,它大肆渲染极端神秘主义,宣扬“先定说”“宿命论”“原罪说”“赎罪说”,鼓吹“禁欲主义”和“尘世虚空”,要求教徒们教条式地对待陈腐的教条教义。当时整个乌培河谷的上空都被这个“神秘幽灵”氤氲笼罩。渴望自由、憎恶束缚的恩格斯极力想挣脱虔诚主义这把枷锁,但是他此时只能无条件接受家庭所给定的宗教信仰,向上帝求助:“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请你下凡,我在苦难的尘世把你祈盼,啊,请你带走一切灾难!”[6](p626)
1838年7月,恩格斯的父亲为了能让他子承父业,迫使恩格斯辍学前往不来梅学习经商。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通过报刊和书籍接触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同时加入了“青年德意志派”——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色彩的进步文学团体。由于受到“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恩格斯对乌培河谷的虔诚主义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在1839年3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在文中,恩格斯凌厉地批判了虔诚主义的荒唐和虚伪,深刻地揭露了工厂主和传教士对劳动者的压榨和迫害。他在文中指陈:“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但在选举教士的时候,他们总是抢先收买自己的人”。[7](p499)在乌培河谷,虔诚主义成了工厂主们的护身符和遮羞布,即便童工身心备受摧残,“但是大腹便便的工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7](p499)恩格斯指出,造成劳动者悲惨生活的根源就是“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丑恶的神秘主义”,[7](p498)但是他坚信“就是这个就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7](p507-508)通过对乌培河谷虔诚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恩格斯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动摇,虽然此时他在思想储备上还未达到对基督教做出根本否定的能力,但却显示出了他在宗教信仰上的危机征兆,预示着他萌生了反叛宗教信仰的意识与趋向。
首先要严格按要求订立合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使其有效约束和规范各方行动,确保合同各项规定得到认真遵守。要严格审核工程设计变更,确保符合要求,防止因设计变更而增加成本。对可能出现的索赔,也要按合同规定处理。注意工程索赔的正当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尽量降低损失,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索赔。一旦出现索赔,也要按合同规定和法律要求进行索赔处理,防止出现不必要损失,确保PPP投资型项目效益提升。
当下,主打食材安全、健康,提倡本源味道的有机餐厅已成为餐饮界的一股清流,部分高档酒店的中、西式餐厅也逐渐将有机食材视为餐厅标配,以满足中高档消费群体对于“吃”的品质追求。
《耶稣传》不啻为一声惊雷,其所彰显与释放的反宗教力量对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动摇与破坏是尤深且巨的。恩格斯通过对其深入研究之后,便深深服膺于施特劳斯“神话起源说”的发现与创见,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宗教与理性、科学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性与神性之间的扞格。他认为施特劳斯对《圣经》中所内含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与破绽作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论证,向人们指明了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耶稣或弥赛亚)和福音书,原来只不过是人们自发无意识地神话汇集与神迹投射,《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耶稣只不过是犹太人获救热望下所产生的神话符号与人神格化的幻象。《耶稣传》对于处于宗教徘徊和信仰危机之际的恩格斯来说犹如洪钟大吕,其振聋发聩之效是深刻的,它为恩格斯注入了一股思想清流,助力其克服精神迷茫与信仰踌躇的焦灼。恩格斯在1839年10月给好友威·格雷培(Wilhelm Graeber)的信中表达了他当时的欣喜之情,他写道:
二、从超自然主义到施特劳斯主义者
真正促使恩格斯摆脱虔诚主义的缠绕,走出超自然主义的迷津,彻底与“乌培河谷旧信仰”诀别,进而获致精神启迪的助力者,乃是黑格尔青年门徒中的反宗教神学先锋——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F.Strauss)及其被誉为“十九世纪神学批判的典范”——《耶稣传》(1835)(又译《耶稣平生》)。这部作品为恩格斯清理以前的旧信仰打开了突破性缺口。
高职会展英语教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现有的方法和教学内容不符合现有的教学环境,不能满足学生自身的需求、教师发展的愿望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会展英语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8]。
在19世纪荆棘丛生的德国,宗教与政治合谋共施,构成统治阶级控制民众信仰的精神武器,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遂成为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们的批判靶向与箭垛。施特劳斯在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无疑成为撬动德国神祇的有力杠杆,揭橥了宗教批判的大旗。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一反前人把《圣经》当作“启示”“先知”和“神谕”,而是秉持历史批判的原则,主张用史实考证的方法来解读和研究《圣经》,他认为只有史实才能充分打破神学上的偏见、揭露教条上的谬解、纠正《圣经》注释上的错误、祛除基督教中的“神迹”。通过对四部福音书与耶稣生平的历史考证,他得出至少以下两个结论:(一)弥赛亚虽然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不过却被人为披上了基督的圣袍,《圣经》里的神话故事只不过是犹太民族把对弥赛亚的美好愿望投射与移植到耶稣身上而创造出来的,并不具备历史真实性;(二)耶稣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普通的世俗凡人,“神迹”只不过是犹太信徒们想象、虚构与杜撰出来的。施特劳斯最后指陈:“通过我的考察的结果,基督教有关耶稣的信仰都好像已经被彻底击溃,所有从之得到信仰的东西都被拿走;他被剥夺了每一个安慰,滋养了人类十八个世纪的无尽的真理和生活的宝藏现在似乎都被破坏了,最神圣的部分撞到了地上;神被剥夺了他的尊严,人的尊严、天地之间的联系分裂了。”[8](p51)施特劳斯通过对耶稣神话起源的历史性考察,解蔽了基督教的神秘基础,揭开了宗教神学的伪善面纱,还原了耶稣的原初本相,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迷思与精神上的混沌。不过,需要检视的是,施特劳斯这种以历史主义批判方式写成的《耶稣传》,其缺点也是昭然若揭的:它是以黑格尔“客观精神”为先决条件来考察和解读福音书的,其实质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随后,恩格斯因受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的影响而成为一个超自然主义者。施莱尔马赫的超自然主义主张情感至上、情感崇拜,他认为宗教根源既不是知识,也不是道德,只有情感才能揭示宗教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他认为基督教里存在着超自然的神,这个神住在每个基督教徒的心里。施莱尔马赫的“情感宗教”显然是一种唯心观念论,它把宗教归结为心灵与情感,不过比起虔诚主义那种扼杀人性、压抑精神的宗教强制,“它为恩格斯更加自由地、更加宽泛地理解宗教提供了理论依据。”[3](p58)此时的恩格斯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无疑是找到了临时的“避难所”。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宗教是心灵的事情,谁有心灵,谁就虔诚;但是谁以推理甚至以理性作为自己虔诚的基础,谁就根本不会是虔诚的。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隐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来自魔鬼。这就是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而我赞同的也正是这个学说。”[6](p511-512)在这一时期,恩格斯虽然还没有找到摆脱宗教信仰的正确解决方案,但是相较以前,他在思想上明显发生了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好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6](p463)由此可知,恩格斯并没有沉溺于传统基督教正统思想而止步不前,而是在继续寻找精神上的出口。
《耶稣传》点燃了恩格斯乃至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反宗教神学的叛逆意识,催生了向神学宣战、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火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恩格斯利用《耶稣传》这个锐利武器斩断了禁锢他的虔诚主义与超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他的精神之困与信仰之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恩格斯虽然卸下了沉重的宗教信仰包袱,为其轻装上阵迈向崭新的思想进阶释放了空间,但是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因为不久后他就滑向了黑格尔式的泛神论。
“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你听听,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这里有芜杂和离奇的四福音书;神秘主义拜倒在它们目前,对它们顶礼膜拜——看,突然间大卫·施特劳斯象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Adios(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6](p522)
三、从施特劳斯主义者到黑格尔式泛神论
施特劳斯及其思想对恩格斯的影响和作用,除了助力其摆脱乌培河谷时期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更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为恩格斯研究黑格尔思想、信仰黑格尔主义、投向青年黑格尔派阵营、最终走向无神论而铺路搭桥。在1839年底,恩格斯在给威·格雷培的信中写道:“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6](p540)通过浸淫黑格尔思想,恩格斯逐渐确立了黑格尔哲学世界观,与此同时,一并把黑格尔的泛神论思想采撷到自己的思想中来,他在给威·格雷培的信中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于是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不会思考的牧师们的大惊小怪。”[6](p544)由此可知,此时恩格斯在宗教信仰上从忠实的施特劳斯主义者转向了黑格尔式的泛神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式的泛神论做一个梗概式的析述。
由此可见,黑格尔式泛神论闯入恩格斯的视野后,对长期经受宗教压抑和信仰彷徨的恩格斯来说是喜出望外的。黑格尔式泛神论主张人神共通一元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帝全知全能的神圣性,降格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突显了人的自我意识,为恩格斯从泛神论走向无神论酝酿了思想酵素。不过,另一方面,黑格尔式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即通过概念自身的辨证运动,“将精神变成了自在自为地创生万物的绝对精神或上帝”,但是“由于概念自身是脱离人的头脑的自在自为的精神实体和主体,它的自我否定和扬弃的运动本身就具有一种更为玄奥幽冥的神秘色彩,因此概念(或理念)神秘主义又在宗教神秘主义的废墟上被建立起来。”[13](p103-108)
恩格斯似乎也逐渐意识到,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所建构的泛神论虽然对上帝的神性加以了消解与祛魅,但它仍然保留了上帝与神明的概念和位置。是故,恩格斯坦陈:“黑格尔毕竟还是哲学,虽然结果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基督教。”[6](p263)言外之意,泛神论依然没有脱离与神和上帝的关系,它同虔诚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一样,它们只不过存在着表现形式上的差异,而在本质上均没有超出上帝与神明的范围,它们都只是论证宗教的工具,而不是驳倒宗教的武器,它们自始至终都在宗教的领地里打转。由此观之,恩格斯此时已经探察了黑格尔式泛神论的破绽,并开始自觉意识到,只有走出上帝的神明之域,才能进入无神之域,而费尔巴哈及其《基督教的本质》助了他一臂之力,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爱啊,爱的上帝降临凡尘,而人是爱情永驻的保证!上帝不正是在你心中长存?你要象对待贵重的器皿一样,爱护上帝的精神!……当最了不起的一位哲学家的神的观念,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我们在神的怀抱中生活着,行动着,存在着!”[6](p95-96)
其它子系统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几个,如人员考勤系统等,是留给未来拓展使用的。现阶段并不重点建设,或者较少涉及,未来有需要再进行补充。
众所周知,在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及其后来的基督教教义传统里,上帝是一种十全十美、全知全能的超自然神圣力量之存在与显现,而黑格尔(G.W.F.Hegel)对此却是极其反感和排斥的。他反对把上帝放在虚无缥缈的彼岸天国,他认为上帝存在万事万物之中,活在现世的众人心灵与精神之中。黑格尔认为:“上帝就是那普遍的、绝对的、本质的精神。”[9](p72)易言之,上帝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是上帝的象征。同时,黑格尔认为:“只要上帝认识他自己,他就是上帝;进而,他的自我知识是他在人里面的自我意识,以及人关于上帝的知识;那将进展到人在上帝里面的自我知识。”[10](p379)详言之,上帝一开始是无知无识的,并不知道自己上帝的身份,他唯有自我意识到他是上帝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者。而他要揭示自己是上帝这一事实就必须依靠他所创造的人及其人的心灵与精神,把他的神性投射与显露在人的人性与活动上加以落实、展现与确证。由此可知,上帝要走上自知之途,恢复上帝身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思想运动过程:上帝—人—上帝,即如台湾学者洪镰德(Hung Lien-te)所诠释,在黑格尔看来,上帝创造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为知性,再由知性和理性形成主观精神,由主观精神迈入客观精神,最终人类达到绝对精神的最高境界,攀升到全知全能的上帝之位。[11](p32)换言之,人与神是共体的,人性与神性是相通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与识别工具,也是上帝的化身,上帝必须依靠人的自我意识才能确认与回归上帝的宝座。黑格尔打破了传统基督教中人与上帝截然不同的两元论,把有限的人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上帝之位,创造了人与上帝合二为一的“宗教哲学”,“使无限者在有限者之中,而有限者在无限者之中表现出来,并使双方之中的任何一方不再构成一个特殊的王国”,[21](p15)企图实现知识与信仰的统一、哲学与神学的和解。
诚然,恩格斯此时是沉湎于黑格尔式泛神论的。在他的《风景》(1840)一诗的末尾一节这种泛神论思想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写道:
四、从黑格尔式泛神论到费尔巴哈的无神论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宗教哲学进行了驳斥和拆穿,同时阐发了他的人本主义宗教哲学的精髓与主旨:“神学的秘密不外就是人本学。”[15](p274)众所周知,在黑氏看来,哲学与宗教是一体两面,绝对精神就是上帝,上帝亦即绝对精神。费氏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黑氏提出的是伪命题,他指陈:“如果在人拥有上帝的意识中首先出现了上帝的自我意识,那么那种人的意识本质上就是神性的意识。那么为何你从他那里异化出人的意识,并使它成为一个明显不同于他的存在的自我意识?……真命题是这个:人的上帝知识是人的自我意识,他自己自然的知识......上帝意识所在,就是上帝的存在——因此,在人里面;在上帝的存在中它只是你自己的存在,那是你的一个对象;在你意识之前表达它自己的,纯粹是在它背后的东西。”[15](p302)易言之,他认为事实上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是上帝的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而刚好相反,上帝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出的客体或它者。对此,费氏在1842年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继续谈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16](p115)因此,费氏认为有必要用“主谓颠倒法”,亦即美国学者罗伯特·C.塔克(Robert C.Tucker)所谓的费尔巴哈式的“转型批判法”,[17](p86)对主体(主词或主语)和宾词(谓语或述语)做一个颠倒、翻转、扶正,把人与上帝的地位对调、身份互易,亦即是说,人是存在,上帝是思维,人是主词,上帝是宾词,上帝(宗教)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处于异化状态下的投射与反映。在费氏看来,黑氏的宗教哲学是一种神秘的理性主义,黑氏在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时用神秘的绝对精神来包装人与上帝的关系,忽视了立足于现实之地的自然人。是故,费氏指陈:“人——这是宗教之秘——投射其存在到客体性之中,然后使他自己成为他自身这一投射影像的客体;如此转换为一个主体……上帝本质上是他遗弃的自我。”[15](p63-64)由此可知,费氏的宗教哲学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尊的人本主义哲学,“把‘人’从抽象的、非感性的精神世界中迎接回来,还原为世俗的、感性的、有血有肉的、自然的人。”[18](p26-40)
在恩格斯通往无神论的归途中,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及其《基督教的本质》是不可绕过的重镇。费氏在日耳曼思想史上虽不及黑格尔那般光芒耀眼,但仍不失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璀璨巨星,尤其是他在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成为日耳曼思想史上的夺目盛事。相较黑格尔思想对恩格斯的影响来说,恩格斯受费尔巴哈思想的震撼与影响是更为深沉和持久的,这是因为恩格斯没有正式上过大学,未曾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而更多是自学自修,比起黑格尔那种行文晦涩、术语繁多、思想深邃,他更容易接受费氏通俗易懂的行文风格。从恩格斯在1886年写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便能窥探到《基督教的本质》对当时恩格斯的影响,他回忆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4](p222)可知,费氏的思想对恩格斯从黑格尔式泛神论进入唯物主义无神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3)空间因素。首先从整体地形来分析,甘肃省地形复杂多样,较为破碎,山脉分布面积广,且纵横交错,另外分布有平川、高山、沙漠戈壁和盆地等类型,海拔相差悬殊。受这种破碎的地形和山脉交错分布特征的影响,对于一些分布面积较小,并未达到数据分辨率要求的水稻土、沼泽土、潮土、灌淤土等未进入分类。因此,研究区域的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土壤分类。
费尔巴哈破译了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密码,对上帝的本质加以了澄清,把神学化约为人学,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与思想武器,给了黑格尔思辨哲学致命一击,把围困在黑格尔观念论中的“囚徒”给解救了出来,它使恩格斯进一步认清了上帝的本质,平复了驳杂的宗教信仰对恩格斯内心造成的搅扰不定,疏浚了堆叠在通往无神论道路上的淤堵,助力他摆脱了神学的羁縻牵绊,呼吸到了新鲜的自由空气。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表达了此时获得精神解放的快感与喜悦,他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哲学比作太阳的升起,他指陈:
“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祭祀的火焰从群山之巅向它微笑致意,从四面八方的了望塔传来的欢乐的号角声宣告了太阳的升起。人类焦急地期待着它的光辉。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奇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天堂降临尘世,它的珍宝撒满人间,就象路上的石子一样,俯拾即是。一切紊乱,一切恐惧,一切分裂都无影无踪。世界又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它砸碎了自己的黑暗寺院的大锁,脱下忏悔服,选择了自由纯净的太空作为栖身之所。”[6](p266)
此外,有一些学者认为母语对二语习得无明显影响,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迁移对他们学习第二语言的影响微乎其微,并没有产生正迁移或者负迁移。但笔者并未搜到文献来证明此观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哲学构成了恩格斯思想嬗变的內驱力与转捩点,使他在历经了重重思想考验后而终于抵达无神论的归宿。不过在另一方面需要审慎的是,在前期,费尔巴哈虽然反对基督教神学与黑格尔观念论,但是在其思想后期又落入了神学的圈套,主张依靠“类本质”筑造一个爱的宗教,其无异于宗教神学的翻版与重构。
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本考察来看,恩格斯早期的宗教观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和艰难的嬗变轨迹。从最初的虔诚主义到超自然主义,从超自然主义到成为施特劳斯主义者,从施特劳斯主义者导向黑格尔式泛神论,最终进入费尔巴哈为其营建的无神论归宿。恩格斯早期在批判与反思中不断克服与扬弃旧的宗教信仰,为其整个思想大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奠基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了睿智哲思。诚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所言,恩格斯在明确放弃了宗教信仰的全部假象后,逐渐“使他成为第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历史呈现一幅草图的人。”[19](p45)通过梳理恩格斯早期宗教观的演进逻辑与嬗变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新时代中国的宗教工作。
参考文献:
[1]楼凡.宗教观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逻辑起点[J].宗教学研究,1992,(Z1).
[2]李士菊,乌云娜.青年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变化——从《乌培河谷来信》到《谢林和启示》[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3]鲁夫,等.社会·群体·个性——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徐琳.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5]韩琦.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J].科学与无神论,2014,(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Horton Harris,David Friedrich Strauss and His The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9][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德]黑格尔.精神哲学[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洪镰德.马克思的思想之生成与演变:略谈对运动哲学的启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12][德]黑格尔.宗教哲学讲座·导论[M].长河,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13]赵林.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理性基础与逻辑结构[J].世界宗教研究,1998,(4).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王太庆,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7]Robert C.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18]吕大吉.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宗教观理论概说[J].社会科学战线,2010,(2).
[1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一种对马克思批判基督教的描述和评估[M].林进平,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中图分类号:A811;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6-0019-06
作者简介:杨睿轩(1992—),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 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