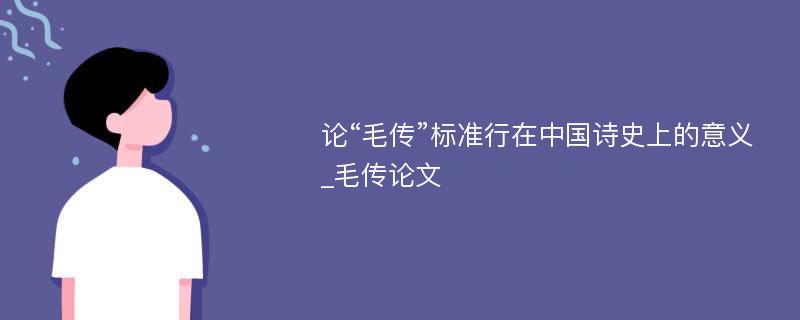
论《毛传》标兴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毛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1-0074-07
《毛传》标兴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自古及今,这一问题总是不断地被人提起,却又总是在稍作掂量或客观说明之后即被丢弃在一边,以致它被提起的频率与几乎无人对它进行深究的事实之间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因为这一问题本身缺乏值得深究的价值,而恰恰是因为论者大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又普遍地陷于一种无法作出深入阐释,甚至无法对它本身作出清楚说明的困境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典诗学在日后的发展中兴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显露无遗,反过来衬托出《毛传》标兴的不同寻常;另一方面,文献缺失所导致的发生源头的迷惘不清使得学者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只能停留在知其然的表层,而难以进入到知其所以然的深层。因此,探明兴的发生源头实为从理论上阐释《毛传》标兴之价值的关键。笔者曾对赋、比、兴的发生源头作过有别于前贤时修的系统的研究(注:参拙文《赋法思维的发生学研究》.《东方丛刊》1996.3;《论兴的思维源头和审美本质》.《原学》第六辑;《论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东北师大学报》1998.5。),本文即想在此前提下对《毛传》标兴的理论意义进行新的探讨,以便重新确定它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位置。
1
对于《毛诗》中明确标示出的“兴”,汉代学者普遍将它作为比喻看待。如郑玄在为《毛诗》所作的笺注中就是将“兴”直接解释为“喻”,他在《诗经》首篇《关雎》开头两句的笺注中就以纲领性、体例性的方式明确指出:“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他皆仿此。”在对《诗经》具体篇目的笺注中,更是将这一纲领性的方法贯彻始终。汉代的其他学者对“兴”的理解也基本不出郑注的范围。从问题的一方面而言,汉代学者以喻释兴确实揭示了兴在修辞学和诗歌艺术表现方面的某些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兴在主观心灵体验上那种“与神同一”的特征,或者说那种曾让原始先民们心驰神往、忘己遗形乃至意醉神迷的境界(注:参拙文《论兴的思维源头和审美本质》。),却在汉代学者偏重语言学、修辞学和以政教为目的的形式化诗论中被遗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学者以喻释兴并未揭示出兴的全部含义,相反却大大忽略了兴最本质的特征,给后世的诗学发展留下了无限的话题。
因此,我们必须把汉代学者包括《毛传》本身对兴的解释与《毛传》“独标兴体”分别看待。因为后者有着更为久远的传统,它至少可追溯到《周礼》关于“六诗”的记载,《毛传》不过本于师说复述了这个传统(注:2001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馆藏新近发现的《战国楚竹书(一)》。其中有29支竹简被学者们通称为《孔子诗论》。有学者据此认为《诗序》“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是经过孔子传承下来的。《孔子诗论》所阐发的诗论观点.与《诗序》极为一致.而且还可以互相发明。”(参《人民政协报》2002.1.29《学术家园》版)。这亦可作为《毛传》标兴有更古老的传统的一个参照。);而前者却是汉代学者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既然这一理解很不全面,那也就意味着,被汉人忽略而在后代却得到了合理发展的兴的其它方面的特征,早已潜含在《毛传》依照古老的传统所标出的兴诗之中。
遗憾的是历来的《诗经》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并未深究。《毛传》的后继者们所做的只是对《传》说的修正、补充,郑玄在毛传之外又定出一些兴诗,朱熹则不仅增加了兴诗的篇数,而且认为《诗经》中的兴诗还有“兴而比”和“赋而兴”两类。直至朱自清先生才承认兴在后世有“两个变义”,一个他称之为“兴象”,照他的理解是指“言外之意”;另一个是“兴趣”、“意兴”,他认为即是“象外之境”(注:参朱自清《诗言志辩》第83-86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朱自清所谓“兴象”.与唐人殷璠所说的“兴象”不同.他在自注中说:“‘兴象’即‘比兴’.今借用此名(笔者案:指殷璠诗论中之‘兴象’).义略同。”)。但具体到《毛传》标兴的问题,他却只承认“兴是譬喻,又是发端。”(注:参朱自清《诗言志辩》第50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至于那两个“变义”是如何变出来?它们与譬喻兼发端的兴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朱先生并未说明,不过他关于兴的“两个变义”的观点却表明他已开始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兴”了。
在此基础上,赵沛霖先生从“他物”与“所咏之词”的关系入手来理解兴,提出了“原始兴象”的概念,直接用“兴象”来解说《诗经》及《诗经》以外的逸诗中含有宗教意义的一部分诗篇。他的解说以《毛传》所标兴诗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如他所举以鸟类起兴的《小雅·小旻》和以鱼类起兴的《陈风·衡门》、《邶风·新台》、《桧风·匪风》、《曹风·候人》等,都不在《毛传》所标兴诗之列。可知他所谓原始兴象并不限于《毛传》之兴诗,并且他所说的兴象,实际是指被纳入到诗歌中的物象,亦即他所说的“他物”,而这些“物象”所包含的宗教内容构成了“所咏之词”。很明显,他是从物象与情意的关系,或者说是从心与物的关系上来讨论兴的问题的(注:参赵沛霖《兴的源起》“第一章、原始兴象与宗教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这正是汉人解释《毛传》标兴时所忽略的那一方面,也正是朱自清所谓兴的“变义”与《毛传》兴诗之间发生联系的关键。
这样,从汉代学者到朱自清,再到赵沛霖,对《毛传》标兴的认识已在逐渐地突破汉人的局限,而表现出从历史发展和艺术审美的角度重新认识兴的趋向。只是,朱自清的认识还较为朦胧,赵沛霖则并未对《毛传》标兴的问题作正面的、具体的说明。
2
在我们看来,《毛传》标兴在古典诗学的发展中有着为前人所未曾认识到或未曾完全清楚地认识到的重要意义。
对于比、兴在原初意义上的关联,笔者曾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二者最初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只是由于巫术、宗教观念的衰微才使其差别淡化,以致形成兴汇同于比的局面(注:参拙著《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但这种汇同并不意味着“兴义”的完全销亡。这是因为:
第一、兴、比汇同是以特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的。它在春秋赋诗言志和楚辞中初露端倪,至汉代基本完成,而后是以特定的诗学术语——“比兴”,来体现其汇同合一的特征。但越到后来,“比兴”中兴的成分越多,甚至出现名为论比兴而专重于兴,乃至最后以兴取代比兴的现象。因此,从兴演进的全过程看,兴、比汇同,并非“兴义销亡”,而只是兴由隐伏,到再显,并走向独立的生命历程的开始。这一点笔者也已作过详细的讨论(注:参拙著《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此处不赘。
第二、在《诗经》中,兴与比的原始差别并未完全消泯。这不仅因为《诗经》本身的古老,更主要的是因为从混融性的原始巫术、宗教祭祀仪式到巫术、宗教与世俗功利杂糅的古代会盟活动,再到诗歌相对独立的献诗、赋诗活动,赋、比、兴艺术思维早已定型,诗歌的运用与创作都无不被纳入到这样的思维模式之下。只不过一切都是潜在的、不自觉的和未曾得到理论总结的。因此,在后人眼中难于理解的兴诗,越是追溯到早期,它的巫术、宗教的含义就越是确定无疑、人人皆知。当巫术、宗教衰微的文化巨变发生之际,一方面因与古人的巫术、宗教信仰直接联系,兴诗变得越来越神秘、难解,处于行将被人遗忘的境地;一方面,因其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是联结古人巫术、宗教情感与诗歌艺术的媒介,所以又具有令人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的神性。兴诗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下被标出,《毛传》不过照录了这一传统罢了。因而,《诗经》的兴诗原本应当都体现了兴在原始的意义上“与神同一”的特点,但到汉代这一特点已为人们所不理解,不过我们却不能因为后一点而根本否认前一点。赵沛霖先生所钩沉出的以《毛传》兴诗为主的四类原始兴象,正说明《毛传》兴诗确有它不同于比的独特性。比如在他所指出的鸟类兴象中,“与神同一”的特点是在“鸟”与祖先本质同一的前提下,通过人对“鸟”的独特感发来表现的。在这类诗中依然可以看到原型意义上兴不同于比的三个特点,即宗教色彩、主观体验性和三元思维结构(注:参拙著《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由上述两点可知,扎根于上古时代的赋、比、兴三种思维方式,在春秋至汉代的发展历程中,其中的兴因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土壤而趋于中绝的状态,尤其是汉代学者以喻释兴,使兴寄生于比,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但这只是兴的历史的一面。
3
另一方面,巫术、宗教的衰微不是限制而是大大解放了兴,因为兴不同于赋、比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即它的主观体验性,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学乃至古典艺术的美学特征之所在,与赋、比两种思维方式相比,它的发展与成熟不仅需要以诗歌艺术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为前提,还需要以诗歌艺术不再仅仅是政治、道德和伦理教化的附庸为条件。这也就是说,汉人对兴的认识正是与他们以政治教化为旨归的诗学思想相一致的,它与兴这种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规律并不矛盾,虽然兴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成熟较晚,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地位,如果说“比兴”是古典诗学教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兴则是中国古典诗歌纯艺术和审美理论的核心。这在六朝以后的诗学发展中历历可征,对此本文不拟展开,我们在此所要指出的是,六朝以来兴在古典诗学中的核心地位与兴之原型及蕴含于上古巫术、宗教乃至政治实践中的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兴之间的历史关联和血缘承续正是通过《毛传》标兴这一转换环节才得以显现的,换言之,《毛传》标兴决不仅仅只是说明了一个修辞学或诗歌表现手法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兴在其发展源头上与神话、巫术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乃在于,它是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兴,从潜含于实践形态的诗学向突显于理论形态的诗学过渡的起点和标志。我们这样说是基于如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毛传》标兴从名称和指义上联结了此前、此后兴的所有历史,以最简洁的方式显示了兴的历史转换的轨迹。在汉代以前,已有“六诗”之“兴”,专指用诗方法的“兴、道、讽、诵、言、语”之“兴”和专指诗歌功能的“兴、观、群、怨”之“兴”。然而,兴的这三种涵义只适用于实践的和实用的诗学,并且赋、比、兴在这里始终是作为一组概念出现的。《毛传》的“六义”说,显示了赋、比、兴从重运用,重功能的实用《诗》学中开始分化出来的趋势,而《毛传》标兴的意义则在于进一步将兴从赋、比、兴的传统组合中单提出来,为它日后发展为重艺术、美学的诗学概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注:参拙文《赋、比、兴的几组相关概念》.《贵州文史丛刊》.1996.1;《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7。)。
在上述五种兴义中,后两种的文献记录年代较晚,其中“六义”由“六诗”发展而来,可以肯定“六义”之兴的产生晚于前三种兴义。至于《毛传》所标之兴,历来往往被等同于“六义”之兴,其实这两者还是有所差别的。从根源上说,《毛传》标兴也不能与“六诗”无关。如果说“六义”产生于诗歌从重乐到重义的演变过程中,“六义”之兴是从诗体兼用诗方法而演变为诗歌表现方法,那么,《毛传》所标之兴的产生却是以诗歌从宗教神性的束缚逸出为背景,从重视诗篇的宗教目的和宗教情感,发展为指称特定的诗篇和这诗篇中的表现方法,由于不再受到赋、比、兴整体组合的限制,也由于它直接与具体的诗歌联为一体,使它不同于“六义”之兴及上述诸种兴义,而能够为兴的原型特征向兴的艺术、美学特征的转变提供一条通道。但同时,《毛传》所标之兴与其它兴义又都是以兴之原型为现实基础、以兴的思维方式为思维基础的。只不过兴发展至《毛传》标兴,与其原型特征的联系已经很不明显,甚至于线脉将绝,而其艺术、审美的特征在此又只是潜含未显、处于萌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传》标兴只以“兴也”二字点出,实在是以不言言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涵盖了兴在此时复杂微妙的特点。
其二,从《毛传》标兴的诗篇之物象来考察,也可看出兴的原型特征向艺术美学特征过渡的痕迹。
除少数的例外,《毛传》兴诗之物象所包含的巫术、宗教意义今天已无法弄清,其实这一点在汉代已是如此。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不能也不必一一去追究诗中物象的巫术、宗教意义,更不必为它的永久失落而遗憾。相反,倒正是诗中物象之巫术、宗教意义的失落,使诗歌蜕去了巫术、宗教的神圣外衣,而回到了世俗中,当神性的外物不再激发出人的宗教情感,而只是以一般的外物引起人的自然情感,虽然后者可能依然遵循了在前者中已固定化的惯常方式,但它毕竟已向艺术的、审美的国度迈进了极关键的一步。可以说,《毛传》兴诗中可以考知其物象的宗教意义的那一类,证明了兴的原型特征对诗歌的决定作用,而其物象的宗教意义已茫然不可知的那一类,则是兴的原型特征审美泛化的必然结果。这一审美泛化过程最终从宗教性的表情方式中演变出了一般性的抒情方式,《毛传》兴诗都以外物起兴,又都将诗歌情感与这外物紧相联结,置于特定的关系之中,实际上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寓情于物,亦情亦物的抒情范式的雏型。因此,从诗歌物象、诗歌情感及抒情方式上说,《毛传》标兴也同样包含着承源启流、继往开来的深层意义。
要言之,古典诗学在先秦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艺术、美学特征,正是以《毛传》标兴为起点,以“兴”为理论核心,渐次展开并日益完善的。《毛传》标兴在中国诗学史上的理论意义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