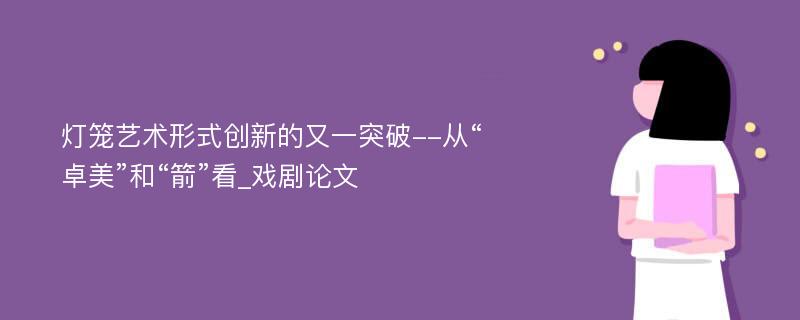
花灯艺术形式革新的又一次突破——《卓梅与阿罗》观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灯论文,形式论文,艺术论文,卓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了玉溪地区花灯团新近创作演出的花灯剧《卓梅与阿罗》之后,精神为之一振,我感到这是花灯艺术形式革新的一次很有意义的突破。
一
从祭社与元宵社火中的歌舞及明清时曲演变而来的戏剧形态的花灯,在艺术形式上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它的歌舞性。花灯在从歌舞形态转化为戏剧形态的初期,节目中有了戏剧情节与戏剧性的人物,然而节目的核心却往往还是歌舞,戏剧情节与人物都将服从于这个核心。歌舞的表现为目的,而情节与人物反倒成为手段。比如《打花鼓》,剧中的公爷与花鼓佬、花鼓婆之间,花鼓佬与花鼓婆之间的冲突,都是为了表现花鼓演唱。《补缸》中的县官要王大娘一道跳“边鱼抢水”才算判了案子,也因为这个节目的核心就是为了表现跳花灯。《霸王下山》也有类似情况,被捉上山的一对青年男女,什么办法都不能打动霸王的心,让他释放他们下山,而当他们唱了调子、歌舞一番之后,马上就被释放了。这些都说明歌舞在花灯戏中的特殊地位。然而这种情况,也限制了花灯的戏剧化,使花灯在艺术形式上歌舞游离于戏剧情节与人物之外。
玉溪“新灯”的兴起,大大促进了花灯的戏剧化,它把节目的核心从歌舞的表现转到戏剧的表现,即转到表现戏剧冲突上来,歌舞成为手段而不再是目的,这是新灯的一大功劳。然而它也有缺陷,由于历史的局限,那时的花灯艺人包括以后的王旦东他们,不可能十分自觉地进行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包括花灯的戏剧与歌舞的交溶。他们在吸取中国古典戏曲为京剧滇剧的艺术形式时缺乏批判与扬弃,缺乏如何将其与花灯之所长交溶的探索,因而使一些剧目丧失花灯原有的韵味,花灯的戏剧与歌舞的溶合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花灯在艺术形式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贴近生活。作为农民与市民艺术的花灯,它不仅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与心态,而且在形式上也反映了、表现了下层人民的艺术趣味。它的语言民歌化,通俗易懂,质朴自然,常用比兴。它的喜剧闹剧色彩浓郁,节奏轻快跳荡。然而它也有庸俗也有糟粕,有生活的散漫与拖沓。
花灯在艺术形式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灵活性。花灯在艺术形式上没有严格的程式,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的演唱,可能同一只曲调不同的艺人有不同的唱法,甚至同一个艺人唱同一只曲调在不同时间也有不同唱法。花灯的舞台形式历来缺乏规范,灵活性不与严格的规范相结合就容易成为随意性,导至花灯舞台艺术形式的不够规范与简陋。
传统花灯艺术形式的这些特点,包括其所长与所短,如何继承与革新,就有待于后来者了。
二
建国以后,花灯面对新的生活与新的群众,不仅在剧目内容上需要革新,在艺术形式上也需要革新。经过从五十年代初期、中期的不断探索,到五十年代末期,这种探索终于成熟而结出了硕果。这一探索的成果,体现于《探干妹》《喜中喜》《刘成看菜》《游春》《闹渡》《老海休妻》等一批节目及《依莱汗》《红葫芦》《孔雀公主》等一批大戏。那么,这一次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形式革新的主要目的。一切形式手段,唱、做、念、舞都为这个目的服务,把传统花灯中只有类型化人物而缺少个性化人物的缺点纠正过来。在塑造好人物形象这个前提下,尽可能继承花灯传统形式之所长而力避其所短。但对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剧目的花灯风格作不同的要求,比如对花灯歌舞花灯小戏,就要求传统风格浓一些,歌舞性、喜剧性强一些,而对大戏则不作同样的强求。同是大戏,就不要求《依莱汗》的歌舞性与《红葫芦》《孔雀公主》等同,而只要求其有花灯的神韵。同是演员,对史宝凤就要求她革新的步子迈得大些,对袁留安、蒋丽华,则要求他们传统的味道浓一些。只有把中心定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一切包装才有目的,而人物形象要塑造好,就必需有好的形式的包装。
第二,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花灯的艺术形式。传统花灯的艺术形式,在历史进程中也在革新,“新灯”就是一次较大的革新。但是它们的革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个根本的弱点,这就是革新的自发性,因而在视角上基本是封闭的、局部的、枝节的。建国后就不同了,我们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继承与革新,是自觉的、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的、开放的革新。虽然有若干干扰,而历史总是证明革新的不可抗拒。因为是自觉的革新,所以有导演制度的建立,有组织史宝凤、袁留安、蒋丽华等演员向刘美娟、夏韵秋、常香玉、盖叫天等戏曲名演员及向北京音乐教学专家学习的安排。有送舞美人员石宏、朱晓华到上海戏剧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举措,有在剧本创作上大胆引入民族歌剧、电影创作手法的举动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花灯具备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本领。
第三,重视舞台艺术的建设。传统花灯本来是社火艺术,是“过街灯”、“走老丑”,以后发展为“团场灯”,从行进中演出到在广场演出,它的包装形式是灯采、手巾扇子、不断地崴等等,没有舞台艺术。等到进了灯棚,以后进了茶室、戏院,有了舞台,开始向京滇戏学了些舞台艺术建设,然而因为条件限制,因陋就简,始终处于半专业半业余状态。
建国后花灯除了下乡下厂外,还经常在城市剧场演出,因此,从舞台景物造型到人物造型,从表演、乐队到导演的舞台设计,都大大有所改进,终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舞台艺术形式。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改革,形成了花灯艺术形式革新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使花灯面目一新,巩固了老观众,获得了新观众,特别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
三
改革开放特别是80年代以来,花灯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在各种艺术形式的竞争下,也堕入不景气的深谷。除开外部条件需要改善之外,就花灯自身而言,又面临一次新的改革。我以为这次新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深刻地、真实地反映这一时代及这一时代中人物的新的生活与冲突。这不仅是个内容问题,也是个艺术形式问题。
许多花灯工作者在近年来对花灯艺术形式的又一次革新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探索,尤其是在《淡淡的茴香花》《情与爱》《金银花·竹篱笆》《风雪马樱花》《斩娥》《净土》《小姨妹过河》等剧中的探索。探索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缺乏理论性的总结,然而它却成为一种无形的历史积累。它和这些年来省外、国外、书本上、舞台、屏幕上传播的新的艺术信息,刺激着那些敏感的花灯工作者的神经,这种刺激加上自己的胆识,玉溪花灯团的朋友们就在《卓梅与阿罗》一剧中,在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方面,取得建国以来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这一突破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集中表现在《卓梅与阿罗》的观赏性,适合于今天这个时代,适合于今天的许多观众的审美水平与审美趣味。具体说来,这一观赏性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任何艺术作品都追求作品的和谐,然而并不一定都能达到这个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花灯舞台剧,包括一些比较优秀的剧目,我常常感到内容大于形式。究其原因,内容变了而形式依然是老一套不能辞其咎。《卓梅与阿罗》的编剧良华从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作品中选择《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花灯是聪明的,因为它居于莎士比亚第一时期的作品。莎士比亚研究者把他在1590—1600写作的作品列入第一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理想,特别是他的那些描写爱情、婚姻、友谊的作品,不仅情节丰富生动,而且生活气息浓郁,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这时,莎士比亚对现实的认识还不像以后那样深化,还没有把笔力着重放在对社会的批判。
写于1595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却有喜剧气氛;虽然主人翁的爱情以悲剧结束,封建贵族间的隔阂却因此得到消除。因此英国诗人柯尔律治说这个剧本“处处是青春与春天”。花灯正适合于表现这种题材。产生于欢乐气氛与期望美好之中的花灯,是下层群众的欢乐的春天的艺术,它负担宏伟壮阔的题材就很吃力,比如要改编《哈姆雷特》给它演,那就不知比《罗密欧与朱丽叶》要困难多少倍。良华选择题材恰当,就便于花灯形式的革新,是他的聪明处。他又把剧本改为彝族生活,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彝族歌舞,彝族风习,彝族装扮,无不给形式的设计以方便,因而便于与内容达到和谐。
二、传统与外来艺术形式的嫁接。戏曲传统艺术形式给当代观众以历史感,却缺少些时代气息;给熟悉戏曲的中老年观众以亲切,却给青年及不熟悉戏曲者以隔膜。因此,花灯的革新,就必需考虑传统形式的改革。改革,就包含新的艺术形式、艺术因素的吸取。这既有观念问题,又有能力问题。我们见过一些缺乏章法与传统神韵的改革,更多地看到一些陈旧的样式。《卓梅与阿罗》在将花灯音乐舞蹈与彝族音乐舞蹈嫁接在一起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而引入通俗唱法也恰如其份,也值得称道。开头结尾的舞蹈也很美,是花灯又不是花灯。齐白石论绘画与生活的关系,说:当在“似与不似之间”。其实,今人创作的花灯样式,如与传统花灯样式比较,也可以说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不改革传统不吸取新形式是不行的,当然乱改革乱吸取也是不行的。而我觉得封闭保守的观念及虽有改革之心而缺改革之“能”的情况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新思路、新方法、新技巧。花灯艺术形式的改革,必须有新思路、新方法、新技巧。我很高兴看到《卓梅与阿罗》所体现的舞台新气象,体现于马雪峰的舞美设计,陈明玉、马丽的舞蹈设计,汤亚青的化妆设计,李鸿源等的音乐设计及演员们的表演,在导演严跃龙、何瑞芬的统一构思中形成一个整体,给人一种新鲜气息。我想特别提出马丽的几次通俗唱法的演唱及戏的末尾坟场中平台的运用及卓梅在舞队中的穿行演唱,是一种新思路新方法的体现。看来,我们的一些花灯工作者已经大大打开了思路,扩张了想像力,拓展了处理舞台空间的自由度,这是非常可喜的。艺术,容不得想像力的萎缩。创造,来源于作家主体对客体深刻感受基础上想像力的扩张。我们既要学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入现实的本质,又要从浪漫主义及现代派艺术创作方法吸取营养,以丰富我们的想像力、创造力。
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必需有花灯各部门艺术人员艺术素质、技术技巧的提高作为保证。在《卓梅与阿罗》的演出中,扮演卓梅的杨丽琼的演唱技巧就有提高。她原来的声音柔美,这次唱了一段近于悲壮的歌曲,显示了她的音域比以前宽阔,表现力比以前加强了。如果她在音区的衔接,对于不同的情绪的不同曲调的掌握能更加自如,那么她在演唱方面的表现力还会加强。扮演阿罗的沈建南,作为一个青年演员,表演上已比从前有所进步。他吃亏在音色不够美,虽由于天赋,更在于缺乏科学发声方法的锻炼。如果加强学习,天赋的缺陷还是可以弥补的。
《卓梅与阿罗》在艺术形式方面的革新令人高兴,感到花灯的改革大有可为。然而我宁可把这个戏的成绩看作整个花灯艺术形式革新的新的起点而不是顶点,而且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并不是只有一种样式而是应该有多种样式。目前这个戏也还有些弱点,戏的中间部分较弱,演员阵容还可加强,某些技术环节还可提高。但我们已可从这个戏提出花灯艺术形式革新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先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的重点应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剧中主要角色的唱念做舞的设计。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克服太随意太缺乏技巧这个毛病。古典戏曲是在程式中取得自由,而花灯演员的表演是太缺乏规范。我们不是要创造一套新的花灯表演程式,但我们要明白,不在前人创造的高级范式的基础之上,是很难有高层次的创造的,花灯至今没有表演流派,这就是个重要原因。我主张要给演员出难题,这次我听杨丽琼的唱,有一个地方我以为她会出现花腔,结果没有,我很遗憾。
另一个方面是一定要重视戏的整体设计,重视包装,不要把形式置于主题、内容之外和之下。
其次,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牵涉到方方面面,牵涉到花灯工作者素质的提高,学校的教学等等,希望继《卓梅与阿罗》之后,出现更多有看头有听头有想头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花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