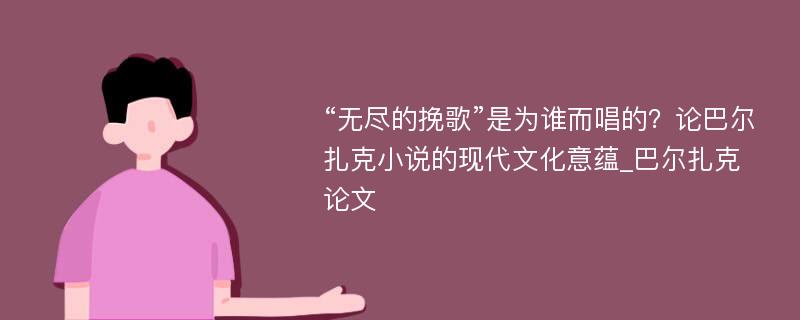
“无尽挽歌”为谁唱?——论巴尔扎克小说的现代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尔扎克论文,意蕴论文,挽歌论文,为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人类生命本体的忧思录。他通过艺术性的集中和夸张把握了金钱时代人性被物化的本质特征,以一种象征隐喻的模式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悖谬现象,为二十世纪文学奏响了现代人异化与悖谬的前奏曲。小说在对人的认识上开始与近代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分离,认为人类的理性和善的力量远不如情欲与恶的力量强大,而且情欲与恶的力量成了被肯定甚至被赞美的“英雄”,这种关于“人”的文化观念超越传统而具有现代化意味。巴尔扎克借小说抒写了自己为人类天性的失落而发的满腔忧情,其文化人格又使他割不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怀恋——希望失落的人性复归,因而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关键词 巴尔扎克 异化 悖谬 情欲 恶
文艺复兴时期的本·琼森说,莎士比亚不只属于一个时代,他属于所有的世纪。其实,真正堪称“大师”的文学家都属于所有的世纪,因为,他们所关注的往往不只是一个时代,他们胸怀的是整个世界,他们也就活在所有世纪的人的心中。巴尔扎克就是这样的艺术大师。他的小说以广阔、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著称,他自称是19世纪法国历史的“书记员”。他的《人间喜剧》也确实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俗史。然而,当我们从深层文化意蕴的角度去看这部人类文学的巨著时不难发现,巴尔扎克对社会与人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还穿透了社会—历史的外壳,剖析人类的生命本体,寻找人类社会深层的破坏力与创造力,因而,他的小说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同时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化哲学意蕴。
一、在异化—悖谬文学母题的关联点上
关于“异化”,虽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与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异化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它作为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现象,其基本内涵是有同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不管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还是在马克思和佛洛姆那里,异化都是指:人的各种有目的活动的总和形成一种盲目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人自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因而,人通过自身的活动反而变得与自身疏远、隔离、陌生了。所以,“异化”也即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悖谬。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根本目的是寻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然而,直到巴尔扎克所处的那个时代,甚至到今天,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自身的种种局限性,人类依然未能完全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避免受异己力量的捉弄,人类也就未能摆脱被异化的威胁,总是处在发展与失落的悖谬之中。不同的时代,异化和悖谬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文学是人学”,它的最高宗旨是实现人的精神与审美的自由、发展与解放。文学总是以审美的形式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的生存状况。它不仅反映人的自由与争自由的外在形态,更关注并反映人因丧失自由所致的异化与反异化的精神、情感与心理状态,表现处于悖谬中的人的尴尬、迷惘与困惑。只要生活本身存在着异化与悖谬,文学就必然表现这种异化与悖谬。
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就以神话隐喻的方式表现了人的这种悲剧性命运。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表现了人类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第一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展,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人的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说明人类从“那种前人类生活的无意识存在升华到了人的水平”。[①]然而,普罗米修斯正因为盗火给人类,才受到了宙斯和命运女神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受痛苦的折磨。空前的胜利与巨大的痛苦成了一种共生现象,这说明人类的痛苦是伴随着第一次与异己力量作斗争并取得胜利而来的,人类向文明迈进时,异己力量就给以报复性吞噬。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是关于人类异化与悖谬的象征性预言。在西方社会进入到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后,基督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被理解为人依赖上帝拯救自身而免遭地狱之灾的历史。上帝原本是人的理性精神的象征,人创造上帝的初衷是扼止人自身的“原欲”以有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随着上帝“权力”的畸形膨胀,人成了上帝的奴仆,丧失了自主性,人由于神性的一味附着导致人性的失落。到了中世纪的晚期,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悖谬处境,并开始了对上帝这一异己力量的反抗。较为充分地表现人被上帝异化和人的反抗的是但丁的《神曲》。《神曲》中,人的痛苦呻吟与默默忍受,便是被上帝异化的中世纪的人的现实图画。不过,在《神曲》的“地狱”中,主持对邪恶的审判的“上帝”身上已经渗透了现实中人的主体意识,而不完全是教会宣扬的那个上帝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曲折地表现出了对宗教异化的反抗。至于“炼狱”与“天堂”则更充溢着人性的内容,表现人被异化的痛苦与对异化的反抗是《神曲》两重性的内在原因。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方面表现人在冲破宗教的枷锁后,高昂地追求人性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所面临的财富与权力的新的异化危机。说明了文明的进步,新的自由获得的同时,新的异化新的失落也接踵而至。哈姆莱特的永恒困惑便是人对自身发展与失落的迷惘与困惑。17、18世纪,西方社会进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后,人的异化集中体现为人被“物化”的现象,而人的“物化”又具体表现为被金钱和财富所主宰。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中的鲁滨逊身上,表现的是以占有财富的多寡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驱使下,“物”将他的自然情感从心灵中挤走了。小说在客观上表现了人被“物化”的悲剧,但无论是笛福还是鲁滨逊,都不曾意识到在占有了物的同时又失落了自我的悖谬结果。因而小说对人在新的文明背景下的异化与悖谬缺乏深层把握,也缺少对异化的反抗精神。只有到了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人类的这一悲剧性命运才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表现。
在巴尔扎克小说的艺术世界里,真正的“英雄”是灵魂交给了金钱上帝的人,被金钱煽起的情欲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他的小说为人们揭示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物化的历史悲剧,巴尔扎克也由此探索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
葛朗台老爹一生只恋着金钱,从来是认钱不认人。侄儿查理为父亲的破产自杀而哭得死去活来,他居然说:“这年轻人(指查理)是个无用之辈,在他心里的是死人,不是钱。”在葛朗台看来,查理应该伤心的不是父亲的死,而是他不仅从此成了一贫如洗的破落子弟,而且还得为死去的父亲负四百万法郎的债。人死是小事,失去财富是大事。妻子要自杀,葛朗台原本无所谓,而一想到这会使他失去大笔遗产,心里就发慌。他临死时最依恋的不是女儿,而是将由女儿继承的那笔财产,并吩咐女儿要好好代为管理,等到她也灵魂升天后到天国与他交帐。葛朗台把爱奉献给了金钱,而把冷漠无情留给了自己,并通过自己又施予他人,于是,他手里的财产剧增,成了索漠城经济上的主人,也成了家庭中的绝对权威。高老头的女儿们领受了父亲的金钱而抛掉父爱,踩着父亲的尸体登上了巴黎上流社会的高层。拉斯蒂涅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受金钱腐蚀而人性丧失的过程,他在经过了人性与物性的反复较量,流尽了年青人最后那点同情的眼泪后,成了所向披靡的强者,建构他的“英雄”性格骨架的是对金钱权位的无穷欲望,而不是人类高尚的情操。伏脱冷习惯于谋财害命,不惜弄脏双手,以毒攻毒,大刀阔斧地杀入芸芸众生,掠取金钱,最后大功告成,上升为暴发户。而高老头这样在发了横财后忘不了一缕发自人性的温情则成了饿死荒郊的野狗;象鲍赛昂夫人那样,企图寻找发自内心的丝丝恋情,则身价一跌再跌,从辉煌的社交界王后沦为乡村“弃妇”;象欧也妮那样痴心地保持“童贞”,却孤独地处身于人性与情感的荒漠之中,成了虽生犹死的金钱看护人。纽沁根在金钱的战争中,用无数人的尸骨垒起了他银行家的高楼大厦;吕西安出卖灵魂而得以平步青云;大卫为保持灵魂的纯洁却身败名裂、锒铛入狱……
上述种种,都告诉人们,谁能尽快地将灵魂交出去,把金钱的上帝请进来,谁就能尽早地成为“英雄”。巴尔扎克的这些描写应该说不无艺术夸张的成份,但这恰如透过放大镜观察微生物,巴尔扎克在这艺术性的集中和夸张中把握了金钱时代人性被物化的本质特征,而且,他的小说还以一种象征隐喻的模式表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悖谬现象:历史的进步是靠财富的创造来推动的,而创造财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性的失落;为金钱所点燃的情欲驱动着人们去疯狂,忘我地积聚财富,而情欲之火又烤干了人性的脉脉温情,也耗尽了追求者自身的精力与生命;人类在与物质世界的不懈斗争中不断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文明,而与之抗衡的对象又不断吞噬着人类,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在人类发展进程的“对物的依赖”阶段尤其如此,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所以,巴尔扎克小说所表现的人的异化与悖谬,虽然与自古希腊神话以来的西方文学有相同之处,前者是后者的延续,但巴尔扎克表现的是“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异化与悖谬,这种异化与悖谬集中体现在人与物之间的畸形关系上,巴尔扎克由此思考与探索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巴尔扎克小说不仅深化了自古希腊神话开始的异化与悖谬的主题,而且,也为二十世纪文学奏响了现代人异化与悖谬的前奏曲。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表现“物”对人的异化更为全面而深刻,对人的悖谬的把握也更透彻深入。在现代派文学中,“物”的含义较之巴尔扎克的小说更为宽泛而抽象,“物”被扩大为包括金钱、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等客观存在物在内的整个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社会形态,人与物的对立关系也就泛化为人与除精神世界之外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对立。而且,巴尔扎克小说在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着重显示物对人的腐蚀和人对来自物的异化的抵御和不接受,而现代派文学着重表现人在物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恐惧感,人已被物质世界抛弃,人类处在一个难以理喻、无法把握和解释的陌生世界,而且人自己已蜕变成了物,世界是荒诞的,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在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已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象征着被物质文明高度挤压下痛苦地寻找着自身归属的现代人。他的悲剧说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使个体的人无法存在。在尤奈斯库的《新房客》中,我们看到的是物威胁着人的生存,整个世界变成了物的奴仆。劳伦斯小说展示了现代机械文明如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的两性关系变得畸形病态。显然,现代派文学表现的是比巴尔扎克小说更深重得多的物对人的异化和人的悖谬现象。但现代派作家对异化与悖谬的广泛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无疑从巴尔扎克那里得到影响和启示。
二、对“恶”的崇拜与恐惧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社会是个人私欲的竞技场,人类的恶欲展现出了巨大的驱动力。这样的描写是不无超时代意义的。这种描写基于巴尔扎克对人类历史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创造力与破坏力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丹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是这样评述巴尔扎克世界观的:“世界是什么?什么是它的动力?在自然主义者巴尔扎克的眼里,情欲和利己主义是世界的动力。它们往往以优雅的姿态出现,伪善把它们的真实面目隐蔽起来,浅薄借用动听的名词将它们装璜起来。但是归根到底,十个行动有九个是发自于利己观念。对此,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极为混乱的世界里,每个人相信的是他自己,这个世界里的‘动物’不断地想的是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使自己生存下去。这些‘动物’维持着这个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把社会看作利己主义竞技场的原因。”[②]丹纳对巴尔扎克的这个评述是十分准确的。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们在以拥有财富的多寡作为人的价值标准的观念驱使下,“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的竞争”。[③]金钱与财富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作用,人类的私欲也就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必然现象。但是,这种新的价值观念严重践踏了平等、博爱的信条,毁坏了西方社会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道德体系。强有力的私欲驱使人们创造财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自由资本主义这个血与火的历史阶段,私欲虽在道德伦理观上以恶的形式出现,但他却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的私欲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④]也如黑格尔所说:“假如没有情欲,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成功。”[⑤]对恶作出此种自觉的认识,是19世纪以来的人才能做到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是不无现代意义的。作为19世纪上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也以自己的方式对恶与私欲作了类似的理解,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表现。
巴尔扎克看到,历史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而历史的发展却以私欲为动力,那么恶的存在就有其历史合理性:既然把魔鬼当上帝的“英雄”是社会的强者,卑劣的私欲可以推动历史的进程,人类社会不过是个人私欲的竞技场,那么,私欲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对“英雄”、对金钱与私欲之魔力给予了赞美,这意味着对人类恶、人的私欲的肯定。巴尔扎克并不认为人性原本就是恶的,而是认为现今这个腐化堕落成风的社会中,“纯洁善良是存在不了几天的”,既然私欲是行为动机的内驱力,达到欲望高峰的人就是时代的“英雄”,恶可以雄居善的神圣宝座,人们也就犹如飞蛾扑灯,从恶如流,善良天性的失落是必然的。拉斯蒂涅原本不是那么纯洁善良吗?然而,金钱、权力的诱惑勾起了他强烈的欲望,经过内心深处善与恶的搏斗,恶占居了他的整个心灵。于是,他宁肯听从魔鬼的使唤走向罪恶的深渊,也不愿为了上帝,为了那点可怜的人性之善而熄灭情欲之火。他最后对大学生皮安训说:“朋友,你能克制欲望,就走你平凡的路吧!我是入了地狱而且还得留在地狱。”他决定以恶为武器,与社会拼一拼,那非凡的气概,恰如视死如归的古罗马斗士!巴尔扎克的善恶论,并不源于基督教。他认为,“人性非恶也非善,人生出来只有本能和能力;与卢梭所说的相反,社会不仅没有败坏人心,反而使人趋于完善,使人变得更好;可是利欲却同时过分地发展他的不良倾向。”[⑥]所以,巴尔扎克认为人性趋恶。趋恶之动力在于私欲;这种趋恶倾向在金钱时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可抗拒性。可见,巴尔扎克小说所表现的性恶论,体现了对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的观念的崭新认识。
人文主义虽然从上帝那里取回了人,人的个性获得了自由与解放,人文主义思想中的“人”却又有浓重的上帝的成份。在很大程度上,人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被人自己放到上帝的位置上,上帝成了人自己。这个“人”不仅具有上帝那样的力量,更具有上帝那样的博爱和理智的秉赋。“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成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中旷日持久、深入人心的信念。人因其具有上帝那样的理性和善,因而就能自觉克制人自身的情欲,善的力量必然战胜恶的力量,人类历史也被理解为善战胜恶的必然发展过程。巴尔扎克的小说固然还表现了近代基督教——人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但在对人的认识上,却开始与近代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分离。在他的小说中,人类的理性和善的力量远不如情欲与恶的力量来得强大,而且,情欲与恶成了被肯定甚至被赞美的“英雄”。这种关于“人”的文化观念是超越传统而具有现代意味的。
不过,巴尔扎克毕竟还处在十九世纪的中期,他的文化人格中的传统成份仍是十分浓重的。他的小说在对人的私欲与恶表现出赞美之情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对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他的《人间喜剧》展现了“遍地腐化堕落”的情景。“在煊红的光亮下,无数扬眉怒目、狰狞可怕的人形被强烈地烘托出来,比真的面貌还要神气,有活力,有生气,在这人群里蠕动着一片光怪陆离的幻景,由金钱、科学、艺术、光荣和权力所缔造成功的梦境,一场广阔无垠惊心动魄的噩梦。”[⑦]这不仅仅是巴尔扎克眼中当时的法国社会,也是他给人类描绘的为人的私欲所创造的那个未来的社会前景。这个情景所昭示的不是人类的光明与希望,而是危机与死亡。由此,巴尔扎克又发出了人性恶的哀鸣。拉斯蒂涅等“英雄”们的悲剧,也正是巴尔扎克所理解和揭示的人类的悲剧:人类在创造自己中又毁灭自己。因而,巴尔扎克的小说不无悲观情调,他的文化价值观念是矛盾的,巴尔扎克小说中表现的这种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思考,在二十世纪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和深化,他的小说的悲剧意识也为现代作家所发扬光大。不过,巴尔扎克对现实生活和人类前途的态度,较之现代作家多了一份热情与执著,而少了一份冷漠与悲观。因为巴尔扎克并没象大多数现代作家那样将人看作非理性的动物,他认为人曾经是善的,只是到了金钱时代,人性被吞噬了。他肯定恶,那只是因为恶是被社会发展所认可了的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和无法抗拒的存在。他在情感的深处鄙视和痛恨这种存在,又无可奈何地承认它并一定程度上与之认同。他承认社会恶这个事实,又为之而恐惧,于是借小说发出了“这个世界将要死亡”的惊呼;他在赞美“英雄”们的雄才大略的同时,又不无谴责之意,那么,巴尔扎克是否自甘陷身于这矛盾之中而无意自我拯救和寻找解脱与安慰了呢?
三、“无尽挽歌”为谁唱?
从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因而常常站在本阶级的立场观察与分析社会,但他同时又有很浓重的封建贵族意识。他追求贵族式的虚荣、渴慕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不断地追逐贵妇人等等。他对1830年七月革命后的金融大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颇为不满,对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大资产阶级不怀好意,对金钱统治下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也是十分厌恶的。所以,他希望通过君主政体的力量来扼制金融大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并希望借宗教的理性力量抑止人欲的泛滥,而对贵族阶级则颇有好感。1871年他参加了保王党,成了一个正统派。尽管他也知道贵族阶级在资产阶级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他对资产阶级的生命力也不无赞美,但是,他的同情依然在贵族阶级一边。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对资产阶级野心家、暴发户的谴责多于赞美,对贵族阶级的同情多于批评。正如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所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⑧]恩格斯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作出如此的评价,无疑是客观正确的。巴尔扎克对没落的贵族阶级的同情不能不说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是落后甚至反动的。
然而,巴尔扎克是一位文学家,他的世界观和阶级观念,他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理想固然会制约他的创作,因而他的小说也不能不具有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价值。但是,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对社会和人作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考察,而是一种审美评价。文学作为人学,它也不是对人作单一的阶级分析,文学除了表现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内容之外,还以象征隐喻的方式,“将世俗生活神话化”,以“揭示人类天性和人类共有的心理及玄学之本原。”[⑨]因此,从文化人类学和艺术的神话诗学的角度看,巴尔扎克对贵族形象和资产阶级野心家与暴发户形象的描写,还寄寓了作者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深层思索,因而也隐含了深层文化意蕴。
巴尔扎克看到,处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私欲和人类的恶以空前凶猛的、不可抗拒之势驱动着人的行动,人的理性和人性的善缺乏生存力。在他的小说中,人的私欲和人类恶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往往是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和野心家,所以作者对他们不无赞美又强烈谴责,既有历史的认同又为之深感恐惧,而人的理性和人类的善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则往往是贵族形象,他们显得“高雅”而“人道”,因而作者对他们不无批评又寄于深切的同情,对他们既有历史的否定又有割不断的依恋之情,从文学的神话隐喻特性上看,资产阶级暴发户和野心家形象乃人的私欲和人类恶的象征,贵族形象乃人的理性和人类善的象征,因此,作者对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矛盾心态,便是对私欲和恶的矛盾心理的表现,对贵族形象的同情与惋惜便是对人性善的依恋。巴尔扎克虽然对私欲与恶有认同甚至有赞美,但他毕竟不愿意看到一个私欲和恶统治下的人类世界;而私欲和恶又有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人类理性和善的失落也成必然趋势,他的忧思与恐惧就油然而生。巴尔扎克对历史的观照是有其深刻的一面的,他在小说中揭示了人性的失落和人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现象。面对这一历史现象,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人类发展前景的展望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巴尔扎克则借小说抒写了自己为人类天性的失落而发的满腔忧情,他恐惧恶的横行的社会的到来,对人类前途感到悲观与失望,他的矛盾的文化人格也决定了他在无可奈何之际,仍割不断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怀恋——希望失落的人性复归。他的小说对贵族人物的惋惜,确实可以认为是对贵族阶级的同情。因为,历史的发展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新的文明注定以人性的失落为代价,并且将要成为人类进步的新枷锁,每逢此时,人类就萌发出思古之幽情,希望回归到旧时代。但从深层文化意蕴上看,巴尔扎克通过这些象征理性和善的贵族形象,寄托了他对人性复归的一丝希望。所以,巴尔扎克的那“一曲无尽的挽歌”,不仅是唱给当时没落了的贵族阶级的,更是唱给被异化、人性失落的人类自身的。这种对人性善的呼唤与眷恋使巴尔扎克描绘的“遍地腐化堕落的”世界透出了一线光明,他的小说也不至于象现代派作品那样让读者感到极度的悲观与绝望。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巴尔扎克的愿望显然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作为文学家,他对人类的思考与审美的观照却是深刻的。由此可以说《人间喜剧》是人类生命本体的忧思录,可以说,巴尔扎克的这“一曲挽歌”从古唱到今,它依然在现代文学中回响;无非其中增加了更多冷漠与绝望的音符而已。这不正是巴尔扎克小说对社会批判和传统文化的超越吗?
注释:
①〔德〕埃里希·佛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②⑦〔法〕丹纳《巴尔扎克论》,伦敦,1906年英文版,第218—220、111页。
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0页。
⑤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该译本中的“热情”应译为“情欲”。
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转引自《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⑨〔苏〕叶·英·梅列斯全《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页。
标签:巴尔扎克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人性论文; 神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