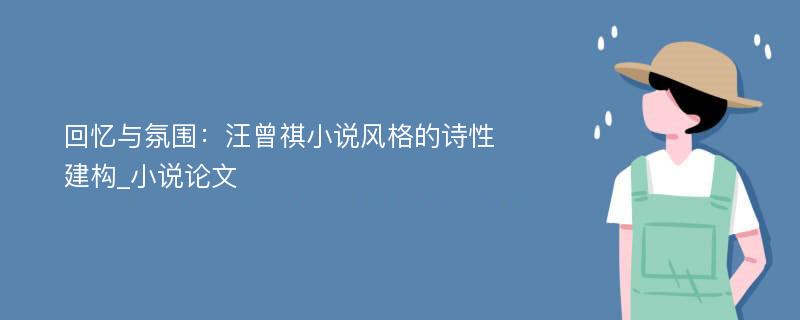
回忆和氛围: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文体论文,氛围论文,汪曾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2-0065-05
诗意建构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客观描写对象的一种心灵化的提升及心灵化的传达,是作家心灵波动与自然人生节律的协调统一所产生的律动的结晶,是作家创作中的诗意追求。也就是说,只有作家心中存有诗意,他才能用心灵去捕捉并撷取美,才能将其在心灵的点拨之下酝酿升华,才能在笔端形成诗意的弥漫。由于文学形态的不同,诗意建构的表现形态也有所不同,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有适应于自身特质的表现形态。
一、“小说是回忆”的诗意生成
回忆作为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诗学范畴,在西方源远流长:海德格尔认为回忆是文学创作的根源:“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于回忆女神的孕育——回忆,回过头来回忆思已思过的东西”[1],他把“思”与“诗”联系起来:回忆就是告别尘世,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叔本华把回忆看作纯粹无意识状态中静观美之本体途径:“回忆到过去和遥远的情景,就好像是一个失去的乐园又在我们面前飘过似的。”[2] 与此类似,尼采认为诗通过回忆唤回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激流:“激起对醉的全部微妙的回忆——有一种特别的记忆潜入这种状态,一个遥远的稍纵即逝的感觉世界回到这里来了。”[3] 马尔库赛认为,真正的乌托邦建立在回忆往事的基础之上;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更为重视回忆在艺术审美中的作用,他认为回忆是真正的仅有的美的源泉,“被现实的无可弥补的缺陷所阻滞的期待可以在过去的事件中得到实现。这时回忆的净化力量有可能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弥补经验的缺憾。”[4] 这些美学家以纯客观的态度回忆往昔,过去的情景如乐园般充满美感。不管是把回忆作为一种诗化力量——“回忆之诗”,抑或是作为一种理性观照视角——“回忆之思”,美学家们都把艺术的本性同“回忆”这种富有原始或深层意味的审美体验联系起来。
汪曾祺对回忆之于小说有独到的诠释:
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5]。
我们的阅读经验中,那些优秀的作品总是使我们沉醉于心醉神迷的瞬间:那一刻,作为审美主体,我们似乎接近了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倾听着他们内心的诉说;超越了我们和现实之间的帷幕,洞悉了平常被遮蔽着的人生的深层奥秘,这一切其实都来自于作者与我们的一种共同人生体验——回忆。就创作生发而言,作家是生活在一个被心灵和审美之光照亮的世界中,虽然回忆总是延绵的,杂乱的,感性化的,但这感性的东西却由于时间的距离而心灵化了,当作家在强大的情绪张力下打开回忆之门时,他把过去及过去的人和事作为一种审美图像纳入自己的深度体验。同时,作家当下的感受、体验也会不断地膨胀并渗入回忆文体的语境,使回忆与当下经验产生重叠反差,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这样小说就带着作家浓重的情感色彩,将过去、现在、未来糅合在一起,以审美的新质袒现诗的光晕。汪曾祺小说中,回忆不仅成为取材的基本纲领,而且成为审美创造的基本原则。他一直在创作中努力让小说走向诗学的审美视阈,以独特的形式表达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回忆”是汪曾祺借来在艺术创造中完成对存在超越的一条途径。回忆已经内化为作者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并直接影响了小说文体的生成。透过汪曾祺为我们提供的大量回忆性文本,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回忆机制对其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影响。
文学创作不是摄像,由生活素材到创作题材可以说都是经过了回忆的。但汪曾祺的“回忆”又有着特定的涵义:一是指旧时代的题材,一是指对生活的醇酿。在《谈谈风俗画》中,作者说:“记风俗多少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带抒情性,并不流于伤感”[6]。汪曾祺的“回忆题材论”,意在强调生活与创作之间的沉积过程,以区别于那些临时现炒、热腾腾还带着体温的题材。回忆是比记忆更带上个人生命的心理活动,它所获得的表象不同于一般的感知,它是陈年老酒。“一个小说家第一应该有生活,第二是敢写生活,第三是会写生活。”[7]“回忆”正是汪曾祺写生活的一种方式。回忆是允许变形的。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较大,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鲁迅十分相似。鲁迅也很注重“回忆”性的题材,他的《朝花夕拾》纯是回忆之作,甚至他的(呐喊)的“由来”也是回忆。但由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的不同,鲁迅的回忆中常常带有“血丝”,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冷峻描摹。而汪曾祺的回忆中,人世的寂寞、辛苦和混杂其中的温暖、超脱,却表现得醇厚而精微,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抒情刻画。因此,一个作家的回忆是他的艺术感受和艺术素质的一个方面,也是他认识世界的艺术方法之一。回忆不仅仅是一种文体选择,也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80年代作品描写的大部分就是存储于记忆中的故乡风物和人事,但这些风物和人事又都不是其原本和自然态,而是凭借想象去抓摸、打捞的,故乡风物和人事在心中存留着印象主义式的心灵感觉,如“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鸡鸭名家》)又如“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茵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岁寒三友》)由于时空迁移造成的心理距离和情感的孵化作用,过去人与事的原色就打上了一层稠浓的情感印迹,那些本属平庸的枝枝叶叶也显得色味弥足,昔日身经的痛苦和磨折也似乎带有一种感伤的甜蜜。如“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这看似实写,实际是想象中故乡老人的独居生活。作者仿佛要从记忆中凸现出来,从故乡收字纸老人的日常生活中寻回往日温馨浪漫的农家生活和自己甜蜜的心境。
“小说是回忆”的叙事立场,包含了汪曾祺对小说与生活关系的独特看法。小说写的是生活,但小说与生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近距离的观照还是远距离的审视?不同的认识会导致不同的创作姿态。汪曾祺显然是选取一种远距离的审视态度,他是有意识地让时间来沉淀生活,除净火气,节制感情。回忆因为时间的生成、记忆的淡化与现实生活分离,对往事的审视从而获得了一种“间离效果”,这种“间离”使得作家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着既往的人和事,虽依然身处境中,但已能做到心于境外,清醒而冷静地审视着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泊的评判,略去应时应有的功利主义,从而使文本获得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如:汪曾祺《受戒》文本的叙事时间是1980年,而文本的故事时间则是1936年,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神秘地使回忆文本具有了某种美学效果。43年的时间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断,对这些片断的审视,由于“间离效果”而获得了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作家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美学理想和人生哲学的人和事删去,而选择有助于表现自己美学理想的人和事,并在其中渗入现时的思想和感情,内化了作家的美学追求。所以汪曾祺“40年前的事”“用80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在40多年后“回想起儿时亲眼见闻过的和尚、村姑,才会觉得他们比现时生活的人更优美些”。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发现:《大淖记事》40多年;《钓人的孩子》43年;《日规》45年;《詹大胖子》、《幽冥钟》53年……大部分小说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不能不说长距离的时间差,造成了汪曾祺小说文本独特的“这一个”,造就了汪曾祺诗意化的小说文体。同时也说明,回忆实现了汪曾祺的美学理想,而这种理想又反过来以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影响着他对回忆中的人和事的选择。
汪曾祺对久远的故乡的人事、风景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诗心和难以尽说的温存。现实是变动不定、难以把握的。在他的情绪记忆中,只有过去才是确实的、可亲近的,过去不会背叛自己,由于时序的迁移造成心理距离,使人能够抽身事外,心平气和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对待。这是一种超脱于唯实唯利生活的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喧嚣、浮杂的现实生活中无暇顾及的那种冲淡、平和、非功利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理想得到了凸现。这种“回忆中的世界”,给现实中疲于谋生,因精神和物质而困扰的痛苦不堪者,提供了一个观念中的崭新的现实、休憩的桃花源。回忆已经不仅仅是心理学、文体学意义上的回忆,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回忆,他是作家通向美学理想的途径,也是主体进行审美体验的方式,因此,回忆诗意建构了汪曾祺小说文体,也规约了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
在小说叙事策略的多种可能性选择中,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体家,汪曾祺选择回忆来诗意建构小说文体。《受戒》是汪曾祺对初恋的一种朦胧感受,叙述了童年在小庵里的生活……可见,回忆对汪曾祺来说首先是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形式,具有文体学的意义,但回忆不仅仅是故事,或故事叙述的技巧和形式。它可以是审美体验和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和中介,也可以是进行回忆和沉思的场所,实际上这种文体学上的回忆,在作为一种叙述技巧和形式被自觉运作时,又总是和他的美学追求相联系的。汪曾祺常常用儿童的眼光、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选择素材、组织情节,正说明了这一点:汪曾祺决意要越过所有的磨难和悲剧,决意要用孩童一样纯净如水的眼光去打量世界,所以,他“把人生看得很美的,是审美的人生。”而在写作中,则有意剔去“畸形怪状的苦难之状”和“对人生的灵魂直接的、无情无意的拷问。”早在40年代初,他就写了《花园》,充满深情地回忆儿时生活。到了老年,童年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异秉》、《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夏天的昆虫》、《冬天》、《同学》、《小学同学》、《淡淡秋光·橡栗·梧桐》、《夏天》、《我的家乡》、《腊梅花》、《紫薇》、《踢毽子》、《非往事·鞋底》、《故乡的食物》、《花·荷花》等作品,或者纯粹地忆旧,或者从当下的景物中勾起对往事的回想,让他再一次重温了童年时代的旧梦。因保有童心,汪曾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对草木虫鱼都倾注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他能从常人认为习焉不察的凡俗世象中体察出美感和诗意来,这与他不泯的童心极有关系。在回忆他文革期间在农科所下放劳动时的《葡萄月令》中,处处洋溢着童心:“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一声“哎”,叹出了孩童式的惊奇与欢喜;“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这是孩子式的想象;“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了!”语调里带着浓浓的孩子气。此时童心已经转化为汪曾祺审视世界的方式。他的不少小说采用了儿童视角,例如《晚饭花》、《昙花·鹤和鬼火》、《异秉》、《黄油烙饼》、《鸡鸭名家》、《职业》等等。他最杰出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更是一片童趣盎然的天真世界。不但小说叙事采用了儿童视角,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都表现出清纯的儿童眼光。一切是和谐朦胧的、诗意的境界。同样是以“儿童视角”为主要叙述方式,苏童、莫言是以童年的感觉和经验,去叙说并非全是童年发生的人和事,在感官的敏锐与意象的流动上,给人以强烈的感染,重在表述人对外界超常的感觉。汪曾祺的“童年视角”与他们不同,他以非童年的感受、经验,去叙说童年发生的人情世态,并非是用直觉,而是以感受回忆式的笔调来书写历史的。
《受戒》采用儿童视角叙述了一片童趣盎然的天真世界:少年明海当了和尚,却又在此时与小英子相爱了,并且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没有半点世故虚情的童稚之心,看到了生活的诗意。小说为我们展露了少年们的生命本色,并且将之置于和谐、明澈的自然环境中,使自然与社会生命个体在真与美中交融。
作品里的一些人物对我们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这部作品以表面上童年、少年的美好追忆的散淡构筑了内部质实的纹理。小英子家三面环河的小岛,是作品人物居住的地方,更是作家个人记忆的家园,而追忆的曼妙中却有着对纯真爱情的赞美,记忆如此鲜纯,打开来,年积月累的蓄水泛着清亮的光泽,不仅使这片土地漫布着润湿的水气,又有着世外桃源的韵致。而小英子、明海等就在“我”的情感追忆中生活在这个诗的世界里。
波德莱尔曾说:“真正的记忆只在于极敏锐而易受感动的想象中,因此,想象依靠每种感受能够展现过去的情景并将之表现为生活的奇观”[8]。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回忆情境是活跃的丰富的,但又是零乱的模糊的不确定的,而回忆使创作主体的审美能力得到了超强的发挥。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回忆就是把自己所体验过的东西呈现在作品中,使它在审美的意义之上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阈中,因而,当汪曾祺走入对往事的回忆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审美意义上呈现了自己所体验的生活。在作品的回忆性叙事中,他以艺术的审美去强调生活的诗意。在他的小说里,他从自己丰富的记忆中选择其中体验最为深切,情感最为深挚的片断,通过想象的加工,同时也借时间上的间离,对过往的情景进行了无意识的却又是精心备至的审美选择,使之成为自足的艺术境界。他追溯往事,以呢喃的诉说传达着他对现实世界和记忆世界的感知,也正是在这样的追溯中,原来幽闭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回忆得以敝亮于读者的审美视阈之中,成为永恒的美,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他小说审美中诗意的成因。
二、“气氛即人物”的诗学意境
从古至今,写文章多讲求“文气”,“气”简言之是指内在的运动。对于“文气说”,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大概汪曾祺最信服的要数韩愈的讲法。汪曾祺说:“讲‘文气说’讲得比较容易懂,也比较深刻的是韩愈。”他打个比喻说:“气犹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轻重者皆浮;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9],“气”简言之是指内在的运动。汪曾祺所理解的文气落实到他的小说中,很大的程度上是指审美意义上的氛围。进入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作家看似不经意而又处处弥漫的氛围中。小说中滚动的情绪流,弥漫的氛围,均被文中特有的情调运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散发着作家审美理想的意绪和情思,体现了作者“天人合一”的审美观与世界观。自然是与人相关联的生命存在,景物也不只是自然的一鳞一爪,不只是个别对象的色、声、味,而是整体的山水、房屋、景色,其中氤氲流动着人的情感。他笔下的自然不是相对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化、对象化的自然,其中孕育着人的思想感情:那荒凉的大漠河泽,与人无干的巨大空旷,恐怖威吓的风雷闪电,经过作家情感体验的积淀与酝酿,在小说中发生了异化,形成了汪曾祺小说氛围感的特质:在总体氛围上呈现了温暖、平和、极具温情气息的纤柔的审美况味,略带一丝凄凉的感伤,和原生态的自然景物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内质。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小说中没有华丽的语言,曲折离奇的情节,悲欢离合的人物情感——这些在传统叙事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被汪曾祺轻描淡写地冲决了,取而代之的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受的氛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氛围制约着小说的情调、人物情感和情节结构的生成和流向;氛围的文本化,是环绕某一人物、事件或场景的基本色调;是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民族情感、地域风情等众多因素与作家个人的文化修养、社会阅历、个性特征的有机结合而最终形成的特殊的精神形态和审美韵致,是作家人生观、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味的凝定和物化。氛围决定着小说文本的存在方式,规定着作家对世界的看取和表达。汪曾祺对氛围的成功营造,即是他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成功。
汪曾祺由衷地赞赏那种不事雕饰的风格[10],吸取了古代笔记小说的精华,又有所创新。表现在文本中,即在小说的结构上讲究“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他的小说不编织情节,不安排巧合,无悬念,无高潮。小说的主体便能够显示各种人情世态的民俗氛围,在氛围的铺叙和渲染中塑造人物。
氛围浸透了人物 在小说《岁寒三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放焰火的描写中,那早早吃了晚饭扛了板凳前来的人们,那满场的各种各样的小吃摊,那“炮打泗州城”、“遍地桃花”的美丽焰火,还有那炎炎火光逐渐消隐之后,你呼我唤吆喝回家的声音,无不洋溢着祥和、欢乐、喜庆的气氛,而其中独不见焰火的制造者陶虎臣。汪曾祺说:
这里写的是风俗,没有一笔写人物。但是我自己知道笔笔都着意写人,写的是焰火的制造者陶虎臣。我是有意在表现人们看焰火时的欢乐热闹气氛中……我把陶虎臣隐去了,让他消融在欢乐的人群之中[6]。
陶虎臣消融在欢乐的人群中正表现了“气氛即人物”二者的合一,也体现了汪曾祺的最高审美理想——和谐。
小说中的环境和氛围、场景的摹写可以看成是一种风情和民俗。小说中的人物可看成被作者用来作为营造氛围和环境的一种“材料”,它发挥的作用相当于“活的道具”。严格地说,并不是实际意义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已异化为习俗的特殊“符号”。他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让字里行间全部浸透了人物。用贴近生活的淳朴民风与古老民俗的描写来代替编故事,这是汪曾祺营构“气氛即人物”的独特方式。这样,不仅增加了人物的生命气息,而且作家恰好借助一些物景作为主体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让那些带有浓郁抒情气质的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构成一种生命活动的“投影”,化为情调,弥漫于浓郁的氛围中。由此可见,人物和情节反倒成了点缀,造成了小说情节的缺失。他在《钓人的孩子》中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一幅民俗小景: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炯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
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栖栖惶惶,忙忙碌碌。谁都希望意外地发一笔小财,在路上捡到一笔钱。
这幅小景先是用直觉画面从“色”、“味”两方面对街景进行了一番展示;然后是富有哲理意味的抒发,对街上行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穿透性透视。前后文字的奇妙组合,使得米市、菜市、肉市这些平常风俗小景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人情世态氛围,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略带反讽的悲怆气息。作者把“货币使人变成魔鬼”这种意绪投影在小街的直觉画面上,接着以一个孩子用钱钓人,而已经好几个人“上当”的简单人物,来纺织一个看似孩子恶作剧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渲染出一股人情淡薄功利性的氛围,他所塑造的人物就浸透在这种氛围中,没有塑造人物,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氛围体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在汪曾祺笔下,凡是自然的,符合人性的,就是美的。人就是要诗意地生存着,自然地向生活敞开生命,活得放达超脱,随心所欲。歌颂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追求美好的人性,这也是作者创作思想中人与自然、氛围高度和谐的审美追求。
谈到自己最负盛名的作品《受戒》,汪曾祺说:
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11]。
在《受戒》里,僧俗的界限荡然无存,做和尚只不过是另一种营生而已。而且这种营生既摆脱了世俗职业的艰辛羁绊,又具有世俗生活的欢愉自由。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小英子和明子的少年情怀才得到了淋漓的挥洒,人性的光辉闪耀无遗,天地之间,人如玉树临风般清新挺立起来。
氛围投射人物的人生际遇 在《晚饭花》中,作者浓施粉黛,绘形绘色。从声、色、光上多角度的铺写了山墙下的晚饭花:
晚饭花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的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在这样一个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多得不得了的红花的图画中,自然的色彩很鲜明,很亮眼。但仅仅是几块装饰色而已。于是,作者就把主人公——王玉英,安置在这明丽的背景上。“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虽然没有描绘王玉英的衣着容貌,而只这“做”、“等”两个动词,就使这幅画化静为动,化美为媚了。因此,在对人物勾画中,欣赏者便也总是自然而然地把她点染在这锦簇的晚饭花背景上。王玉英的形象在哪里?在晚饭花中。花即人,人即花,花和人统一在美的境界中,所以当王玉英和晚饭花分开,嫁给那个与寡妇相好的浪荡公子钱老五后,她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尽管李小龙仍时时见到做新娘子的王玉英,可他却认为“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这世界上再没有王玉英了。”也就是说王玉英从原有的氛围中游离了出去。“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中,”臭水河边淘米的王玉英与晚饭花前做针线的王玉英的人生际遇不同,因而在美学评判上便不能相等。在这一氛围中,人与景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于是人物的生命活动、人生际遇便也在此产生。
汪曾祺的小说不是在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中勾勒人物独特的个性,而是渲染一种氛围,把人物恰到好处地点缀在氛围之中。人,是氛围中的人。营造“气氛即人物”的诗学意境,是汪曾祺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另一种审美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