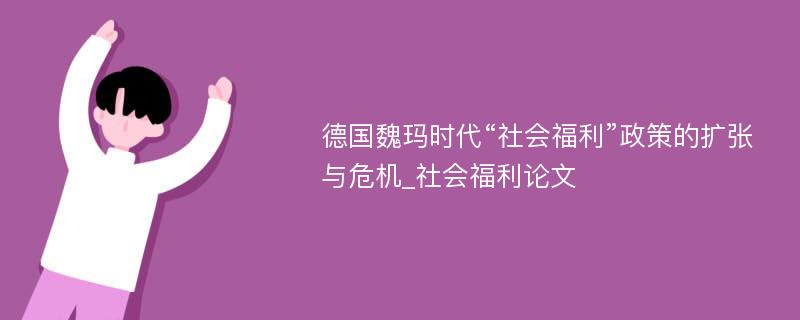
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玛论文,德国论文,社会福利论文,危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工业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社会裂变”的压力下,俾斯麦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接受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改良理论,于1883年在世界上最先创建对工业受雇者阶层的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保险制度。这一制度的成功贯彻,曾在帝国时代获得过“社会内部集合化”的效果。然而,在随后的魏玛共和国时代里,福利制度尽管有着远比帝国时代大得多的扩展,却不仅未能获得在帝国时代的效果,反而陷入了危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本文力图通过对魏玛时代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试作回答。
一、魏玛时代“福利国家”原则的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并没有出现一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出现了一场政治结构的大变动。雇主联合会与自由工会通过双方领导人于1918年11月15日签定的《斯汀纽斯—列金协定》宣告了“中央劳动共同体”的诞生。劳动与资本达成的这场利益妥协构成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前的魏玛国家历届“大联合政府”的政治基础。随着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建立,普鲁士容克政治精英以及大资本的权力垄断也被打破,大量来自中间等级的民主派成员与天主教徒进入了政治决策机构,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工会运动也摆脱了政治上受歧视的地位并参与了对国家的负载。这种政治力量的新组合无疑有利于福利保险制度的扩展。
然而,魏玛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远比帝国时代广泛得多,也严峻得多。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已因战争的失败而大大加剧了,而且还出现了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转轨过程中安置800多万潮水般涌回社会的士兵复员问题,400万以上的伤残者和阵亡者遗属的救济问题,几百万被战争中的通货膨胀掏空了社会福利金的投保人的生存问题,以及提高受雇者的工资问题。所有这些都证明,战后具有现实性的困境已开始突破过去“社会问题”仅仅只与“工人问题”相联系的传统界限。
新执政者们决心以“另一场斯泰因改革”来拯救战败后的德意志危局,帝国时代福利保险制的成功经历使国会中大量专家、教授与学者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国家干预和在经济上的投入找到它们理性上的解决方案,正如医学的进步能杀死细菌那样。”[1] “讲坛社会主义者”信奉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工程技术论”思潮现已得到了跨党派的拓宽。因此,这个新建的民主国家一开始就在“阶级合作主义”的试跑中进入了“进化式社会改良的轨道”[2]。 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至少从法律上勾画出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特点,第161条规定:“为了保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为了保护母亲,为了应付由于老年和生活中的软弱地位以及情况变化造成的经济上的后果,帝国(魏玛时代仍称国家为“Reich ”)将在投保人的决定性参与影响下,创造一个全面广泛的福利保险制度。”[3]
因此,《魏玛宪法》使战败后的德国在西方世界中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即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决断生、法制性、福利国家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新生共和国的威望也就与福利制度的发展荣辱与共了。
二、魏玛“福利国家”制度上的客观发展
大联合政府面临的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如何供养150万伤兵和250万遗属。在过去伤亡不过几千人的情况下,这笔供养费是很容易由军费来担负的。但战争制造出来的400万人供养负担不仅使军事当局无力承受,而且《凡尔赛和约》也明文规定了对这类军事供应机构的“非军事化”。因此,1919年10月,这种供养责任被过渡给国家劳动部。1920年3月的《帝国供给法》和《健康严重受损者法》将这种源于传统的处理程序正式纳入福利体系之中。“战争牺牲者们”获得了有关医疗、职业恢复、教育培训,以及养老金方面的法律保证和许诺[4]。
共和国福利制度的第二次扩展,是“社会救济制”的出台,它源于中世纪“贫民救济”的传统。在当时,贫穷极少被视为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而被视为个人的无能,凡接受这种由地方乡镇提供的源于基督教精神恩惠的人同时也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5]。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物质上造成的影响嘲讽了这种原则。失去财产和收入的数百万人——首先是那些拿社会福利金的人——既不是由于自己拒绝工作也不是由于个人的过错,唯一真实的公共性原因就是国家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并引起了通货膨胀,而且在没有公共资助的情况下已不能生存下去了。对这种经历的理解,其法律上的结论就是1924年2月《关于救济义务的帝国条令》和4月的《关于公共救济的前提、方式、程度的帝国原则》的出台[6]。尽管贫穷不再与不光彩相提并论, 受济者也不再被剥夺政治上的权利了,但是只有当一个人的收入低于工人平均工资的1/4时,才能领取到救济费[7]。即使如此, 也仍耗去了通货膨胀期间国家金融支出的4/5。
传统的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三大保险制带着机构的空壳熬过了通货膨胀。在1924年进入“相对稳定”后,它们不仅重新开始正常运转,而且很快得到了如下扩展:首先,所有的保险都考虑到家庭,并增加了给投保人子女的津贴费。在残疾保险中,子女津贴费由战前每月的2马克提高到10马克。在工伤保险中,每位受伤索赔者子女也有权领取保险金的10%。在医疗保险方面,规定了对投保人家属全面提供医疗处置。病假津贴不仅支付工作日,而且也支付星期日和节假日。由于人口政策方面的原因,所有的生育妇女,无论是否投保人的家属,均能获得生育后的免费助产服务、医药、分娩津贴,以及先是8周,后是10周(1927年)的产假补助。其二,工伤事故保险自1925年以后不仅只对劳动事故进行赔偿,而且也对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以及看护劳动工具时发生的事故进行赔偿。越来越多的职业病也列为工伤事故并给予赔偿。其三,养老保险将家庭手工企业的雇员也纳入其内。投保人所获取的养老金已由战前最后几年的每年平均180马克提高到1929年的400至700马克;根据工龄长短,工人每月为33至58马克,职员每月为65至70马克[8]。其四,在遗属年金方面, 丧失就业能力的工人寡妇能享受亡夫年金的6/10(过去为3/10),孤儿享受5/10(过去为2/10)。若孤儿在接受教育,这笔年金可从18岁延续到21岁(过去是16岁)[9]。
1927年7月16日《劳动介绍与失业保险法》的颁布对魏玛国家社会福利体制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法规定,将用职业咨询、职业进修、改行培训等方面的福利对失业保险金加以补充,所需费用由入会费支付,入会费占工人毛工资的3%,由雇员与雇主各缴纳其中的一半,但国家保证用财政手段平衡会费筹集与资助总额之间的差异。一位有两名子女的失业者,根据其工资等级,最长能在半年时间里获得他最后劳动收入的50%至80%。半年后如有必要,将由一种“危机救济金”来替代这种失业保险金[10]。这笔救济金需根据个人需要的程度来测定,并完全由公共开支支付,其中,国家财政负担4/5,地方乡镇财政负担1/5[11]。
至此,魏玛德国的“福利国家”政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不仅扩充了帝国遗传下来的对工人、职员的三大保险和遗属保险,而且还新增设了对战争牺牲者供养、社会救济、失业保险和危机救济,仿佛“福网恢恢,疏而不漏”了。然而,它能够像帝国时代那样获得“内部集合化”的效果吗?
三、经济上的结算与利弊争端
战败及战后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魏玛德国经济的发展,《凡尔赛和约》又给德国带来了领土和资源的损失,铁路和商船均被没收,尽管后来有《道威斯计划》的扶持,但1320亿金马克的沉重赔款义务毕竟造成了强烈的出口压力。所有这些不仅使魏玛德国处于比帝国时代狭窄得多的发展框架内,而且也严重干扰了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仅以工业生产为例,若以1913年发展水平为100,整个魏玛时代只得到起伏不定的缓慢恢复(见下表)[12]。
年代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工业年代 385566724770
年代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工业生产 8380100
103
104
91
60
要维持这个民主共和国,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企业家集团与工会集团之间的平衡。大联合政府便借助通货膨胀手段来苟延残喘。因为通货膨胀可以使企业主将成本上的负担转移到价格上去,同时又能使国家用滥发纸币来支持社会福利金[13]。总之,通货膨胀一时掩盖了一系列的分配问题,并奇迹般地维系着“中央劳动共同体”这个共和国民主大联合的政治基础。
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本已造成了保险金的大幅度贬值,依靠帝国银行的大量贷款来发放国家津贴,却促进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了保险机构的支付能力,并导致德国丧失赔款能力和法、比军队强占鲁尔。“消极抵抗”更使通货膨胀于1923年11月15日达到了1美元兑4.2万亿马克的空前绝后的高峰[14],从而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但是,对民主制的挑战,主要并不来自在“消极抵抗”中仍能保持合作关系的企业家集团与自由工会集团。当1924年1月的货币稳定结束了“通货膨胀魔术”之后,“中央劳动共同体政策”的物质基础便趋于瓦解。劳资冲突的加剧迫使大联合政府开始频繁使用“国家仲裁制度”。坦率地讲,“在贯彻工资原则时,85%至90%的仲裁处理,以及75%至80%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是应工会的建议才形成的”[15]。但由于稳定时期工资起点定得很低,因此,雇员平均的实际收入直到稳定结束时才提高到与1913年平均实际工资大体相同、略有波动的水平[16]。
企业家们不仅反对工资的提高,而且也反对保险制度的扩展,因为工人保险入会费的一半要由老板来支付。当用通货膨胀来转移生产成本负担的方式成为问题时,他们便“寄望于生产合理化运动,来达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为工人和职员所支付的保险入会费,进而达到重新夺回由于战败和革命而失去的地位,并再度成为世界市场和国内经济生活中主人的目的。”[17]与之相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通过合理化运动获得一种改良社会的推动力,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可能为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创造更好条件的[18]。由于企业主与工会都拥护合理化运动,为了应付合理化运动必然造成的失业,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提案“在1927年7月16日被国会以几乎闻所未闻的多数票通过,就仿佛社会合作伙伴的精神终于得到了贯彻并能变成对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负载力量一样。”[19]
然而,这场合理化运动并没有打开通过社会管理技术上的领导使经济生活井井有条的理智王国的大门,更通常地是在企业主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中造成了一种日益加速的对工人的“磨损”。每一位在流水线上向新生产率纪录冲刺的工人也正在制造他自身结构性失业的可能性。但是,失业保险入会费是在1927年工业生产刚刚恢复到1913年水平时,按低于80万失业金领取者的规模设计出来的,而德国失业工人人数从1927年至1929年底已由5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这自然得进一步求助于增大国民经济对社会保险的支出额来缓和社会矛盾[20]。
魏玛共和国福利制度的扩展本身就是由战争后果、稳定货币危机、出口困境、合理化、生产过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它同时又是靠对一种几乎萎缩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引人注目的重新分配来发挥影响的,即使在美元扶植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国家财政也一直是赤字。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便增加税收,这就降低了企业的赢利性,加重了企业资本构成的困难,并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企业便更疯狂地合理化,其结果是更多工人的失业,国家又得投入更多的津贴费。这种恶性循环使德国经济早在1928至1929年冬已缓慢滑入危机轨道[21]。而到1929年,国家和地方当局财政为各种新、老保险机构支出的总额已达93亿马克,而不是1913年的13亿马克了,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3%,而不是1.8%了。即使考虑到货币价值的上升,也是1913年的5倍多[22]。因此,它已经越来越难以为国家财政能力所负载了。
大危机的到来终于使一场围绕着福利国家利弊的争端公开爆发,其实质则是一场关于共和国政治经济体制利弊的争端。企业家集团将福利制度的扩展和工资增长视为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自由工会和国家各级劳动和社会福利当局则提出反驳:“社会福利金和工资的增长稳定了购买力,它所造成的影响,如其说削弱了生产和经济的繁荣,还不如说刺激了需求。”[23]这场争端已经表明,共和国要想继续贯彻一种能同时满足它两个主要合作者之愿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已无可能。这就标志着魏玛时代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最后破产。
四、魏玛共和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
在高失业率的背景下,罢工已不再是一种对企业主有威胁性的斗争手段了。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主持的联合内阁倒台,标志着企业家集团掌握了主动权并占据了上风。靠总统委任上台并向右转的布吕宁内阁企图用经济紧缩政策来寻求避难所,为此目的,便于1930年7月26日、1931年6月5日、1931年12月8日先后通过三个“紧急条令”,对经济生活施加有利于大资本家的干预,并对社会福利金进行大规模的削减。而继布吕宁内阁之后的巴本内阁所颁布的1932年6月14日“紧急条令”,则急欲撤除社会福利保险制。
传统的医疗、工伤、残疾—养老三大保险首先成为攻击对象。1930年7月“条令”规定,医疗保险公司须等候3天时间再支付病假津贴。1931年12月又规定,取消所有免费医疗项目和疾病预防支付。工伤事故保险不再赔偿发生在上下班途中的事故。就业能力损伤度不足20%者,不再得到工伤年金。其它损伤程度的工伤事故年金缩减15%。残疾养老保险中发放的儿童津贴费由每人每月10马克减少到7.5马克。寡妇年金由亡夫最后工资的6/10减少到5/10,孤儿年金则由5/10减少到4/10。15岁以上的孤儿不再享受孤儿年金[24]。
受到最强烈震动的是失业保险和危机救济。由于失业率猛升,保险入会费的筹措自然减少,已由1929年的52亿马克减少到1932年的35亿马克。而布吕宁政府的几个条令逐步将失业保险入会费由基本工资的3%提高到6.5%,从而使个人所有入会费由1929年毛工资的15.5%上升到1930年的19%。[25]通过入会费的提高所筹措的款项仍不足以满足长期不断增长的要求,布吕宁、巴本政府便不断通过大幅度削减失业保险金和危机救济金、延长领取这些金额的等候时间、缩短支付持续时间等手段来减少福利金支出。1931年6月,失业保险金已被削减了14.3%,而到1932年6月,所剩的失业保险金又被削减了23%。同时,危机救济金也减少10%,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等候时间却不断延长。1931年6月以后,一位单身汉要在失业的21天后才能领到失业保险金。但是,失业保险金最长的支付时间已由半年即26周减少到1932年6月后的6周,危机救济金的最长支付时间则由39周减少到32周[26]。
然而,撤除社会福利制度的动机并非意味着撤除的绝对后果,因为大萧条的动力反叛着这种企图。当登记注册的失业人数于1932年上升到612万时[27],个人失业持续时间也明显变长,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在6周之内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尽管拿失业保险金的人因支付时间缩短而持续减少,但领取危机救济金的人以及被停发了危机救济金而被转入到地方乡镇的公共救济领域中的人都不断增加。由于这两种救济都是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来支付的,这就自然又扩大了公共费用的支出。布吕宁,尤其是巴本“紧急条令”在不断地恶化这种关系。例如,在1928至1929年的结算中,国家给180万失业者资助了14.1亿马克,而在1931年至1932年的结算中,国家给550万失业者资助了39亿马克。但个人平均费率则由780马克降为560马克,其中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120万人中,每人平均领到1045马克,在领取危机救济金的150万人中,每人平均领到605马克,而在领取地方乡镇公共救济金的190万人中,每人平均领到463马克,还有90万失业者什么都没领到[28]。这一局面到希特勒上台之时仍在恶化。
布吕宁、巴本的紧缩政策带来了极为荒唐的局面:一方面,投保者个人所得的费用在不断减少,这自然导致了民怨沸腾;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支出却增加了一半,1932年底,这种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已由1929年的13%上升到20%以上[29]。其结果是,紧缩政策既克服不了危机,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的厄运。更重要的是,由于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将其威望与“福利国家”的许诺联系在一起,因此“福利国家”的危机自然使它失去了人心。
五、两点结论
如果将魏玛时代福利制度从扩展到危机的过程与战前帝国时代“福利国家化政策”相对成功的经历加以比较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福利制度的顺利运行和扩展,必须有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因为根据投保和法定标准索赔原则运行的保险体制,作为一种经营体制,是要以投保人多而索赔者少才能维持下去的。在这里,低失业率是关键。而低失业率,只有在经济稳步发展中才可能出现,而且也只有在生产增长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更多的分配。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是有可能使福利制度的扩展与经济稳定增长同步的,同如一战前德帝国时代所呈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0万人,失业率也是在1%至4.5%之间滑动的[30]。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发展线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福利制度的扩展却往往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紧张局势逼迫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这种形势又往往与经济不景气联系在一起。魏玛时代正处于这样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特别是在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国失业率在1932年甚至高达43.8%[31]。当失业人数猛升而使投保入会费猛降的时候,也正是保险费支出的任务猛然增大的时候,它迫使国家财政唯有向福利保险制作更大的投入才能保证它的运转,而财政困难的国家采取的一切平衡财政的措施又必然导致更多的失业者。这种恶性循环充分暴露出福利制度运行机制中固有的基本矛盾:当需要帮助者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最大的时候,也恰恰是他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帮助最小的时候。这是西方福利国家直到今天都一再面临的,也是远未得到解决的矛盾。
(2)福利制度本身有着发展方向上的绝对要求,只能使它朝增加福利金、扩大保险面的方向扩展,而不是相反,否则它不仅不能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
当福利制度在德帝国时代被开创出来时,它是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绝对量的变化上都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开始滑动的,因而也就使这种滑动成为生产者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了。生产者不仅不愿再度丧失已争取到的条件,而且还要去争取更好的条件的。因此,任何减少福利金、缩小保险面的措施都是在不断加剧穷人的痛苦。但是,这种方向性上的绝对要求,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局势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民主党人和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看到了前者,但没有看到后者,更没有看到福利制度的扩展是要受到经济发展条件和时代特点的制约的,宪法许诺与状况现实性之间的鸿沟,甚至仅仅只有在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可能有步骤地去跨越。而他们的福利国家纲领却是在没有考虑到实现它所需要的物质前提的情况下拟定出来的,因而终于成为这个“新的社会福利工程师阶级”平庸的证明。布吕宁、巴本政府的愚蠢甚至反动则表现在,他们看不到:不断削减个人福利保险金恰恰能起到激化社会矛盾的效果。因此,他们不惜以工人那点可怜的福利保险金为代价去满足大资本家的利益。当然,削减的幅度是与激化矛盾的程度成正比例的,更不要说撤除福利保险制了。尽管1929至1933年间数百万失业者个人拿到的各种福利保险金从实际价值上讲并不少于战前的帝国时代[32],然而由于这种款项是处于急剧减少的过程中的,因此它在受济者心理上造成了安全保障感的完全丧失。这就自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也为纳粹党力量的壮大提供了良机。
魏玛共和国尽管扩展了福利保险制,但是福利保险制并没有能挽救魏玛共和国。这一历史性的结论,充分说明魏玛时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固有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然而,福利保险制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它带着深刻的教训、内在的矛盾和固有的规律度过了纳粹时代,最后被传递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为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福利保险制度就不能生存。
注释:
[1][3][12][13] 德特勒夫·J.K. 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38、135、125、114页。
[2][18]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 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191、117页。
[4][8][23][24][25][26][32]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25、122、128、134、130、131、135页。
[5] 沃尔夫拉姆·费舍尔:《历史中的贫民,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与解决尝试》,哥廷根1982年版,第33页。
[6][7][9][19][29]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 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魏玛共和国,1918—1933》,杜塞尔多夫1987年版,第208、209、211、213、217页。
[10] 《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年鉴》,柏林1927年版,第93页。
[11][16]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9、310页。
[14][20][27]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希:《1914至1978年的工业化德国》,慕尼黑1978年版,第66、130、97页。
[15] 帝国劳动部:《德意志的社会政策,1918—1928》,柏林1929年版,第109页。
[17] 埃尔哈德·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1984年版,第88页。
[21]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哈根·舒尔策:《魏玛—一场民主的自身代价》,杜塞尔多夫1980年版,第228页。
[22] 联邦统计局:《人口与经济,1872—1972》,斯图加特1972年版,第219页。
[28] 《经济发展趋势统计手册》,柏林1936年版,第165页。
[30] 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1990年版,第806页。
[31] 迪特马尔·佩策依纳:《两次大战之间的德意志经济》,威斯巴登1977年版第16页。WW吴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