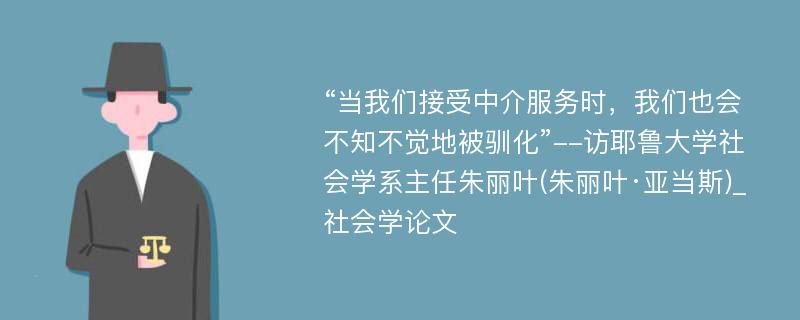
“我们在接受代理服务时也不自觉地被驯化”——访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朱丽叶#183;亚当斯(Julia Adams)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斯论文,耶鲁大学论文,朱丽叶论文,也不论文,系主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丽叶·亚当斯(Julia Adams)于1990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密歇根大学从教从研达14年之久,2004年受聘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致力于发展该系的历史社会学。她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曾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的副主席与主席。她从事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性别研究、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与帝国、全球与跨国政治、近代欧洲的国家形成。 朱丽叶多次获得过巴林顿·摩尔论文奖,代表作《家族式国家:近代欧洲的统治家族与商业资本主义》讨论世袭制在近代社会的作用,对国家形成领域的主流话语构成挑战,所合编的《重塑现代性:政治、历史与社会学》、主持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丛书和创办的杂志《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她着重反思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社会学发展,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搭建起桥梁,更深远地推动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朱丽叶目前是美国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但她把历史社会学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的尝试也引起了各种争议。本报特约记者、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郭台辉教授于近期对朱丽叶教授进行了专题访谈。 郭台辉:您是如何开始研究西欧的家族式国家与世袭制,尤其是关注荷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国家?毕竟,家族式的国家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热点”话题。 朱丽叶·亚当斯:以前当然不是热点议题。即使家族式国家曾构成为历史上许多国家,但现代研究国家形成的西方学者依然非常抵制把家族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来研究。他们只愿意把家庭设想为私有的核心家庭,只是用来处理日常亲密关系的问题,并不愿意视之与宏观权力相关。但是家庭与国家的确在某些层面是关联在一起的。然而当代美国的社会学家是非常难以打破自己已有约定俗成的惯性思维的,他们固守公私领域二分法的现代主义范畴,只想把所有问题都纳入到这种二分法范畴中加以认识。这种盲目自大至少是晚近政治的不幸。无论是学术界的研究者还是社会的一般大众,在试图理解当代中东的某种政治形式时,都往往会非常惊讶地观察到家族关系在政治中依然扮演很关键的角色。我以前阅读过历史上同时代的往来信件和其他的档案材料,我从一篇又一篇的记录中发现,家庭在国家和帝国层面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中,格瓦(Dorit Geva)正在做的有趣工作就是研究法国与美国的父亲地位与服兵役的关系。此外,卡纳迪(Margot Canaday)的《直接国家》(The Straight State)是一部社会科学史家的著作,得了很多荣誉奖,也是这个领域最有前景的研究著作之一。 郭台辉:荷兰这个国家以前是没有理性-法律统治的官僚机器,没有一部权威的宪法作为基础,政治稳定性更多倚重于一种父系主权的权威,而且紧密关系到宗教与文化。同时,这种家族式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可能来自于相对应的家族式社会与经济并且与之密切联系,这显然不是现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那么,这种家族式国家形态是如何衰落,或者说如何退出现代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在现代早期的荷兰,这些世袭的社会、经济与国家形态之间是如何作用的? 朱丽叶·亚当斯:历史社会学家在分析具体的家族概念时,不仅通过经济概念而且还通过贸易概念来讨论,但我的研究只是关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关注到社会与经济层面。你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术规划,但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很多人一起来研究这个宏大的课题。 在西欧和美国,家族式的国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衰弱了。但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却是相反的情况,家族式国家与世袭权力形式在近些年里一直得到强化,尤其是精英家族关系因新资源的流动而不断得到政府的重新授权,还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有着裙带关系,而且还相对僵化,这种情况不太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在荷兰和法国,家族精英对于企业所采取的被社会排斥的落后运营模式应承担实质性的责任,其最终在竞争中失败,原因就是世袭主义的继承制在制度顶层太过于根深蒂固了。我们了解很多关于拒绝继承制以及提升父权制家族的话语,但究竟“父权制”最终如何变为个人权利,这对于当今世界范围内世袭制的转型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郭台辉:世袭制作为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理想类型,但在您之前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重视。您如何评价世袭制在当代社会的遗产? 朱丽叶·亚当斯:当具体说到统治以及统治的家族形式时,我们可以分析在欧洲这些世袭制国家政权形式的优劣。一方面,这些统治形式的更深层次的基础,明显是确立在对家族血缘几代人的信任以及对家族统治者的信任。这种信任让政权在建构过程中减少许多成本,增强诸多能力。但与此同时,家族式统治也带来权力的僵化,内部充满厮杀竞争。这不仅出现在近代法国,而且也出现在18世纪的荷兰与英国。可见,这些统治形式有其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能,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形式可以支持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崛起,就像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格兰一样,但在另一些情形下却会导致诸多问题。欧洲的世袭制国家是以家长制统治为基础的,家庭、家族与血缘关系是第一位的,然而政治共同体是无法完全由家族来控制的。这是我们在所有世袭权力中看到的一个共同逻辑,同时也是突破点,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求家庭具有想象力,为了完成某项事业,为了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并承担责任,就必须让其统治具有合法性,因此这些想象力也潜藏着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危险。 郭台辉:查尔斯·蒂利在2008年的一篇未刊稿中写道:“在所有的后现代烟雾弥漫之后,历史与历史社会学的逻辑何在?”“如何让历史知识抵制后现代怀疑主义的过度蔓延?”您如何回应这种尖锐的批评?历史社会学第三次浪潮是否存在历史社会学本身提供的一个认识论或本体论呢? 朱丽叶·亚当斯:如果我更早地被问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应可能不同于我现在的观点,因为我是十年前提出历史社会学的现代性概念,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有一个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是查尔斯·蒂利已经去世了。在这里我不想再去评价他的贡献,因为他的确是杰出的历史社会学家,是我硕士导师之一,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实际上我一直在向查尔斯·蒂利学习。我想,如果我在十年前回应他的表述的话,那就具体涉及什么是后现代性?他所指的后现代是什么意思?他是否作了几种政治观点的区分?他所批评的人是否追随福柯及其支配概念?他是否把后现代的概念过于界定在文化指向性意义层面?这些问题都可以运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性的概念来讨论,但其内在要素却是非常不同的,并且可能常常混杂在一起。我想有些人把这些要素混在一起可能很有意思,而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这些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哪里更有效。此外,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蒂利所做的工作就是记录这种变化。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确不那么固定,但对蒂利来说并没有后现代主义所阐释的那些威胁。蒂利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家还是历史社会学家,都是有着惊人的创造性与高产量的,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和旗帜,引领着我们在方法论上进行突破的,这是过去一个世纪在知识界的一场革命。但就我个人而言,福柯的观点对于我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来说非常有帮助和启示,比如他关于权力对于范畴性体制的重要性与那些体制本身对个体或群体的影响,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等观点。 郭台辉:关于“社会科学史中的代理”,您主张代理关系在现代性中并没有得到美化和超越,而是为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这些术语改变了表现形式。这是否表明,虽然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有着相当复杂而颇有争议的历史,但通过运用“代理”这个概念,您有意识地区别于其他并不倾向于历史的社会理论家,也以此来澄清批评者对您的误解?如果这样的话,“代理”是否将成为历史社会学家或者更为普遍的社会学家们探讨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新角度? 朱丽叶·亚当斯:是的,现代性概念听起来的确是非常抽象,我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我的理论与历史兴趣具体来说在于研究欧洲殖民主义的各种形式,而且,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启示。以那种范式作研究的学者似乎大部分都认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都涉及宗主国的政治权力如何规范与监管广阔的领土与资源,如何征服以不同社会文化为基础的抵制力量。帝国的权力中心不是把各种秩序直接授予殖民地统治者,再转而把秩序施加给臣民。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是非常简单,但我再一次认为,这并不能用来反思国家与帝国的诸多理论形式。虽然殖民主义基本上是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但我们完全低估了代理问题的巨大力量,因为统治者之间的整合是代理问题的主要特征,这也关系到帝国的持续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着手研究的课题,这不仅关涉殖民主义研究领域,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世界统治者的问题。 这些代理问题在如今的美国依然表现得很明显,但我的研究更为微观、也更有意思一些。举一个例子,我在社会科学史学会上做过一个主席发言,关注“1800我怎么开车”这个呼叫服务系统。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卡车后部粘贴的广告。我对这种小广告以及类似的标记充满无限的想象,而且还联想到沃尔玛超市女服务员和职员穿着的统一制服,他们都会问:“我能为您服务吗?”这是一种新的代理形式,不管你、旁观者还是顾客,都自动卷入其中,这种代理会培训大量的工人来为你的生活提供方便,但在代理服务的背后你也不自觉地被驯化。你可以看到,在“我”对服务员的指手划脚或者责难中,服务员也正在邀请你循规蹈矩地进入他们的监控体系。我正在研究所有这些服务系统的代理-监控方式,并且关注工作人员与顾客之间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