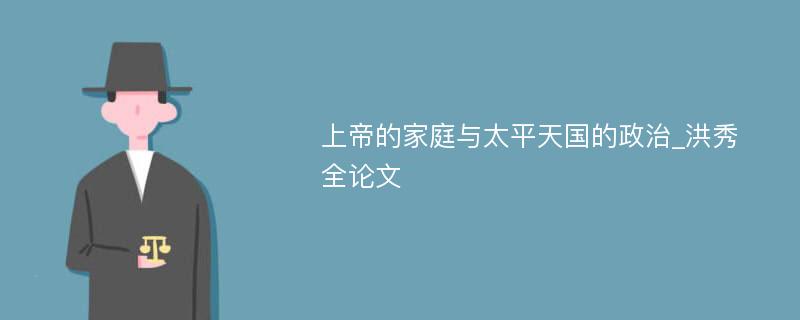
上帝家庭与太平天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上帝论文,政治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上帝家庭的建立及其在早期太平天国历史中的作用
“太平天国上帝家庭”的建立,源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宗教发动。当时“拜上帝教”宣称,洪秀全是以“异梦”的形式接受“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圣旨,下到民间“斩邪留正”,张扬对上帝的信仰,所创立之国家即为“太平天国”。洪秀全以上帝之子、基督之弟自命,在天上的“天国”与地上的“小天堂”之间建立起神灵启示关系。太平天国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以宗教发动起义,而是努力把宗教组织和未来的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并把宗教组织加以国家制度化,使之成为政教合一的形态。而上帝家庭即为此制度化政权的关键构件。以前的农民运动所采取的宗教形式,一般均与中国民间宗教与信仰有关。这种民间宗教和信仰具有原始性和随意性的特点,教义简单幼稚,形式粗糙草率,在易起事的同时也容易自生自灭。但拜上帝教不同。拜上帝教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又受到有自觉目的的政治家的改造和操纵,因此,洪秀全等人在发动和吸纳信仰者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会众的意识形态改造与同化,强调对信仰者的“洗脑”工作,试图通过教条的灌输和准军事化宗教团体的组织,使之笃信不渝。忠王李秀成回忆道:
“是(至)廿六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惟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1] (P95)
周锡瑞如此评价太平天国在宗教组织上的努力:对于太平天国来说,为了贯彻其革命计划和实现天国的梦想,必须要有一个具备明确的权限,严明的纪律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必须对人人都得以称神的可能性加以强制性杜绝;而神的权威,恰恰是洪秀全返回广西后所扮演的角色。[2] (P374)这一努力的关键环节,在于当冯云山蒙受讼狱、洪秀全避祸回乡,广西拜上帝教基地群龙无首时,杨秀清和萧朝贵以降僮巫术的方式染指了拜上帝宗教组织的最高权力。其意义在于,这是中国民间宗教对拜上帝教的一次冲击。当时洪秀全、冯云山苦心经营的宗教,从信仰到组织都面临着一次考验。最后他们觉悟到,必须建立一套免疫系统来抵抗来自各方面的瓦解。他们因此被迫承认了杨秀清、萧朝贵的代天父天兄传旨的权力,尽管这将使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至尊地位受到削弱。但是如果听任诸多降僮者们形成各自的信仰中心,就如同日后的义和团坛场一样,那拜上帝组织将会被无数个天父天兄们的下凡所瓦解。而洪秀全、冯云山采取压制和不承认的态度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降僮这种民间巫术是为广西广大客家山民普遍接受的宗教形式,比拜上帝信仰更容易得到大众心理的认可。因此,洪、冯采取了怀柔策略,承认势力最强大的地区首领、紫荆山区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为天父天兄下凡代言人,从而使“天父天兄下凡”成为拜上帝信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样使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力被削弱,但从起义运动发展的全局看,由于采取的是为广大会众更易于接受的宗教形式,拜上帝会众的信心反因“天父天兄下凡”下达旨意、“下凡”指导而增强。事实证明,此后一系列权力分配,基本上都是通过天父天兄下凡的垂询而得到确认。因此,把源于西方基督教教义的拜上帝教,包装在中国农村社会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形式的外衣之中,是太平天国起义区别于其他借宗教发动的农民起义的根本特点。
杨、萧之所以能通过降僮巫术行使最高宗教权力,有效推动拜上帝会组织的政治化与军事化,正是因为他们利用民间宗教,使会众能够直接感知宗教内容,从而增强了拜上帝信仰的感染力。在此之前由洪秀全与冯云山主持拜上帝教的时期,其宣传内容仍然重在“劝人修善”,宣传水平仍然停留在“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的高度。[1] (P79)这种宣传虽然比较容易把握当时比较愚昧的客家山民的心理,但是难以在民众中迅速形成团体凝聚力,并将这种力量上升到政治斗争觉悟的高度。可是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就不同了。他们每次下凡,都能借助天父天兄之口,把上帝与耶稣的启示,即拜上帝教领导层的意志,化作向会众灌输的政治倾向。这就迅速强化了拜上帝组织的政治化与军事化。再加上杨、萧采用的是为广大客家山民喜闻乐见的降僮巫术,这就使他们的宣传与启示更易于为广大会众所接受。信息传播方式和信仰吸纳方式的垄断,迫使外来人洪秀全、冯云山不得不接受这种拜上帝信仰的“紫荆山化”,否则他们将自我毁弃自己构建的信仰体系。洪秀全本已通过“异梦”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上帝之子下凡诛妖的形象,他虽然不情愿自己梦中的父、兄真的由真人降僮下凡,但是作为教主的他,已无法推翻这种广大会众都乐于接受的宗教形式。对他来说,立即承认杨、萧的权力是划算的。如果他不承认杨、萧,要么就听任杨、萧以外的另外多起降僮事件,使他们的宗教陷于瓦解而不可收拾;要么就眼看杨、萧会借广大会众对本土巫术的笃信,以他们已经到手的天父天兄的名义下凡降旨,制造出另外的上帝之子、天兄之弟。无论怎样,都将使洪、冯二人在广西多年的辛苦努力化为乌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洪、冯才不但立即默认了杨、萧的代言权力,还主动参与了拜上帝中枢的构建。在参与这一中枢构建的过程中,他们主要通过扩大上帝家庭的范围来平衡杨、萧的权力。他们在继续宣扬洪秀全造神神话的同时,在上帝第二子洪秀全之外,又添加冯云山为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石达开为第七子。另外通过把洪秀全的舅父黄为政之女黄宣娇认为洪秀全胞妹,并将洪宣娇妻于萧朝贵,让萧朝贵成为“帝婿”,从而将这一上帝家庭组建完成。有学者认为洪秀全是以此来拉拢萧朝贵。[3] (P1349)其实,洪宣娇是先由黄易姓为杨,被杨秀清认作己妹,然后再被洪秀全以表兄身份易姓为洪,认作洪姓胞妹,最终成为洪宣娇的。所以萧朝贵不仅是洪秀全的妹夫,也同时是杨秀清的妹夫。这正可说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相互夺权而又彼此妥协的复杂关系。
这一上帝家庭的组建在太平天国史上意义重大。家庭宗法关系的形式符合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传统心理,容易被广大会众认可,便利了教义的传播。另外,这一上帝家庭集体的构建,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的政治思维定势。因此,由杨、萧发轫、洪、冯参与构建的、以家庭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中枢,为实现拜上帝领导层的团结打下了基础,并为以后的起义与立国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在金田起义和杨秀清执政时期,洪秀全以天王的名义把上帝家庭成员称呼为自己的“胞”,所谓“清胞、山胞、正胞、达胞”等,称萧朝贵为“妹夫”。可见他们是以宗教名义宣布为上帝家庭成员的,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与他们各自家庭亲族的肉亲关系不同。上帝家庭成员的涵义要比肉亲的涵义更神圣,等级自然也更高。太平天国领导人彼此配合,把这种高于肉亲关系的上帝家庭关系制度化。己酉年八月二十三日萧朝贵借天兄下凡对韦昌辉父亲韦元玠说:“尔子韦正肉身是尔生尔养,亦是尔子,但在高天论,又是朕老弟。尔不好看小他也。”[4](P18)所以韦元玠虽是北王生身之父,但在太平天国的宗教制度面前必须对韦昌辉这位上帝之子奉若神明,“遇有喜庆大事亦随时称贺,甚至跪于其子之前三呼千岁,韦贼恬然受之”。[5] (P55)
在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里,洪秀全作为天父次子、耶稣二弟,他自然有一套在天堂上的亲属关系。他有天父上主皇上帝,自然就有天妈;有天兄耶稣,自然就有天嫂。同时,洪秀全仍然被认可在凡间的肉亲关系,只不过其与肉亲亲属的关系肯定要低于其与天上诸位亲属的关系。因此,王长兄、王次兄虽贵为天王之胞兄,但因为是肉亲,他们的地位当然不比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亲近与尊贵,只能与杨秀清的宗族杨辅清、韦昌辉的宗族韦俊等人地位相当。上帝家庭亲属关系凌驾于凡间肉身宗亲关系之上,这是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宗法制度的主要特征。
二、洪秀全重建上帝家庭的努力及失败
天京事变使洪秀全、杨秀清等共同创建和维护的上帝家庭烟飞灰灭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位上帝之子,或被杀、或出走。而洪秀全不得不尽力挽回信仰危机造成的损失。事变之后,他不得不策略性地立即给杨秀清恢复名誉,甚至把东王被杀的日子定名为“东王升天节”,以示纪念。这样一来,似乎杨秀清之死与萧朝贵的死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仿佛是因为杨、萧二人完成了在凡间的任务自然升天了。可是事变的性质是一目了然的,这毕竟是明显的政治谋杀,他不可能同时保全韦昌辉的名誉。于是,北王被官方否定,在官书中不再有“北王”名号而只留有“昌辉”的名字;韦昌辉成了天京事变的责任人。对于出走的石达开,洪秀全保留了他的位置,但地位降低了,涵义也发生了改变。
洪秀全重建后的上帝家庭,分为两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他有限度地恢复起上帝家庭的旧格局。只是他在旧格局的原来位置摆放了新人。他在原东王、西王、南王的位置上,分别摆放了幼东王、幼西王(萧有和)、幼南王。但鉴于他们还是黄口小儿,于是他把自己的胞亲填充到这个层次中去。这些人是:天王的两个儿子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以及他最信赖的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这两位天王的胞兄在朝天朝主图上,和原来上帝家庭成员的继承人幼东王、幼西王位置并列,站立在荣光大殿的前排,受到特殊礼遇。第二个层次,是洪秀全为了满足天京朝臣与地方实力派将领的荣誉要求而设置的。这些人在朝天朝主图上依次排列站立在大殿的中、后排,与前排的四人有明显距离。在这个层次上,最早的成员是,首为洪仁玕,次为远走的石达开,再次为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林绍璋等。在后期天国文书上,洪秀全把这个层次的人一概称为“胞”,所谓玕胞、达胞、恩胞、玉胞、秀胞等;同时洪秀全让幼主称他们为“叔”,即所谓玕叔、恩叔、玉叔、秀叔等等。洪秀全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们是洪秀全上帝家族的成员,是洪秀全宗教意义上的兄弟。这两个权力层次的范围随时在扩大。到天国晚期,洪秀全已在第一层上添加了他的多名侄儿即王长兄、王次兄的几个儿子洪和元、洪利元等,以及两个女婿黄栋梁、钟万信。他们在朝天朝主图上,虽然不能和幼东王、幼西王等并列,但是他们站立的位置为队列内侧,把洪仁玕、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天京朝臣和地方实力派将领挤到了外侧。在第二层权力圈上洪秀全还加进了幼豫王胡万胜。[6](P673)这样,洪秀全家族的胞亲成员,都先后在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家庭里得到了位置,主要朝臣与实力派将领,也都被纳入了他设计的家庭框架之中。可是,洪秀全的计划虽然周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谐的上帝家庭并没有建立起来。
首先,洪秀全把王长兄、王次兄列入新上帝家族的第一层次,与几个原上帝家庭成员的继承人并列,这缺乏制度根据。当初,洪秀全是靠宣传上帝派他下界斩邪留正的“异梦”来树立自己的宗教地位的。这是洪秀全惟一可以使用的护身符。但洪秀全的这种自我宣传,很难比杨、萧借天父天兄下凡的降僮巫术更有煽惑力,很难取得杨、萧通过降僮获得的实际宣传效果。杨、萧巫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们能够制造一种特定的情境使会众相信他们的指令来自于上天的饬令,甚至洪秀全其“天王大道君王全”这一由教主到君主身份的转变,也必须经过天父、天兄下凡的确认[4] (P10);各级会众由普通会众到上帝选民的名义变更,也是必须经过天父、天兄的“超升”来实现[4] (P45),甚至领袖人物冯云山、秦日纲也不例外。相比之下,洪秀全仅仅把自称为梦的内容转达成圣旨,这很容易招来臣民的怀疑。因此,在杨秀清时期,洪秀全的梦境转述未能得以发挥,除了杨秀清刻意压制的原因外,其自我标榜的形式很难令人信服也是重要的原因。天父天兄下凡这种宗教制度随着天京事变而消亡,可洪秀全却不可能创造出比以前天父天兄下凡更有效的宗教仪式。虽然他确立了几个孩子如幼东王、幼西王等人的宗教地位,可他并不准备也不情愿恢复他们的前辈东王、西王原来代天父、天兄下凡的权力。他只好仍乞灵于自己1837年“异梦”的形式。但他无法像杨秀清那样创造出一个令臣民神魂颠倒、痴迷忘情的特定情境,更何况他宗教仪式的表演也并不高明。李秀成就曾说他“一味问天”,说的“俱是天话”。[6] (P507)特别是他让自己的两位兄长来为他当梦的转述见证人,则更令臣民怀疑他宗教语言的可信度。何况王长兄、王次兄被强行与原上帝家庭成员的继承人并列,在宗教意义上本来就缺乏说服力。所以,洪秀全的宗教活动,其形式缺乏普遍的认同,带有随意性、个体性、主观性的缺点,不可能有效摄取大众心理,因而难以形成集体崇拜。
其次,洪秀全虽然把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纳入他的上帝家族圈,可是他并没有真正提升他们的宗教地位。从他把洪仁玕排在石达开之前这一做法判断,洪秀全已经不再留恋金田起义时期的上帝家庭关系了。他称陈玉成、李秀成为“胞”,并不是真正上帝家庭意义上的,而只是一般的异姓结拜关系。洪秀全既然坚持以宗族关系作为建设上帝家庭的基础,那陈玉成等人的地位将永远是处在边缘上的。这一点在洪仁玕的地位问题上更能得到启示。洪仁玕是列在第二层次人物名单的第一位,且位列首义五王之一、上帝第七子翼王石达开之前。洪秀全这样做,是因为他要在洪仁玕身上体现这样的政治涵义:洪仁玕虽然是天王族弟,备受恩宠,但他毕竟不是天王的胞弟,于是不把他纳入第一层与王长兄、王次兄并列。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中,在最通天的胞亲关系与李秀成等异姓结拜关系的过渡性人物。洪秀全让洪仁玕在上帝宗教圈所处的地位与他的军师地位性质相应,其目的都旨在隔断李秀成等人对最高权力的向往。洪仁玕虽姓洪,但与王长兄、王次兄相比,他毕竟不是天王的至亲。洪秀全在后期太平天国权力分配,即“排座次”问题上用心良苦。对前期重要人物石达开,他通过把洪仁玕排在石达开之前,断然否定其原有的上帝之子的宗教地位。翼王不再被荣称“五千岁”,而称作“喜千岁”,这便和干王“福千岁”、英王“禄千岁”的意义等同。但这一切并不能逃过李秀成的眼睛。忠王抱怨道:
“朝中非我之长,长者重用者,我天王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1] (P328)
可见,李秀成把洪秀全编织的上帝家庭关系看得十分透彻。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经过与李秀成等实力派互动而形成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是一个能够调动军政各方人员积极性,协调军事行动与政权建设关系的机制。实践证明这一机制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复苏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但是,洪秀全的做法,是在破坏正趋完善的、为各方接受且运作良好的制度。他逐步强化以自己为核心、以其胞族为核心权力圈的“家天下”的宗教家庭关系,把上帝家庭凌驾于军政制度之上。这严重干扰了文武大臣在制度内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不必要的矛盾与隔阂。为了实现自己“家天下”的目的,洪秀全不断为被他所重用的亲族人员创设新的官职。如他设“殿前贲奏”安排幼西王萧有和,使此职位凌驾于掌率会议和主将集体甚至洪仁玕的军师职位之上。此类职位的设立,严重破坏了文武官员的协调合作机制。因此可以说,洪秀全对上帝家庭的建设越热衷,他对政权建设的干扰和危害也就越大。
洪秀全煞费苦心地构建他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但这只能引起无休止的内耗。洪秀全最终不仅没能建立起高效率的、使自己游刃有余的权力结构,而且,他在一次次与李秀成等人的冲突中变得日益固执,甚至连自己的族弟洪仁玕也不能容忍。他最终走入任人唯亲而绝无亲人的政治泥潭中。
总之,太平天国的上帝家庭在起义酝酿和开国初期曾经作为重要的宗教、政治制度构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后期洪秀全以自己胞族为核心重建上帝家族的努力,却因为他试图以这个上帝家庭凌驾于权力中枢之上而遭到了失败。
标签:洪秀全论文; 萧朝贵论文; 李秀成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杨秀清论文; 石达开论文; 韦昌辉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军师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