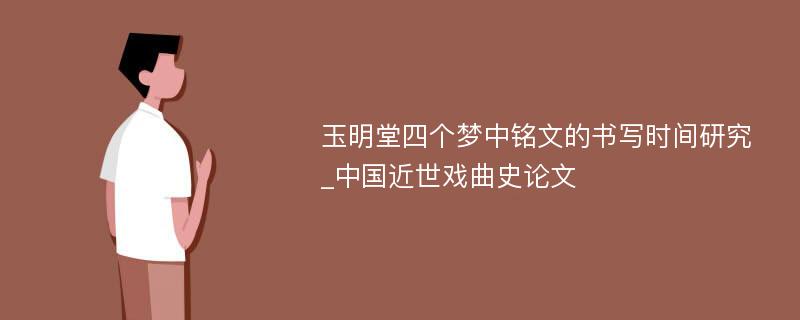
“玉茗堂四梦”各剧题词的写作时间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玉茗堂四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原非撰于一时一地。各剧卷首均有作者“题词”,但今存之明刻单行本或合刊本大多未署撰写时间,惟臧晋叔《玉茗新词四种》本,四剧的题词均署有完成的时间。臧氏为汤显祖同时代人,且两人原有交谊,故今人多将臧本所署,视作汤氏“自署”,在讨论各剧的完成时间时,亦以臧本所署为据,以汤氏诗文集所见行历,以作印证,而未曾想过臧本所署时间,是否出于臧氏个人的推断。
稍稍令人踌躇的是,臧氏改本《牡丹亭》的题词,署作“万历戊子秋清远道人题”,即万历十六年(1588),而另有多种明刊本均署作“万历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两者仅一字之别,时间正好相差十年。从汤显祖的行历来看,此剧肯定不可能完成于万历戊子,所以,一般认为,“戊子”应是“戊戌”之讹①。
最近,霍建瑜博士刊出《〈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②一文,亦据臧本所署时间立论,主张“戊子”原无讹,《牡丹亭》实成于万历戊子,署万历戊戌者或为修订本。笔者不甚赞同霍博士的观点,以为其采择的文献及具体的释读,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笔者查核了“四梦”今存明代的合刊本、单行本中各剧“题词”所署的时间,发现问题还不仅仅是“一字之讹”这么简单。因为据笔者在日本访得的明万历间金陵唐振吾刊本《南柯记》与《邯郸记》,其题词所署时间与臧本相差五至六年。这意味着四梦中,有三种剧本的题词所署,存在臧本与他本的不同,时间分别相差五至十年,不仅何者为汤显祖自题成为问题,而且此三剧的具体撰写时间也需要重新加以考虑。故撰此文,对“四梦”题词的所署时间作一个专门的讨论。
“四梦”中,《紫钗记》惟万历三十年继志斋刻本及臧晋叔雕虫馆《玉茗新词四种》本的题词署有写作时间,均作“乙未春清远道人题”,未有分歧,无需讨论。而其余三剧,他本与臧本所署时间均有不同。
(一)《牡丹亭》
《牡丹亭》,今存明刻本甚多。其录有“题词”者,可分署作“万历戊戌”、“万历戊子”及未署时间三类。
署作“万历戊戌”而可确考刻印时间的最早刻本,当推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石林居士序刊本。此本卷首为《牡丹亭还魂记题辞》,署“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此外,尚有万历间刻本、七峰草堂刻本、朱氏玉海堂刻本、槐堂九我堂印本等四种万历刻本,所署相同。另有泰昌元年(1620)吴兴闵氏朱墨印本、天启五年(1625)《词坛双艳》本,明末怀德堂刊《重镌绣像牡丹亭》,明末冯梦龙改本等,所署亦同③。今人多主张《牡丹亭》成于万历戊戌,实据此署。
但臧晋叔雕虫馆刊印的《玉茗新词四种》本《牡丹亭》,却署作“万历戊子秋清远道人题”。按:《玉茗新词四种》是臧晋叔为汤氏“四梦”所作的改本,初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书版后为吴郡书业堂所得,有明末清初印本及乾隆二十六年印本。这也是目前仅见的署作“万历戊子”的明刻本。若依臧氏改本题词所署,则《牡丹亭》是四梦中最先完成的作品,故刻印时列于四剧之首。
霍建瑜《〈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一文,列举了署作“戊子”的九种版本来证明别有一个戊子本系统,这九种是:三妇合评梦园刻本、三妇合评芬阁刻本、三妇合评绿野山房刻本、三妇合评两截本、康熙五十九年抄本、文渊堂本、清怡府本、暖红室汇刻传奇本。按:此九种均为清代抄本、刻本,其中四种显属三妇评本系统,三妇评本系统在清代得到广泛传刻,故署同“戊子”的三妇评本系统清刻本其实远不止四种④,但它们都已经远离汤显祖所处的时代。霍文又谓其新发现有文立堂刊本及荷兰莱顿大学所藏《牡丹亭记》,亦署作戊子,但未说明两本属明刻本抑清刻本。
此外,尚有多种明刊本《牡丹亭》,有题词,未署撰写时间。如著坛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秋实堂印清晖阁评点本、安雅堂刻王思任评本《还魂记传奇》、天启刻《汤义仍先生还魂记》,四种同出一源,所录题词,只署作“清远道人汤显祖题”。又有蒲水斋校刻本,署作“清远道人题”;独深居刻本,署“临川汤显祖自题”。
一般认为,此剧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题词亦撰于此年。
(二)《南柯记》
《南柯记》,以往学者著录、介绍过的明代刻本,有万历刻本、明刻《玉茗堂全集》本、著坛刻本、明末朱墨印本、崇祯间独深居刻本、明末汲古阁刻本。各本或未录题词;或录有题词,但未署时间,如独深居本仅署作“临川汤显祖自题”。此外存有清人刻本多种,其有题词者,如竹林堂刻本、带耕书屋刻本,均作“清远道人汤显祖题”,而未署时间。仅臧晋叔改本《南柯记》署作“万历庚子夏至清远道人题”。由于人们只见到臧氏刻本署有时间,亦只能据臧本所署,将《南柯记》的完成时间定在“万历庚子夏至”,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至。
笔者在日本大谷大学得见万历间金陵唐振吾刻本《南柯梦记》一种,所署时间与臧本不同。此本原经王国维、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递藏,半叶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内文题“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署“临邑玉茗堂编,门人周大赉校”;内封左右两行大字作“镌玉茗堂新编/全相南柯梦记”,中行小字作“金陵唐振吾刊”;卷首之《南柯梦题词》,署作“万历丙午夏至清远道人书”。
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臧本所署,前后相差六年。
(三)《邯郸记》
《邯郸记》,今存之明刻本,有明刻《玉茗堂全集》本、万历末年柳浪馆刻本、天启元年闵光瑜朱墨刻本、崇祯间独深居刻本、汲古阁刻本。各本或未录题词,或有题词而未署撰作时间,惟天启闵氏刻本署作“辛丑中秋前一日临川居士题于清远楼”。
按:闵本所署,实袭自臧晋叔《玉茗新词四种》所录之《邯郸记题词》。臧本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闵本刻于天启元年(1621),闵本“凡例”第二条谓:“新刻臧本,止载晋叔所窜,原词过半削焉,是有臧竟无汤也。兹以汤本为主,而臧改附旁,使作者本意与改者精工,一览并呈。”可知闵本实以臧本为主要参考,其所署时间,即从臧本来。又,闵本凡例谓“旧有柳浪馆本”,因知柳浪馆本实刊于天启元年之前,而此前之泰昌仅有一年,既称“旧”,相隔当不止一年,故柳浪馆本实刻于万历末年。而以往只笼统称柳浪馆本为明末刻本。
由于此两种署有题词时间的明刻本,均署作辛丑,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所以一般认为《邯郸记》成于是年。
稍有争议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谓“《邯郸记》据自序,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⑤,似其所见版本为题作万历癸丑者。或谓青木氏所说的四十一年(即癸丑),当是“辛丑”之误⑥,则其所据当即臧本。按:青木正儿旧藏书今归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据笔者查核,其中并无《邯郸记》版本;而日本东北大学藏有《邯郸记》二卷(丁B2—5—1·35),正文署“临川汤义仍撰,吴兴臧晋叔订”,即臧氏改本“四梦”的零本。青木正儿撰写《中国近世戏曲史》时,正在东北大学任教,故其所见者,应即此种臧氏改本。可证青木氏所说,确为移录时笔误。
笔者又访得日本立命馆大学所藏万历间金陵唐振吾刻本《邯郸梦记》一种。此本半叶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正文题“镌新编全像邯郸梦记”,署“临邑玉茗堂编,门人周大赉校”;内封左右两行大字作“镌玉茗堂新编/全相邯郸梦记”,中行小字作“金陵唐振吾刊”。首为《邯郸梦传奇题词》,署“丙午中秋前一日题于清远楼”。
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臧刻所署时间,前后相差五年。也就是说,据唐氏刻本,《邯郸记》完成时间的下限,可延至万历三十四年。
以往学者因仅见臧本署有时间,遂将臧本所署,视同汤显祖本人自署;也因为如此,当看到《牡丹亭题词》不同版本有“戊子”、“戊戌”之差别,便以为臧本存有讹字⑦。然讹字之说终属推断,并无的据。又两说均出汤氏同时代之手,理当各有其据,故亦有欲为之作调和者,如日本学者八木泽元即认为汤氏当是在万历戊子完成《牡丹亭》的初稿或未定稿,万历二十六年秋始完成出版⑧。前举霍建瑜文,亦认为《牡丹亭》实成于万历戊子,而万历戊戌则是修订本,故“《牡丹亭》存有两种版本系统:即‘戊子系统’与‘戊戌系统’……‘戊戌系统’本较‘戊子系统’本成熟;‘戊子系统’本与‘戊戌系统’本是初版本与再版本的关系”。其说实取八木泽元的观点而加以发挥,惟取证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据上所述,汤氏“四梦”,除《紫钗》外,其他三剧之题词所署时间,均存在臧本与他本之不同,故究竟何者为汤显祖自署,便须加以探讨。
《牡丹亭》之明刻本,署作“万历戊戌”者,有多种万历刻本为证,且天启、崇祯间多种刻本均从之,其与汤显祖的行历亦相吻合,应属原署。
署作“万历戊子”者,意味着《牡丹亭》成于万历十六年(1588)。这与汤显祖的行历及《牡丹亭》剧中的具体描写不相符合。
汤显祖在万历十九年(1591)贬官广东徐闻,途经广州、澳门等地,撰有《听香山译者》、《香岙逢胡贾》等诗,记述当地风土民情。他在粤地所见人情风物,后来还被写进了《牡丹亭》中,如第六出《怅眺》钦差识宝使臣苗舜宾到香山岙多宝寺赛宝;第二十一出《谒遇》述及“香山岙里巴”,即澳门的三巴寺;第二十二出《旋寄》中,梦柳梅又提到“香山岙里打包来”、“五羊城一叶过南韶”;《圆驾》出提到“岭南人吃槟榔”等;又将《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中的四川成都府人柳梦梅,改为广东广州人⑨。可知《牡丹亭》一剧必作于贬官徐闻之后。
又,王骥德《曲律》中《杂论》第三十九下:“(孙如法先生)与汤奉常为同年友。汤令遂昌日,会先生谬赏余《题红》不置,因问先生,‘此君谓余《紫箫》若何?’(原注:时《紫钗》以下俱未出)”⑩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始移遂昌,而当时四梦俱未出,可知《牡丹亭》必作于赴遂昌之后。
徐朔方先生指出,《牡丹亭》第四十一出《耽试》对考场策论题目的描写,原是影射时政,剧中考官苗舜宾出的策论与柳梦梅的回答,实以万历二十四年明廷对朝鲜战争政策的争论作背景(11)。则《牡丹亭》应完成于万历二十四年之后,亦惟有成于万历戊戌之说,方能符合。
霍建瑜博士试图用《牡丹亭》存在两个系统的版本,来调和两种署称之间的矛盾。但上述与澳门及岭南风物相关的内容,是今存所有的《牡丹亭》版本均有的;即使在臧氏改本中,也删而未尽,仍有叙及,说明臧氏所据之本即同今之通行本,而不是别有一种版本。戊子说既然不能成立,则霍文的结论也就失去了依据。
《南柯》、《邯郸》二记应非作于一时,唐氏刻本《南柯梦记》、《邯郸梦记》题词所署时间均为万历丙戌夏至及中秋前一日,这应是二剧初次付刻的时间。汤显祖与金陵唐氏书坊关系密切,唐氏刻本所署时间,必自有据,而非臆定。吴书荫先生曾指出:“万历时金陵书坊林立,以刊印戏曲而著名的唐氏书坊主人,大多来自江西金溪。金溪与临川毗邻,明代同属抚州,万历间‘四梦’的刊本,多数由江西老乡所刻印。”(12)事实上,前举《紫箫记》有富春堂刻本,疑为初刻;《牡丹亭》也有唐振吾刻本(13),可以证明吴先生所说是可信的。今观唐振吾刻本《南柯》、《邯郸》二记,题名均标作“镌新编”、“镌玉茗堂新编”,既然以“新编”为号召,可知其所刻,应在二剧问世未久。两种刻本正文均署作“临川玉茗堂编,门人周大赉校”,表明两本均经汤显祖的门人校订,亦即出自汤氏本人传授,唐氏刻本当即此二梦的初刻本。
臧氏刻本问世时(1618),汤显祖去世(1616)已经两年。汤显祖生前对他人改动其剧作深表不满,甚至以此引发“汤沈之争”,一时众多的戏曲家与评论家都对此发表过意见,影响晚明剧坛甚巨。臧氏当然也清楚汤显祖的这种态度,所以他不可能事先向汤氏表达欲作改本的意愿,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直接从汤显祖那里得到诸剧的具体写作信息,则臧氏改本四梦题词所署时间,有三剧与他本存在不同,应非是臧氏另从汤显祖本人处获得信息,而是因为他觉得当时存世的刻本所署题词时间,不符合他个人的推断,所以作出变动。而且从臧本题词的署称与他本之比较,可以看到臧氏实据他本加以改动的一些痕迹:
《牡丹亭》,石林居士等本作“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臧本惟改“戊戌”作“戊子”,仅一字之差;《南柯记》,唐振吾刻本作“万历丙午夏至清远道人书”,臧本惟改“丙午”作“庚子”,亦仅纪年有别。《邯郸记》,唐振吾刻本作“丙午中秋前一日题于清远楼”,臧本作“辛丑中秋前一日临川居士题于清远楼”,实仅“辛丑”与“丙午”纪年之别,又以为较其他三种若无作者名号,未免不谐,故添“临川居士”四字。两相比较,显然臧氏实是依据他种刻本改动了年份。即臧本与他本所署时间的不同,实是出于臧氏个人的臆改。臧晋叔在编集校理他人戏曲时作随意改写,是一贯的态度,如其编《元曲选》,即对所选剧本据己意加以改删,而以为元曲之功臣。另笔者所见日本内阁文库藏朱墨套印本《昙花记》,亦是臧氏改本,有序称“盖长卿于音律未甚谐,宫调未甚叶,于搬演剧节未甚当行,遂为闻见所局,往往有谬处。因病多暇日,取而删定焉”,将原剧五十五出,压缩为三十出(14)。至其改汤氏四梦为《玉茗新词四种》,序中亦谓“予病后一切图史悉已谢弃,闲以四记,为之反复删记,事必丽情,音必谐曲”,盖实以己意以作绳律,截鹤续凫,故清晖阁刻本称臧氏为“临川之仇”(《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凡例》)。臧晋叔将《牡丹亭》断为戊子年所作,并列于四梦之首,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值得注意的是,泰昌元年(1620)吴兴闵氏朱墨印本,署“臧晋叔评”,题词亦署作“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即不同于臧氏改本所署的“万历戊子”。臧晋叔卒于泰昌元年,此刻本乃是其乡人所刻,很可能臧氏确实参加过此书的评阅,若然,则在此刻本中,他是同意“戊戌”说的。即使此本所署“臧晋叔评”是出于伪托,或只涉及“评”而未涉及题词时间归属,至少也表明其乡人在看到臧氏改本之后,不取其所署戊子,而仍用“戊戌”,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佐证臧氏署作“戊子”,仅属个人的判断,并没有得到时人的认可。
据唐振吾所刻本,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南柯》、《邯郸》二剧的初次付刻时间应在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也正是这一年,南京周如溟的文斐堂刊印了《玉茗堂集选》十五卷。唐氏所刊二梦,正文均署作“门人周大赉校”,周大赉当是汤氏在南京任职时所收的“门人”,而且很可能就是周如溟一族中人。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唐振吾刻本的来源应当是十分可靠的。不过,细观此两种刻本,书版内间有剜改痕迹,则此本原版虽印行甚早,而今传本之实际印行,也可能较晚,并且经过剜改(15)。但题词所署处并无挖改痕迹,所以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南柯》、《邯郸》二记,若按臧本所署,其创作时间相差不过一年,今人已疑其间隔过短,略显仓促,惟别无可证,只能姑依臧氏之说。今据唐氏刻本《南柯》、《邯郸》二记题词所署,与臧本存在着五年到六年的差异,即其下限可以放宽到万历三十四年,则其创作时间,自当重新斟酌。
徐朔方先生所撰《汤显祖年谱》,于万历二十八年设“夏至,作《南柯梦记题词》”一项,注谓“明刊臧懋循刻本题词署‘万历庚子夏至清远道人’。传奇同时作”。又引《答张梦泽》信:“谨以玉茗编《紫钗记》操缦于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盖惟贫病交连,故亦啸歌难续。”徐谱谓“张师绎任新喻知县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此信作于明年”(16),即认为此信撰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此封尺牍,徐朔方先生笺校本《汤显祖诗文集》收入卷四七,笺曰:“据《玉茗堂文》之八《渝水明府梦泽张侯去思碑》,张师绎任新渝知县三年,万历三十年以丁忧去职。此信作于万历二十八年,时《南柯记》已成,《邯郸梦》犹在写作中。”(17)则又以为此信撰于万历二十八年。
按:张师绎,字梦泽,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十八年任江西新喻知县,至三十年夏丁忧离去,汤显祖为撰《渝水明府梦泽张侯去思碑》。故《答张梦泽》一信,必作于此三年间。信中既称“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则《南柯记》亦必成于这三年间。徐先生因只见到臧氏改本之题词署有撰写时间,所以把《南柯记》的完成时间定在万历二十八年夏至;至于《答张梦泽》一信的写作时间,则在万历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间徘徊不决。其实,据徐谱,汤、张二人万历二十八年方是初次定交,则此信当撰于二十九年或三十年初。而《南柯记》的完成时间大约在万历二十八年左右。这一点上,臧氏将题词改署作“万历庚子”,倒是与此剧的完成时间大约相符;只是臧氏据唐本改删而坐实为是年“夏至”,仍略有不妥。
汤显祖又有《与钱简栖》一信,谓“上巳入章门一月,张相国、丁右武念兄甚。……贞父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如醉玉茗堂中也”(18)。此信已经提到“四梦”。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年谱》于万历二十九年引此信,并有解释谓:“据诗卷二(一六)《丁未上巳,同丁右武参知、王孙孔阳、郁仪、图南侍张师相杏花楼小集,莆中蓝翰适至,分韵得楼字》,事在万历三十五年。贞父黄汝亨内征在万历三十三年,当时‘四梦’俱全,且有‘善本’矣。”(19)年谱于三十三年再引此信,谓作于是年;又《汤显祖诗文集》卷四七收录此尺牍,笺语亦云:“作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20)
按:此处徐先生似未注意到所述存在矛盾。此信既述及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上巳发生的事情,则自不可能作于万历三十三年,也即意味着万历三十三年时还未必有“四梦”善本。若此信作于万历三十五年之后,则与唐振吾刻本二梦题词署作万历三十四丙戌并不矛盾。或许正因为唐氏刻本问世,意味着“四梦”全部有了刻本,所以汤氏才会不无得意地对钱简栖说,可于西子湖头,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如醉玉茗堂中吧。
本文的结论是,臧本四梦题词所署时间,并不能直接视作汤显祖本人自署,而是臧晋叔参酌当时所见版本情况,所作出的新的判断。这种判断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如《牡丹亭》不可能作于万历十六年戊子,因为它与剧中所描写的汤氏在万历十九年之后在岭南的所见所闻存在矛盾;其他多种明人刻本题作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这应是汤显祖本人自题,《牡丹亭》即完成于这一年,这一通行的结论仍是可信的。而臧本题作万历戊子,也并非是一时粗心造成的“一字之讹”,而是出于臧晋叔个人主动的推断,但从剧本内证看,这一推断不能成立。唐振吾刻本《南柯梦记》,其题词署作“万历丙戌夏至”,当是指付刻的时间,参照汤显祖的诗文,它应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这与臧本所署的时间基本相合,说明臧氏在改署题词时间时,也确曾对四梦的具体写作时间作过某种考量。另据唐振吾刻本《邯郸梦记》题词所署,并参考汤显祖的《答张梦泽》信,《邯郸记》的完成时间,应在万历工十九年至万历三十四年间,至少可以确定其题词撰于万历三十四年中秋前一日。参照《牡丹亭》、《紫钗记》的情况,将此剧的最后完稿时间定于此时,亦无不可。至于此剧究竟完成于何时,仍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注释:
①参见徐扶明《汤显祖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②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第77—85页。
③此处所列版本,主要参考日本学者根山彻的《〈牡丹亭还魂记〉版本试探》,为其所著《明清戏曲演剧史论序说》第六章,日本创文社2001年版,第254—291页;郭英德《〈牡丹亭〉版本现存明清版本叙录》,《戏曲研究》第7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同时也采择了霍建瑜《〈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一文所列的“戊戌系统”本。并参见拙编《日藏中国戏曲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28页。
④参见拙编《日藏中国戏曲综录》,第118—126页。
⑤见王古鲁译著、蔡毅校订本《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0页。
⑥参见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⑦见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2页;又见《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徐朔方集》第四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4页,较前一版本有所增补。
⑧见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谈讲社1959年版;另有罗锦堂译著本,香港龙门书局1966年版,第423页。
⑨此点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年谱》及其附录《玉茗堂传奇年代考·牡丹亭》已有述及,《徐朔方集》第四卷,第487页。亦可参见陈梅雪《汤显祖的戏曲艺术》,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第43—46页。
⑩《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11)参见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7页。
(12)见吴书荫《“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戏曲研究》第72辑,第8页。
(13)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1页。按:毛氏未说明藏处,其依据不明,原本存处不详。
(14)参见拙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242页。
(15)参见金文京《〈邯郸梦记〉明万历间唐振吾刊本初探》,李晓、金文京《邯郸梦记校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页。
(16)《徐朔方集》第四卷,第391页。
(17)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页。
(18)(20)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第1466页。
(19)《徐朔方集》第四卷,第4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