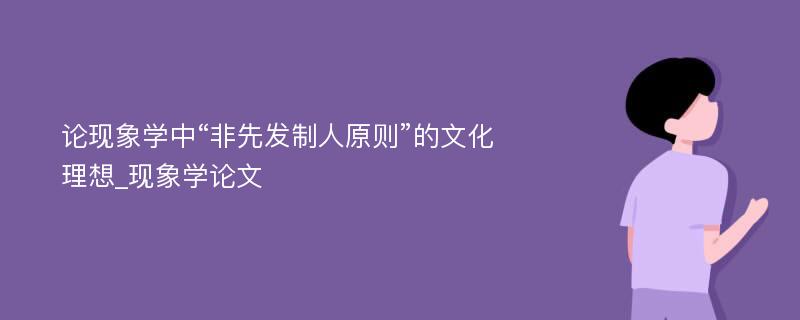
论现象学“无前提性原则”的文化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前提论文,原则论文,理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3-0012-04
胡塞尔一生十分关注文化学,表面看来与文化学离得最远的“纯粹逻辑学”,尤其是它的“无前提性原则”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现象学的著名纲领“回到实事本身”(或“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表明了一种新的文化转向的口号(注: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这也是在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中提出来的。尽管“回到实事本身”也许不是什么高蹈的哲学理想,但在各种未经批判的理论及其前提充斥理论市场的时代,“回到实事本身”作为现象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就具有了浓厚的理想色彩,尤当它的目的和方法——即“为什么要回到实事本身”以及“如何回到实事本身”——与“严格科学的哲学”和“无前提性原则”相联系时,现象学的这种理想(尽管笛卡尔等人对此曾有过不彻底和不自觉的意识)就变得十分突出了。而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就是理解现象学的文化内涵和它的基本精神的人口,由此,胡塞尔后来所说的“悬搁”和“还原”等等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胡塞尔认为“一项具有严肃的科学性要求的认识论研究必须满足无前提性原则”,是因为“现象学的对象是‘纯粹’的认识的本质结构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组成。在它的科学确定中自始至终都不包含丝毫有关实体存在的判断;就是说,任何形而上学的论断、任何自然科学的论断以及特殊的心理学论断都不能在它之中作为前提发生效用”(注: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道家的“绝圣弃智”,而是一种现象学的目光转向:转向实事本身(或者转向“内在”)。无前提性原则对先入为主的哲学性理论化(philosophical theorizing)的弃绝,是为了对现象本身进行更纯粹的描述,并让思想仅仅关注内在直观中的被给予者(注:参见Dermot Moran,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London:Routledge,2000,p9.)。因此在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中,本身就开启了一条“正确”理解胡塞尔所谓“实事”的道路:它不是日常语言中的实在论立场所理解的那种存在物,而是指直观中的被给予者或内在的意向对象和意向相关物。不幸的是“‘走向事物’这个号召有时被过于天真地解释为‘转向外在世界的客观事物’,而不是转向‘主观反思’”(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0页。),而且类似“天真的”的“误释”还经常发生在对其后期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上。其实胡塞尔自己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现象学”条目中早就说过:“对意识到的世界的普遍悬搁(对它的‘加括号’)将对相应主体而言始终存在着的世界从现象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但取代这个世界的位置的是这样或那样被意识到的(被感知、被回忆、被评判、被思考、被评价等等)世界‘本身’,‘括号中的世界’,或者,取代这个世界或个别的世界事物的位置的是各种类型意识的意义(感知意义、回忆意义等等)”(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70-171页。)。
如果说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原则意味着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的要求,无论这种中介是来自权威,还是来源于习性,也就是符合“要暂时排除先验认识之范围的诸问题的必要性”,那么它对实事的诉求所搭起的是内在的意向性的舞台,或者说进行了“向内”的转向。胡塞尔后来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进一步细化了无前提性原则的内在性转向,他说:“在先验还原的意义上,这无疑意味着:它在开端上不能设定任何别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这个自我和包含在这个自我本身中的东西,以及连同一个不确定的可确定性之外”(注: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41、215、9页。)。胡塞尔无前提性的向内思考,是要构建先验的主体性或先验的唯我论,进而对世界进行构形性的把握,因此所谓“无前提性原则”(它的具体实施就是其后期的“悬搁”)的用意就很明显了,胡塞尔在对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和奥古斯丁的箴言的思考中,表达了这种无前提性原则的功用:“人们必须首先通过悬搁而放弃这个世界,以便在普遍的自身沉思中去重新获得它。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不必外求,请返回你自身,真理就寓于人的内心’”(注: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41、215、9页。)。
在胡塞尔那里,无前提性原则既有可能性,又是任何哲学理想的必然要求,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理想的基本保证。就其可能性而言,一方面有笛卡尔和康德等先哲所开辟的先验道路(不过胡塞尔在无前提性原则的“批判”性方面更为彻底:如果说康德所批判的主要是“纯粹理性”,那么胡塞尔批判的是“一切理性”,这种批判不仅能使康德理想中的形而上学成为“未来的”科学,而且能使整个哲学成为科学),另一方面也有现象学的“悬搁”为具体的手段。而无前提性原则的必然性其实就是思想本身的必然性,也是思想的禀性:纯粹地对无限的追求。在胡塞尔看来,真正哲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达成一种“建立在最终可设想的无偏见之上的哲学”,这也是“一种在现实的自主性中由它自身最终产生出来的明见性所形成、因而具有绝对的自我负责能力的哲学”(注: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41、215、9页。)。哲学如果舍弃了无前提性原则,那么就不再是哲学,至少不再是纯粹的哲学,而只是一堆意见或成见而已(倪梁康先生后来在《现象学概念通释》中把“无前提性”译成“无成见性”,可为明见)。
胡塞尔的无前提性原则同海德格尔——德里达的“解构”很相似(在这一点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学理上的继承关系?),“在胡塞尔那里‘没有前提’所表示的只是企图消除未受彻底审查的前提,或者至少从原则上说是未被提供给这种审查的前提。因此,所涉及的并不是取消全部前提,而只是取消在现象学上未被澄清的、未被证实的以及不能证实的那些前提”(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1页。)。胡塞尔的无前提性原则或悬搁方法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一样,它的“破”(包括对心理主义的“破”)是为了“立”,即“完全不受超越解释影响地获取纯粹”,并以此建立严格科学的哲学,为这种哲学奠基,实际上,“对于理解胡塞尔整个发展过程及他的哲学思考最终所承接的品性来说,最富有启发性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精心抉择,这一抉择牵涉到他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性哲学打下基础的规划。”(注:劳尔(Quentin Lauer):<胡塞尔的科学理想>,见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4页。)即便在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中,胡塞尔对“哲学究竟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都是十分清楚和自觉的(注:参见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虽然学界一般都认为胡塞尔的思想经历了几次转变,但从其早年“前现象学时期”的《算术哲学》到晚年的《危机》,他对绝对、纯粹、彻底的追求都是一以贯之的,坚持不懈地从各个可能的角度追求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因此简单地说,胡塞尔无前提性原则中所蕴含的现象学理想就是要解决这个千百年来一直未得到完满解决的问题: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如何可能的?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哲学使命,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样的科学才是“严格的”,或者像海德格尔那样追问:什么是科学?对于“严格”这一概念,尽管胡塞尔“从来也没有详细论述过这个无所不在的名词的意义”(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9、219页。),但从前面已有论述可以简单地说:严格即纯粹和彻底。至于“科学”的含义,胡塞尔欲拯救的断然不仅仅是极度扩张之后已颓落的“科学”,而是古希腊式的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一种彻底的,并因而引为哲学榜样的激进(按:彻底?)精神重新恢复从绝对奠基出发的真正的科学的观念,即古代柏拉图的观念,这也就是说,追问作为包括所有实证科学的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前提的最初的基础”(注:胡塞尔:《<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导论》,张庆熊译,载于倪梁康编:《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39页。)。除此之外,其间更有深意在焉。在“上帝之死”以后,面对纯粹性和确然性的丧失,人类精神如何安身立命就成了大问题。因此,与其说胡塞尔提倡“无前提性”,不如说他勇敢地“面向”了无前提性,为生活、认知、意识等“现象”寻找可靠的基础(注:在这一点上,德里达评论道:“现象学,在理想性的形式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同样是一种生命的哲学”(《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页)。)。尽管他对认识的批判是要超越出“人的认识”之外(注:胡塞尔对“自然思维”的认识观念批评道:“因而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且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物的自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3页)。),这自然会遭到猛烈的抨击,但人间还有什么能比重建万有的根基更伟大的事业呢?
胡塞尔在“欧洲人的危机”和“科学的危机”中,提出了解决这种危机的方向:追求严格科学的理想所设置的无限的目标。或者说如果人类要正视已经到来的危机,就必须在科学哲学的精神中重新诞生一次(注:劳尔:<胡塞尔的科学理想>,见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8页。),为思想订立“新约”(在此意义上,“无前提性原则”是不是就相当于精神世界的“大洪水”,或者彻底清除[尽管只是暂时的“悬搁”]理智世界中的“恶”的“灭世洪水”?)。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主张“不能为先验哲学附加任何前提”,(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或许就是为了达到永恒的纯粹性,以免思想(甚至人类自身)陷入变动不居的无序经验之流中,结果就会丧失一切。从肯定的方面看,无前提性原则在人间世的理想,就是“保持纯粹,导向无限”(注:“它(按:指现象学经验)自身本质中显然包含着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在方法上保持纯粹性的前提下连续地导向无限”(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
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注:海德格尔的组诗<从思的经验而来>第六首,载于《海德格尔选集》,同前,下卷,第1159页。),胡塞尔现象学恐亦不能例外。但正是这些伟大的迷误,或者“把他引向绝路”(施皮格伯格语)的那些现象学理想或目标,才充分显示出他的伟大之处来:胡塞尔敢于面对哲学的困境,在文明的危机和人性的重建方面自觉担当苏格拉底式的“牛虻”(注:施皮格伯格说:“胡塞尔越来越多地看到并强调这种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责任。实际上胡塞尔把哲学家称作是人类的公仆(Funktion?re):他们通过检验我们受到威胁的我们的基础,为重建人性准备基础。胡塞尔按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精神,以一种非常乐观的心情把哲学的这种使命描绘成是道德上‘复兴’的使命”(《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3页)。),并勇于碰撞“有限—无限”这个永恒的问题,勇敢地踏上了“以有涯随无涯”之旅,“由他的局部成功以及他的失败而产生的许多灵感就保证了使他具有在一种新的哲学研究道路上的‘可尊敬的创始人’的地位”(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9、219页。)。而且,“有限—无限”的问题对于人类的有限理性来说是永远不可解决的,但又是必须要面对的,于是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就像历史上众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用自己“西绪弗斯式的苦役”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增添了华美的篇章。因此下面罗织的一点点“意见”,不仅丝毫无损于胡塞尔的伟大,恰恰反衬出胡塞尔思想的巨大魅力。
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在纯粹逻辑学(或现象学)中的贯彻并不彻底,或者说无前提性原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任何研究中,无前提性原则都是一种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从不严格的角度来说,无前提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原则,或者说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就是它的前提性原则。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既无前提,又何以出发以及何以构造?所以德布尔认为:“《逻辑研究》并没有澄清这样一个悖论:在世界中并且是世界之一部分的人同时又构造着世界”(注: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6页。)。胡塞尔自己只是到了后来的《危机》时期,才提出了这个悖论,并进行了消解(注:参阅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6-226页。)。但这个消解也许只是暂时的,或者只是在现象学内部的消解,因为“意识”本身就是现象学未曾言明的隐含前提,而这个前提就从外部破坏了现象学内部的纯粹性。而且,这个前提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我有意识’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命题”,维特根斯坦也类似地反对“我知道……”之类的说法(注:参阅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页。)。就无前提性原则(或普遍悬搁)这种温和的不是怀疑的怀疑态度来说,可能即是维特根斯坦所批判的那种在理论上就不可能的“对一切的怀疑”,因为“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注: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On Certainty),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以下简作OC。),理由就在于“如果你想怀疑一切,你就什么也不能怀疑。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设了确实性”(OC,§115)。在这里,当然不存在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谁高谁低的问题(即便存在,我也看不出来),而毋宁说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性,即对确实性和纯粹性的追求(维特根斯坦也追求纯粹性或“无条件可靠的东西”,这是我们借以有把握地、不带任何怀疑地行事的根据,OC,§196)。我们或者可以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有充分理由根据的信念的基础那里存在着没有理由根据的信念”(OC,§253),这和海德格尔对“根据的本质”的探讨一样,都可看作是不同形式的“无根据颂”,胡塞尔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亦当作如是观:这在面对“无限”时应当采取的一种态度。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些态度分成五种:神学的态度,先验的态度,实践的态度(比如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等),经验的态度和与这四者相对立的“否定的态度”(或回避的、解构的态度)。胡塞尔坚定地站在先验的立场上,用“无前提性原则”这根探针寻找“无限”中的可靠基础。
胡塞尔在生活世界路向上的“思”的推进工作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辞世了,因此从生活世界或生活意义的可能性角度来看,胡塞尔在批判时代精神的错误倾向以及对现象学的艰苦思考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可能还是一朵尚未开透的花蕾。在一定程度上说,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等人接着胡塞尔的路子往前走,在某些方面多有推进(注:参阅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丁耘译,载于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112页。他们之间的差别也许主要不在基本理想之上——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同一的,而是在于实现这种理想的基础和方法,以及对这种理想进行某些调校。)。
胡塞尔对纯粹、彻底、严格哲学的追求,其实是哲学和哲学家“自我负责”(注:参见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9页;以及《<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导论》,张庆熊译,载于倪梁康编:《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36页等处。)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外化,而这种自我负责精神还包含了对现实的严重关切,胡塞尔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施特劳斯说:“在我们的世纪中,没有一个人像胡塞尔那样如此清晰、纯粹有力、大气地主张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注: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丁耘译,载于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为什么胡塞尔要如此主张,其间就包含着一种“彻底自律的精神气质”和“伦理动机”,胡塞尔本人越来越强调地提到一种应该详细说明的伦理动机,这就是人对于他自己和他的文化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只有通过那种给予我们的全部主张和信念以尽可能充分说明的科学和哲学来满足。具体说来,“胡塞尔排除了使许多思想家感到气馁的原因,他消除了对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忧虑,他给年轻一代哲学家注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而且胡塞尔的鼓舞作用和他对哲学未来的信心传播给了许多卓越的哲学天才,这是意志幸运的历史命运”。(注: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上卷,第129页。)这就是胡塞尔“理性的英雄主义”为时代精神所赐赠的福荫。因为胡塞尔的思考是既是现象学的起点,也是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历史的起点,更是人类迈向“无限”的新起点。
尼采把自己的身体存在变成了一种思想,采取一种尖锐形式践履自己天才的洞见,最后以自身对未来文化的献祭昭示了他所理解的一切:把自己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注:尼采在精神崩溃后写下的最后一张纸条上就署名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见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载于刘小枫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第319页。)而海德格尔则跪在十字架下祈祷,并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漫游于心灵的废墟中向世界宣布着真正的福音,期候着上帝的到来。那么,胡塞尔就是海德格尔后期苦苦期候和寻找的那种“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的人,更是勇敢地“探入于深渊”的人。(注: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载于《海德格尔选集》,同前,上卷,第408页。对深渊的强烈感受,也许就是二十世纪“陆沉”意象(image of“collapse”)如此突兀的一个根本原因。)不但如此,胡塞尔还试图把一座“没有了至圣的神”的庙宇,(注:黑格尔曾打过一个比方:“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见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上卷,第2页)。这里化用黑格尔这个典故,来概括“上帝之死”以后的思想状况。)改造成“生活世界”的场所。或者说,胡塞尔不是在等待,(注:胡塞尔的“构造”和“直观”等思想即为明证。比如就直观而言,“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种‘直观’不应仅仅是对于某种具有灵感的启示的消极等待”(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67页)。)而是发下了宏大的誓愿,企图以移山之力填平“超越性”陷落后所留下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