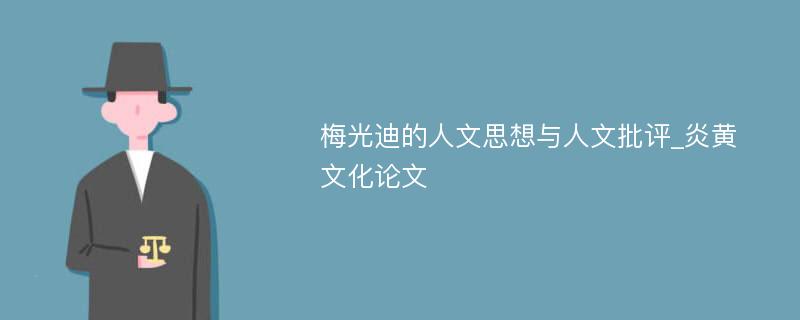
梅光迪的人文思想与人文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批评论文,思想论文,梅光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1—0013—08
一
在1945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时年已经55 岁的梅光迪又为自己拟订了一个不能不说宏大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此计划内容就像他最初所宣扬的人文主张那样涵盖中西、通贯古今。其中有关中国文化部分,梅光迪说:
予近年来蓄志关于中国文化撰述,有以下数种,曰“洛下风裁”,述东汉末年党锢事实;曰“正始遗音”,述魏晋清谈状况;曰“韩文公评述”,曰“欧阳公评述”,曰“袁随园评述”,曰“曾文公评述”,曰“中国两大传统评述”。其中“韩文公评述”,可阐明吾国自唐代以来之文学源流;“欧阳公评述”则可窥见北宋文化及其士大夫生活之一斑;而“袁随园评述”,可描写乾嘉极盛时代之景象;“曾文公评述”则可将中国固有文化最后之光荣表露作一颂词,作一总结。
不仅如此,雄心不已的梅光迪还计划将上述各书“用中英文并写,一以昭示中国,一以传诸西方”[1]。
与上述有关中国文化的撰写计划相比,梅光迪这次为自己拟订的有关西洋文化的撰写计划同样庞杂得惊人,几乎涉及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主要的思想潮流和主要作家:
吾拟作以下各种之介绍,曰“近代西洋思想述要”,将自文艺复兴以来之思想于人生上发生效力者,如理智主义(Rationalism)、 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以及十九世纪至今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帝国主义等,作一简要说明。纯文学方面则曰“近代西洋文学趋势”,叙述文学上之各派……又欲取近代作者声势最显赫者二三十人个别评述。其名单暂定如下:Voltaire、 Rousseau、
Johnson、Goethe、Schiller、Scott、Byron、Richardson、Wordsworth、MadameStael、Chateaubriand、Hugo、Heine、Carlyle、Emerson、 Arnold、Tolstoy、Ibsen、Nietzsche、France、Whitman等。
这样一份涵盖中西、贯通古今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不要说对一个年已半百之人,即便是对一个拥有充裕时间和旺盛精力的年轻人来说,多少也是过于庞杂和散漫的。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纪之初的《留美学生季刊》上由胡適编辑的、从梅光迪的日记和与胡適往来信函中摘录下来的那些评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人物的文字,只要看一看《学衡》创刊初期梅氏所发表的那些批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梅光迪这份研究与写作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呢?
遗憾的是,当梅光迪因此而祈祷上苍能够赐予他“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时间,以完成上述计划的“十之三四”的时候,殊难料到的是,上天竟然只给了他不到一年的时间!也许是他已经预见了大限将至,并因此而愧感于往者与来者,才匆匆忙忙地为自己制定了这样一个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安慰色彩或者理想色彩的研究与写作计划?不管怎样,至少梅光迪自己不应该感到吃惊的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友人或同事编辑出来而且未能公开出版的一本《梅光迪文录》,竟然总共只收录了十几篇文章、十万字左右!尽管有人称梅光迪“深恶标榜,文不苟作”,但是,对于一个直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并一度置身于论战中心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对于一个作为一种个人思想表达方式的批评处于极度膨胀发达时代的文化批评者来说,即便是不与同时代那些著作等身的人相比,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教学写作生涯与十几篇文章、十来万字的文字成果之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达成平衡的。但这是事实,是梅光迪一生研究与写作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还有一些早期文论没有被《梅光迪文录》收辑进来,但总数量也不会有多大的突破了。
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留学异域之时的梅光迪在致好友胡適的信中所时时流露出来的那种少年豪气和远大抱负,只要稍微领略一下20年代初梅光迪对“新文化者”所展开的那些激烈犀利的批判,我们就不能不为如此单薄的一本《梅光迪文录》、为梅光迪一生的学术道路和成就——他那未曾完成的思想而感到惋惜。惋惜之余,禁不住生发出一些感慨。排除天不假年、时局动荡的因素,梅光迪自己又该为他未遂的理想和宏大的计划担负多少责任呢?
除此而外,对于一个并不仅仅把自己视为文学批评家的现代人文思想的鼓吹者和倡导者来说,如果说吴宓尚有资格把主持《学衡》、组创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视为自己一生值得欣慰的几件现实事功的话,梅光迪则终其一生,可说是一事无成(注:梅氏主持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及后来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应不在此议论之列。)。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留美中国学生中,梅光迪是最早发现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及其学说的现代价值的人,是至为痛彻、至为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近现代一步步走向解体和流散,并为此而扼腕叹息的人,是最有计划地要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转换作不懈努力的人,也是在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一直表现得最无畏、最坚决的人。
对于留美时期坚持以孔孟思想的“原意”以解近世学术与思想之弊的梅光迪来说,白璧德的出现预示着他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机。
转学到哈佛大学研究院之前的梅光迪,与他后来的论敌、新文化的鼓吹者胡適的思想实际上是有“颇多相合之处”的,至少在对当时乃至更早一些时期知识界状况的不满上,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在该时期,梅光迪致胡適的信札中经常出现“字字如吾心中所欲出者”,“极合吾意”,“与弟意正合”一类的文字。这些文字都与胡、梅二人所讨论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相关(注:上述引语未加注者均见1915年《留美学生季刊》及胡適的《藏晖室札记》。)。而梅、胡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始现于文言、白话之争。据梅光迪自称,在1915年读到白璧德《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一书之前,自己“也曾陷溺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思想”,但是既经皈依于白氏的新人文主义,“才终身未改其操的”[2]。所谓“当时流行的浪漫思想”, 结合梅光迪这一时期与友朋的论学以及他自己的论述,可以知道主要是指那种思想上的怀疑主义、重估传统价值的现代意义的自由精神和主张,也包括当时在一般知识者中及社会上所流行的“世界潮流”,即“大同主义、平民主义、社会主义”[3]。但是,这一时期梅光迪思想上的“浪漫”, 主要表现在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上,而不是他自己具体的思想观念上。譬如,梅光迪曾经断言,“不推倒汉宋学说,则孔孟真面目终不出也”,但他并没有同时指出什么是所谓的“孔孟”真面目。在一封写给胡適的有关孔教的信函中,梅光迪毫不掩饰地抒发了自己的“原初主义”(Primitivism)情怀,“仆思吾国风俗,其原始皆好, 惟二千年来,学校之制亡,民无教育,遂至误会太甚,流弊遂深。吾辈改良之法,尚须求其原意。盖原意皆深合哲理,无所不实用于今也”。梅光迪显然是把“原意”局限于原初的思想和经验,仅就此而言,他算得上是一个文化思想上的复古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欧文·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此时所谓的“复古”,并不是复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有的“古”,而是求孔孟之说的“原意”,或者说原初的、原典的“真理”。
在梅光迪看来,一部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所谓的原典思想和原典精神不断被遮蔽、谬传、误解的历史,所以,作为一个“有血气的男子”,“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这种文化思想上的求原和存原的主张,不仅不同于胡適的进化的历史观和文化发展观,不同于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的倾向(至少是启蒙思想的主流倾向),而且与他后来所膺服的白璧德的人文思想也不尽一致。
但是,梅光迪却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当时的思想寻找到了一个临时性的归宿或者出路,为自己纷乱的思想清理出了一个可供暂时休憩的空间,他自以为在那种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长廊里,既找到了造成今日中国思想文化日渐衰落的根源,也找到了医治这种衰落的方法。梅光迪因此而进一步地阐发了自己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将国内思想文化界正在展开的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评归咎于批评者对国情的不了解,对孔教原意的不了解,对孔孟原意和原典精神不断被遮蔽的历史进程的不了解。“试观吾人自家执笔之徒,有几人能熟悉本国情形能代表吾人者乎?”“今之妄人,以国势之不振,归咎于孔教,从而弃之,而卑辞厚颜,以迎合方兴之外教。”所以,在梅光迪眼里,只有那些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的人,“乃为豪耳”(注:上述引语未加注者均见1915年《留美学生季刊》及胡適的《藏晖室札记》。)。不过,也许正是这种孤木独厦、力挽狂澜式的文化英雄意识和对孔孟原初思想的坚定信念,将梅光迪一步步推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面,也一步步推向近现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反面。一种游子对于故园传统文化的精神皈依和心理眷念,被简单地放大成为对于中国文化原典精神的学术皈依和精神信守,这是梅光迪在走近白璧德之前自我呈现的精神处境和思想状况,这种思想在梅氏接触到白璧德思想之后,迅速地与白璧德的人文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并最终决定了梅光迪一生的学术路向和学术成就。
有学者认为,梅光迪的思想“半自因袭、半自白璧德,或者未必深入”[4]。这种认识是符合梅光迪一生的思想实际的, 前两者说明了他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即历史文化和批判意识;后者则大略地指出了他对这些历史语言资源理解体会的深度。白璧德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化、尤其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Scientific humanitarianism)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泛情人道主义(Sentimental humanitarianism )(注:科学人道主义和泛情人道主义这两个概念均出自白璧德的《两种类型的人道主义者》一文,见白璧德所著的《文学与美国大学》一书。)传统的清理和批判,是依托于他对古希腊人文传统的清理认同来展开和完成的(当然,就像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否则他就不会区别于他的那些思想上的“敌人”[5]),尽管白璧德对古罗马哲学、基督教、 早期印度佛教以及中国的孔孟思想都保持着知识上的兴趣,并成功地将这些人类思想文化遗产转化而成为自己的思想语言资源,并成为他抵御、批评西方现代思想语言的依凭;而相比之下,梅光迪当时则是站在昌明孔孟“圣人之学”原意的立场上,对“汉宋学说”展开批判的。这些批判在思维方式上,与白璧德显然是有些“暗合”的。与此同时,对于白璧德思想学说的皈依,又使得梅光迪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自己在思想上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正大力宣传、方兴未艾的西方新学的批判。
梅光迪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反现代倾向”或者思想文化上的反进化观倾向,又与他性格上的某些成分纠缠在了一起,对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和现实人生都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这一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集中表现在梅氏对胡適的批评上。
应该说,梅光迪与胡適之间的分歧,在胡適尚未完全清理出自己对于文言白话的思想主张之前,至少在胡適还没有明确、系统而且大胆地提出他的白话文学主张之前,也就是胡、梅之间的那场文言白话之争展开之前,并非已达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但是,当胡適因文学改良主张而在国内一时暴得大名、声誉鹊起的时候,梅光迪对于胡適的批评就已经不仅止于文言、白话之争了,也不仅止于思想文化范围了。梅光迪迅速地、单方面地夸大了两人之间的观点分歧,并由此引发,将自己在思想上和精神立场上完全推到了与新文化运动截然对立的位置。如果按照白璧德的另一个弟子艾略特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意见,梅光迪这种文化行为本身就是反“人文主义”的(注: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T·S·艾略特《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一文。该文收入《T·S·艾略特文学论文集》中,由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胡適的才华与见识,留美时期的梅光迪已多有领教,并且最初一直是深怀敬佩的。在当时一封致胡適的信中,梅光迪真诚而又略显夸张地写道,“中人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正所谓梦梦我思之者也”;在另一封信中,梅光迪同样毫不掩饰地写道,“足下论阴阳极透澈,论大同小康亦详尽,谓孔子不论来生,以为诚实不欺,尤令吾叹赏”。此时的梅光迪还是在坦诚而努力地与朋友谈学论道,毫无后来的门户之私见。然而,短短几年之后,梅光迪对以胡適为代表的提倡新文化者的评价,竟一变而成了“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其锋芒所指,明眼人一目了然。而个中原由,却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就是这篇《评提倡新文化者》,因其言辞激烈,锋芒毕露,被柳诒徵评说成“《学衡》一出,言者不敢置喙”[6]。 其文风的强悍凌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或许正是有对胡適从最初的羡慕钦佩到后来的不满与妒忌,才会有梅光迪在留美学生中“到处招兵买马、搜求人才、联络同志,准备归国后与胡適作一全盘之大战”的计划与行动[7],才会有当别人把吴宓引见给梅光迪时, 梅光迪所作的那番“慷慨流涕”的诉说和“今彼胡適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的责骂。梅光迪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就是在这种个人情感的笼罩下一步步展开的。这种在文化批判的面罩下偷渡个人私愤的举动,与他的论敌胡適相比,显而易见缺乏一种学术大气。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偏狭最终成为影响梅光迪一生学术成就的致命伤,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梅光迪偏偏自认为是在行批评之正道。
梅光迪此种“领袖”意识的强烈和性格上的偏狭以及争强好胜,还可以从他与吴宓之间初和终离的朋友关系上窥见一斑。吴宓对于白璧德及其思想学说的认识是因为梅光迪的介绍;而吴宓推掉与北京高师的前约,归国改就南京高师的聘请,也是源于梅光迪的力劝。同梅光迪一样,吴宓也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宏大理想来到当时文化思想空气还相对沉闷的南京的。但是,吴宓绝对没想到,他与梅光迪之间的分歧会来得那么快,并会发展到彼此难以相互共处的地步。细察其中原委,表面上看,引发两个争执的是彼此在《学衡》栏目内容安排上的不和,实际上恐怕与吴宓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学衡》编辑一栏,“违背”了《学衡》同人最初的约定,从而引起了力倡学术人格的梅光迪的不满有关,以致于仅在《学衡》创刊一年后,梅光迪就愤然宣称:“《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8]1924年, 梅光迪干脆离开新旧之争还方兴未艾的中国,到美国投奔他的导师欧文·白璧德去了。所谓与胡適“大干一场”的宏愿,到此也只能是不了了之、抛给别人了。
在《吴宓自编年谱》中,有一小段文字涉及到对梅光迪的评价,“梅光迪君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盖一极端个人主义者与享乐主义者耳”。曾经一度为梅光迪同志的吴宓当然不会不知道自己该为这种评价所承担的道义责任,不会不知道一个人文主义者与浪漫派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之间的思想界限和精神界限。但是,吴宓的上述评价虽略显刻薄,却并非无中生有。我们只要翻看一下梅光迪1945年2月以后的日记,就可以发现, 梅光迪在当时物质供应极度匮乏的境况下,却依然保持着日常物质生活上的美国标准以及每天因此而耗费的个人精力(当然,这与当时贵州的物价昂贵以及大学教授的生活清贫也不无关系)。不仅如此,从这段日记中,我们还可能看到梅光迪对于自己当时所担任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身份的在乎、平素读书的漫无边际以及笔头的疏懒。王焕镳在《梅光迪文录·序》中,称梅光迪“春容间旷,极趣盎然,出辞隽永,辙轰座人”,又称他“超迈而不失之放,谨严而不入于拘,狷洁而不沦于隘,非夫悻悻亢亢,以为直者也”。此番评说生发于斯人已逝之时,多少是有些溢美而有过的。
作为批评家的梅光迪,一生中有三个人对他来说极为重要;而与这三个人的关系则又构成了梅光迪一生中的三个重要时期,并引发了梅光迪思想和现实行止上的三次转向。
首先是胡適。梅光迪同胡適的关系是始同终异或者貌同质异。梅光迪以自己对孔孟“原意”的探寻和信奉、以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皈依,完成了自己在文化思想上与胡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裂,也就是完成了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主流和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主流的决裂,同时也以此确立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立场。其次是白璧德。最后一位与梅光迪的学术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吴宓。曾经有人比较过梅、吴二人的性格,认为吴宓“肃穆寡言,动止有程”,“勤于撰述,朝夕兀兀”;相比之下,梅光迪则是“春容间旷,极趣盎然,出辞隽永,辙轰座人”。这种评价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或许还算是一种褒扬,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未尝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沉潜不足、张扬有余的批评。与吴宓的始合终离,却使梅光迪因此而较长时间地疏离了二三十年代国内相当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后来他又与这一知识分子群体走到了一起,但却已经失去了他个人思想与学术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如果说学术上的切磋交流、学问上的从游聚谈对于个人学术水平的提升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的话,梅光迪却因为自己的性格而自动放弃了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重要的人力思想学术资源。1924年,梅光迪再度赴美,任哈佛大学汉语讲师,后升任副教授。1927年返国,旋又赴美,直至1939年归国。梅光迪就让自己大好的学术年华在这种一去一来的奔波忙碌中渐渐地耗散了。等他再度返国之时,已是抗战烟兴,各大学纷纷辗转迁移,知识分子读书写作的环境已非二三十年代可比,其恶劣程度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一个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心怀宏愿的梅光迪,就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任上,忙忙碌碌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时期。他所拟就的那份雄心勃勃的研究与写作计划,也只能被视为未遂的宏愿,让后来者扼腕吁叹不已了。
二
正如白璧德另一个中国弟子梁实秋所描述的那样,整个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和学术氛围都是偏于浪漫的,这倒不是说五四时期即已引进介绍了多少西方浪漫主义的思想观点,而是指当时整个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气质。这是一种普遍的、尤其是在知识青年中弥漫着的时代情绪,梅光迪置身其中,自然未能幸免。
梅光迪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与介绍有一个基本观点作支撑,那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是有一种时间上的内在关联的。也就是说,精神文明的变迁速度与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之间是需要有一种内在平衡的。因此,他指出,“以吾国近二十年之历史观之,国民性之变迁速度洵远渝于寻常,虽事实与思想悬绝。征之事实,吾国物质文明之不振如故,而思想上国人早已超越改革物质文明之时代,从事于精神文明之改革矣”[9]。然而,在梅光迪看来, 这种过于快速的状况带来了整个思想文化上的“变迁性胜于保守性”,已经为精神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只是此时在他那里,所谓“保守性”还没有后来的批评者所使用的那层含义。梅光迪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应该说直接沿袭了白璧德的观点,将培根以降的科学主义和卢梭以降的浪漫主义思想视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而近现代物质文明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改良思想大都源于此。
但是,当时国内整个知识界对于他们所热衷介绍的西方思想观念的认识,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对此,梅光迪始终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的。在他看来,那些留学西洋欧美者,“大率多年少而学未成之士。其于西洋思想能贯彻会通者,有几人耶!其于西洋学术有评判取舍之能,何者为适用于吾国、何者为不适用于吾国,又有几人耶?”[10]所以,梅光迪一方面呼吁青年学生应该有独立研究的意识,不要附和所谓的思想权威;另一方面,他又为怎样才能够对西方文化思想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指出了方向,认为“若吾国青年忽同时俱得欧美名师之指示,或读尽欧美现行之书报,得知世界思潮之趋势,而又于本国之文化与社会制度彻底研求,晓然于其病原之所在,今乃得一海外之万应良方以救之者”,方为思想界、知识界之正途[11]。但是,这种正途,这种一劳永逸式的、足以医治社会人生百病的救世良方、会通正途的现实性又何在呢?
然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上对最高之绝对和完整全面的信任和追求,显示出梅光迪思想意识中的非现代倾向。梅光迪是在1915年前后开始接触到白璧德思想的,这是在他自美国西北大学转学于哈佛大学之后。正如前面所述,梅光迪与胡適之间或者说与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也是发生在梅光迪走近白璧德之后。
这场冲突是围绕“文言白话”而展开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对于新文学的批评,实际上成为了梅光迪有限的文字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对于这场论争,胡適日记中有完整的记载。胡適《藏晖室札记》中记载,“再过欹色佳时,觐庄亦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其时间当在1915年夏。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梅光迪当时的观点主要有三:其一,认为文学乃知识阶级的特产,反对将文学“普及到大多数之国人”(这种观点在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但是根据胡適自己所说,当时还并不是要用白话来替代文言,而只是“想要改良文字的教授方法”[12]而已。而实际上,胡適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又说自己当时已经在身边的一些朋友中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概念),并认为胡適普及文学的主张是出于功利目的而败坏文学和学术;其二,文字无死活之分,白话俗不可挡,根本不可能作文入诗;文字的变动更改需要经过“数十百年”,还需要“文学大家承认”,而后才被使用。所以,再造新文学的说法和想法都是荒唐的;其三,“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不同,求“诗界革命可”,但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则不可;但梅光迪这时对于从“俚语文学”入手进行“文学革命”,似乎并非一概否定,只是他不能够同意胡適“再造”新文学的“大胆”,坚持认为文学及文字须经“有美术观念者之口”,“经美术家之锻炼”,不认同文学进化中人的能动性及其作用。
从这一时期梅光迪与胡適之间就文学革命所展开的讨论看,梅光迪从不完全赞同到完全反对胡適主张的理论依据或者思想资源,并不是欧文·白璧德的人文思想,而是他原有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和一个具有这种历史文学修养或者常识的读书人的“良知”。尽管梅光迪也提到过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一类的概念术语,但都并不是企图从文化思想上清理出胡適“文学革命”思想的根源,包括清理出他的西方思想渊源。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胡適时代的文学观,即他后来简化而成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主张,与梅光迪的真正的文学是经过时间检验积淀而成的经典文学的观点,在思维方式上是冲突的。
但是,梅光迪从白璧德思想中找到了他当时需要的系统理论,他从白璧德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批判中,发现了自己回击新文化倡导者们最便捷、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正是从这里,梅光迪一步步走近白璧德,走近他所谓的“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的中西方文化传统,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反现代潮流者。当然,梅光迪不会知道,他自己这种反现代潮流的思想和行为本身又成了现代潮流之中的一部分。
梅光迪正面涉及到对白璧德学术思想介绍的文字并不多,就像他正面论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不多一样。即使是他的集中论述西洋人文主义思想的《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一文,也是肤泛粗疏,议论多于说理研究的。综其所述,大抵有如下几点,从中我们也多少能够看出他思想学术的大致路向:
其一,文化介绍当求那些“有本体性之价值”,而且“实用于吾国”者,不应只是为解决“一时一地之问题”。梅光迪这里所谓的实用于吾国,是指所介绍引入的西方文化思想,“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13]。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符合梅光迪上述标准的西方文化呢?梅光迪认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文派批评可当首选。在他看来,白璧德和P·E·穆尔(P.E.More)两人之学,“综合西方自希腊以来贤哲及东方孔佛之说而成,虽多取材往古,然实独具创见,自为一家之言。而于近世各种时尚之偏激主张,多所否认,盖今日思想界之一大反动也。……两人固皆得世界各国文化之精髓,不限于一时一地,而视今世文化问题,为世界问题者也”[14]。既然新人文主义所提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命题,而且是综合考察了世界文化史上几大主要历史语言资源而后提出的“济世救人”良方,自然就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界大力引进的西洋思想。
其二,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但又不赞同当时新文化倡导者们的启蒙主张;坚持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历史文化传统对今日个人创造的指导作用,但也并不坚持认为拘泥于传统就是对传统的最好的维护。
其三,学术研究与文化介绍一样,当求彻底研究,“悉其原委”,“以极上下古今融会贯通之功”,“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等,强调知识者个人对待当时引进介绍的西洋文化思想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批判性。
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白璧德思想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并不是最为关键重要、最具历史性的那部分,而是其中最抽象、最原则性的一部分。我们几乎有理由相信,梅光迪并没有真正理解白璧德人文思想的真义,并没有真正领会白璧德人文思想一方面源于对西方近代文化主流思想的痛切感受,以及对于这些主流思想文化的始作俑者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中对“自然美”张扬的部分肯定的内在矛盾性,至少他不是像吴宓那样,从白璧德那里理解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在所谓的“超自然的”(Supernatural)、“自然的”(Natural )和“人文的”(Humanistic)三个层面之间的痛苦挣扎和艰难选择;也不是像梁实秋那样,从白璧德那里理解了对于卢梭以降的西方浪漫的文艺思想的批判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之所在。梅光迪的思想,无论是他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在《学衡》派与新文化倡导者论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几乎就一直是停滞不前的,而且一直未曾充分地展开或者成长起来。这也几乎残酷地应验了胡適早年曾经对他所做的评价:“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15]。
胡適此说不是没有根据。细察梅光迪文论中对于西方有些作家的批评,简直令人怀疑那些观点会是出自于一个主张文化介绍必须“悉知原委”的批评家之口。譬如他评价卢梭、托尔斯泰派之“归真反朴,反抗文化”,马克思派之“阶级斗争说”,尼采派之“超人论”等,“其本体之价值,毫无足言”[16]。如此议论,确实令人费解。另外,梅光迪对培根的科学思想的评说,也与白璧德对培根的批评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识与个人精神体验相距甚远,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怀疑梅光迪是否清楚了白璧德清理培根对近世西方思想影响的深意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9—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