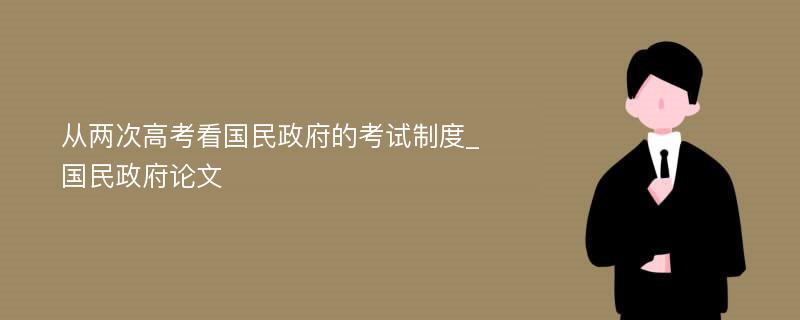
从两次高考观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两次论文,考试院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09-0069-06
1928年10月国民党成立五院制国民政府,以考试院来创立并推行现代意义上的考试制度。长期担任考试院长的戴季陶任职伊始就声称,如果要彻底推行考试制度,就必须“做到考试院长有权可以撤换阻碍这种制度的部长或省主席才合理想”,(注:转引自徐矛:《戴季陶与考试院》,《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 )否则就不能说考试制度得到确立。可见考试院满怀信心,打算努力推行考试制度。但是,考试院虽然有此雄心壮志,却在实际中发现步履艰难。从国民政府举办首两届高等考试(以下简称高考)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考试院虽然一方面认真推行考试制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低头,使考试的制度难以得到真正推行。
一、公务员非经考试不得任命
考试院于1930年1月正式成立。院长戴季陶声称, 考试制度目的在于“使一般行政人员将来完全经由考试出身”。(注:戴季陶:《考试的理论与根据》,《中央周报》1931年第162期。 )副院长邵元冲补充说,“要使国家安定和发展,一定先要使社会能够安宁,政治能够清明”,就必须推行考试制度,“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各得其所,供给社会之用。”(注:邵元冲:《考试制度之运用与最近考试之筹备》,《中央周报》1931年第160期。)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 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1929年6月17 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对五院职权范围作出明确划分,规定:“在考试院成立以后,一切公务人员考试权皆属于考试院。其不经考试院或不遵考试院所特定之办法而行使考试权者,以越权论。考试院不提出质询者,以废职论。”(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76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从而对考试院的地位与职权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戴季陶上任后,首先从组织上建立考试机关:在考试行政上,以考选委员会为主管机关;考试时设立临时机关典试委员会,主管命题、阅卷、录取标准以及试务;在公务员人事管理上,以铨叙部为主管机关。
考试院组织建立起来之后, 戴季陶着手从法律上建立考试制度。 1931年公布、1933年2 月修正的《考试法》规定考试分公职候选人员考试、任命人员考试、依法应领证书的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考试。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是任命人员即公务员实即官吏的考试。任命人员考试,主要指正轨的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高考主要招收大学(包括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毕业生,考试及格后以荐任职公务员任用。普通考试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考试及格后以委任职公务员任用。对于那些没有学力的人,则规定如果参加高等或普通检定考试,全部科目及格者,就可以参加高等或普通考试,以鼓励自学成才。
根据所学专业,考生可以报考高考各类,计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经济行政人员、土地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司法官、外交官领事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建设人员等。普通考试也分若干类,除司法官、外交官领事官、建设人员外,基本上与高考相同。无论是高等还是普通考试,都分为甄录试(可称为公共课考试)、正试(专业考试)和面试。甄录试科目有国文、国民党党义、历史、地理以及按专业不同而分的一科如经济学、宪法等。正试则考专业科目。“甄录试不及格者,不得应正试;正试不及格者,不得应面试”;(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337页,下册第1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面试不及格者,即使前两试均及格,也不能录取。因此要经过三试,不但要熟晓甄录试与正试科目,口才与仪表也很重要。能够通过这种考试的可谓高才。
最重要的是,考试院还从法律上保证录取人员的任用。1933年3 月以国民政府名义公布的《公务员任用法》规定:“荐任职、委任职公务员,应就考试及格人员尽先任用。”“考试及格人员应按其考试种类及科目,分发相当官署任用。”(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337页,下册第15页,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为具体落实高考、普通考试或相当之特种考试及格人员的分发任用,国民政府还公布了考试院起草的各种及格人员分发规程。就高考及格人员分发来说,国民政府根据《公务员任用法》的规定,特于1931年9月12日、1933年10月17日分别为第一届、 第二届高考及格人员颁布分发规程,规定铨叙部根据高考及格人员考取名次、拟分机关及人数,分别造具清册呈由考试院转呈国民政府,向中央或相当机关分发。各机关对分来的及格人员不得拒绝,“如该机关无相当员额时,得先以委任职叙用。”(注: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10月18日。)其他考试及格录取人员的分发任用规定,与高考类似。
从上述规定来看,国民党政府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制度,是科举制度的变种。就当时社会环境而论,的确在法律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考试体制,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来推行,即:毫无政治背景的寒上是否真正能通过平等考试而成为政府官吏?现任官吏是否只有接受制度上的铨叙才能确定继续为官的资格?
二、考试院竭力推行考试制度
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非常赞赏国民党政府的考试制度。他说,考试院的成立与考试制度的确立,“确使中国政府从基本上改观。”“随着时间的演进,各部人员中经过考试的越来越多,部长能够控制的位置越来越少。”(注:《蒋廷黻回忆录》第175页,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否如此呢?下面就从考试院直接主持的高等考试情况来作出回答。
从戴季陶上任到1948年“行宪政府”成立卸去考试院长之职为止,考试院共举行高考14次,共录取荐任级文官4046人。其中轰轰烈烈的、考试院成立初期举行的首两届高考最引人注目。首届高考于1931年7 月至8月在南京一地举行,有2185人报考普通行政、警察行政、 教育行政、外交官领事官等,录取100人。第二届高考于1933年10月至11 月在北平、南京两地同时举行,有2630人报考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会计人员、统计人员、外交官领事官、司法官七类,录取101人。 从考试过程来看,考试院确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推行考试制度。
其一,严肃认真执行“入闱扃门制”。
1930年11月17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规定考试院“限制实行各级考试,厉行铨叙甄别之各种法令”。(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91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考试院奉令后即积极筹备举行首届高考。1931年7月6日,院长戴季陶亲自出任主考官,陈大齐、焦易堂等13人为典试委员, 伍非百等40人为襄试委员,于洪起等8人为监试委员。宣誓就职后,即仿照科举考试时的“入闱扃门制”,进入考试场所,由监试委员将各门关闭,加贴封条。从此在屋内的考试大员不但禁止外出,还禁止同外界通信联系,一直要到考试结束、名单公布后,才由监试委员撕下封条,恢复考试大员的“自由”。第二届高考由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出任典试委员会委员长即主考官,入闱情况同第一届相同。在这种“扃门制”下正体现出考试院严肃对待考试制度的态度。比如,首届高考适值长江大水灾,考试场内水深三尺,监试委员于洪起掌管闱内钥匙,随身携带,“铁面无私,同人皆有坐水牢之感。”(注:《谢铸陈回忆录》,第82页,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再如,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被抽调借用的谢健入闱后,因公务堆积如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训令他出闱处理。监试委员于洪起根据《典试法》的有关规定加以抵制,迫使国民政府收回训令。更值得称赞的是,襄试委员于能模的夫人是法国人,以为丈夫一个月不见,误有外遇,请求法使馆协助交涉。典试委员会拒绝批准于能模出闱,只准许夫妻二人门内门外“互相对望相见”。(注:《谢铸陈回忆录》,第81页,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其二,一丝不苟对待试务。
考生在座位上坐定后,监考官逐一核对姓名、相片,确认无误后方发给试卷。试卷采用双重密封法,即每一试卷上只有密封的编号而无应考人姓名;试卷封面上贴上浮签,写明应考人姓名与编号,考生在考毕交卷时,监考官撕下封签,粘贴在一本专用簿册上,此专用簿册由专人严格保管。这样,即使试卷上的密封被人私拆,也仅暴露编号而不知考生姓名。只有在阅卷结束后,登录成绩时,才能从撕下的浮签上查对到姓名。
考试大员对阅卷也很认真。在首届高考中,戴季陶鉴于60分以上者仅为40人,于是请求国民政府批准将55分以上者加至60分。当时有名考生为56分,而考试大员误看为51分而被排除在外,发现错误后,戴自感责任重大,说承办人员忙中有错,情有可原,处分不妨从宽,而他本人急于放榜,督促过迫,领导无方,应受严厉处分。同时,秘书长陈大齐亦自认失察,与误算之科长科员均引咎请罪。最后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会议上决定:“主考官罚俸三月,秘书长一月,科长科员记过。”戴“尤以为轻”。蒋表示,“如必再重,以后将无人敢作主考。”(注:《谢铸陈回忆录》,第83页,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戴才不再说什么。
口试的场面也极为庄严。考官高坐一排,应考者单独入场,面对考官站定。试题预先放在大花瓶中,从中抽出一题,稍作思索即站立回答。口试除检验应考者学识外,还重在观察仪容、应对、态度、修养等。口试成绩与笔试成绩合并计分,笔试占总分4/5,口试占1/5。口试也很重要,第二届高考通过甄录试、正试的102人中, 就有一名因口试不及格而落第。
其三,尽力分发考取人员。
邵元冲指出:“如果举行了考试而不用,就等于没有举行考试。”(注:邵元冲:《考试制度之运用与最近考试之筹备》,《中央周报》1931年第160期。)因此考试院根据高考及格人员分发任用规程, 命令考取人员限期到铨叙部报到,领取分发任用凭证,向被分派的机关报到。首届高考于1931年8月9日正式放榜,10月15日以前分发完毕,将所录取的100人分发到国民政府、五院及一些省市政府实授、试署或学习。 为了引起全国对高考的关注,戴季陶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监察院长于右任商量,打破高考及格人员只能担任荐任职官吏的规定,仿古制之台谏由考试出身,将第一名朱雷章任命为监察委员,为简任职。第二届高考1933年11月26日放榜,考试院规定所录取的101 人中“凡曾任委任职二年以上”者“分发各机关任用”,“其无曾任经历或经历不满两年者,则分发各机关学习。”(注:南京《中央夜报》1933年12月15日。)12月28日,国民政府核准分发任用,铨叙部发给任用凭证,分发到国民政府、五院、省市政府等政府机关任用或学习。
为了保证这些考取人员真正得到任用,考试院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一)各机关“对于甄别或登记不合格者,应即免职;任用审查不合格者,不得任用。所遗之缺,以考试及格人员依法递补”。(二)“公务员考绩不良者,分别降级或免职,所遗之缺,以考试及格人员依法递补。”(注:分别见陈天锡编:《考试院施政编年录》,第二编第 327页,考试院1941年铅印。)可见,考试院对这些考取人员的任用真是费尽了心力。
从上述看出,考试院仿照科举制度的方法,竭力推行现代意义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考试制度。戴季陶等人严肃认真的态度,确实反映了“考试院负责者初心很想做事”。(注:伯玄:《革新县治与县长》,《人民评论旬刊》1933年第1卷第12号。)但是, 进一步分析就可看出考试院是白费苦心。
三、推行考试制度步履艰难
考试院刚成立不久就隆重举办高考,的确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第一届高考报名考生2185人中,“或为专门大学毕业,或为服务委任官三年以上,或两者并具;现任官吏亦复不少,且有荐任官亦请假前来报考”,足见“一般有学之士重视考试,欲取得考试及格之资格以为有学说经验之证明”。(注:分别见陈天锡编:《考试院施政编年录》,第一编第238页,考试院1941年铅印。)国民政府也命令交通部、 铁道部给予考生来往车船减半价的优待;请假报考的官吏按因公对待,薪水照付;凡考生住宿之旅馆不得乘机提价。从考试制度的规定和国民政府推行的姿态上来看,国民党政府似乎真正要从考试中选拔人才。但是,首两届高考的报考人数均为2000多人,为什么每届仅录取百人呢?恰恰从这一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考试院在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下推行考试制度的步履艰难。
考试院在举行高考之前公开表示,平均分数满60分以上者即为及格,可以录取。这就是说,并不规定录取人数,只要及格了,均可以录取。但是,考试院随即在呈国民政府的报告中“预定录取多者200人, 少不下50人”。(注: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8日社评《第一届高等考试揭晓》。)国民政府核准折中取100人,这就预先规定了录取名额。 典试委员会在公布首届高考及格名单之前曾对此作过解释:“日本从前高等考试,因为多取无用,考试院有鉴于此,故主张此次取录从严。”(注: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14日。)在第二届高考时, 考试院又保证“取一用一,绝不会投闲弃置,所以宁少毋滥,与其考而不用,不如少取”。(注:林厚祺:《第二届高等考试的回忆》,《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这样,考试院为了避免出现及格人数太多而使自己陷入难以分发的困境,从两方面来防止及格人数过多:其一,甄录试科目并不是大学教育中所开设的;其二,考试题目偏难,考生如不通晓政治、经济、历史现状等,就难以回答。
考试院确定国文、国民党党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为各类报考人员(外交官领事官不考史地)甄录试必考科目。戴季陶对此解释说:国文是必考的,“尤其是这几年来大家不注重国文,我们应首先注意”;国民党党义是必考的,因为这是在“以党治国”制度下“做一个国民应该了解的”;史地也必考,因为中国人“存在着史地知识缺乏的现象”,“应该急起直追”。(注:戴季陶:《第一届高等考试的经过与感想》,《中央周报》1931年第167期。)大学一般都开设了国文, 但未普遍开设国民党党义和史地,“大学各科除专攻史地外,概无史地之课程”。(注:分别见陈天锡编:《考试院施政编年录》,第二编第264 页,考试院1941年铅印。)虽然有人批评指出应该根据大学所开课程确定考试科目,但是考试院辩护说:既然是公务员考试,就“不应将学校所习科目重复考试,而应专在任用所需方面另定科目,以考验其从政之能力”。(注:分别见陈天锡编:《考试院施政编年录》,第二编第263页, 考试院1941年铅印。)
甄录试科目既然是公共科目,就应该重在基础,不能出一些非专业学生不能回答的偏难题。在第二届高考甄录试中,地理一科及格人数最少,原因除了大学未开设地理外,正在于地理题目过难。地理题目有三:第一是从过去形势、将来形势以及当前事实,推论开发西北应以何地为中心,才能统筹兼顾全国;第二是根据中国产棉情况、英日棉业竞争情况,论述中国棉业统制的先决条件;第三是根据孙中山实业计划,论述山东、辽东两大半岛上各港口之天然形势与内地之连络。(注: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10月22日。)没有专门学过地理、不熟晓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考生,很难回答这样的题目。时人指出:“题目应别轻重。重要者,试题无妨精深;否则,只试其概略。”(注: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14日。)这正是对考试院出题刁难的不满和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首届高考加10分才够规定的百人之数,第二届超过两人,则使1人在面试中落第。是不是录取太多,没有职位提供任用呢?参加过首届高考而落第的龙韻兰回答说:“(一)以死亡出缺计,每年可补充简任荐任之官员1300余人;(二)以按照我国官吏普通三年一罢之情形计,每年可补充20000余人; (三)以现在简任荐任审查不及格之人数计,则可因更换而补充36000余人。 ”(注:龙韻兰:《第一届高等考试》,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19日。 )比较而言,这区区200人太少了,如按规定任用,只是杯水车薪。 考试院在竭力推行考试制度的情况下录取过少,以保证“取一用一”来维护考试院荣誉的苦心却又被击得粉碎:考试院举行它成立以来轰动全国的首届高考所录取的100人,到1934年仅有8人“得其所求之职”,(注:(美)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第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以致于及格人员留南京代表金华等1932年10月13日赴考试院“请求维持政府信用”,(注:天津《大公报》1932年10月14日。)分发到审计部任职的胡某虽“向部报到,而分派无期”,失望自杀。(注:天津《大公报》1935年1 月13日。)可见真正得“沾恩惠者”不过像朱雷章这种遇到特殊恩遇的极少一部分人。
是什么原因使得考试院难以推行考试制度呢?邵元冲回答说:“考试的责任固然由考试院去担负,而对所录取之人任用,就非考试院一院所能担负,而需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共同去担负的。”(注:邵元冲:《考试制度之运用与最近考试之筹备》,《中央周报》1931年第160期。 )这就是说,考试院虽有严密的组织和众多人员,却是一个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机构,无法完成许多预定任务,还必须要其他政府机关“共同去担负”,才能推行考试制度。
正是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粉碎了戴季陶上任伊始时的雄心壮志。时人在评价考试制度深受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左右时一语中的地说:“本来以考试方法来为国求才,实在是颠不破的道理,只可惜在现状之下,引荐的力量太大了,政治上升官的黑幕总是不绝的演出来。”(注: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5日社评《现公务员之考绩与淘汰》。 )学者胡适也指出:“今日任官的方法全由于推荐介绍,而考试制度至今最多只能有万分之一的补救。”(注:胡适:《公开荐举议——从古代荐举制度想到今日官邪的改正》,天津《大公报》1934年3月4日。)事实证明了情况正是这样,每个新任主管长官往往带着自己夹袋子里的人去上任,他们公开表示:“蒙各方友好旧日宾僚或仗策来投,或荐贤相助。”(注:《孔祥熙启事》,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11月8日。)
进一步来看,国民党执政时树立的考试制度难以推行的实质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同封建社会相比,并未发生什么实质性改变。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核心人物,尤如封建王朝的君主,站在国民党政府的顶端。在他之下支撑门面的是国民党各派系,主要有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孙科派等;蒋介石派中又分政学系、CC系、黄埔系等。每一派系的头子如无任意提拔用人的特殊权力,就根本无法取得派系成员的拥戴。考试院在竭力推行考试制度时,却又不得不向派系政治低头,不得不限定名额,为私人钻营、保荐种种关系留下活动空间。戴季陶上任时所宣布的考试制度根本未得到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