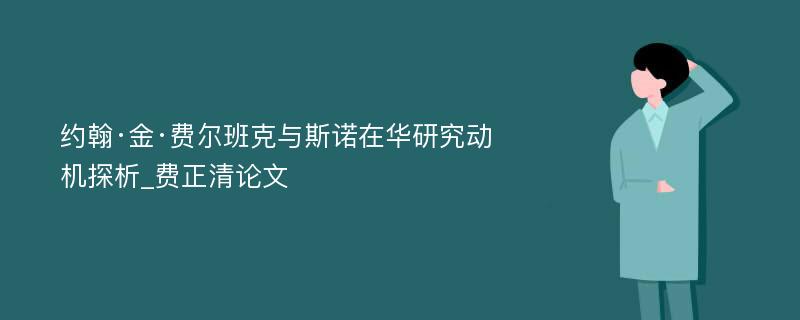
费正清、斯诺中国研究的动因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中国论文,斯诺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两个美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一个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k 1907-1991),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灾难深重但却具有古老灿烂文化的中国,引发了他们的同情和极大的研究兴趣。从此,这两个人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的问题。
费正清和斯诺著述甚丰。费正清一生写了约60本书,100多篇论文。斯诺一生写了11本书和数量庞大的报道。他们的著述,绝大多数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长征,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从国共联合抗日,到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绵延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他们的著述中,几乎得到了全程性的反映。费正清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以宏观的历史视野,纵向性地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向美国和西方人介绍了古老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该书不断修改增补,陆续出了四版,被称为是“一部不断赶上时代的经典著作”(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版序。)。至于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影响更为广泛,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它首次真实地报道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正顽强地活跃于中国的西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斯诺的报道,冲破了反动派的层层封锁,让人们眺望到红星照耀的中国,给中国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国内外赢得了巨大的道义支持。
到了本世纪70年代,当中美建交提上历史日程时,费正清和斯诺的著作又成了中美相互研究的重要文献。1971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夫妇。1972年,周总理邀请费正清夫妇访华。他们两人,尤其斯诺在中美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贡献。
费正清和斯诺在本世纪初,在通讯、交通还不很发达的年代,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个美国青年,忍受一个多月海上颠簸之苦,来到中国。众所周知,美国文化是一种断层多元文化。美国开国才200余年,它没有因袭单一的精神文化传统的束缚。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民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等地。移民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使美国文化呈现一种多元性与开放性的特点。移民到达北美后,先是集中于东海岸一带。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寻找财富,成千上万的移民,借助各种简陋的交通工具,克服千辛万苦,从陆路和水路向西进军,终于开发并繁荣了美国的西部,同时也孕育、锻造了美国人民乐于探险与开拓的性格与素养,并代代递传,相沿成习。正像美国著名史学家特纳指出的那样:“除非这种素养对于一个民族不再产生影响,否则美国人的这种劲头总是要找一处空旷的场所来施展一番的。”(注:余志森:《美国史纲》第10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费正清的先辈,是从英国朴茨茅斯来到美洲新大陆的移民,而斯诺祖先是乘坐英国第一艘移民船到美洲的。从心理传统看,他们先人都具有一种为改变自身地位而向外远征的精神。影响于后代的(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潜意识影响的),则是“远方崇拜”思想。“远方崇拜”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生命不断追求和扩大对外部世界感知、以及由近及远的发展规律的反映。尤其是在青少年身上,会产生一种憧憬、遐想漫游以及探险的欲望。“远方崇拜”一旦跟适宜的地缘环境结合,则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诱惑。
费正清出生的南达科他州和斯诺出生的密苏里州,在美国版图六大区划中都属“中西部”区。这地区是欧洲移民向西开发的“新区”,也是向更远方的“远西”进军的走廊。尤其是密苏里州,它几乎是处于美国本土的中心,是去“远西”的中间站。它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就是移民开拓与经营的硕果。斯诺出生地堪萨斯城,是在荒漠草原上建立的新城,它带有强烈的西部地域特性。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堪萨斯城由私人公司所建成,从一开始就是冒险事业,以后也一直是这样。”(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7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西部人这种拓展、冒险与远征精神,对费正清和斯诺童年心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早就孕育了一种远走高飞、超脱平庸、独立开创个人前程的意识。费正清回忆道:“童年时代,我总想离开家,想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故乡南达科他州辽阔的平原,宽广的牧场,渺远无垠的地域特点,造就了他“远方崇拜”的心理特质。他曾说:“正是南达科他州那种开阔无垠所留给我的印象引导我涉足研究遥远的中国。”(注:《费正清自传》第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跟费正清相比,斯诺则更富有先人开发西部的原始冒险意识,这意识既来自祖先的遗传,更直接来源于家乡密苏里作家马克·吐温。他酷爱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至小伙伴们都说他“生来就读马克·吐温的书”(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2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在这些作品的刺激下,他17岁时就计划坐木伐顺密苏里河飘流旅行,但未能实现。以后和两个伙伴驾车冒险远游。他们先到科罗拉多州,再奔新墨西哥州,横穿过半个美国,直到濒海的洛杉机。因车子损坏,才不得不爬火车返回。首次远征,跑了三个月,见闻很多,但斯诺最感兴趣的“只是那种冒险旅行和他所遇到的普遍百姓,他在以后的生涯中,经常回忆起第一次看到太平洋东岸的奇异情景”(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3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
费正清和斯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成熟,思想的发展,原先怀有的“远方崇拜”,渐渐从浅层次的追寻刺激和好奇心态,进入较深层次的对美国民族进取精神的承继与融合,把先人为改变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个人奋斗精神,转化为对自己前途、事业和追求建树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在费正清身上显得更为突出。
费正清16岁时,父母沿习边远地区上层人士习惯,把他送到发达的东部接受教育。他进了埃克塞特学校。该校多是上层人士子女,追求事业功名的气氛比较浓厚。费正清提到当时的心态:“我像大多数埃克塞特同班同学一样,切望以权力机构(事务或专门职业)为将来就业目标。”他一心期盼的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我始终瞄准的就是要确立自己成为一个一流学者身份。”(注:《费正清自传》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为跟“权力机构”结缘,他渐渐瞩意于国际政治。1925年,他以一篇论述英美世界作用的论文获得论文比赛奖,奖赏是一笔赴英旅游资金,附加一封拜谒英国首相的介绍信,他的照片还被登上了《纽约时报》。他踌躇满志地在苏格兰、伦敦、巴黎游历了几星期。这大大开阔了他的社会视野和政治视野。他说此行“使我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存在多中心的看法”(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2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这种世界“多中心”的意识,为他后来确定职业与研究方向,无疑是造就了适宜的思想温床。
如果说,费正清之成功导源于青年时代追求卓越的心理特质,那么,斯诺的成功则更多导源于地处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地缘环境和他的性格。斯诺生性好动,好游历,好冒险。他生活于堪萨斯城,但却认为城市种种工作就像机器齿轮转动那样,太刻板单调,不适合他的天性,他认为“城市中找不到特殊的职业”(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2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为找“特殊职业”,他中学毕业后进了密苏里大学,因为这所“学校的新闻学院吸引着像斯诺这样有意利用职业来旅行的青年就读”(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3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斯诺进校时,新闻学院已有40多位毕业生去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工作。学院里最吸引斯诺的是那块刻有子午线的纪念碑,上面标记着密苏里到世界著名城市的距离。子午线碑引发着他心猿意马的遐想。他写信给父母:“对我说来,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渴望冒险!我要使青春充实,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那些拖累我的枯燥单调的日子更使我向往神话般的远方,那些远方城市的名字不断地牵动着我的心绪,吸引我的注意力。‘加尔各答’!一个轻微的声音说:还有‘巴勒斯坦’!‘上海’!‘巴格达’!‘麦加’和‘大马士革’!当这些城市在我耳边欢唱它们名字时,我怎能继续在毫无生气的岗位上工作!?”(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6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这时,一个意外的机遇促他远行。他在股票交易中赚了800美金,他计划用这钱去旅行一年,于是就动身到东方去了。少年时代跟他一起驾车漫游的查理斯·怀特说:“斯诺在青年时期并不存在什么因素可决定他将来的伟大或成为争议人物,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年轻时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6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
就青年时代自我设计的自觉性、明确性和功利性而言,费正清远远超过了斯诺。费正清先是进威斯康星大学。原本在中学时就崭露的才华和出人头地怀想,在大学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说:“我面临着我要成为大学校园内大人物的前景。”(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3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为给自己营造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环境,他转学到哈佛大学。哈佛是培养杰出人物沃土,出了好几位美国总统和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学院式浓厚的学术氛围,更激发了费正清建立个人功业的抱负,他埋头苦读,“以求在世界上出人头地”(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3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促使费正清研究中国最重要契机是他得了罗兹奖学金。这是难得的殊荣,可以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美国许多政界要人、学界巨子年青时都得到过这项奖学金的扶持。得奖者无疑成了国家栋梁的后备军。费正清确信,这是“前程远大的证明”,他已经有望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界,“以摆脱人们只知赚钱糊口的那种世界”(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5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差不多就在得奖的同时,他的老师韦伯斯特告诉他:中国的机密外交文件正在北京公布,这将开辟外交史上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费正清还看到,日本已在觊觎中国,世界军事冲突交叉点可能落在这块土地上,中国研究极有潜在价值,大大有利个人前程的开拓。虽然此时他对中国所知甚少,但他意识到,这是实现自己功业欲和成就欲的天赐良机。他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兴奋地说:“查理·韦伯斯特对研究中国的建议吸引着我,……看来还没有别的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可能是一个开拓者,将继续成为学术上的和独一无二的人,这是令人振奋的强烈挑战。”(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6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1931年,他申请到中国学习汉语,收集史料,撰写博士论文。可以看出,费正清之研究中国,起因于“出人头地”的思想和日臻强烈的功业欲望。
斯诺到中国的动机与费正清大相径庭。他来中国,直接动因是漫游世界,“他要带着马克·吐温的农业美国的观点到国外见识一番”(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7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同时,他还怀揣股票交易中赢得的800美金,也想到东方碰碰运气。他告诉友人:“那时我二十二岁,刚从华尔街的投机中弄到一点钱,使我有了本钱来进行设想的、为期一年的节衣缩食的环球旅行和冒险。我计划一年后回到纽约,在三十岁之前发财致富,然后致余生于闲适的读书和写作。”(注:《斯诺在中国》第345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诚然,对于费正清和斯诺,我们还应当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思潮背景上进行探究,才能更深入了解他们到中国后思想上所产生的巨大变化。
由于异常强烈的个人成就欲和家教以及环境的影响,费正清的言行常常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从历史上看,功利主义是把个人利益置于核心地位的一种思潮。他常以个人得失为评断事物的标准和行动的依据。功利主义思潮跟美国文化传统结合,使美国人的功利主义带上了更加善用机遇、务实、讲求实际利益的色彩。他总结以往的人生经验时说:“谋求在社会上立足,多半有点像一种游戏,成功与否,取决于面前的铺路石。”(注:《费正清自传》第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他一到中国,当即尊奉这一信条,巧妙地为自己成功“铺路”。首先,他借重未来岳父、世界著名生理学家坎农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关系,辗转引荐,居然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一下子切了中国一流学者胡适、丁文江、蒋庭黻等社交圈,吸取高水准的学术影响。其次,结识一批具有丰厚文化素养的留美学者,如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等,多方提高自己中国文化素养。再次,借完成英国剑桥大学论文的机会,利用英国在中国海关的巨大权力,通过英国外交机构出面,到各通商口岸领事馆查阅原始档案,并借机周游华南沿海一带,广泛考察中国社会,为自己研究中国获取大量感性知识。可以看出,费正清的种种谋划,意在尽快完备研究中国的主观条件,以便回哈佛谋职与发展。
异于费正清的动机,斯诺到中国,只不过是环球漫游的一个部分而已,他原只想在中国呆六星期,结果却一延再延,以至在中国生活了13年,把自己的生命跟中国革命紧紧联结在一起。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是人道主义精神引发的结果。
斯诺的人道主义思想,除受先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外,还受书籍的影响。斯诺的先人,经历了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独立的建国历程,他的玄祖威廉姆·斯诺就参加过革命战争,后来安家于肯特基州。斯诺常常为肯特基自己老家没有蓄奴而特感骄傲。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马克·吐温。马克·吐温那种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奴役黑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很早就对斯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对他思想也产生过影响。如雨果、肖伯纳、杰克·伦敦等。尤其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更强烈地激发了他对“贫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他说:“我读了《悲惨世界》,在这本书里我发现了一些‘外国的’人物,使我想起在夏季冒险期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和失业者。对社会名流来说,他们只是些叫化子,可是我喜欢他们。”(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7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同时,这本书还启迪他触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思考。他说:“雨果为我展现了一个充满各种观念以及重大道德问题的陌生世界,使我关注起遥远的动荡年代的历史。(注:《斯诺文集》(一),第3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他归结出促成他中国之行的原因:一是冒险游历的欲望;二是读了《悲惨世界》。
斯诺到了上海,告诉雇佣他的报纸主编:“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啊”,“我只打算在中国呆六个星期,不再多住了。”(注:《斯诺文集》(一),第3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人道主义思想不断地激发了他的良知,一次比一次深刻地掀起他感情的波涛,以至振撼了他的灵魂,使他改变了初衷。这种变化,是他对中国人民苦难从浅表了解,到深入认识,直至理性感悟的过程。
初到上海,他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这个东方巴黎的喧嚣与繁华留下肤浅的观感:“上海就是中国”。但在此的所见所闻,渐渐搅乱了他的心境。他跟环境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加深,为此还遭到某些人的强烈攻击与毁谤。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人”观念的迥异所引发的。比如,看到有的电梯只准外国人用,中国人不得入内;一些俱乐部、公司及外滩花园也不许中国人进入。对那些“优等民族”歧视中国人的做法,他感到厌恶,他的文章写道:“不可容忍的白人统治观念”,是对人的“公然的污辱”(注:《斯诺文集》(一),第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结果遭到上海外国社团中一些人的谩骂、攻击,甚至叫嚣要把斯诺“赶出本市”。一次,他跟一位美国姑娘外出,撞上一个浑身着火却无人救助的中国人,情急之下,他毅然脱下新衣裹住那人灭了火,但却受到这位美国姑娘的嘲笑与奚落。后来,斯诺再也不愿意见这姑娘了。可以看出,牢牢扎根于斯诺思想深处的人道主义精神,已变成一种本能,使他不由自主地把不同民族,不同肤色,贫富不同的人,统统视为平等的“人”,给予应有的同情与尊重。斯诺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的视线更多地投向生活底层的“人”。在上海,令他感触尤深的是,许多穷人的子女完全被当成货物一样买卖,男的当劳工,女的当奴仆、娼妓。饥荒或战乱时,卖儿鬻女情况更加严重,甚至饿殍遍野。他用沉重的笔触,记下了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者的惨状:“有一个租界,公共掩埋队不断出动,据报道仅1930年一年中,就‘埋葬了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了’两万八千多具在街头或河里发现的尸体——大多是婴儿——在以后的年月里,死尸的数字从未低于这一年,被卖作奴仆固然可悲,但有些人的命运比这更惨。”(注:《斯诺文集》(一),第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过去,他只在雨果作品中间接地知道悲惨世界,如今,他却看到了现实中的“悲惨世界”,身心不禁为之震颤。
使斯诺人道主义思想升华,并导致他人生发生剧变的事件是萨拉齐之行。萨拉齐是现属内蒙的一个偏远地方,而在当时,中国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灾荒频频,民不聊生,萨拉齐正在闹饥荒。斯诺一路上所见,满日疮痍,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连树皮也被饥民刮光。他写道:“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神精麻木。我在一处看到一个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涨得像只气球。他使劲摇着他父亲的尸体,想要唤醒他。父亲光着膀子刚刚死在路上。……在我访问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运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注:《斯诺文集》(一),第9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人道主义思想发展从量化递增到突变的一个转折点。斯诺总结说:“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终于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在很长时期内,我见识过各种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惨象,这一情景是最令我震惊的一幕。”(注:《斯诺文集》(一),第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这种“觉醒”与“震惊”,是人道主义引发的灵魂振撼。萨拉齐之行后,斯诺怀着更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广泛考察中国,亲历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社会动荡。他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军的浴血奋战;参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到云南矿井了解被他斥为“罪大恶极”的童工奴隶制;他还访问了宋庆龄、鲁迅,多方了解中国社会。渐渐地,他的思想增添了政治色彩,甚至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不过,他同情共产主义“倒不是出于喜欢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讨厌共产主义的敌人”。(注:《斯诺文集》(一),第16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之所以讨厌,是因为纳粹希特勒“否定了甚至人类的兄弟情谊原则,颂扬野蛮行径和血腥的迫害”(注:《斯诺文集》(一),第16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他谈到自己思想变化时还表白:“给我以社会主义逻辑的影响的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也不是毛泽东。”(注:《斯诺文集》(一),第16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却是肖伯纳费边派和平主义缓和渐进的历史观。他申述道:“*
是肖伯纳使我相信,人类的进步能够超越相互掠夺的阶段”,“合作可以取代现有弱肉强食的经济制度”,合作也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必由之路”(注:《斯诺文集》(一),第16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不难看出,他的思想确有很大变化,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人道主义思想。
当斯诺不由自主地参与中国人民斗争事业的时候,费正清正在北平的书斋里埋头史卷,撰写论文,创造条件,一步步地迈向哈佛大学中国学术开拓者的殿堂。他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学术界上层人士。交往的多是留美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传教士以及通商口岸领事馆人员。他留迹的地方,多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迹胜地。他不像斯诺那样广泛接触中国严酷的现实生活。因而这一时期费正清眼中的中国,更多还是他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东方古国。在中国期间,他利用中国独有的文献资料,完成了第一篇博士论文。他对中国不像斯诺那样是投入者,而是一个以历史学家自诩的冷峻的观察者。他自白:“一个区域研究专家是一名旁观者,他有幸观察人世戏剧如何展开而又不落入俗套。”(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5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当中国政治状况日渐恶化,日本帝国主义威胁日加严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他顺利完成了学业,夫妻双双离开中国。其时心情如他自述:“我们觉得自己像老鼠一样匆匆地逃离即将下沉的船只。”(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6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哈佛讲坛,去筹谋自我设计的“费正清事业”。
至此为止,费正清和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发展趋向的把握,还只是初始阶段,还不能决定他们日后在中国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就他们原本的思想与意识而言,他们都欣赏费边社温和的渐进论,他们都寄希望于国民党。一直到日本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并最终挑起侵华战争,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段动荡的政治风云,目睹了国共两党所作所为,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斯诺冲破层层封锁,到陕北根据地考察,跟中共领导人直接接触,才使他的一生,跟中国革命真正融合起来。他说:“当我后来与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结识之后,我的命运便与这一事实联结在一起。”(注:《斯诺文集》(一),第2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斯诺红区之行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费正清奉召暂离哈佛校园,到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由于广泛接触了战时中国社会,有机会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方人士交往,了解到民心所向,他凭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与洞察力,相当准确地判断出国共两党兴衰与权力消长的必然趋势,思想取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谈到战时这段重要的经历,他说:“它使我走出书斋,投身世界事务之中,并显而易见地重新塑造了我。”(注:《费正清自传》第2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费正清和斯诺这两个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下,由“远方崇拜”的诱发,产生了外拓性的人生追求。而后,一个由功利主义驱动,一个以人道主义发端,在中国剧烈的政治变动中,锻造并成就了个人的功业。可以说,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及其多蹇的历史,为他们发挥才智,施展抱负,提供了巨大的历史舞台。是中国,为美利坚合众国造就了两个世界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