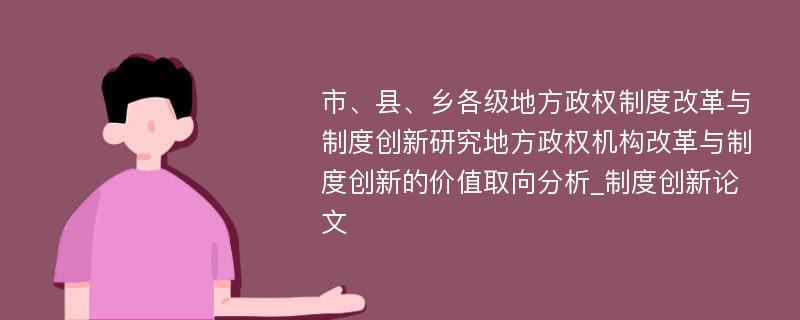
市、县、乡三级地方政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研究——2.地方政权机构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权论文,机构改革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地方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71-1351(2006)06-0021-04
一、“地方政权”的界定及其推进改革的意义
“政府”一词的含义有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理解,即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三部分组成,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国家政权机构;二是狭义上的理解,专门指行政机构,不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多年来,国家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政权层面上的,即使是狭义上的政府机构改革也由于政治体制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改革不仅仅是行政层面所能包含的和完成的,必须从更广的层面,即从整个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推进改革。因此,我们统一采用了“政权机构”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地方政权机构”呢?我们认为所谓“地方政权”是指这样的机构:(1)国家为了有效管理而设置的各区域或地方公共权力机构;(2)由法律规定的拥有相对独立的事权、财权或许还有立法权等权力的建立在一定管辖范围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1];(3)中央派驻地方的机构外的地方公共权力机构。在我国,由于省级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国家战略、方针、政策的传输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又是一个省域的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者的双重角色,而具体政策的执行则由市、县、乡(镇)三级地方政权来承担。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地方政权特指市、县、乡(镇)三个层级。
市、县、乡三级地方政权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在地方自治迟迟不能建立的情况下,地方政权机构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它作为国家战略、方针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体现者,其最大的特点是与民众的距离很近。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市县乡机关直接面对基层和群众,具体担负着组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在整个党政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系统中处在基础的位置。市县乡机关是否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关系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三个代表’要求的贯彻落实。”[2]可见,我国市、县、乡三级地方政权不仅肩负着推动一方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重任,而且肩负着中央正确的极具人文色彩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在基层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给当地的百姓带来实惠,从而使他们体察到国家的存在、发展与主人翁感,体察到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执政能力等重大使命。因此,大力推进市、县、乡三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应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对市、县、乡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之述评
正是因为地方政权机构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中国社会中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县、乡三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就成为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财政学、党建学说等领域的热门课题。国内知名学者薄贵利[3]、苏玉堂[4]、曹沛霖[5]、谢庆奎[6]、林尚立[7]、郑贤君[8]等人对此均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同时,《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习与探索》、《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地方政府管理》等期刊均刊登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尽管相当一部分成果不是专门研究地方政权的,但其内容无不涉及地方政府或地方政权机构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学者还是地方政府官员在论述地方政权机构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时,大都指向了民主。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一书,在谈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时,认为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和加快发展的价值取向”。[9](P28)诚然,“民主”一词,自从古希腊人提出来后,就受到人们的青睐,步入近代以来,民主更是成为文明政治的标识,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0](P25)民主既是现实存在的政治运行机制,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政治过程;既是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结构原则、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只能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存在和发展,只有在各种因素间,尤其是在自由与平等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与平衡,才能存在并有效运转。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指的民主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后才转化为政治现实的。古典民主向现代民主的跨越,不仅表明民主由古代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向现代国家的代议民主制的跨越,而且意味着民主理念的一次革命,即民主的核心价值已由集体本位转变为个体本位,民主的存在形态已由结构转变为一种政治过程。也就是说,民主成为一种政治秩序与生活方式,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侵蚀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对于政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不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对最后期望的结果做出专断的重新安排来达到,而只能诉诸于渐进的改良。而这一过程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及其运行状况等无不是需要建立在一系列的基础和条件之上的,即物质条件(核心是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具体制度安排)、法制条件(如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政治竞争、权力的和平交替、法律至上的制度安排等)、思想文化条件(如普通民众具备现代政治文化素质,具有基本的政治技能和民主经验等)和心理条件(如政治体系及其公民应当有错误难免的态度、宽容、怀疑、批判的精神,具有对制度坚定的忠诚等)等,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需要时间,自身的发展也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观念的急剧转变,没有人否认推进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必要性。但客观地讲,我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的基础和条件仍然是不充分的。除了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经济实力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表明我国能够承担民主运行的成本外,其他条件还远未具备。众所周知,人的观念指导行为,新的价值理念的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在前提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谈民主制度的创新无异于纸上谈兵。在我国,推行依法治国多年,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的法律规范,“法治”体系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法可依”已经基本确立,但“法制”环境还是严重欠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没有达到要求,其根源是法律至上的观念与制度安排还未建立起来。在我国市民社会还十分弱小或还未形成的情况下,法制完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高层,即中央和省而非地方;绝大多数公民根本不具备现代政治文化修养和基本的心理要求,这在十几年的基层民主实践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政治的特性。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呢?诚如刘新生先生所言:“(政权机构改革)不要忌讳什么‘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俗谈,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就首先特在这里。执政形式与执政内容必须与执政目标与实质统一起来,执好政、用好权、让人民称心如意,令世界刮目相看,这是最终目标。”[11]这也是考察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前提。宪政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法律赋予拥有现代政治理念与修养的公民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有序竞争的政治安排对民主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中国的变化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可谓不辱使命,是一个能够在不断总结成就与失误中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政党,是一个合格的有能力带领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的政党。如何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寻找、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实践表明,在一个远未具备民主条件的国度推行民主,“就使这种选择蜕变为一种把民主的种子撒在贫瘠的土地上幻想即刻长大成树的危险选择。”[12]因此,塞缪尔·亨廷顿在考察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实践后,集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问题,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序”。[13](P1)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建立有效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的政治程序过程。
随着人类步入新的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机遇把握得好,政策制定得好,运用得好,中国完全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渴求的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甚至是危机,涉及到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各领域各方面的考验。[14](P81-93),(P120-133)客观地讲,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是无法逾越的,只不过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国家掌握的资源较为充足,而且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及其文化冲淡或降低了问题的烈度,从而使得国家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来应对。相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家所拥有的资源本就匮乏,但各种问题在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却以十分集中的方式出现,且各种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经济起飞国家十分危险的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公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对问题的艰巨性缺乏了解,对国家的发展方向难以形成共识,对制度的忠诚度较低的情况下,倘若复杂的问题不能较快得到解决的话,全国上下经常会涌动着一股急躁感,进一步降低了国家的权能甚至最终丧失解决问题的大好机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平稳度过困难的过程中,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央及其各级地方政权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一方面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显著增强国家的整合能力,保持良好秩序。这是国家应对诸多挑战所必需与充分的条件和要素。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秩序的保持都与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相生相长,形成良性互动的政治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关键在于其民主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的,公民对国家制度有着坚定的忠诚,即使是政治反对派也是“温和的反对派”,反对的是具体的某一届政府或其行政首长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制度。相反,在一个民主条件欠缺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实行不但不能带来秩序和发展,反而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分裂、无序与严重的政治衰败,使得民主不是国家进一步发展强大的动力,而是国家发展史上的一场灾难。非洲与苏东地区的民主化实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结论
具体的国情民情,国家在新的世纪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严峻挑战与大好机遇,决定了我国的市、县、乡三级地方政权机构改革与制度创新,应把重点放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上,放在带领当地人民走上富裕安康之路上,放在培养基层民众的现代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与修养上。通过机构改革与制度创新,一方面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并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积累经验,积聚改革的基础条件与环境。总之,通过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市、县、乡地方政权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科教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者,成为基层人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引领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实践者,党的光辉形象的体现者,从而为我国最终走向民主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才是积极而稳妥的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