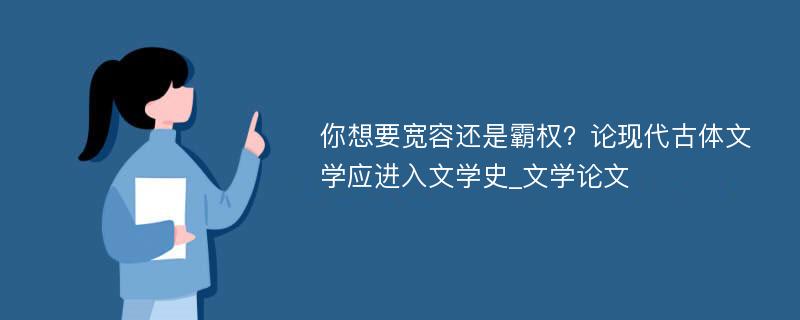
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体论文,霸权论文,文学史论文,也说论文,宽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篇文章应该说是一篇读后感,系拜读《粤海风》杂志2001年第3期所刊黄修己先生《现代 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一文后的一些感想。黄先生在此前所发表的《拐弯道上的思想—— 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一文的基础上(注:黄修己《拐弯道上的思想——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文学评论》1999年 第6期。),更加明确和集中地提出将现代旧体诗 词写入现代文学史,并举出诸多充分理由。笔者此前对这一问题曾思考过一段时间,但还未 成文,此刻得读黄先生的大作,十分高兴,所受教益颇多。笔者对黄先生文中所谈观点,大 多赞成,此外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在此写出,向黄先生及同行专家请教。
笔者以为黄修己先生所说现代旧体诗词范围太小,不能涵盖现代旧体形式的创作,因此用 现代旧体文学一词代替。现代旧体文学的能否写入现代文学史问题,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屡 有 争论,近些年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赞成者有之,如黄修己、钱理群等先生;反对者亦有 之,如唐韜、王富仁等先生。笔者以为,现代旧体文学的写入现代文学史并非研究陷入 困境后的一种突围,也不是以新奇的题目来哗众取宠,更不是贬斥新文学、为旧体文学张目 的复辟行为,而是出于一种直面历史的使命感,出于学术研究的理性思考,它可以说是现代 文学研究日益深化的一种表现。无论是作为古代文学在现代的余绪还是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 组成部分,现代旧体文学都应该被纳入研究视野,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体系。但是,长期 以来,现代旧体文学成了文学研究中的三不管地区,古代文学史乃至近代文学史都因超出时 间下限而弃之不论,现代文学史则以其旧体的形式而不予理睬。因而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 奇特人文景观:一边是社会各个阶层对旧体文学的广泛参与,源源不断的创作、刊印;一边 是文学史家们的视而不见、闭口不谈。尤为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从8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重 写文学史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到整体框架的设计,从一流作家的重新审视 到二三流作家的多方挖掘,从地域文化的探讨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方方面面都曾谈论 到,并加以落实,但一直未能解决现代旧体文学的入史问题。因此,现代旧体文学的写入现 代文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补上现代旧体文学这一课,为现代文学史增加一些章节,这很容易 做到,而且更可由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观照视角来反思先前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
笔者注意到,现代文学史著作在书名上有一个明显的前后变化:建国前和建国之初,多冠 以“新文学”之名,如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 仪的《中国新文学讲话》、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后来的此类著作则大多以“ 现代文学”命名,如唐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间或也有用“新文学” 者。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将新文学等同于现代文学,一般不做区分而混用。但细究起来,两者 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进行严格的区分也是十分必要的。“新文学”一词所涵 盖的范围明显要小于现代文学,使用这一词语其实是有一个潜台词在的,那就是“旧文学” 。对“新文学”一词,使用者可能以为其含义十分明显,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解释,因此对该 词一直没有准确的界定。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该词的含义进行了探讨,比如蔡仪先生将“新 文学”界定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简单 地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注:蔡仪《中国新文学讲话》第22页,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刘绶松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 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向 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注: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这种界定与一般研究者的理解差别较大,不 仅带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将“新文学”的范围定得十分狭窄,将相当多的作家 作品排除在外,难以操作,事实上《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两书对“ 新文学”的界定并未涉及到文体问题,按说符合其定义的旧体文学应该也在论述之列,但实 际上他们都没做到。倒是王瑶先生的定义较能为研究者所接受:“这个‘新’字的意义是与 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相对而言的,说明它‘从思想到形式’都与过去的文学有 了不同的风貌。”(注: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尽管这一定义仍有含混和难以操作之处,但它大体说明了研究的对象 和范围,实际上也暗示了不收现代旧体文学的理由,尽管这种理由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但 “现代文学”一词则不同,“现代”标志着研究的时段范围,“文学”则是研究的对象,这 里并没有新文学、旧文学的特别界定。既然标明是研究现代的文学,并无新旧文学的限制, 则凡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重要作家、作品等 自然是都应该在研究之列。至于过程的描述、现象的剖析、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所占章节 的多少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作为一部完整的描述现代文学曲折复杂发展历程的现代文学史, 显然不能无视旧体文学创作的存在。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的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应该 说是名不符实的,它们应该被称作“中国现代新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的 研究者将“现代”理解为对文学发展形态的说明,淡化其时间描述的含义,这样则会使问题 更加复杂,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需要重新确定其研究对象和时段范围,比一 般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或“新文学”更加难以把握和操作。
除对意识形态冲突的过分关注外,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十分强调新旧、雅俗的对立。应 该说有不少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新旧、雅俗的描述和分析是有欠公允的,有些研究者总是以一 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新、雅的态度,旧和俗的一方总是作为批判靶子 的 身份而出现,被断章取义地丑化、妖魔化,其正面主张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将“新 文学”与“现代文学”混用,就是这一思路最明显的体现,不管这种混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 意识的。这种扬新、雅抑旧、俗之举基本上沿袭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路, 正像黄修己先生所说的,这是“‘五四’启蒙者早已设定的格局”(注:黄修己《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这种沿袭固然有捍 卫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用意在,但它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特殊文化语境 ,或者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误读。这一时期,有不少人如刘半农、钱玄同、周 作人等在评述旧体文学如旧诗、旧剧时往往将话说得很满,在今天看来不无偏激,他们之所 以表现出如此激进的姿态,意在突破传统文学的重压为新文学争得一席之地,其实他们在内 心深处未必真正认同自己公开发表的那些言论,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先 驱者们后来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向。正像刘半农后来所总结的:“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 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 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 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而且有熊佛西先生等尽心竭力的研究着,将来的希望,的确很大,所 以我们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的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于 把已往的优点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的造成一种完全的戏剧。正如十年前, 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 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注:刘半农《梅兰芳歌曲谱》序,徐瑞岳编《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刘半农作为“五四”过来人的这段回顾是很值得 研究者认真回味的。在今天看来,“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旧诗 、旧戏的批判有许多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倒是反对者如张厚载、朱经农、任鸿隽等人的意 见 不无合理之处。
王富仁先生同意“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旧体诗词作为研究对象,但不同意将其“写 入 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他承认“这里有一种文 化压迫的意味”,同时又认为“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 略”(注: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 2 期。)。新文学确实是在同旧文学的激烈交锋中生长壮大并逐步取得话语权的,因此在其 成长阶段对旧体文学的抗争和排斥自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当新文学取得文坛主流地位、 为社会广泛接受之后,对已经居于边缘地位的旧体文学是否有必要一直保持以前那种排斥的 态度,能否转而以一种宽容平和的姿态来重新审视昔日的对手?正像周作人所说的:“当自 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压迫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 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注: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杨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从昔日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到后来直至当下新 文学对旧文学的压制,不过是话语霸权的一种简单置换,都难以称得上客观公正,正如钱理 群先生所言:“我们既不能因为‘五四’时期‘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而否认今 天‘旧文学’争取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过来否认当年‘新文学’对 ‘旧文学’统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注: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第23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事过境迁,自应根据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调 整文化策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旧文学的态度后来都发生了 很大的转变,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不复昔日的偏激。如曾在“五四”时期认 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的周作人,后来就说道:“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 的时候,我们的恶骂立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 一分子……这未免有点错误了。”他认为“国语文学”应该“包含所有以汉文写出的文学连 八股文试帖诗都在里边”(注:周作人《国语文学谈》,杨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连刘半农、周作人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都在不断调 整视角,都能比较平和地看待文学的新旧变迁,而后来以“五四”新文化传统传人自居的研 究者们却还在延续着新旧对立的思路,实行着文学上的专制,这就形成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 颇为耐人寻味的错位。
“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回 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注:唐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转引自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 与写作》一书。)这是唐韜先生反对旧体文学入史的理由。王富仁先生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在我们已经有了大量 优 秀的中国古代格律诗词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一代代的读者阅读并熟悉现当代格律诗词的创 作,我认为是一个应当严肃对待的问题。”(注: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 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也不是 它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注: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 第2期。)。笔者不 同意上述意见。为旧体文学争取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这更多的是出于严肃的学术立场,意在 探讨和复原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其中并无“提倡写旧体诗”及抬 出旧体文学否认新文学的“险恶”用心,何况旧体诗词的写作从“五四”以后直到现在并没 有停止过,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要远远超过新诗,不仅旧派文人在写,一般文化人士在写, 就连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也在写,其中不乏佳作名篇,根本不存在走不走回头路 、提倡不提倡的问题。相反,旧体诗词在新文学多年的严厉打击排斥下,尚能保持如此顽强 的生命力,打而未绝,斥而不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特别是在新诗创作走上绝境 的今天,旧体诗词的写作仍然是一派红火气象,其中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长期以来,扬 新抑旧的观念经不断宣传强化而深入人心,人们对现代旧体文学的创作一直持一种排斥态度 ,影响之下就连写旧体诗词者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进行辩护,只是以消遣娱乐之类的名 目进行掩饰,一旦说到年轻人,则立即一本正经地劝戒他们不要做旧体诗,生怕毒害了他们 。固然,对旧文学的压迫是新文学为求生存发展所采取的一种有效文化策略,有其合理性 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文化策略造成了人们对旧体诗词的普遍误解和歧视,其中最 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旧体诗词不适合表达现代人的生活情感。其实,这只要回顾一下现代 旧体文学的创作,看一看其参与的广泛程度及作品的实际水准就会知道,这一说法不过是站 在新文学立场上的一种“谣传”,并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论证,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郭 沫若等人放弃新诗而改写旧体诗词。按照这一说法的逻辑,新诗适合表现现代人的感受,而 且形式自由,不像旧体诗词那样还要受着格律的严格束缚,显然有着各方面的优越性,但问 题在于,既然新诗如此优越,为什么它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取代旧体诗词,就连写作新诗的那 些先驱者们也纷纷回过头来改写旧体诗词呢?从“五四”到今天,已80多年,按说时间也足 够长了。再者,一种经历数代文人千锤百炼而定型的文学样式是不是社会一发生变化就显得 不合适宜,一定要加以废止呢?新诗除了生存权发展权的维护外,是否有必要一直拒绝旧体 诗词,而不是从中汲取营养呢?“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 正之讥,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以偏 激,反失社会之信仰。”张厚载这位被视为“五四”新文化反对者的意见在今天听来是否也 像当年一样刺耳呢?
通过对现代旧体文学的重新审视,不仅可以改变将新文学等同于现代文学的“单边主义” 局面,而且更可以通过文学发展的新旧消长来反观新文学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憾,抹去人为 加在新文学头上的一些光环,这并不是有意否定新文学,而是将旧体文学纳入研究视野的必 然结果,至于有人要借旧体文学来否定打压新文学,那已非学术之途,是另外一回事,事实 上也不可能做到,毕竟还有了认清时代潮流的问题。近些年来,文化界对近现代国粹派、学 衡派乃至新儒家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多,一些现代文学史家对这一“复古”思潮一直抱有警惕 心理,担心由此引发的对新文学的全盘否定。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至少说是过于敏感 。被歪曲的东西迟早要得到纠正,文化层面的“拨乱反正”也就不可避免。近现代文化史上 的保守或守旧者固然有不合时宜、敌视新文学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立场和见解自有 其正当合理的一面,他们也确实经受了过多不公正的指责,其形象长期以来被严重歪曲和丑 化。而通过文化考古,恢复他们的本初面目,抹去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这一行为的正 当性是毋庸置疑的。维护新文学不能总是以丑化、压制对手的手段来实现。正视对手,才能 认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何况研究并不等于欣赏,也不等于提倡,至于愿意写新诗还是写旧体 诗,这更是个人的私事,谁都无权干涉,不能以自己的不喜爱旧体诗词而给别人扣上遗老、 遗少的帽子。因此对现代旧体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不必过于“警惕”,对于新旧文学的“大防 ”也不必一定要守得那么严。
此外,王富仁先生还认为“现当代格律诗词一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我们的文学史就 不再主要是现当代作家创造的文学史,大量的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教授、宗教界 人士就将占据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为此他主张“让对这些作品有兴趣的人自己 去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可以另写中国现当代格律诗词史,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依然维持新文学的固有性质”(注: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这种观点显然让人无法苟同,能否进入文学史的主要依 据不应当是作者的身份,而是其创作实绩与文学主张,如果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 教授、宗教界人士的作品写得比专业作家还好,见解比他们更高明,为什么一定要将其拒于 文学史之外呢?能否进入文学史、能否进行文学创作,任何人都没有特权。现当代文学史应 当是全民的现当代文学史,而不是专业作家的现当代文学史。
如何对待现代旧体文学也并不仅仅是其能否进入现代文学史、为现代文学史增加几个章节 的 事,它关系到如何客观公正地对待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变革问题。笔者以为,旧体文学写入 现代文学史只是迟早的事,关键是现代旧体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如果收入旧体文学, 只是作为映衬新文学的靶子,批判一通了事,或只是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陪衬,写个三两节敷 衍,表示一下自己的宽容,还不如不收。以往的研究对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传承关系注意不够 ,近些年情况虽有改变,但还留有很大的学术空间,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不过这也是个很好 的契机,正可通过现代旧体文学的研究,对现代新旧的交替消长进行一番新的审视,对一些 文学现象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复原现代文学的曲折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展示出现代文学 发展的原生形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写入现代文学史的并不仅仅是现代旧体诗词,还应包括这一时期所创 作的旧体文赋、戏曲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类旧体文学的写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 人包括一些新文学作家在写作书信、序跋时还经常使用这类文体,或骈或散,颇有妙笔佳作 ,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特别是现代传奇杂剧的创作,迄今为止还没见人专门论 及。传统戏曲发展至清代中后期,出现了有戏无剧的现象,表演成分突出,剧本的功能被淡 化,依宫调格律形式创作戏曲由于过于繁难,逐渐成为绝学。但在民初之后,由于吴梅、王 季烈等人的努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复兴局面,他们精通曲律,创作了一批传奇杂剧,成为 传统曲学之绝响。这些剧本虽然大多没有上演过,但从文学角度看,还是颇有值得注意处。 除吴梅、王季烈外,顾随、卢前、冒广生、刘咸荣等人也创作了一些传奇杂剧。尽管这些传 奇杂剧作品大多没有得到上演的机会,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理应得到 研究者的关注。
从“五四”到今天,现代旧体诗词的别集、选集不断刊印,数量很大,以新文学作家而言 ,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郁达夫、老舍等人都有专门的诗词集出版。但有关研究 还很缺乏,应该说连最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都还没有做。笔者以为,可先从这一基础工 作入手,集合三五同志,下数年苦工夫,理清现代旧体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编制目录,汇 编资料,系统地出版一些专集、选集,同时展开研究,写出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现代旧体 文学史》,然后再不断深化拓展,将现代旧体文学的研究纳入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体系,在 此基础上,写出一部全面反映现代文学发展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刘半农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