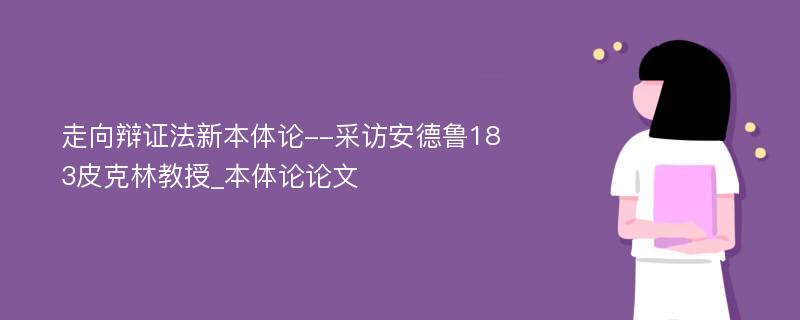
走向辩证的新本体论——访安德鲁#183;皮克林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安德鲁论文,克林论文,走向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1-0104-05
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哲学社会学系主任,当代STS领域中的代表人物。2010年9月13-17日,他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张异宾教授的邀请,在南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在宁期间,我就皮克林教授的冲撞理论及其主张的新本体论等问题与他进行了访谈。经他同意,现将访谈内容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问:您在《建构夸克》中指出,仪器的不可通约性将新旧物理学相互隔离,那么物质基础在您所说的物质—社会—概念集合体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呢?仪器的不可通约性进一步完善了库恩的范式间不可通约的观点,你甚至直接承认了由此所引发的相对主义。您能解释一下您所理解的相对主义吗?
皮克林:我的想法是科学文化的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元素在某种模式中共同进化,也就是在《冲撞》中我所分析的那种模式。总的来说,这些要素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优先的,物质、社会和概念以一种无法预期的方式共同生长,彼此相关。你提到的“物质基础”促使我要对我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澄清。因为正如我所认为的,聚焦于物质文化和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非常乐意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我绝不赞同任何将科学或社会因果性或解释性地还原为其物质基础的方式。我不认为科学的物质文化能够决定或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或其社会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想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对社会存在的分析必须始自对实践的聚焦。而且,一般而言,具体的科学文化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事物;科学文化由多种多样的异质性要素所构成,科学研究的工作通常在于要使那些还没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形成结盟或产生关系。
《建构夸克》和《实践的冲撞》当中的相对主义只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即新的文化(机器和仪器、它们所引发的现象、各种理论和模型、各种社会结构等)生长于旧有的文化。因此科学知识总是与一些特定的初始的文化配置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配置不同,那么从其中生长出来的知识形式就会不同。在好几项研究中,包括我最初的著作《追踪夸克》(1981),我正是试图要展示这一点。在《实践的冲撞》当中,我指出,这种相对主义的形式并没有它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危险,因为知识同物质世界一样,总是生长于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中——正如我后来所称的“力量的舞蹈”。因此知识是相对的,但绝对不是“仅由社会建构”。
即便如此,在粒子物理学的具体情况中,我还是被一种历史转换所震惊,即在该领域的整个机器基础中,那种我所称的从“旧物理”到“新物理”的转换。截然不同的机器和仪器出现在两种物理学中,生产着各种相互脱节、不同种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物理学和新物理学的理论是与不同设备领域及它们所产生的不同种类现象相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仪器的不可通约性”的意思——无法用一个共同的经验性的公式来评估他们的有效性。这听起来像不可通约性的标准哲学定义,虽然关于不可通约性的通常争论集中在理论、语言、可翻译性问题,但是在这里,不可通约性却存在于它们所参与的那些经验性仪器和现象的领域的相互脱节。
问:《冲撞》之后,您试图在超越科学的更大尺度上思考本体论。您认为现代科学的本体论掩盖了世界在实践中冲撞的过程,我们能够打开这个蔽障从而展现生成的过程。而拉图尔的ANT也主张打开黑箱,追踪网络建造过程,从认识论进入了本体论。您和拉图尔似乎采用同样的“展现”的立场思考本体论,您能谈谈两者的关系吗?
皮克林:首先要说的是,我非常钦佩拉图尔的工作。1987年,《科学在行动》的英译本出现时,作为一种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转向方式极大地触动了我。社会建构论试图将科学知识还原为社会的特定方面,比如社会利益,而拉图尔则找到了一种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即社会自身在知识和机器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对于试图去理解现实的技术社会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论的很多方面,拉图尔和我都站在“后人类主义者”立场上。
然而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是不同的。其一,虽然拉图尔一些著作显示出对物质文化的兴趣,但这并不是他的中心问题。他的大部分作品集中在新视角的详细阐述上,即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的惯常疑问,并且他的很多学术影响也都与他关于表征的思想有关。相反,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困难但却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关注力量和操作。在《实践的冲撞》中,我所称的由表征性语言转向操作性语言便是这一问题的关键,而拉图尔却不情愿这样,即便他也使用“力量”或“操作”这样的词。
第二个分歧涉及对于现代性的分析,这是拉图尔最早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提出的。他将现代性描述为多重模糊的人与物的系统联结,这极富洞见。但他是一个现代性的热衷者,他认为我们仅仅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他完全不愿意严肃地对现代性进行真正的抉择,这便是他的政治学颇有保守意味的原因所在:他的“物之议会”只是一种安置人类决策过程的新方式。我并不像拉图尔那样热衷现代性,我更偏爱一种以不同方式制造事物的实践政治学,正如我最近的《赛博大脑:勾画另一种未来》一书所证明的那样。我确信拉图尔不会喜欢我在这里所考察的这种非现代性的课题。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政治学,对拉图尔的一些想法》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问:为什么生物进化论成为你的“冲撞理论”的一个如此重要的资源?您多次提到实用主义对您的影响,并称威廉·詹姆斯是您的英雄。请您具体谈谈实用主义是如何影响您的思想的?在你的理论中,生物进化论与实用主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皮克林:实用主义是首要的。1984-1985年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在那里库恩促成了我对科学知识和世界之关系的理解。1985年的夏天,当我阅读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真理的意义》时,我开始寻找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从詹姆斯书中获得的思想是,承认知识与实践、世界的一种构成性的交互,而又不陷入一种幼稚的实在论,这是可能的:在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时,知识可以是实实在在有用的,而不必成为一张唯一准确的地图来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从詹姆斯那里获得的思想还有,新的文化产生自旧有的文化,并且呈现出源于其中的特有的物质。这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相对主义的一种特有形式的观点,《实践的冲撞》也确实以詹姆斯的一段引言作为开始。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关于新文化从旧有文化发展出来的这个想法是很难把握的。于是我认识到(感谢约翰·兹曼(John Ziman)对《冲撞》一书的评论),生物进化论有着相同的形式:新物种从已有的物种中发展起来。这也与我的思想一致,即冲撞是一个非还原的普适理论。进化论帮助我们把握人类文化和有机物的生成。
问: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您的冲撞理论及相应的生成本体论似乎并非难事。此次中国之行,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您能谈谈冲撞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不谋而合吗?
皮克林:中国之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对传统中国的思想的把握仍然是比较初步的,我的想法也不断在改变,但我第一次试图写一些这个领域的东西,最近完成了一篇我称作《化学之道》的小文章。我开始以一种流动与生成的眼光来看待化学。之前对化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执着于知识、理论和认识论问题。然而如果关注并突出物质性及其流转性的生成过程,我们将会看到化学物质的流动和转变,以及伴随它们的知识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去中心的过程中涌现并生成的过程。这转向了另一种非现代的辩证本体论。而道家的基本图景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异质性、自发流转的世界,作为其一部分的人类应尽最大努力与这种流动协调一致,而不是企图控制它们。道家思想为我们思考化学及现代科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本体论框架。不管化学家承认与否,化学的世界是一个道的世界,一个海德格尔所讲的展现的世界。尽管在这种流动的展现中,化学又采取了一种掌控和支配的立场,正如海德格尔所称的座架,而不是一种创作(poiesis)的立场。我的理解是,道的本体论或多或少地与我的冲撞的本体论相同——作为永无止境流动与生成的世界之图景,人类是置身于其中,而绝不是受控于其中。在西方我们很难认识到这点,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科学本身就企图去夺取控制权并企图支配各种流动与生成。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比如,化学污染和环境污染共存,但是我们把这种失控当作是科学和工程的一种“无意识后果”或仅仅是“人类的失误”,从而忽视了这种世界观。
问:您的冲撞理论更多以西方现代科学为背景,展现二战后科学、技术、军事、社会等相互缠绕式进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学术界更为关心地方性科技如何融入当代西方科技之中,两者在实践中相互冲撞,相互改造与缠绕式进化的问题。如何从您的冲撞理论来思考这些问题,您的冲撞理论能否提供某些有益的方法论启发?
皮克林: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我倾向于将非现代的科学与技术——表达非二元本体论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看作是与现代科学不可通约的,看作是对世界感知和行动的不同方式。我不认为它们能够被简单地相加,也不认为它们可以逐渐变成另一个。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对各种不可通约的传统之间的交叉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他比较了他所称的“自由”互动和“引导”互动。在自由互动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各种各样无法预期的新奇事物都可能突现。这听起来很精彩,但是我想不出这种突现事件的任何真实的例子。相反,在引导互动当中,一种传统一直处于优势,且以某种方式迫使另一种传统符合它自己的标准和实践,几乎不能指望有什么新事物出现。对此我倒能想到很多令人相当沮丧的例子,其中非现代性的知识和实践形式被裁剪以适应现代科学和工程。我之前的一位学生金宗洋所写的关于传统韩医与西方生物医学之交汇的文章极有洞见。他采用了费耶阿本德引导互动的其中一种形式,研究韩国传统碎片状地被剥离出来,比如,纯净的化学药品仍然是药用植物的活性成份,并被作为一个简单的增加物塞进生物医学库中。韩医制造的任何迥异于西医的事物都被沿途丢弃。西方杂志的支配地位和科学引文索引(SCI)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的个人倾向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利对科学和工程采取非现代的研究路径,以表明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不必非要遵从现代西方的方式。这可能会对现代科学和工程及其时常灾难性的“无意识后果”进行一种有效的校正。与李曙华教授的交谈,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古代都江堰的事——这个难以置信的工程伟绩没有利用任何现代科学,但因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自建成后上千年来一直都运作良好而千年不衰。
问:在现实时间维度中考察您的生成论主张,即在研究科学史时,进行前瞻式的考察,而非回溯式的解释。如何判断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值得关注的力量?这是否与著名的“认识论的鸡之争”有关?
皮克林:我反对在历史写作中的回溯,传统历史研究路径将现在的知识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原则来解释过去。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因此我们应该试图去理解已发生的实践,而不是关于那些后来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要在真实的时间中研究实践,那些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的。一个科学家可能会试图建造一个新的仪器或做一个新奇的实验,在各种实例当中,我注意到与物质文化的各种内容进行斗争是构成实践之演变所必须的部分。我起初用“阻抗”这样的术语来谈论这些在物质实践中引发的斗争:在通向某些目标的路途中突现出的障碍物,虽然现在我更喜欢称之为“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舞蹈”。因此,对于如何去决定何时是值得关注物质(或人类)力量的时机来说,我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处方:这取决于当你看到特定的情况时你发现了什么。
在我编辑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柯林斯和耶尔莱对卡隆和拉图尔指出了方法论困境。这个困境的关键在于这样的问题,即在卡隆关于圣布里厄海湾扇贝农场的著名文章中,他如何可以断言他知道关于扇贝等这些非人类力量的操作的情况。对此的意见是,卡隆必定重复了科学家所告诉他的东西,那也就意味着向幼稚的科学实在论的倒退,而这正是社会建构论将我们从中营救出来的地方。于是柯林斯和耶尔莱主张,如果我们不想做出这样的倒退,就应该把科学家的知识主张看作是社会学分析的对象;我们要么成为科学实在论者,要么成为社会实在论者,两者必居其一,而卡隆和拉图尔却想同时拥有两者。对此,卡隆和拉图尔的答复是,他们哪一个也不是,面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的马路,他们处在这条马路的中间,不像柯林斯和耶尔莱之类社会建构论,犹如胆怯的鸡,恐惧公路上的疾驰而来的汽车而匆忙跑到社会一边。卡隆和拉图尔等人破除了自然与社会两分的做法,提出了本体论意义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即对称性地对称自然与社会。这一原则使我们摆脱了社会建构论的困境,但他们并不是在谈论所有的真实实体,而是在谈论符号学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我发现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它没有跳出表征主义的传统(这又回到了我之前关于我和拉图尔在“力量”这个话题上存在分歧的评论)。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我提出了“实践的冲撞”理论。它关注自然、仪器与社会之间机遇性相聚集的空间或场所,即物质-概念-社会的聚集体。我现在把这一聚集体称为物之涌现处(The thick of things)。这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交汇点,是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时空。在这种时空中,社会就会像自然一样,是建构科学的实践过程中的异质性要素之一,科学不再由自然或社会单向度地因果决定。如果以这种去中心化的观点去理解科学史,我们就不会把社会视为一种外生的变量,一种统领着科学史的发展的预先存在的解释性框架。相反,社会同各种自然、思想、工具等文化因素一样内生于科学史之中。在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性因素(自然、社会、物质、工具等)交织在一起,共同编织了科学发展的历史。相对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主义的社会建构论而言,这种去中心化的科学观通常被称之为后人类主义。显然它更具辩证的历史感,使我们走向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和谐发展、共同进化的哲学。
问:在阻抗与适应的辨证法中,充满了瞬时突现及斗争性的描述。因而,您的冲撞力量关注的是“制造事物的过程”,那么,关于“我们应该制造什么”又如何呢?冲撞中包含价值取向吗?
皮克林:在我的文章《新本体论》中,我就主张,现代科学和工程采用了海德格尔所称的“座架”的形式。它们试图将人类置于中心,并通过知识来支配世界。海德格尔认为,座架对我们内在本性而言是“最高的危险”。他恐怕是对的。座架无疑带来了灾难和祸患。因此我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去记录,分析并鼓励那些非座架的过程,它更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创作”(poiesis)过程,一种实验性的、操作性的开放,即向世界所给于我们的东西保持一种开放。我在《新本体论》中讨论过一些例子,在《赛博大脑》中还有更多的实例,涵盖了范围广阔的领域,包括脑科学、精神病学、机器人技术、生物计算、复杂科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艺术、音乐、建筑、灵性甚至19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因此我的价值取向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座架,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创作。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险恶严峻、灾难频发之地。
问:您在演讲中几次提到要从“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转向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两者间的差异及这种转向的意义?
皮克林:传统观点是,科学最重要的是知识体系。因此历史学家会去研究一些物理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再如,哲学家会试图建立关于一套观念被另一套观念所取代的合理性。这和技术没有任何关系。它和社会学也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思想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和理性展开。这就是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传统的学术图像。1970年代早期,“科学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诞生了,但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一样的:那种科学家生产出来的知识。1980年左右,当人们开始注意到物质文化和科学实践时,这种将“作为知识的科学”几乎是唯一兴趣中心的做法开始被拆解了。科学实验室充满了机器和仪器,它们作为科学家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科学家们要与之斗争。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工程师也是同样如此的,因此从这个视角看,科学和工程显得极为相似。这是由“科学研究”导向STS的其中一条思路,即“科学研究”由一个只专心于科学思想的领域,发展出一种对科学和技术两者进行统一分析的领域——科学技术研究。当然,如果你把物质、概念和社会看作是共同进化的,那么社会也成为研究对象一个主要部分——从在实验室中发现的微观社会秩序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秩序。
问:在您对本体论的思考中,蒙德里安和德·库宁的绘画成为了您的重要的思考资源。在之前交谈中,当问及您今后的研究计划时,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艺术!这多少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回答。您能具体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考虑及其原因吗?
皮克林:当我第一次想到蒙德里安和德·库宁时,仅仅是作为一种试图对普通听众讲解我的思想的方式,也即关于冲撞和力量之舞蹈的思想,因为这些普通听众可能对科学研究实践的性质根本不感兴趣。差不多就在同时,2000年,我开始对控制论产生兴趣,因为这个领域以某种方式运作着冲撞的本体论。在深入了解控制论的历史时,我接触到了各种奇异的艺术作品,我便开始将其理解为本体论的剧场——既可以编写一个非现代的本体论,又可以将它表演出来。在《赛博大脑》中有很多实例,包括闪烁现象(flicker phenomena)、脑波音乐(brainwave music)、一种物活艺术(hylozoist art)(将涉及行为的过分天性主题化,超出了我们表达它的能力)、交互式机器人艺术作品(interactive robotic artworks)、交互式剧院(interactive theatre)(观众可以组织任何给定的表演,安排使其如何实时地进行演变)、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衍化音乐(generative music)。我还发现这种形式的艺术是一个目前非常活跃的领域,我认识到,相比于学术著作,这种形式能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讲解。因此,回到你问的关于我的价值取向的问题,我目前的课题就是去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工作的一系列当代艺术家,探究那种让他们的工作能够在其中成为本体论剧场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与其他非艺术的项目联系起来,如对工程的适应性处理。我希望我的工作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介入,试图将我自身文化中的边缘要素集结为一个格式塔转换的一部分,使它们走到公众认知的显著位置中。我想,如果发生这样一种格式塔转换,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再回到我的中国之行,我同样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强烈兴趣,尤其是在各种环境中兼有艺术作品之功能的大石块。作为本体论剧场,它们诉说着一种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与现代西方艺术传统截然不同的。除此之外,我还不确定该怎样去表述。现代西方艺术传统是以人类为中心,并赋予人类艺术家以创造者的权利。相反,中国的石块却不存在人类创造者。它们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制造,它们以多种方式发挥着作用,提醒我们那些更加巨大的自然形成物,那些我们可以适应它们,它们反过来又滋养我们的自然形成物。这把我们带回了冲撞和道之间的共鸣。
本文标题取自皮克林教授2010年9月14日在南京大学的演讲“一种辩证的新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