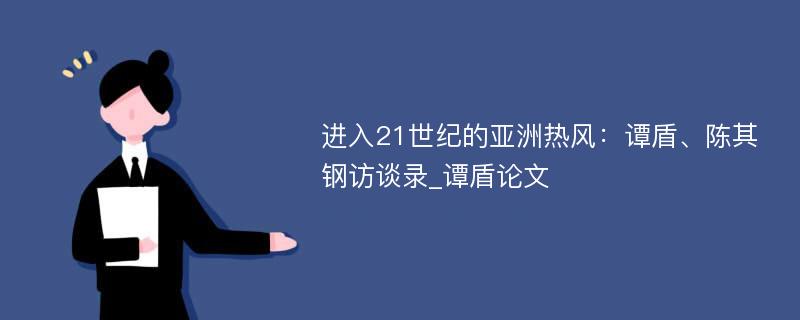
亚洲热风吹向二十一世纪——访谭盾、陈其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热风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吹向论文,访谭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神奈川艺术节举办的“亚洲之声”活动期间,与韩国的姜硕熙、白秉东、李万芳,台湾的马水龙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作曲家——纽约来的谭盾和巴黎来的陈其钢。谭盾1957年生于湖南;陈其钢1951年生于上海。虽然年龄相差较远,但两人都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同班同学。在这同一个班上,因为还有包括瞿小松(1952~)在内的几位最初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人才,所以这个班在中国被人称作“七八届之星”。谭盾于1986年受周文中之邀前往美国,而陈其钢早在1984年作为官费留学生奔赴巴黎,直到88年为止一直师从梅西安。两个人不仅天赋不同,而且留学所在地也极不一样,一个是纽约,另一个是巴黎。为此他俩在作品风格上显示出来的不同使人们发生了兴趣。实际上他俩最近经常在一起活动,正积极策划着在世界各地举办亚洲人的音乐会。
石田:我最早听到陈其钢的代表作《抒情诗》是在1992年的ISCM华沙大会上。这是以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为蓝本创作的一首男声与十一件乐器的作品,它那精密的刻画与淋漓的诗情留给人极深的印象。现在中国这一代作曲家受到了世界的注目,而这当中陈其钢的音乐显得非常与众不同,至少跟最近在日本开始受到注目的谭盾的作品风格极为不同,所以我早就想过有了机会一定要把陈其钢介绍给日本。恰好这次神奈川艺术节举办的“亚洲之声”在邀请谭盾的同时还请来了陈其钢。这次你们两个一个从纽约、一个从巴黎在日本碰上了头,我想请你们介绍一下包括过去的你们的有关情况。首先,作为同班同学能否请谭盾向我们谈谈陈其钢呢?
谭:石田先生来纽约时,我曾让他在我家听了陈其钢的录音带,并特别希望他能把这位优秀的作曲家介绍出去。不管怎么说,我跟陈其钢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学校、而且在同一个班里共同学习了六年的朋友。尽管后来逐渐分开并各自独立,但就像植物一样我们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枝。尤其应当说的是,就像日本有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一代一样,我们这批人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与我们的前辈、以及现在二十岁左右的后辈的不同,就在于这场“文革”的经历,实际上“文革”对我们的冲击和影响是相当大的。
石田:谈到“文革”,我听说陈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文化人,作为一名艺术家知识分子,据说在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当中受了不少罪。
陈:确实如此:我父亲是书画家,母亲是音乐家,他们都是领导干部。我从小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家庭里长大的。由于“文革”当中知识分子变成了“黑帮”,“文革”一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从天堂掉到地狱里了。明明是同样的事物,感觉起来却完全不同于以前。那时候音乐学院的院长、教授都成了“黑帮分子”,挨揍、被批,看到的这种情况使我觉得难以忍受,就好像受罪的是我自己。因为想不通,我就发表了我自己的看法,结果“文革”一开始就挨了“打倒反革命言论家陈其钢”的大字报。那时候我才十四岁。那个时候,我被当作“反革命”被工宣队批了三年。在中国,一个人一旦被认为在政治上有问题而遭到批判,你的前途是很黑暗的。不过像这样的经历我并不很想谈,有同样经历的人在中国是太多了。
我的父亲是个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很着迷的人。在我五、六岁的时候自己什么也没感觉到,成人之后才发现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是十二岁进的音院附中,因为母亲是搞音乐的,所以我进校之前接受了她的启蒙教育。我确实有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环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给了我一种束缚,使我很难从中国古典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脱离出来。
石田:跟陈其钢完全不同,谭盾是在几乎没有接触过西洋音乐的情况下考上音乐学院的。而两个人都是在两千名考生当中经过激烈竞争,最后作为考取的二十六人当中的一员踏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七七届。同学间最开始的感觉怎样呢?
陈:同一个班里也有各种不同的人。像谭盾、郭文景他们,尽管音乐学习开始得比较晚,但是在思想上十分活跃,在这方面我很佩服他们。毕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最开始时,我觉得他们和我很不一样,但是最近感到我们追求的精神很接近。在这些人当中我和谭盾的想法更为接近。不过谭盾当年可不是一个好学生(笑),从老师的角度看,他属于那种不听话的学生。
石田:音乐学院当时的教育制度是苏联式的吗?
谭:里姆斯基—科萨可夫的管弦乐法、斯波索宾的和声法、对位法是苏联编的教科书,老师虽然是中国人,可是大学二年级为止学的都是苏联的古典音乐。像卡巴列夫斯基、哈恰图良、斯克里亚宾都学了,可是像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这些人的东西都是被否定的。梅西安、布列兹、武满彻当然都不行……
石田:我也曾查看过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资料,没有找到什么海外的有关资料。你们当时能得到外国的信息吗?
谭:资料是没有的。学校里只有武满彻的一首、梅西安的两首作品左右。当时中国在音乐信息方面是很保守的。
陈:可就在这种情况下,谭盾没听老师的,创作了第一首交响乐,就是这个作品在中国的第一次作曲比赛上得了奖。老师很吃惊,都没去听。由于谭盾擅自跳过了当时的教学大钢,老师是十分恼火的。他这一步与学校的要求完全不同,可以说是迈上了独自的创作道路。
谭:我那时并不懂西洋音乐,不过是写了自己想写的东西,规则并不正确。
陈:尽管老师不高兴,可是同学们一个个都很兴奋,都支持他。
石田:那次比赛的评委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谭:音乐学院的老师和校外的老师各一半。《离骚》这首交响乐是我读了屈原作品之后试着表现一种愤怒的感情。
石田:《离骚》的作者屈原是中国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吧。
谭:这个人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评委会说“谭盾这个作品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的反动作品,必须进行调查。”为此,比赛完了之后开了一个星期会,结果没受审查反而得了特别奖,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陈:倒不是作品本身写得好不好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预示了当时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想潮流。
谭:从这个曲子之后,我们这一代作曲家开始被称作“新潮派”了。不过,《离骚》虽然算是我的一份宣言,但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现我自己。从五年级时创作《道极》开始,我才渐渐自觉起来。《道极》初次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听众直笑,说“这叫音乐吗?”
陈:当时我们班里被人称作“新潮派”的那部分学生当中并不包括我。我那个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算是个好学生。
谭:那时候我们都管陈其钢叫“教授”。(笑)
陈:在谭盾他们为参加比赛写东西的时候,我只是在学习学校的功课。我觉得我还不成熟,打算将来有机会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而且我认为我在一段时间里只能做好一件事情。直到现在我搞一部作品的时间也是很长的。作曲系毕业的时候正好有出国留学生考试,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
谭:他是最棒的一个。当我们大家听说他不但考上了去巴黎的留学生而且还成了梅西安的弟子,都羡慕得要命。
石田:你和梅西安的师生关系怎么样呢?
陈:我作为梅西安的入室弟子一共跟他学习了四年,确实是很幸运的。梅西安给予我的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个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我从他那里还学到了许多音乐之外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启示。
石田:那你有没有受到梅西安基督教观念的影响呢?
陈:我从他那受到的影响主要是:一个人应当怎样活着;一个人应当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这些都不是宗教性的内容。他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一点是“走你的路,做你自己”。所以后来不管梅西安对我说什么,我都按照“做我自己”的原则去行动。有时候梅西安都不太高兴了,可是当他想到欧洲人在思想上、生活习惯上与我之间的巨大差距,他还是对我表示了理解。我认为,东方人在向他们学习的时候如果丢掉了自己,东方人写的东西只是投西方专家的趣味,那是很危险的。
石田:从1984年以来,陈其钢先生住在巴黎,你对欧洲音乐界、作曲界的情况是怎么看的?你今后在那里继续从事创作活动的依据是什么呢?
陈:我就依据我自己。既不依赖某种思想,也不凭借过去什么人的规矩,我应该追求的就是现在的我。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像“要现代”“要中国风格”,都很抽象。
说到欧洲,这三十年实际上很封闭。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半期,巴黎、西柏林等等为了尝试新的东西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作曲家们写了不少试验性的作品,可现在能留下来的不多。六十年代欧洲的评论家们曾预言说:“虽然这些作品如今不能被理解。但若干年后必定为人所理解。”可是现在这些预言并未实现。我也曾相信过那种预言,可现在已十多年了听不懂还是听不懂。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活跃的欧洲年轻作曲家们也不再信那些试验作品。我们中国人正好是这个尝试阶段进入尾声之时得到了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西方已经开始注意中国、日本这些东方国家。我们正在以我们的思维和文化向欧洲注入新的血液。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也许日本人不这么想。和中国不一样,日本受西洋影响可能更深。
谭:不,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比方说日本、美国。就像经济一样,现代音乐创作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现象也将渐渐消失,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像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当时的西德——花大笔的钱去支持和支援文化发展这样的事情,今后恐怕是不会有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人为的破坏,而当时西欧的做法又是一种生硬的人工栽培。就像我吧,以前是很难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的,现在却不同了。可见欧洲也在寻求多元化的因素。
正是这种“现代”的状况,正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同时展开着。稍微大胆一点说,这种正在展开的新状况已经以二十一世纪为其目标了。对我来说,二十世纪早就已经完了。二十一世纪的一切的一切并不是从2000年才一下子开始的,而是已经开始了。比方说石田先生的看法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现在谈论的话题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音乐既是悲剧性的,又是极其复杂的。中国哲学有一种看法,即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表现最复杂的东西。这样的东方哲学恐怕会在二十一世纪发挥其作用。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时一种主张、一种主义有可能扩及全球的话,这种情况在二十一世纪恐怕是难以办到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种情况的出现,那就是二十一世纪将与二十世纪相反,会变得更简单也更丰富。就是说,将不再是一个主张而是更多种的风格。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亚洲,日本和中国将作为文化的主力推动整个东方。
陈:我认为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一定会碰到阻力。那些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先生们的影响力难道那么容易超越吗?其实还是很难的。
石田:二位的发言谈到了这十年当中的情况,那么中国现在的年轻一辈又怎么样呢?
谭:就说我,1985年写了《道极》,十年之后的1995年又写了歌剧《马可·波罗》,从今以后还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而我们下一代的作曲家、音乐学院的学生已经很不同了,老师们也不同了。跟我们那时候相比开放得多了,对二十一世纪也怀着相当的兴趣。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代有一个根本上的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摸索过来的,而他们是靠在学校里学习得来的。我感觉他们当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不多,比起我们来,他们更听话、保守。回国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谈话中介绍世界音乐潮流,但他们好像不大听得进去。他们好像又进入了一种新型的封闭,对此我是有些担心的。
陈:我有同感。中国现在是把十二音技法作为新的东西在教。中国人现在富裕起来了,有钱谁都可以到国外去学习。但是因为他们缺少我们那样的背景,既便是到了国外,究竟应该看些什么、学些什么还是不清楚。现在只要去德国、英国常常就会碰到一些人,他们的生活过得和欧洲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他们不但没有属于自身的生活,更不曾考虑去开辟自己的道路。那些从日本、台湾、香港来的学生不少是这样。
谭:我们应当向着二十一世纪携起手来,共同构筑现代音乐的桥梁,与更多的人合作、搞更多种音乐节,不是光为一小部份人而是为更多的人——努力。
石田:谢谢。
采访日期:1996年11月13日
小草 译自1997年3月号 日本 《音乐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