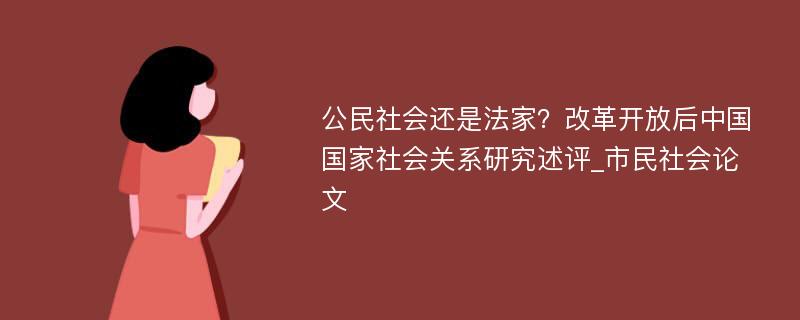
市民社会抑或法团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社会关系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6-0112-07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重组引发了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重塑。一个总体的趋势是,原先的全能型国家已经开始从某些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中逐渐退出,党与政府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少,具体控制方式也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逐步降低自身对于国家的依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①。因而,无论是原有意识形态化的集权主义分析范式,还是基于多元主义理论的利益集团范式②,都无法准确描述与分析中国社会不断变迁的现实。随着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博弈互动格局的逐渐产生,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思潮。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社会研究呈现出了从市民社会到法团主义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对于中国社会国家—社会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及其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地位的形成,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立论基础。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控制与管理以及社会组织主动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实践策略,反映了法团主义理论的适用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法团主义分析视角,都将其研究重心落于社会面对国家之时的自主性问题之上,并形成了大量经验研究成果。本文主张,两种理论视角的综合运用才有可能准确透析处于持续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一、市民社会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
从市民社会视角分析我国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研究,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与民主化运动。而就现实层面而言,则是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的逐步出现与发展的回应③。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为载体,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的学术争论,为理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以及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建构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争论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的概念界定及其规范意涵上。而几乎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开始将市民社会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经验现象分析,并逐渐发展为指导中国政治研究的主导性范式④。
1.基本概念与理论架构
关于“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较常见的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种中文表述,大体上都是指处于国家(政治领域)与家庭(私人领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地位与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其中,“市民社会”的译法最为常见,主要侧重于从经济关系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公民社会”则更多地强调这一社会领域的政治功能,即公民的参与以及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民间社会”概念多为我国台湾研究者所采纳,往往应用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研究之中⑤。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源自于近代欧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反思。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之后经由马克思的完善形成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概念⑥。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三种分析路径:洛克的一元论,即把市民社会等同于国家或政治社会,强调政治民主;黑格尔的二元论,把市民社会区别于国家,强调经济自由;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三元论,把市民社会既区别于国家或政治社会,又区别于经济社会⑦。
受到上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基本定位也存在着不同理解,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以邓正来为代表的“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的二分架构。他认为,所谓政治社会是指政府与政党所构成的政治领域,而公民社会则是指除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非官方领域⑧。另一种则是“国家—公民社会—私人领域”的三分法,以何增科、俞可平等学者为代表。何增科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在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⑨与何增科相类似,俞可平提出了“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经济社会”的三分法,即公民社会主要体现为由非政府组织、志愿团体、协会等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⑩。
进而,关于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的规范架构也形成了三种观点,即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国家高于社会说”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维度的形塑作用,从而认为社会乃是国家之附属。而“社会高于国家说”则相反,认为社会先于国家,国家乃是实现社会目的之工具。第三种则是邓正来提出的“国家—社会良性互动说”,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应当形成“良性的结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并为其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保持对社会的合理调节与干预,从而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的结构关系(11)。
2.从规范理论到经验研究
政治理论传统下的规范性分析,形塑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戈登·怀特认为,市民社会反映了一种界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尝试,它将国家与社会区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暗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能够限制国家渗透与控制社会的能力,使其成员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在自主的社会权力与空间领域,市民社会意味着是由社会成员志愿组织起来的结社领域(12)。换句话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地位以及社会对于国家的制约能力是衡量市民社会的三个重要尺度。与此相适应,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经验研究则主要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即: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如何?判断中国市民社会是否存在的标准是什么?市民社会理论是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吗?
对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持否定看法的夏维中认为,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来看,市民社会并不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之内,市民社会相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是一个异质性概念。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其未来前景也可能只是一个“近期难圆的梦”(13)。而萧功秦也持有大致相同的判断,即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建设存在三重障碍,即专制主义传统、近代国家政权的羸弱,以及1949年之后国家全能主义(14)。但另有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如俞可平就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社会分化与独立地位,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以及相关法律规章政策的修订,将有可能形成促进市民社会发育的良好局面,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将会在中国逐渐出现(15)。另外,朱英关于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否定了中国历史中不存在市民社会的判断(16)。
判断市民社会是否存在的标准为何?就经验层面而言,研究者们多从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现实状况,即以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市民社会是否存在的标准。其中最有代表性、且最早进行关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实证研究的是戈登·怀特。怀特通过对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实证分析说明,与改革开放前缺乏自主性、由国家控制的社会组织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组织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点,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成分,也有自下而上的成分。介于政府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民间社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受到官方的限制,但他们已经开始利用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空间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地位,为自身及其成员谋求利益。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逐渐影响政府决策。对于怀特来说,社会团体活动空间的扩大和体制外沟通渠道的形成,意味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预示着中国正在迈向市民社会的前景(17)。朱健刚则通过对于草根志愿组织的分析提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生产,拓展了社会公共空间的范围(18)。裴敏欣虽然认为,由于国家的限制与约束,市民社会的产生并不会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依然认为市民团体的大量出现可以说明中国市民社会的萌芽(19)。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之中(20)。
3.市民社会理论适用性问题及其修正
早在1993年,俞可平就指出,“市场经济新体制对我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影响将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事实上,这样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正在悄然出现,在现存的社会政治理论框架中引入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概念已显得很有必要”(21),较早地提出了市民社会的适用性问题。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市民社会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同样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在持续快速的增加,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参与公共事务,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伴随着自身独立性、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22)。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发育更多地依赖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从而未能打破强国家—弱社会的利益格局,政府通过注册登记管理、资金和人事管理等方式,紧密控制着民间组织的活动(23)。由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对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修正,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概念。怀特虽然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迈向市民社会的前景,但是就现实而言,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正在出现一个“不成熟的市民社会”、一个“半市民社会”或“国家主导的市民社会”。而对于作为市民社会重要指标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上,同样有研究者质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及其对于市民社会出现的意义。有研究者就指出,中国的新社会团体仅仅具有自治团体或法人团体的外形,而无作为独立自治组织的实质(24)。
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反思性修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转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经验分析。即使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支持者也同样认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始终无法完全脱离政府的影响与控制,更不用说形成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制衡力量。非政府组织始终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与资源(25)。因此,研究者发现,另外一种与市民社会理论相互冲突却又存在交叉渗透的分析框架即法团主义,能够更好的分析社会组织对于国家在政策层面的影响及其依赖性关系。
二、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
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复杂性,造成了单一理论必然无法适用于所有现实的状况。市民社会视角因其过度强调组织自主性以及社会—政府之间的制约制衡关系,就显得过于单薄。相比于市民社会视角,法团主义因为与东亚政治传统及其社会性质具有较高的亲和关系,从而成为解释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26)。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因为其全能主义的历史背景以及国家主导改革的基本转型格局,也促使研究者开始运用法团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27)。
1.基本概念与理论架构
法团主义理论起源久远,其理论渊源也极为多样,可以追溯到圣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而中世纪的天主教思想、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民族主义观念也对现代法团主义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28)。在法团主义看来,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国家对抗社会,而是国家整合社会,进而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社会组织与其说是与国家相对抗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国家主导之下的利益代表组织,是协调整合组织成员利益与政府政策的中介(29)。根据施密特的经典定义,法团主义是指“一种利益代表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组成单位被组织到数量有限的,具有单一的、强制的、非竞争性关系的、等级制的、功能分化等特征的各个部门之中。这些部门得到国家的承认或者授权成立(如果不是由国家直接创建的话),并被授予其在各自领域中垄断利益代表的地位。作为交换条件,国家对于这些部门的领袖选择和需求表达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30)。基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关系的差异,施密特进一步区分了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中,上述六种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通过强力形成的,国家依照行政或立法的手段赋予某些社团在具体领域中的利益代表独占权。而在社会法团主义模式中,某些领域中社团的地位是通过竞争性淘汰或相互合作交易形成的。国家并未禁止某一具体领域中社团之间的竞争,但会选择支持或承认某些社团的地位以维护其利益代表的垄断权。在施密特看来,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其是一种利益聚合与协调的方式,利益代表、聚合与协调方式的差异就构成了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
在中国,法团主义模式的引入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推动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解释力的反思与质疑,另一个在于中国自1989年之后对于社会组织的严格监管和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共存的现象,引发了研究者的注意(31)。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法团主义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同时也是我国现实发展的可行之道。在法团主义制度安排之下,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得以形成稳定的互补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国家—社会相互依赖、合作共赢的局面(32)。孙双琴认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国际环境的角度来看,法团主义模式更契合于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应当以法团主义模式形塑中国未来的“国家—社会”关系走向(33)。顾昕同样认为,法团主义视角有助于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观念,通过国家主动的整合与介入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推动社会发展(34)。另外,与市民社会理论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析一样,亦有研究者通过对于1949年之前武汉工会的分析,论述了法团主义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运作机制(35)。
2.实证研究与经验分析
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格局是法团主义式的吗?从当前我国国家—社会关系格局的现实状况看,法团主义似乎很适合于用来概括中国(至少某些具体领域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36)。工会、企业家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工商联合会等等,都具有单一性、非竞争性、等级性、要求国家承认、代表地位的垄断、领袖选择及利益表达受到国家控制等特征(37)。顾昕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监管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色彩,相关行政法规的出台正是为了维持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有效控制。在对1998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规定与施密特关于法团主义的界定进行比较后,顾昕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法团主义特征(38)。在中国,社会组织的成立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并要在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狄忠浦同样认为,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当前的法团主义策略(39)。在法团主义安排中,通常每一领域社会组织的数量都是受到限制的,社会组织由于其独占性的地位往往不存在相互竞争的现象(40)。从社会组织领导人的任命和构成上来看,很多社会组织尤其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常常是由主管单位领导,或者退休、退居二线的领导兼任。社会组织中的专职成员有很多也是由从国家机关中退出来的前公务人员担任(41)。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他们或者倾向于官僚制度内的晋升,或者利用这些机会改善关系、扩大受益(42)。陈佩华在关于工会的研究中提出,中国的工会具有单一性、等级性、非竞争性以及代表地位的垄断性等特征,而与此同时又能够在工资、住房、工作条件、社会福利等方面从事政策参与,在代表工人利益与协助政策执行两方面起到作用(43)。
法团主义视角的解释力还体现在其能够深入到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内在维度之中。对于中国法团主义研究者来说,他们除了宏观制度层面对于中国法团主义制度安排加以论证之外,还充分注意到了诸如政府的层级、政权机构的利益、市场化的力量等等因素对于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影响。首先,从中央—地方关系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力变化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央政府依然保持着对于社会组织的国家法团主义管理方式,但是一方面由于控制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使得我国的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没有能够自上而下较好的加以贯彻。赛奇就认为,国家在形式上的控制与实际控制能力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社会组织获得了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进行利益博弈的能力,即与国家进行协商。这是因为,政党的管理和动员职能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另外,党员身份、地方官员角色或经济行动者的多重身份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44)。其次,地方政府中的不同层级,如省级、市区级与县级之间的差异,同时官员的个人利益以及组织部门利益等多种因素对于政府—社会组织关系同样会产生影响。“简言之,即使中国的法团主义要素在持续的增长,也不能认为它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体划一的法团主义机器。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拥有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国家与地方各自的法团主义安排并不和平共存,有时也存在相互对立。”(45)所以说,地方政府的法团主义安排是在中央与地方团体(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方)的夹缝之中发展起来的。
3.法团主义的转型与未来
基于大量经验个案的分析,研究者们进而开始期待中国国家—社会关系更多地体现出由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甚至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趋势。由于工会、妇联等官方社会团体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加,政府对于社会组织逐渐放弃直接的控制,更多的通过人事、注册登记等间接的制度化手段来进行监管。与此同时,这些社会组织本身也逐渐受到其成员利益的引导,成为组织成员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安戈和陈佩华认为,虽然中国的官方社会团体依然体现出“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但是至少已经出现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变的倾向(46)。顾昕与王旭也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从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的过渡,并期待进一步转向社会法团主义(47)。
三、对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的综合分析
究竟何种理论更为适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理论框架的适用性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不断变化的国家(48)。基于一种“低度共识”,市民社会视角试图从社会公共空间的开放、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以及国家全面控制的转型之中发现市民社会的萌芽,但是,无论是在制度安排还是在现实实践中,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的监管,其行动也往往更多地体现为与政府合作、互利的生存策略。法团主义视角则主张国家—社会相互整合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于分析中国的社会团体以及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对于草根NGO以及其他领域的社会组织运作的解释则不那么令人满意。正是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内在多维度特征,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将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理论综合运用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倾向,其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
在理论建构层面,研究者开始尝试借用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框架构建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独特路径。如郁建兴就提出,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应当具有明显界限,但是这种界限同时应当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动状态,而不是被严格的限定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应当是基于二元划分的对抗与分离,而毋宁说是相互增强的合作关系(49)。而在实证研究维度上,康晓光、韩恒建构了当前社会组织管理的分类控制体系,依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公共物品提供能力,相应的区分了政府的不同控制手段。研究者提出,中国当前的国家控制呈现出弹性状态,针对社会组织的不同控制策略与强度,取决于政府的利益需求和控制对象的挑战能力(50)。范明林的研究也同时运用了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两种分析框架,按照法团主义式监管中的“授权”、“控制”和“垄断机构”,以及市民社会框架下的“自主性”、“自治性”和“契约化”为指标,考察了不同领域中的多个非政府组织,从而形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的“强控型、依附性、梯次性、策略性”的类型学划分(51)。
总而言之,无论是关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路径与制度设计,还是当前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理论解释都是值得充分借鉴的理论资源,而鉴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内在复杂性与多维性,应当综合运用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两种理论视角,通过经验剖析与理论建构的来回往复,才有可能阐发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取向,进而真正有助于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更具意义且更为细致的分析。与此同时,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相互依赖与增权的关系模式也并非没有可能实现。
注释:
①罗兴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学术界》2006年第4期。
②E.J.Perry,“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no.139,1994,pp.704—713.
③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关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三个理论视角》,《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④Da-hua,David Yang,“Civil Society as an Analytic Lens for Contemporary China”,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2,No.1,2004,pp.1—27.
⑤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另可参见张康之、张乾友:《对“市民社会”和“公民国家”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周俊、郁建兴:《Civil Society的近现代演变及其理论转型》,《哲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⑥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⑦李略:《市民社会和社团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模式》,(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第25期。
⑧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⑨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⑩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
(11)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载于邓正来著《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3页。
(12)(17)Gordon White,“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1993,pp.63—87.
(13)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5期。
(14)萧功秦:《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三重障碍》,(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5期。
(15)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16)朱英:《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几点商榷意见》,(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7期。
(18)朱健刚:《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21)俞可平:《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关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问题,另可参见郁建兴:《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文史哲》2003年第1期。
(24)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质异”与社会团体的发育——以中国青基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载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24页。
(19)Minxin Pei,“Chinese Civic Assosiations:An Emprirical Analysis”,Modern China,vol.24,1998,pp.285—318.
(20)Gordon White,Jude Howell and Xiaoyuan Shang,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22)C.E.Nevitt,“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The China Journal,no.36,1996,pp.25—43.
(23)Anita Chan,“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1993,pp.31—61.
(25)Gordon White,“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1993,pp.63—87.
(26)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no.33,1995,pp.29—53.
(27)通常而言,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市民社会概念,就其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方式而言,实际上等同于多元主义。因此,通常所谓的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应当是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对立。对于这一观点,可参见吴建平:《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8)参见张静:《法团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47页。
(29)颜文京:《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第三种模式——试论组合主义》,《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
(30)(40)P.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6,no.1,1974,pp.93—94.
(31)最早使用法团主义理论并将之与市民社会理论加以比较的研究者是陈佩华,可参加Anita Chan,“Revolution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1993,pp.31—61.
(32)许婷:《法团主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33)孙双琴:《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法团主义视角》,《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34)顾昕:《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35)胡悦晗:《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法团主义视角下的武汉工会(1945—1949)》,《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36)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37)吴建平:《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38)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39)Bruce Dickson,Wealth in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2008.
(41)Margaret Pearson,“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1994,pp.25—46.
(42)C.E.Nevitt,“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The China Journal,no.36,1996,pp.25—43.
(43)Anita Chan,“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1993,pp.31—61.
(44)(48)Tony Saich,“Negotiating the Stat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61,2000,pp.124—141.
(45)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no.33,1995,p.48.
(46)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no.33,1995,pp.29—53.
(47)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49)郁建兴、吴宇:《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50)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51)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