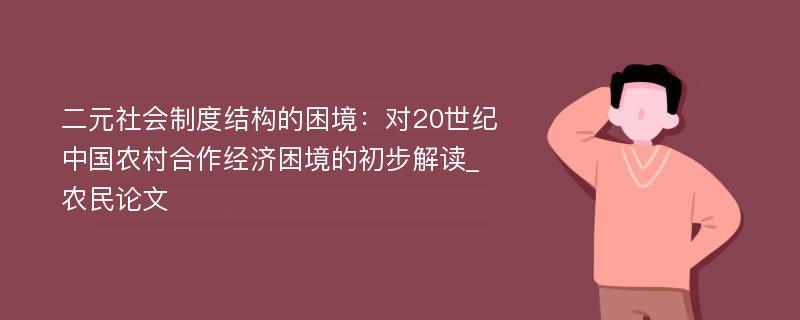
二重社会制度结构的困厄——对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一种尝试性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厄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乡村论文,社会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7)09-0038-11
制度结构的特征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选择的空间。这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诺思(D.C.North)认为,制度结构是“指那些我们相信是决定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是经济社会中国家、市场组织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机制。在制度结构中,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与其他产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博弈过程往往就形成了演进的路径①。存在于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在被移植“嵌入”②到中国这个制度结构背景与之不同的地域中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强制”状态下单兵推进时,其原来与之匹配的各种制度之间协调演进而形成的均衡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系统)已不复存在,故而在运行方面出现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指出的:“合作社在自己的发源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把它移植到不发达国家的企图却失败了”③。其给人们留下的是至今仍然难以消解的困惑和现实:缘何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农业中不乏虎虎有生气的“合作化”④(或“集体化”),相反全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也最需要组织化的中国乡村社会合作化却命运多舛而难以很好成长呢?本文以中西方社会制度结构差异为切入点,对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社(包括前半期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及建国后的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等)⑤发展困境做一简要剖析,以有资于今天政府倡导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
一、中西方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差异
西方的现代社会制度结构奠基于中世纪社会的晚期。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存在着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在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之间,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尤其是在王权和领主、基层民众等社会力量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主体权利”⑥,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原始契约” (英国学者梅茵语)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包括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王室法等“世俗法”(或称为“习惯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多元的法律体系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反映了多元的社会力量:庄民、商人与领主相对,领主或贵族与王权相对,王权与市民社会相对,市民社会与领主相对,教会与王权相对等等。这种自由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存在,使法律体系及司法管辖权具有多元性,最终使法律的最高权威成为必要和可能。因此,西欧中世纪时就有尊重法律,一切须经过法庭以及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独立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带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世俗法,是对不同经济活动的主体之间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这样就为自由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法制和法治的基础。正如现任哈佛大学名誉教授伯尔曼(J.H.Berman)所指出的:在西欧那样的条件下,“所谓封建制度的法律,不仅维护当时通行的领主与农民的权力结构,而且还对这种结构进行挑战;法律不仅是加强而且也是限制封建领主权力的一种工具”,故而在一定限度之内确保了每一经济主体 (包括农民)的财产与财富的独立发展,“这样的法律调整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形式”⑦。可以说,原始契约关系的因素是西方多元社会结构的前提。
西方社会的分化程度较高,是“由较为特异的和复杂的群体与阶层组成,诸如各种土地贵族、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民以及强大的宗教团体和组织。”⑧相对应的,其制度结构至少是三重的,即在国家与社会下层民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而活跃的中间阶层,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共存而又相互制衡的制度结构。这一中间阶层的角色,在西方封建社会初期主要是由领主、贵族扮演,而在封建社会后期,商人、企业家、银行家和许多类型的经济组织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社会经济结构稳定的中间层。此种具有主体权利的中间结构,居于中介位置,以法律为依据,一方面,它把人们组织在各种纵横交错的社会结构中,使社会成员在与国家权威的“讨价还价”中摆脱了“孤立无助”的窘境,避免了作为个体来直面国家权威的压力,防止了其对个体自由、权利的过度侵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途径,它在将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诉求合理化的同时,为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凝聚与表达疏通了渠道,代表社会成员向上层国家权力转达信息,避免将任何冲突都导致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最终在彼此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以法律为归宿,形成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缓冲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使国家与社会处于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进而促进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平稳演进。
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制度结构而言,中国的制度结构比较独特。众所周知,一直以来,“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几乎不存在、也不需要旨在保护产权与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结构;同时儒家学说作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互为补充,另一方面又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考核内容,从而把信仰儒家意识形态的士人制度化地转变为国家官员,官僚机构具有的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防止了官僚世袭,演变为贵族领主。而且,这些国家官员缺乏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也谈不上维护自己的权利,完全是中央集权的附属物和统治工具。此种情形下,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间阶层,国家具有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对民众的广泛支配权,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往往没有任何可以匹敌的对手,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偏好由上而下的行政强力控制;与此相对,个体权利及其微弱的下层结构所获得的经济自由及产权是极不稳定的,因此,中国的制度结构是二重的。其基本情形可以概括为: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呈分散化、原子化的下层结构,上下层结构之间缺乏严密有效的富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也正是这一中间协调机制的缺乏,形成了资源无以聚集,社会无以快速发展的局面。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M.Weber)曾指出:“按照法律,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与小农民,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中国都不存在”⑨。在中国这种上下层直接相对的二重结构中,官民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契约关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与境况一直偏离某种均衡状态,并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获益机会分布结构,也就是说,获益机会主要分布于社会的上层结构(即官的层次)⑩。
中间阶层同时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但是其得以存在的本质特点在于它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质与自身逻辑的存在。其自身对社会就具有凝聚力、约束力和秩序化的功能。所以,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否,或者说中西方社会制度历史结构的差别,对于合作社制度的演进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这一点上说,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运行的制度基础是社会的三重制度结构。其一方面在市场与法律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起到屏障作用,即对政府的权力活动进行边界约束,使国家的暴力潜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又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避免国家对社会个体的过度侵犯,为社会营造了相当的自主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发挥驱动作用,使分散于下层的资源得到充分动员与有效配置。双重作用的契合,造成社会成员与国家在对话、协商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均势,由此促使了具有主体权利的民众,以平等、民主为原则自发地组成了可以降低生产要素在其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合作社制度,将内部关系非市场化与外部关系的市场化有机结合,最终以自下而上的途径形成了具有声势的“社会化”合作运动及“自治性”的合作经济制度。从而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在“制度化的彼此妥协”中实现了基层社会经济活动的秩序化和有机化。难怪一些学者在论述20世纪初期德国的合作运动时认为:“合作运动紧紧控制了农民社会”;合作社对农民的作用“比所有关于农业与关税的法律加在一起都要多”(11)。显然,中间层的存在,不仅可以对权力与“政统”构成一种“社会制约”,而且还是实现社会有效整合、造就社会的自我组织以及自我形成秩序能力的重要社会力量,它决定着一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制度演进绩效。
在中国社会的二重机构中,一方是具有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的、“原子式”的个体化民众阶层。这种“头重脚轻”阵式和力量极不对称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上层的偏好与决策缺乏来自下层的制约与纠偏,由此决定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的权威性、所采取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代理人的廉洁(道德自律)与办事效率。但这些在缺少契约理念和未经民主化洗礼的国度中就显得特别苍白无力了。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的合作事业推进上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二、二重社会制度结构下乡村合作运动推行的强制性、行政化
中国的合作事业是在“凌驾于私有产权之上的国家为最高产权或最终决定权”(12)的笼罩下,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缺少制度化的协商和谈判,政府遂从自身意愿出发强力推行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compulsiv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与西方不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人是基于现实的观点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民生主义之实现的角度来认识合作社的,并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明确提出“为谋国民经济之发展,国家应提倡各种合作事业”(13)。因此,合作事业在中国从其滥觞阶段起就呈现为一项重要的建国政策,并从中产生了合作事业“自上而下”进行中的强制性约束力与法律性效应。农业经济学家张德粹对此解释说:我国之经济政策是以三民主义为依据,“三民主义之经济政策当为计划性且富于统制性者,而非一种放任政策。又因合作原则与三民主义相符合,故政府素采发展农业合作之策略,以为组织农民,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此与以往少数欧洲政府之放任合作或嫉视合作者,情形殊不相同。且以农民知识之落后与农村豪强恶势力之横行,对于合作阻力甚大;因农民之无知识,故不知自动合作;因豪强之阻碍与破坏,纵然农民自愿合作,亦有所畏忌而不敢合作;倘非有政治力量强制推行,而全赖农民自愿与自动之力发展合作,是无异‘俟河之清’,亦不知须期待若干年代”,故借政府力量以“强迫性质”推进合作,势所难免(14)。合作事业在中国变得“国家化”和“官僚化”,致使其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性,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呈现为崛起于底层的社会经济运动。同时,由于缺少拥有足够谈判能力的社会力量对国家进行制约,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随时进行制度变迁(如建国后的“公社化”运动而形成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下动作的)。
制度变迁的这种强制性与随意性行为,表现在政府颁布的各种合作法规多如牛毛,混淆不堪,有时行政命令或解释的效力甚至超越了合作社法(15)。这一点,尤其是在政府1940年8月颁布的《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中显露得最为充分,其中认定“县各级合作社组织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机构,应与其他地方自治工作密切配合”,并规定“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的组社、入社原则;在此之上,大纲还严令:各合作社“一律用保证责任”,业务方面采取“兼营制”,同时又竭力限制合作社的解散与社员退社(16)。行政强制,显然有悖于合作经济的自身发展规律,但其基点却是统治者的偏好和政府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的“有限理性”:通过此“不仅确定合作为发展国民经济事业之基础,且将合作社成为政府对人民实施‘管’‘教’‘养’‘卫’之基本组织”(17),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与经济秩序的重新构建。也正是上层的过度强制与有限理性,导致了合作社性质、“功能范畴”的“异化”:即在西方“弱者”结合而成的合作社,主体性诉求是在实现个体或团体利益的组织化,仅具单纯的经济性质,多与政治无涉,而在中国则既有挽救农业衰败、缓解农人疾苦的经济功能,还要有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稳固基层统治秩序的政治功能,更要有整合意识形态、强化民众对政府及其主义顺从或认同之功用。更多追求的是政府的利益或政治利益。国民政府在倡导合作时曾明言:合作事业不但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可以使人民的精神能够团结,行动能够统一,力量能够集中,即以造成健全的现代社会,而为新政治上的坚固基础。带来的绩效是一场理应为“经济的改造运动”,却因政府的偏好和其权力对下层的过度干预,导致了合作制度“变异”成为“政治的改造运动”(18),“百分之百的,政治作用重于经济作用”(19)。建国后的人民公社体制也是一种“政社合一”、“政经合一”的组织,公社制度“统揽”和“束缚”着农民的行为,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还包括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与政府的官僚机构有着莫大关系。合作事业的“国家化”和“行政化”,使国家政权、地方政府及社会领袖成为推进中国农村合作事业的主导力量。事实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机制,是造成合作社为官方任命的行政人员即权势阶层所操纵、控制的制度根源。合作事业的重心在县乡基层,县各级合作社组织,除所谓的专营合作社外,“均系以乡镇及保甲为基础”。故此,国家的代理人的行为,即地方政府及保甲人员的素质状况就对合作社的构成产生重要影响。而官僚机构的情况如何呢?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关于各级干部人物,“国外归来的洋学生,固然是不便屈尊,就是国内制造的大学专门学生,也难望其低就,事实上,那里仍旧是豪强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后生小子是无法插进或站稳脚跟的。结果,在这传统社会关系改变得较少的农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较少嗅到新时代气息的人们行使统治。不过通过层层的组织与训练,通过他们被赋予的新管治任务,以前他们仅‘俨然’是官,而现在‘简直’是官了”(20)。换句话说,就是在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容忍、选择、联合并依靠了村落中的旧势力,以之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这样,也就为其进入并控制、利用合作社进行谋私利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ra)说:“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而且“土豪与其他政治领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追求权力的动机不同:他谋求公职主要是为了追逐私利,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以牺牲他所领导的集体利益为代价。”(21)国家权威性的有限性,使政府没有能力去超越这些占有资源优势的“分利者”之特殊要求(个人福利目标),以实现普遍的制度利益(社会福利目标),加之社会和民众的孱弱无以对之有效制约,结果只好任凭“权力精英”运用手中握有的政治资源取得既得利益。犹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言:“官僚阶级控制了流经政府渠道的银行信贷,在地方上与地主放债者有着许多共同的联系。”(22)最终形成了“异化的合作社”和造成合作事业上动而下不动的“有头无干”之困境:入社者多是有产者或中产之家,而下层社会的大部分贫农“便不能不徘徊于‘合作之门’以外”,享受不到合作社的便利,“任其自生自灭”。就此,有论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变质的合作社,是“官绅商的‘合作’,于百姓一无裨益”,“替膨胀的商业资本找到一条出路,而结果造成高利贷资本”;再者,合作社“大都带有官办性质,办事人员还脱不了官僚典型,官僚气息的浓厚存在”,使民众望而却步,“尤其在乡村,合作社每如摊派,缴不出股款的农民要被官厅逮捕,俨同罪犯,缴了股款,好处全无。”(23)异化的合作社,说明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因制度供给方式的失当降低了政府行为的有效性,扭曲成了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的组织。其实,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仰仗于既存的行政机制来推行合作事业,很容易造成合作制度与现有政治制度的连通或“叠合”,进而使得合作社制度受制于现有的政治制度环境,而且使人们在合作社内易于“移植”甚至于“复制”现有的政治制度,终为合作社组织内部的“寻租”开启了便利之门。
三、总结性评论
社会中间组织,或曰由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民众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是与人类共始终。
而且中间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克服有限理性、节约制度成本与实现经济协调的装置。它的缺乏,不仅会造成官僚机构对下层事务特别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影响了社会的自主性。正如王亚南所说,中国的官僚政治包摄范围极其广阔,官僚政治的活动与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都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它的支配作用相当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24)而且还会出现政府设计的利民政策,在实施中因官僚的自利性行为未受到有效制约而带来的自主性受损,最终使民众个体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可怜群”,制度绩效也因之大打折扣。孙晓村说:乡村中的地主豪绅往往借信用合作社之名,向银行借得低利借款,再用以转借于农民,转手间利息便提高。“这种合作社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的新式工具”——“集团高利贷”;“在没有信用合作社以前,高利贷者只能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剥削农民,现在他们可以自己不费什么力,利用信用合作社向农贷机关借得钱,假公济私,赤手来剥削农民。而且以前用个人名义出借的款项,收回借款比较困难,现在利用合作社的名义,不但多了一层保障,必要时还可凭借官厅的权力,加压于欠债的农民。这就是‘集团高利贷’的好处。”(25)国家、官僚机构在推进合作事业过程中出现的“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现象,足以证明政府“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对制度变迁绩效的损伤。美国经济学家鲍威尔森(J.P.Powelson)说:国家过分控制别人生活的权力足够分散,是保证制度的效率与公平之重要因素。因此,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建立一种恰当制度,其中心作用是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如贵族与农民之间,建立权势平衡,并确保下层次的集团拥有“杠杆”,即他们能从上层权势集团那里得到支持。只有当权势得到扩散,才会出现基础广泛的持久经济发展(26)。这一“恰当制度”的实质,就是促进中间层的培育。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崔敬伯也说过:“中间阶层,主要是属于经济意义的”,“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在没有达到社会化的阶段以前,中间阶层的存在,对于社会的组成,成为绝对的必需,因而对于社会的治乱安危,也必然发生很大的作用。这个中间阶层,等于西洋所指的‘Middle Class’,它不仅是中间,而且是中坚。因为是‘中间’,所以它能够黏合上层与下层,使之成为一个生存的有机体。因为是‘中坚’,所以它能够左右上层与下层,使上层不致横施过度的权,使下层不致妄动广泛的力。中间阶层得到适当发展的时代,也便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中间阶层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压迫,叫它没法子站在中间,演变所及,可使一个只剩下尖削的上层与广泛的下层的悬殊对立,中间却成了真空,其结果,不是招致倏忽的崩溃,也必是凌迟的混乱。”(27)所以说,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国家与选民(当然也包括小农)之间的“二重结构”关系,更多带来的是政府花费大量的成本用于农户与乡村的控制,而不是驱使也不可能促进基层社会自主性或自治性空间的增大,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聚集。
毫无疑问,合作经济制度是西方的多元社会制度结构与其他制度协调演进的“内生”产物,而将其移植到中国的二重社会制度结构中靠政府外力强制性作单兵推行,因缺少相应的制度与之配套协调,出现了合作社的“异化”现象,并造成了许多“异化”的合作社(如被“政治化”的人民公社等),这不能不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经济学者方显廷早就剖析说,中国的合作事业是政府的一种政策,而非一种运动,各种行政机构“既未能使舶来之合作事业,适合中国之国情,以令其发荣滋长,亦未能使农民对合作事业,真正了解。政府此种欲求速效之政策,实为目下合作事业失败之主因。”(28)应该说,社会组织化或合作化是西方现象,我们在学习西方社会组织化或合作化时却只看到了器物层面 (技术、工具、概念),看不见背后的制度层面(产权、组织、激励),更不见精神层面(价值观、预设、信仰)。器物或制度层面的东西往往容易学,文化与精神层面不配套,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总体而言,合作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文化与经济等背景因素。由此决定靠国家行政力强制进行的制度变迁,只能是一种缺乏下层机构有效参与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这也是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事实上,在西方良好运行的合作经济引入中国后却命运多舛,其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就是:一个组织和制度的形成、生长和嬗变,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组织结构及其制度模式内在的构造或重构过程,而必须考虑到组织嵌入其中的整体社会的“结构性环境”,也必须考虑到组织自身“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惰性,不考虑这些,在组织与制度变迁或创新的具体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拔苗助长”、“淮橘为枳”的效果,也有可能使一些本来有本土社会基础并能自发生长的组织系统受到破坏。当然,言此并非是说中国农民就不需要合作社组织。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已从单纯的受自然资源的约束向受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转移,以及小农与市场之间矛盾已成为农业经济的基本矛盾并且越来越尖锐化的客观现实,使得中国农村已经不是“农民要不要合作”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领域中促使或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的问题。为避免重蹈覆辙,一方面政府要力求在农民组织化中角色的合理定位。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应该说,行政力量适当介入与影响 (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而问题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对合作组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自身角色定位的认识和介入方式的把握。必须承认的是,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是合作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而政府在其中只能扮演着“从旁协助”、扶持和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从宏观层面为合作进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提供宽松政策环境及制度空间(如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绝非是在微观领域中盲目的、过度的“行政介入”或对农村建设的“嵌入式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相信农民,给农民以自由,并确立起他们的市场主体性地位。只有在市场制度的长期磨练和熏陶下,具有独立“经济人格”(具有财产、劳动和契约等权利,同时又能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经济人”)和公民意识的个人,才会为维护其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而组织起来。也正是因此,自愿、互助、服务、互利、自律则成为合作经济的灵魂。这对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农民和农业企业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只有依靠农民和农业企业的主动性,才能把合作组织办成、办好。所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确立起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而不是使其“边缘化”,是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然逻辑。这也是农民理性由传统“生存理性”转向现代“发展理性”的内在规定。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所指出的,“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29)
一句话,市场化进程中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给农民以自主性空间和“自治性”领域,并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这是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制度逻辑的基点。
收稿日期:2007-06-20
注释:
①D.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②20世纪中国在农村推行的合作经济制度,并非是本土社会自发内生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参阅笔者2002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政府·合作社组织·乡村社会》,和2004年度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西方合作经济学说与20世纪中国》)。
③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1~342页。
④诸如建国前的合作社沦为金融资本尾闾的“合借社”;建国后“政经合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等皆为“异化”的合作社。即或是现在合作社发展也不尽如人意,据农业部 2006年统计,全国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万多个,成员2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与67万个村相比,每4个村不足1个,所占比重极小。在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极高的许多欧美国家,合作社力量甚大,如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98%的农民都是合作社社员,每个农户平均参加3.6个合作社;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分别占市场份额的95%、78%、70%,在美国,4/5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80%,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数据来自于《中国合作经济》2007年第3期)。中外之间农业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建国前乡村合作运动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若撇开“政治”因素,从制度变迁的机理、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行政国家化”背景下政府通过自上而下路径对农村社会建设的“嵌入式”干预),合作运动所追求的绩效(体现和实现“国家意志”:整合乡村社会,挽救农业危机和发展农村经济,对分散小农的组织化和社会动员),以及运动最后结果(都是以合作社的“异化”和“异化”的合作社大量存在而告终)等“社会经济”领域去思考问题的话,二者有着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更多地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禀赋使然(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这也是笔者以此为切入点,将它们有所连接用“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经济”这一个时间段概念来做共同剖析和尝试诠释的“最大”缘由。也正如许多学者一致强调的,我们对某一事件分析评述应从全局出发,不能只重结果、忽视过程,更不能因为政治歧见而否定一切。
⑥此处的“主体权利”之内涵非指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或人的基本权利,而是指中世纪的一种与某一社会个体所处的地位相对称的身份权利或等级权利,或称之为潜在的个人权利,既包括中世纪的个人权利,又包括某个等级或集团的集体权利。
⑦参见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第647~664页。
⑧参见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63页。
⑨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当然,对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中间层,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民清以来“士绅—地主”构成的民间统治精英是国家社会的国家与民众间的较有效的中介。其实不然,中国的这种所谓“中介力量”,是不能与西方社会相提并论的,它只是弥补国家控制超大社会的空缺而已,其活动基本上局限在国家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对上层权力不及的有效补充,而不是反叛与挑战或制衡。中间层的相对缺乏与西方社会是有着明显差别。对此著名学者梁漱溟指出:“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之不同,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⑩参见张杰:《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11)参见J.H.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 253~259页。
(12)王家范:《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辨析》,《史林》1999年第4期。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很不完整的私有产权制度,土地虽然私人可以买卖,但国家可在其认为需要的时候,任意干预这种产权,强制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措施。因此,他强调说,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特征。
(13)参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48页。
(14)(17)参见张德粹:《我国政府与农业合作》,《中农月刊》1943年第4卷第2期。
(15)参见赖建诚:《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139页。
(16)参见:《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2期。
(18)(19)参见程启钧:《中国合作事业的前途》,《合作经济》1948年新1卷第5、6期合刊。
(20)(24)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177页、第39页。
(21)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38页。
(22)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23)参见沈立人:《合作制度和中国经济的出路》,《合作经济》1947年新1卷第3期。
(25)参见孙晓村、张锡昌:《民元来我国之农村经济》,转引自朱斯煌:《民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48版,第361页。
(26)J.P.Powelson:Centuries of Economic Endeavor:Parallel Paths in Japan and Europe,and Their Contrast with the Third World,Ann Arbor,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27)参见崔敬伯:《经济激流中之中间阶层》,《经济评论》1947年第1卷第11期。
(28)参见方显廷:《中国之合作运动》,《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第3卷第1期。
(29)参见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标签:农民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经济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二重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合作社论文; 法律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