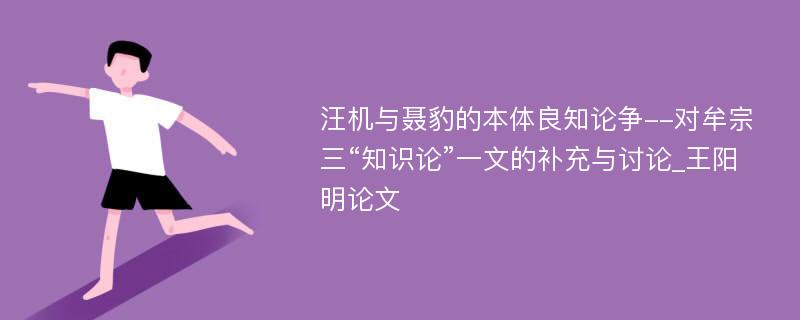
王畿与聂豹关于本体良知之辩——兼对牟宗三先生《致知议辩》一文的补充和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良知论文,一文论文,宗三论文,致知议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王畿与聂豹的“致知”之辩,涉及王学的良知是否为心的最高本体和能否起主宰作用的根本问题。两人在“先天心体”、“已发未发”、“寂感”、“诚”、“乾知”、“自然之觉”、“知爱知敬”等七个方面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次辩论,说明王阳明卒后仅十年左右,王学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也反映了朱学复兴的萌芽。
关键词 王畿 聂豹 王学 良知 致知 心体
WANG JI AND NIE BAO'S DISPUTE ON SINCERITY
AND HSING TI
Fang Zuyou
Abstract
The focus point of the dispute between Wang Ji and Niebaoon "intritive knowledge" involves the fundamcntal argument inWang's theory in terms of whcther sincerity is the highestand dominant implicit existence being. In eight issues thetwo scholars had heated debates,which indicates the apparentsplitting of the Wang's school 10 years after Wang Yang-ming's death and which marks the revival of Zhu-school.
Key words Wang Ji
Nie BaoWang's schoolsincerityutmost knowledge
hsing ti
王畿与聂豹的致知之辩,是王阳明卒后王门弟子的第一次大辩论。先有王畿的《致知议略》(以下简称《议略》),后有聂豹的《答王龙溪》,再有王畿的《致知议辩》(以下简称《议辩》),最后又有聂豹的《答王龙溪》(聂豹文集中二篇答文名称相同,为辨别起见,以下称《二答王龙溪》,简称《二答》)。牟宗三先生在《〈致知议辩〉疏解》〔1〕一文中,把二人的答难归纳为九辩。牟先生分析细腻, 有不少真知灼见。然牟先生未看到《二答》,故他的分疏尚有不足之处,由于九辩涉及王学不少重大问题,非短短一篇论文可以说清楚,本文仅就两人关于良知是否为心的最高本体〔2 〕和对意与身能否起主宰作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某些问题上试图对牟文予以补充和商榷。
对王学上述两点根本问题,王畿持肯定的态度,而聂豹予以否定,他们在下列八个方面进行辩难,兹分别叙述于下。
一、关于先天心体之辩
王畿在《议略》中说:“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3〕聂豹回答说:
先天之学,即养于未发之豫。豫则命由我立,道由我出,万物皆备于我,故曰:“先天而天勿违”。……乘天时行,人力不得而与,与则助,助则去天远矣,故曰“后天而奉天时”。邵子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先天言其体,后天言其用,盖以体用分先后,而非以美恶分也〔4〕。
聂豹在这里提出了先天之学的“天”是什么的问题,他引用邵雍“先天之学,心也”的话,认为先天的天就是心之体。如果仅仅这样说,与王畿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他是针对王畿上述话而发的,回避了王畿所说的“良知者,……先天之学也”中的“良知”二字,隐晦地表明“养于未发之豫”的先天的心体并不是良知。此外,关于“奉”(“后天的奉天时”)、“乘”(“乘天时行”)的所“养”的工夫,王畿与聂豹也没有矛盾,但如何奉、承以及所养的是什么?二人却意见不同。王畿对聂豹的责难回答说:
良知是天然之则。……“养于未发之豫”,先天之学是矣;“后天而奉天时”者,乘天时行,人力不得而与,曰“奉”,曰“乘”,正是养之之功,若外此而别求所养之豫,即是遗物而远于人情,非在尘出尘作用,与圣门复圣之旨,为有间矣。〔5〕
王畿的回答很含蓄,他的“外此而别有所养之豫”的“外此”,有两层含义:一,“后天奉天时”,先天不能外后天,否则,“遗物而远于人情”;二,良知是“天然之则”,外良知的先天天则而别求所养,则与“圣门复性之旨”有距离了。聂豹对王畿的回答十分不满,他再次回信责难,并对所奉的“先天”,即“圣门复性”的心性是什么,作了明确的说明:
“圣门复性之旨,当自有知者在。佛经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凋。’朱子叹曰:‘你看他是什么的见识,区区小儒,如何辟他下。’盖‘有物先天地’,言先有此物而后有天地也。‘无形本寂寥’,言其至虚至无也。‘能为万物主’,言万物统天一太极也。‘不逐四对调’,言其不垢不净,不生不死,真常得性也。”〔6〕
他在这里表达了他所追求的先天心体是什么?根据这一表达,“有物先天地”的“物”,近似良知而实非良知。王阳明对心体或良知是从无前后内外一体不二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的。他确也讲过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7〕,但他更多的是讲:“虽天地与我同体, 鬼神也与我同体”,“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良知),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了”〔8〕, “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中流行”〔9〕……等等。 他从没有如朱熹的“先有此理,便有此天地”〔10〕那样讲过:“先有此良知,便有此天地”。而聂豹则违反了王阳明的良知与万物同体的观点。“无形本寂寥”,王阳明确讲过:“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11〕,但他从未讲过良知是“至虚至无”的,他的良知是不着于有无虚实的,而聂豹所说的显然执着于虚和无。把“不逐四时凋”说成“不生不死”,这是把他所说的至虚至无的心体,从人的主体中抽象出来,成为一种客观的宇宙精神。然而王阳明讲的良知或心体,常常与主体联系在起,如说:“自己良知”〔12〕,“尔那一点良知”〔13〕,“我良知”〔14〕,“吾心”〔15〕,“汝心”〔16〕等等。主体的良知或心,是有生死的,聂豹抹去了王阳明良知的主体性一面,则其心体近似朱熹的“理”,不完全符合王阳明的原意了。总之,聂豹所求先天心体,并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他所说的“能为万物主”的“太极”,也不是良知,所以王畿隐约地批评他是外良知而别求所养之豫。
牟宗三先生分疏说:“双江不信眼前呈现者为良知,以为不足恃,必闭关归寂别求未发之寂体以主之。”〔17〕这一断语是正确的。然牟先生对王畿的回答又分疏说:“此种养既从‘奉’、从‘乘’而说,自是完全从心体着眼,在‘无’处立根,自亦必涵着顿悟也。如此用功,即是‘四无’。”〔18〕其实,从聂豹的再难来看,他的‘奉’,‘乘’之说,也是从心体着眼,在‘无’处立根的,他的“至虚至无”说,实比王畿的“无”有过之而不及。刘宗周曾说王畿“直把良知作佛性看”〔19〕,聂豹则“直把佛性作良知看”。“有物先天地”这四句话正出自南朝齐梁间被后人称作禅僧的双林善慧大士傅翕。〔20〕
二、关于未发已发之辩
王畿在《议略》中说: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若在良知之前别求未发,即是二乘沉空之学;良知之外别求已发,即是世儒依识之学。……受症虽若不同,其为未得良知之宗,则一而已〔21〕。未发已发,语出《中庸》:“喜怒衷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原意指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宋朝理学家把它作为重要的哲学概念进行讨论,“未发之中”已由人的情感,变而为表达人的心体,成为心性学的一部分。聂豹对王畿上述观点发难:
良知是未发之中,先生尝有是言。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一个心体,则用在其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若曰:“良知亦即是发而中节之和”,词涉迫促〔22〕。
聂豹只同意王畿的前半句话:“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但不同意后半句的良知“即是发而中节之和”。他引用师说,目的是把阳明的“成就自家一个心体”句与他的体认“寂体”说一致起来。他认为,只有执体才能应用,不体认心体而说“良知亦即发而中节之和”,就“词涉迫促”了。他责难王畿的“良知之前无未发,良知之外无已发”的观点,“似是混沌未剖之前语。”〔23〕
王聂两人未发已发之辩,在心体方面,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未发之前有否未发?王畿明确说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如果在良知之前别求未发,意即良知并非未发之中,即并非是心的最后,最高的本体,在良知之上还有一个本体在,他认为这不但属“沉空”之见,且违背师说了。但这一说法是符合聂豹对寂体的描述的,这寂体为“万物统天—太级”,太极即是最高的本体,但不是良知。王阳明说:“良知之虚,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24〕,如果在良知之前更求一个虚无的本体,即聂豹所说的“至虚至无”的寂体,那的确如王畿所指摘的,是二乘(声闻乘与缘觉乘,皆属小乘)的沉空之学。牟宗三先生指出:“夫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体,即是最后的,如何可再于良知之前求未发?然则说‘良知之前无未发’,不误也。”又说:“此不算数,又有未发之寂体,此方是真良知,此种分析对于阳明所说的良知,未有谛解也。”〔25〕牟先生这一分析指出了聂豹的要害问题,不过,聂豹在这里并未承认有一个“真良知”在。
二,未发是否即已发,已发是否即未发,还是两可分?这一问题,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说得很清楚,他说:“未发之中即良知也”,而“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他指出这就是“无前后内外浑然一体者也。”可见王畿的未发已发不可分的观点,是根据师说而发的,而聂豹指责王畿这一观点,恰恰说明自己已背离了师说,所谓“混沌未剖之前语”,首先说的正是王阳明。聂豹把未发已发分离,是为了在分离后求未发之中的寂体。
三、关于寂感之辩
王畿在《议略》中曾谈及他的即寂即感、寂非内感非外的观点。对此,聂豹表示强烈反对,他说:
寂,性之体也,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内”,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内乎?〔26〕
在寂感有否先后内外的辩论中,聂豹提出了“寂,性之体”的命题。然这一“寂体”是什么?是良知,还是良知之外的另一心体,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王畿抓住了这一要点,向聂豹指出:
良知是寂然之体,物是所感之用,意则其寂感所乘之机也。〔27〕明确表示,良知就是寂体。但不知怎么一回事,王畿这段话转到聂豹手中时,“用”与“意”这二字却对换了一下,变成:“良知是寂然之体,物是所感之意,用则其寂感所乘之机也。”〔28〕聂豹抓住了这一点,向王畿发难:“来云:‘良知是寂然之体’,是以良知为主脑,而以寂感为两股,故曰:‘用则寂感所乘之机也’,疑与经传之意大别。”〔29〕他接着引用程朱以寂感为心之体用的话后,诘问王畿:
今曰:“良知是寂然之体”,不知寂然之上又有一体也?邵子曰:“先天之学,心学也,阴阳消长之理,吾心寂感之机,妙哉,妙哉!”夫赞先天之妙,以其具阴阳,该寂感。今谓:“用为寂感所乘之机”,无乃近就已意之太过乎〔30〕?
聂豹的意思是应以心为主脑,寂为心之体,感为心之用。他在后面用邵雍的话来批评王畿“用为寂感所乘之机”,是对的,无奈王畿的原文并非如此。王畿的命题,说的是良知就是心的寂体,两者是同一的。聂豹则认为他把良知与寂体分而为二,变成良知是寂体之上的心体。他引用程朱或邵雍的话是说明应以心体为主脑,寂与感是心的体用关系,并用来责难王畿以良知为主脑,以寂感为两股(两股并非体用,两股的地位是并立的,体用则以体为主)。姑无论这是不是符合王畿原文原意,但他在批评王畿这一命题时说:“不知寂然之上又有一体也。”“又有一体”的“体”,指良知,暴露出他不同意良知在他的寂体之上。在他看来,最高的心体是寂体而不是良知。
聂豹在《答王龙溪》中,对王畿的“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的话,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为学者立法。王畿则在《议辩》中对这两句话作了解释,指出这“正是合本体之工夫,无时不感,无时不归于寂也。”聂豹乘机抓住“归于寂”这句话,说:“无时不感,无时不归于寂,正是合本体之功,则功在归寂,言下亦自分晓。”〔31〕牟宗三先生指出王畿“语涉疏阔”,而聂豹则“以为必把良知之寂感为一而无内外,分析而为有内外有先后,以闭关归寂,然后可为致良知之工夫”〔32〕。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聂豹正是利用王畿的“疏阔”,把寂感分而为有内外先后,从而得出“功在归寂”的判断。不过聂豹所说的寂感的主体(主脑),不是良知,而是他所说的寂体。
如王畿在《议略》中谈独知问题时说:“不睹不闻,良知之体。……致知格物之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日用伦物之感应而致其明察者此也。”这“此也”即不睹不闻的良知,聂豹反诘说:
致虚守寂,方是不睹不闻之学,归根复命之要。……其曰“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不知指何者为无形声而视之听之?非以日用伦物之内别有一个虚明不动之体以主宰之,而后明察之形声俱泯。是则寂以主乎感,静以御夫动,显微隐见通一无二是也〔33〕。
聂豹所说“归根复命”应归复于何处?他仅说归复于“虚明不动之体”,实即主乎感、御夫动的寂体,根本不提“不睹不闻是良知之体”。当王畿在《议辩》中提醒他良知“即是虚明不动之体”时,他在《二答》中仍强调这个“虚明不动之体”,即是不睹不闻,因此,“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始可以言归根复命之学,始可以言致知”,也就是说,只有戒惧于不睹不闻的虚明不动的寂体,才可以言致知。这样,他已把致良知落于工夫的第二层,落于归寂之后。由此可见,王畿指责指他“疑致知不足以尽圣学之蕴”〔34〕,确揭示了聂豹违背师说的要害问题。
四、关于诚之辩
聂豹在《答王龙溪》中提出了“诚”的问题,他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诚精而明,寂而疑于无也,而万象森然已具,无而未尝无也。
按:诚作为本体论的范畴,出自《中庸》。把诚与寂联系起来的是唐李翱。他说:“诚者,圣人之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35〕聂豹显然吸取李翱的思想,又把《中庸》的诚,《易》的寂感与佛教的有无联系起来来说明他的寂体。他在同一段引用了《易经》的“介如石焉”,又引用朱熹的注释说:“介非寂然不动之诚乎?”证明诚即他的寂体。按王畿在《议略》中讲的是良知寂感、有无,其主体是良知。而聂豹谈寂感、诚神、有无,只字不提其主体是什么,更不提良知二字。
王畿在回答中捍卫了王阳明的良知说:
周子云:“诚神几曰圣人”。良知者自然之觉,微而显,隐而见,所谓几也。良知之实体为诚,良知之妙用为神,几则通乎体用而寂感一贯〔36〕。
指出诚神即良知的体用。
正如聂豹把王畿的“良知为寂然之体”命题中的良知与寂析而为二那样,聂豹又把良知与诚析而为二,并以此来为自己辩护。他同意王畿的“良知之实体为诚”的命题,但却说:
致知之功,要于存诚以立其体,存存不已,则精而明,应而妙,自然之几也。精明属寂,故曰无。应妙属感,故曰有。……介石是良知的实体。前谓良知之实体为诚,主诚而后可以言介石。……介石之外,别求良知,能免驾床而叠屋乎〔37〕。
王畿的“良知之实体为诚”,意指诚为良知之实体,诚即良知。王阳明说过“诚是心之本体”〔38〕,又说良知是心之本体”〔39〕,王畿的命题是符合师说的。聂豹表面上同意王畿的命题,但他把良知与诚析而为二,意指诚是良知之上的实体,所以接着说:“致知之功,要于存诚以立其体”,即致良知之功,在于“存诚”以立“良知之体”。他说“诚精而明,寂而疑于无也”,所以其所说“存诚”,实即他一贯所主张的“归寂”说。“介石以外别求良知”,在他看来是多余的。就这样,他以诚,介石,即以寂体代替了良知。他后来说:“前既以诚为良知之实体,实体便是主物”〔40〕,他公然以诚即寂体为良知的主宰物了。
五、关于乾知之辩
王畿在《议略》中说: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混沌初开的第一竅,为万物之始。……中和位育皆从此出,统天之学。
聂豹不同意王畿的观点,从两方面发难,第一,不同意“乾知即良知”的解释。他引用朱熹的“知,犹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41〕为据,因此,乾知即乾主,并非良知。至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聂豹说:“知字原属下文”〔42〕,下文指《易·系辞》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知”字。对“乾以及知”,朱熹解释说,应从上面“乾知大始”处说来,“言乾当此大始,然亦有知觉之义。”〔43〕牟宗三先生解“乾以易知”的“知”字为:“此知应作主解”〔44〕,似不符合朱熹与聂豹原意。
第二,不同意王畿把良知作为“万物之始”的统天之学。他说:“《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是以‘统天’赞乾元,非赞乾也。”〔45〕
王畿对聂豹这两方面的责难,在《议辩》中亦予以回答,第一,他指出,“乾知大始”,讲的就是“知”字,“不须更训‘主’字,下文证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为‘易主’可乎?”第二,“乾知大始”,讲的就是“大始之知”,为“混沌初开之竅,万物所资以始。……此是统天之学,赞元即所以赞乾,非二义也。”
牟宗三先生对王、聂两人关于“乾知”之辩是否符合经义,作了详尽分疏。不过自宋开始出现了一股疑经思潮后,学者往往以己意释经。明中叶王学出现后,陆九渊所说的“六经注我”成了一代风气,甚至出现了粪土六经的现象。所以重要的是,通过王聂两人对“乾知”的不同解释,来进一步探讨他们是如何在为自己的哲学宗旨服务的。
王畿以良知释“乾知”,是为了说明良知是万物之始,也就是说,良知是世界最高和最后的本体,再没有比良知更高的本体了。而聂豹反对王畿的也是这一根本观点。“乾知”非良知,以统天赞乾元而非赞乾,这就是从经学上,即从根本上剥夺了王畿上述命题的充足理由,所以聂豹在《二答》中再次强调:
训“知”:为“主”,本文原注(指朱熹注),即以“易知”为“易主”,有何不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非乾为之主,而谁资之?故曰:“乾以君之”。若如尊见,何不曰:“大哉乾知,万物资始”,则以乾知为良知,又何所疑?!
他最后嘲笑地说:“必如公等只以一”知”字尽天地古今之变,又恐过于易简者也”。他这一嘲笑,不仅嘲笑王畿,而且在嘲笑王学的宗旨——良知。
六、关于自然之觉之辩
王畿在《议略》中说:“自然之觉良知也。觉是性体自然之觉,即是天命之性。”王阳明曾说:“心之虚明灵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46〕,这正是王畿的良知是“性体自然之觉”之所自。聂豹自然知道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这段话,他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但仍坚持自己的“归寂”宗旨,他这样回答王畿:
良知是:“性体自然之觉”是也。故欲致知,当先养性。……圣人体《易》之功,则归重于“洗心藏密”一语。“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后有“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由是观之,致知格物之功,当有所归〔47〕。
“洗心退藏于密”、“神明其德”,语出《易·系辞》。前者,朱熹注:“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聂豹借用此语来表达自己的宗旨:闭关静坐,使心不缘外境(洗心,无事),则可窥寂然的心体(退藏于密)的归寂说。如此,则可以“神以知来”。朱熹注:“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48〕聂豹引用朱熹此注,用来说明他的“感生于寂,和蕴于中”〔49〕的观点。
对聂豹所说的“当先养性”,王畿在《议辩》中反驳:“良知即是‘性体自然之觉’,又孰从而先之耶?”又说:
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灵也。“洗心退藏于密”,只是良知洁洁净净无一尘之累,不论有事无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肃然的,是谓“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退藏之后有神知之用也。
良知即是神知,神知即是神明,神知为用,神明为体,体用不二,何必洗心退藏,把体用分而为二,先归寂而后再求用呢?
牟宗三先生对“养性”问题分析得好,他说聂豹分“性体与良知为二层”,“因双江自然之觉为已发,属下层,须别有一物以主之故也。此别有一物,即是他所说的寂体。”〔50〕然牟先生认为王畿直驳聂豹的“退藏于密”是“无益”的,则尚可商榷。王畿所说的“有事”、“无事”,指朱熹注释中的:“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指的是心的寂感、体用。但朱熹把两者析而为二。王畿则认为,并不是无事寂然,有事感应,而是不论有事无事,良知是即寂即感、即体即用,其本体洁净湛然是贯彻于体用之中的。换句话说,即见成良知便是本体良知。聂豹则步朱熹后尘:神知是用,神明是体,体用为二。依王畿:“神知即是神明”,即用即体、即感即寂,并不是先归寂(洗心退藏于密),而后才有神知感应之用。因此,聂豹的“洗心退藏于密”,并不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的“以复神明之德与神智之用”〔51〕,聂豹自己亦申明:“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并无提及“神知之用”。聂豹这一提法,确相当于王阳明早期的“默坐澄心,以收敛为主”的主张,是为他的“故欲致知,当先养性”,即致良知以前先需归寂的根本宗旨服务的。故王畿问他责难:“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复将何所归乎?”要归的应是良知。
对王畿的责难,聂豹在《二答》中仍为自己的“洗心藏密”论辩护:“神智之用,随感而应,本由洗心藏密而后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佛学来为自己的理论找根据:“佛书谓:戒生定、定生慧。今谓神知之用不在洗心藏密之后,只因尊兄以无内外先后一言横亘其中,随处掀翻说过。”说明他的静坐归寂说与佛教的定慧学说在思想上是相通的。
七、关于知爱知敬之辩
这一问题,涉及良知学说的根本问题。王畿在《议略》中说:“孔门致知之学所谓不学不虑之良知也。”众所周知,“不学不虑”与良知良能,出自《孟子》,也是王学良知说的历史渊源。王畿此言原无问题。可是聂豹不以为然:“先师良知之教,本于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学不虑,知爱知敬,盖言其中有物以主之,爱敬则主之所发也。今不从事于所主,以充满乎本体之量,而欲坐享不学不虑之成,难矣。”他这里所说的“有物以主之”和“主之所发”,考《孟子》原文,并未言及在“知爱知敬”的良知良能上还有一物作为主。从王学来讲,王阳明曾说:“知是理之灵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全是他本体。”〔52〕“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53〕知爱知敬就是良知,并未提及其中尚“有一物以主之”。王阳明生前即同聂豹说过:“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54〕可聂豹却认为在知爱知敬的良知外,还有一个“物”以为爱敬之主。据聂豹学生宋仪望说:“先生自丁亥(嘉靖六年,1572年)以来,其论致知工夫,则以孩提知爱知敬为良知本来面目,反而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致书阳明、南野二公,盖极言之。”对他早期“知爱知敬”说,王阳明并不同意,向他点出“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但当时聂豹尚称“良知”。至“戊戌(嘉靖十七年)以后,先生有悟于本体虚寂之旨。……自平阳归(嘉靖二十二年),与同志论学,一以涵养本体虚寂为归。”〔55〕已以“寂体”代替良知了。
看来王畿是知道他思想的这一转变的,故在回答聂豹时,特别提出良知:“不学不虑,乃天所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学虑,故爱亲敬兄。”“自然之良即是爱亲之主,即是寂,即是虚。”他责问聂豹:“若更于其中有物以主之,欲从事于所主,以充满其本然之量,而不学不虑为坐享其成,不几于测度渊微之过乎?”他抓住了“主”的问题说:
公平时笃信白沙“静中养出端倪”与“把柄在手”之说,若舍了自然之良,别有所谓端倪、把柄,非愚之所知也〔56〕。
最后,他说如果自然之良还不能为学问之究竟,还须另求一物以为主,这岂非怀疑良知,岂非矫枉过正!
牟宗三先生在自然之良这一问题的分疏中,认为聂豹把良知分析为已发与未发,“然双江把这当机的表现(知爱知敬)看成是已发,尚不算真良知,逐抽象地思那无任何表现的良知为寂体〔57〕,我觉得尚可商榷,因为聂豹认良知为已发,因而在已发之上的寂体并非良知,或真良知,请看聂豹本人对王畿上述责难的回答:
“把柄”、“端倪”,白沙亦指实体之呈露者言之。必实体呈露而后可以言自然之良,而后有不学不虑之成。兹不求自然之良于实体之充,则所谓良者,卒成一个野狐精,其与自然之觉远矣〔58〕。
他明确指出,在良知之上尚有一个实体以为主,这实体便是“端倪”、“把柄”。有此实体,才可言良知,否则,便是野狐精。野狐精一语出自佛教禅宗,指旁门外道的见解。聂豹显然已把良知置于实体之下,指责王畿是野狐精的异端了。
以上七点分歧,集中在良知是否为心的最高本体和良知能否对意和身起主宰作用问题上,其实质是否定还是肯定王学的宗旨。在王阳明卒后仅十年左右,王学就开始出现了分化。聂豹虽尚未越出心学的籓篱,然他一方面借助于朱学,另一方面又借助于佛学来为自己学说作依据。这既反映了明中叶以来朱学复兴的萌芽,又说明了当时矛盾、复杂而又色彩缤纷的思潮。
收稿日期:1996年9月1日
注释:
〔1〕〔17〕〔18〕〔25〕〔32〕〔44〕〔50〕〔51〕〔57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四章, 第336、342、338、348、380、383、373页。
〔2〕本体即最高、最终的,原无上下之分。 由于聂豹讲良知之上的实体,故顺其思路,暂作如此分析。
〔3〕〔21〕〔27〕〔36〕〔41〕《王龙奚先生全集》卷六, 光绪八年海昌刻本。
〔4〕〔26〕〔33〕〔34〕〔42〕〔45〕〔47 〕《明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九《答王龙溪》,清云丘书院藏本。凡字为楷体者,《王龙奚先生全集》所收《致知议略》中无。
〔5〕〔6〕〔23〕〔28〕〔29〕〔30〕〔31〕〔37〕〔40〕〔49〕〔56〕〔58〕同上书卷九《答王龙溪》。按此《答王龙溪》与注〔4 〕不同,为辨别起见,本文称《二答王龙溪》,简称《二答》。凡字为楷体者,王畿文集所收《致知议辩》原文亦无。
〔7〕〔8〕〔9〕〔11〕〔13〕〔14〕〔16〕〔24 〕《传习录》下。
〔10〕《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原文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中华书局1986年版)。然钱穆《朱子新学案》(上)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先有此理,便有此天地。”疑所引版本不同。
〔12〕〔39〕〔46〕〔53〕〔54〕《传习录》中。
〔15〕〔38〕〔52〕《传习录》上。
〔19〕《明儒学案·师说·王龙溪畿》。
〔20〕《五灯会元》卷二《双林善慧大士》。
〔22〕聂豹《二答王龙溪》。凡字为楷体者,王畿文集中无。牟宗三先生对为何“语涉迫促”作了详尽的分疏。聂豹引用阳明成就自家心体,然后才有发而中节之和句,用来批评王畿忽略心体而说中节之和,故“词涉迫促”。牟先生未看到《二答》,所以有此分疏。
〔35〕李翱《复性书》上。
〔41〕〔48〕朱熹《周易本义·系辞上传》
〔43〕《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易十·上系上》
〔55〕宋仪望《双江聂公行状》、《明文海》卷四四四《墓文》,第4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