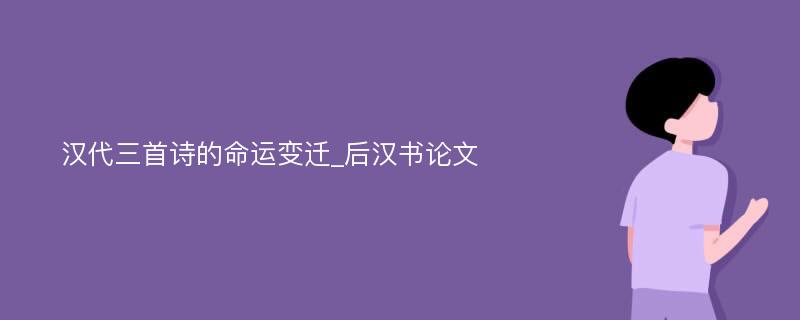
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三家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82(2010)01-0040-05
一种学说只有与时推移,才能行而不衰。东汉是一个神学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宗教化、儒学神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导致了不同的发展曲线。
一、《鲁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在西汉最为强大的是《鲁诗》学派,其间因明经术而身蹑高位如韦贤父子者,不在少数。到东汉,这一派虽仍在继续传播《诗》学,但却没有西汉那么幸运了,而且几乎成了四家《诗》中最不景气的一家。在这个队伍中,尽管没有出过像先前韦贤那样显赫的高官,但从西汉末以来,在这个学派中却出现了一批沉心经典、淡漠权力、富有节操的人,如:陈宣,博学明《鲁诗》,遭王莽篡位,隐处不仕;李昺,习《鲁诗》、《京氏易》,公车征,不行;李业,习《鲁诗》,王莽居位,隐藏山谷,后因不失节于伪朝,饮毒而死;高嘉、高诩父子,世习《鲁诗》,王莽时父子称盲,逃去不仕;魏应,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鲁恭、鲁丕兄弟,习《鲁诗》,闭门讲诵,绝人间事。
这种现象的出现,虽有可能与《鲁诗》鼻祖申公不阿于世的为人传统有关,如申公当日就曾忤楚王刘戊,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鲁诗》的现实批判精神。《鲁诗》讲经有两大主题:一是“政衰始于衽席”,一是“贤人遭贬”。这两大主题在与现实产生联系时,其必然的手段都是借古讽今,而其基本的态度都是不满于现实。在西汉初经典复原时期,《鲁诗》借着其最先出世、并占据鲁地儒学独盛的优势,很快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并在官方的支持下迅速传播开来。又由于当时汉王朝处于上升时期,有一种容纳不同政见的恢宏气度与光复旧艺的信心,使得明于古礼的《鲁诗》派学者,顺利地走向了权力中心,成为西汉《诗》学流派中势力最大的一家。但到西汉后期,政局的变迁,使这一派学者在与统治者的合作中,出现了心理上的障碍,导致了背离政治走向纯经学的人生发展道路。
在学术的发展上,此一学派也不太理想。《鲁诗》派从申公始,就缺少理论创新,除了在经文的本事探求与文字训诂上有所成就外,在对“经”义的阐发上只是浅层次的比附,其所关注的两大主题,也只是在情感的层面上徘徊,并没有在义理的层面上作深入的开掘,因而当章句之学兴起、“诗”的研究开始转向“经”的研究、“经典研究”转向“经学研究”的时候,此一派就显得后劲不足了。除了在西汉末期出现了韦氏、许氏两种章句著作外,整个东汉近二百年间不再见有新的章句产生。在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及清儒三家《诗》辑佚的著作中,曾汇集了有可能属于东汉《鲁诗》派的诗学观点与解经文字,但这些文字,除了在文献研究中略存价值外,几乎看不到其理论上的建树。以下就拿最集中的一组蔡邕《独断》所陈《周颂》31篇看其解经文字:
《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
《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将》一章十句,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
《时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执竞》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工》一章十句,诸侯助祭,遣之于庙之所歌也。
《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谷于上帝之所歌也。
《振鹭》一章八句,二王之后来助祭之所歌也。
《丰年》一章七句,烝尝秋冬之所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乐,合诸乐而奏之所歌也。
《潜》一章六句,季冬荐鱼、春献鲔之所歌也。
《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
《载见》一章十四句,诸侯始见于武王庙之所歌也。
《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来见祖庙之所歌也。
《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乐所歌也。
《闵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之所歌也。
《访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谋政于庙之所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群臣进戒嗣王之所歌也。
《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
《载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耕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报社稷之所歌也。
《丝衣》一章九句,绎宾尸之所歌也。
《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所歌也。
《桓》一章九句,师祭讲武类禡之所歌也。
《赉》一章六句,大封于庙,赐有德之所歌也。
《般》一章七句,巡守祀四岳河海之所歌也。
因熹平石经《鲁诗》出自蔡邕之手,故一般认为蔡邕属《鲁诗》一派。但《后汉书·赵晔传》言:蔡邕至会稽,读赵晔所著《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为《韩诗》派,蔡邕叹服其所著《诗细》,并亲传其学,由此可知,蔡邕并不死守《鲁诗》家法。蔡邕所引《周颂》诗旨可注意者有二:第一、内容与《毛诗》相同,甚至连诗篇的排列次序都与《毛诗》无异,特别是与《大武》乐有关的几篇(《武》、《酌》、《桓》、《赉》、《般》),《毛诗》的排序有明显的错误,而这里《鲁诗》则将错就错。朱彝尊曾言:“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今《独断》所载《周颂》三十一章,其序与《毛诗》虽繁简微有不同,而其义则一。意者《鲁诗》、《毛诗》,《风》之序有别,而《颂》则同耶?”[1](P736)其实这个“同”字正是破绽之所在。第二、所述仅诗篇的原始功用,对诗义没有任何发挥。这里披露了一个信息:《鲁诗》派因缺乏创造力,到东汉末,在《毛诗》的冲击下,其特色已开始消退。大儒如蔡邕亦不能坚守其学,而有了改传毛、韩之嫌,故而其后魏晋间虽仍有传者,但终气力不竟,不过江东而亡。
二、《齐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与《鲁诗》派相比,《齐诗》派因与谶纬之学同趋,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并努力发展其章句,故而一度势力很大。就以著述来说,《鲁诗》在东汉一朝没有著述,号称“五经复兴鲁叔陵”的《鲁诗》学者鲁丕曾称:“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2](P884)这样自然是述而不作了。而《齐诗》家则不然。西汉时曾做过成帝《诗》学老师的伏理,即著有《齐诗伏氏章句》。到东汉,其子伏黯“传理家学,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勲,以授嗣子恭。”[3](P20)伏恭以为父亲所传的章句文字太繁多了,于是“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4](P2571)省减之后的章句竟还有二十万言之多,其初内容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位《齐诗》学者景鸾,撰有《诗解文句》[5],《后汉书·儒林传》称:“景鸾字汉伯……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凡著述五十万言。”可以看出,此一派学者很少拘束,有旺盛的著述热情,故动辄数十万言。
此外,荀爽著有《诗传》。关于荀爽的派系归属,有不同看法。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曰:“《太平览御》五百八十六引颜延之《庭诰》曰:‘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似即《诗传》中语。本传不言爽治谁家《诗》,证以《汉纪》‘希得立于学官’之语,则其为毛氏诗审矣。陆元朗云: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毛公传荀氏学。慈明为荀卿十二世孙,传《毛诗》,即所以传其家学也。”[6](P2316)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叙》则说:“荀悦叔父爽师事陈寔,寔子纪传《齐诗》,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后汉书》言荀爽尝著《诗传》,爽之《诗》学太邱所授,其为齐学明矣。”又于叙录曰:“陆德明《叙录》言:寔子纪传《齐诗》。则太邱之受业太学,其所习当为《齐诗》。荀爽师事陈寔,尝著《诗传》,《后汉书》载爽对策语:有闻之师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即本翼氏《齐诗》之义。是爽治《齐诗》之学无疑。”[7](P1280,1282)陈氏之说较姚氏为优。
陈乔枞谓“《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安危之故。”此说甚得《齐诗》精要。东汉《齐诗》的著作已全部散佚,从《齐诗》派学者遗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齐诗》在理论上是有所发展的。他们的发展趋向主要有二:第一是对于基本诗义的把握,并由此而对其中的人伦道德意义进行开掘,以求在现实中体现其存在价值,起到导引人心的作用。如《齐诗》名家伏湛,光武时因其为“名儒旧臣”,甚受器重,一度代邓禹为大司徒。彭宠造反,光武帝要亲征。伏湛上疏谏曰:
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8](P894~895)
这里所引为《大雅·皇矣》文,重在言文王之德,不轻事征伐,终为天命所归。意在谏光武帝应以周文王为楷模,对征伐之事要慎重。再如郎顗上书言事云:
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浊。[9](P1054)
“《周南》之德,《关雎》政本”,主要是从“修礼遵约”的角度说的,目的是要匡正“时俗奢佚,浅恩薄义”的社会风气。而且认为匡正时俗必须从根本上开始,这在上不在下。只要为政者“修礼遵约”,就可以“风行草从”。
从伏湛、郎顗的称引《诗经》中,基本上可以看出《齐诗》派在东汉的发展态势,仍然坚持着对诗义的把握与通经致用方向,不媚于世,并有一种从经典的基本意义出发,规范帝王行为的勇气。这可能与《齐诗》派学者对天命的认定有关。在他们心目中,天命远远大于帝王的权威。因而他们的第二个发展趋向就是完善《齐诗》推算国运的功能。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郎顗。《郎顗传》称顗“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看来他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人。西汉《齐诗》推休咎,有所谓“四始”、“五际”之说,郎顗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诗》学概念,即“三基”说。其上顺帝条便宜七事言:
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潜龙养德,幽隐屈戹,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竞,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9](P1065)
“诗三基”不见于前汉记载,当出自东汉《齐诗》学。李贤注曰:“‘基’当作‘期’,谓以三期之法推之也。《诗泛历枢》曰:‘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故王命一节为之十岁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钱大昕曰:“案‘诗三基’者,盖《诗泛历枢》之别名,犹《稽览图》称《中孚传》也。其法盖以三百六十岁为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别为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竞,来年入季’也。”由此看来,“三基”与“四始”、“五际”同类,也是一种推算国运的方法。“四始”、“五际”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说,“三基”则据阴阳气周而复始为论。各家在论“三基”中,都没有说清楚是哪“三基”。参李贤注引《诗泛历枢》,疑所谓“三基”者,三百六十岁为一周,此为一基;一周中分十二辰,一辰各三十年,此为二基;一辰分孟仲季三节,王命一节为十岁,此为三基。阴阳变化之数就藏在这“三基”的周而复始之中。
《齐诗》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与阴阳术数之学联系过密,在汉代神学兴盛之际,这一派尚可乘风破浪,显其身手。随着汉王朝统治的衰亡,神学思潮的消退,《齐诗》很快便退出历史舞台,故在三家中最先失传。
三、《韩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在东汉,《诗》学中势力最大的一家是《韩诗》派。唐晏曾言:“大抵《鲁诗》行于西汉,而《韩诗》行于东汉,二家互为盛衰。故《韩诗内传》至六朝尚存,亦以习之者多也。”[10](P229)《鲁诗》过于本份,自然易于僵化;《齐诗》过于玄虚,自然难以承传;而《韩诗》所具有的晋学、鲁学与齐学的混合性格,以及其对《诗》作为文学的鲜活性与作为经学的经典性的保持,使其具有了多重生存能力,因而不仅在东汉神学思潮中能得以盛行,即使在《毛诗》理性说诗的冲击下,也未即刻倒下。传授之盛,逾于其它各家。在《后汉书》中,时可见到“薛汉……世习《韩诗》……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郅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召驯……少习《韩诗》……侍讲肃宗……入授诸王”、“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馀人”、“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唐檀……习《京氏易》《韩诗》……教授常百馀人”之类的记载。在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于东汉三国之世,列《鲁诗》17人,《齐诗》7人,而于《韩诗》,则列有41人之多。此一派的著述似亦较齐、鲁为多。今知者有:薛汉《韩诗章句》,杜抚删定《韩诗章句》与《诗题约义通》,赵晔《诗细》、《韩诗谱》二卷、《诗神渊》一卷,张匡亦为《韩诗》作章句。《汉车骑将军冯绲碑》称冯绲治“《韩诗》仓氏”,“仓氏”一派文献失载,但其作为《韩诗》的一个支派,在章句之学盛行的东汉能得以传播,亦宜有自己的章句。从这里也披露了《韩诗》在东汉,又不少派别出现。
东汉《韩诗》一派的著述,与齐、鲁二家一样,今已无存,只从前人的引述中可见得只言片语。薛氏《韩诗章句》是当时影响最大、至今残存最多的一家。此章句非一人之力所为,前汉有薛夫子《韩诗章句》,其后其子薛汉又对《韩诗章句》作了较大辐度的修改。当时各家章句都比较烦琐,即如《汉志》所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薛汉父子所传授的章句,估计也不例外,故薛汉的高足杜抚为了使《韩诗》之学便于传播,对其师的章句作了认真删定,尊之曰《薛君韩诗章句》。马国翰辑有《薛君韩诗章句》,此外黄奭辑《韩诗内传》、陈乔枞辑《韩诗遗说考》,亦将薛君章句一并收入[11]。据各家所辑,《薛君韩诗章句》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有二,一是继续探讨诗之原义,在诗本事与文字诠释上,尽可能的结合文本,使其解释合理化,如关于《郑风·溱洧》,《毛诗序》曰:“《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引《鲁诗》说:“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吁之乐,勺药之和。”又引《齐诗》曰:“郑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12](P371,367)此三家所言,显然背离了诗篇产生的背景。而《后汉书·袁绍传》注曰:“《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这从郑国民俗出发,对诗进行理解,显然要比三家合理。故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说:“按《韩传》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兰,祓除水滨,与所悦者俱往,而无他词。其曰‘所悦者’,谓士与士,女与女,各有平日所悦之人。即‘伊其相谑’,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悦者,与之相谑耳。世无道路相逢,士女杂沓互相戏谑淫奔之理。乃《毛传》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诸语,无论诗中绝无兵革流离之意,即‘秉兰’‘赠药’,安必为目成期约之物?皆非诗中所有之义也。但暮春水涣,男女群相祓禊,袵交趾错,风俗之弊,自在言外。诗人但直叙其事,而含刺已在。《韩诗》之说,深得风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语。”[13](P551)他如解《君子陶陶》曰:“陶,畅也。”解《葛屦》“纤纤女手”曰:“纤纤,女手之貌。”解《园有桃》“我歌且谣”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解《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扼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所以冒突先启敌家之行伍也。”这都是就诗之文本立说的。
薛君《韩诗章句》第二个价值取向是,阐发诗义,寻绎其与现实政治与人伦道德间的联系。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朱辅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朱辅所引为《周颂·天作》篇诗句,其所说的“传”,当是指韩婴的传,所言甚为简略。所谓“岐道虽僻,而人不远”,意思是通向岐下周国的道路虽然险阻,而人心归向,不以为难[12](P1007)。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韩传”中对于“有夷之行”的理解,乃是指人心理上的感觉,因为人心向往,所以就感到道路平坦通畅,故曰“而人不远”。薛氏的章句则对原初的韩婴传作了发挥,李贤注引薛君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归矣。’‘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不仅对诗之文字作了详释,而且还将“有夷之行”与“仁义之道”联系起来,认为这句经文是有象征意义的,表面上是行走的道路,实际上指的是“仁义之道”,这样于经义中便注入了人伦道德意义,将诗学的诠释完全转向了经学的诠释。再如《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对策曰:“《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迭。’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李固引为《周颂·时迈》篇语,释“迭”为“应”,是《韩诗》义,《毛传》则释为“惧”。“动之于内而应于外”,当是《韩诗》传统的解释,指的是王家的声威,但所言何王,也未详说。《鲁诗》言是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亦未言为何王。《毛诗》以为是指武王,《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云云,是以为武王事。《国语》言为周公作,而李贤注引薛君传则曰:“薄,辞也;振,奋也;莫,无也;震,动也。迭,应也。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则天下无不动而应其政教。”以为此为成王事。是武王还是成王,其意义完全不同。武王能威震天下,在于其开国之威;而成王是守成之君,其能够震动天下,则在于其能“奋舒文武之道”,在于“政教”。在东汉守成之世,更重要的是继承先祖伟业,是以文安邦,即所谓“政教”。因此这个解释,无疑是对经典的“现代诠释”,其意义指向显然在于政治上的长治久安。
四、结论
总之,《韩诗》在东汉的发展势头要好于齐、鲁二家,但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尽管三家在东汉,就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有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韩诗》虽然因其“混合性格”与多重生存能力的发挥,获得了比齐、鲁两家较好的发展,但随着神学思潮的消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也终难逃衰亡的命运。
收稿日期:2009-10-28
注释:
① 景氏书.朱氏《经义考》、侯氏《补后汉书艺文志》皆题作“齐诗解”,姚氏《后汉艺文志》曰:“按:‘文句’即章句之异名,《隋志》礼家有皇侃《丧服文句义疏》十卷,此其证也。殆汇众家诗解而为之章句欤!《侯志》据《经义考》题作《齐诗解》,以‘文句’二字属下读,今考本传云‘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华阳国志》云:‘撰《礼略》、《河洛交集》’,则《河洛交集》别为一书。此书名《诗解文句》审矣。”今从姚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