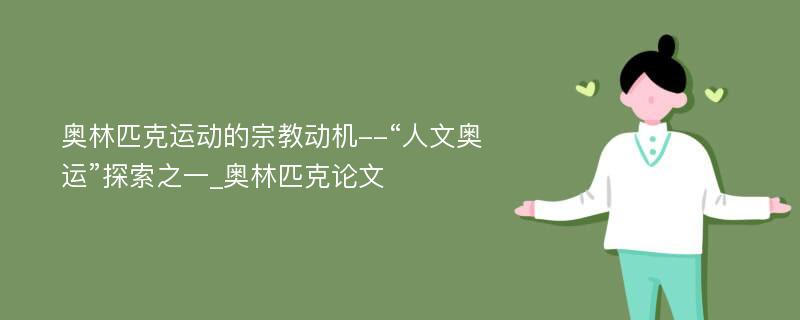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动因——“人文奥运”探索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林匹克论文,动因论文,宗教论文,人文奥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点燃圣火,是奥林匹克运动开赛前的第一项活动。虽然这项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仪式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以花样翻新的形式在每次比赛中重现,但是,由于时间的久远、资料的匮乏、生活方式的日益改变,圣火背后的宗教精神已被世俗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渐渐淡忘了。于是,在今人的心目中,奥林匹克运动有政治背景,有经济收益,有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唯独没有了宗教神学的内容。然而,作为一项源远流长的文化创举,奥林匹克运动是否仅仅意味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形而下动机,而没有更为深邃的形而上诉求呢?进而言之,这种诉求为何只在古希腊出现并在中断之后又得以复兴呢?这便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1894年在法国人顾拜旦倡导下所兴起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再生与延续。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先是一个宗教活动,其次才是一个体育活动。或者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儿,是在宗教精神支配下的体育活动。
早在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举办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如今的奥运会不同,古代奥运会原本是一种泛希腊的宗教庆典,它是以各种方式来祭祀神灵的活动,体育竞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项目涉及赛跑、拳击、摔跤、格技、武装赛跑、战车赛跑等。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竞技活动不只奥运会一种,与之并列的还有皮西安、伊斯玛斯大林和尼米亚三大祭神竞技会。另外,还有专为妇女组织的赫拉竞技会。在这些竞赛中,人们通过肉体的拼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在英语中,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词主要有五个:(1)用于地名的Olympia(奥林匹亚),指希腊南部大平原,该地区每四年举办一次竞技比赛,祭祀宙斯神;(2)用于时间的Olympiad(奥林匹得),指两次运动会之间的间隔,希腊人用以纪元和纪年;(3)用于人群名的Olympian(奥林匹安),指充当选手的奥林匹安人;(4)用于会议的Olympic(奥林匹克),指在奥林匹亚山附近召开的运动会;(5)用于山名的Olympus(奥林帕斯),指古希腊诸神的居所。由此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最初与希腊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相传,远古时候,英雄佩罗珀斯向皮萨国王俄诺马俄斯的女儿求婚,俄诺马俄斯要求,凡向他女儿求婚者,必须同他赛车,胜者方可得到她的女儿,败者则必须处死。在此之前,已有无数求婚者被俄诺马俄斯杀死,佩罗珀斯用海神波塞冬赠给他的飞马牵引金车,再施巧计取得了赛车的胜利,俄诺马俄斯则被摔死……等到英雄佩罗珀斯死后,他被葬在阿耳甫斯河滨的奥林匹亚,在那里被当作神受到人们的崇拜,而在他的葬礼上,为了纪念他在与俄诺马俄斯神判中的胜利,人们为他举行了竞技会。这是奥林匹克竞技的最早雏形。后来,由赫拉克勒斯将这一竞技会恢复起来,但把它献给宙斯神。经过一度中断之后,公元前776年,奥林匹克竞技会重新举行。以后每四年进行一次,这一届竞技会被当作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这一年也成为按奥林匹克竞技会计算的希腊纪元的开始”①。
除了神话传说之外,考古发掘的成果也证实了古代奥运会的宗教性质。在当时用于竞赛的奥林匹亚运动场上大大小小足足设有六十多座祭坛,较典型的就有六座,它们依次是:祭祀宙斯和海神波塞冬的第一祭坛,祭祀天后赫拉与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第二祭坛,祭祀太阳神阿波罗与猎神阿尔忒弥斯的第三祭坛,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命运女神摩伊拉的第四祭坛,祭祀森林女神狄安娜和阿尔菲斯河神的第五祭坛,以及祭祀木星萨顿与星河仙女的第六祭坛。因此在盛会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宗教仪式。其中以主神宙斯的祭祀最为隆重,它通常被安排在运动会的第一天,且以数量可观的百头公牛作为牺牲以献祭神坛。然后,隆重的奥运会便在熊熊的“圣火”中开幕②。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本文开篇时所提到的“圣火”问题。从历史上看,点燃圣火既是奥林匹克的宗教仪式,也是其最早的竞赛项目。据说,最初的“圣火”仪式是这样的:手持火把的运动员从同一起跑线出发,争先恐后地跑到宙斯的祭坛前,其中最先到达者以点燃圣火作为其获胜的标志。在这里,火炬来自人,圣火来自神,于是,这个“点燃”的过程也便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我们知道,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不仅有着无限的智慧,而且有着无穷的力量,神可以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而不占用任何时间,因为神的感性能力是无限的。与之不同的是,人的肉体能力则是有限的,人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必须占用一定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占用时间最少的人也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最接近神的人。惟其如此,他才有权点燃圣火;惟其如此,他才有权接受荣誉。这,也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含义!
与今天的奥林匹克竞赛不同,古代的奥运会为优胜者颁发的不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金牌,而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花冠;颁奖者也不是官员,而是神职人员。作为神的化身,奥运会的主教祭祀会把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郑重其事地给优胜者戴在头上。这顶花冠是由一名纯希腊血统且父母双亲健在、并在道德上无任何污点的英俊少年,使用黄金制作的镰刀,在宙斯神殿后的“神圣橄榄林”(平时严禁杀生和伐木的神域)中割下并亲手制作的。与此同时,诗人会为其朗诵赞美的诗篇;音乐家会为其弹奏妙美的音乐;雄辩家会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对其进行赞美和歌颂;雕塑家则为那些在运动会中连续三次夺冠的运动员塑像留念③。
从世俗的角度看,一个打破百米短跑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只不过比我们这些常人快那么几秒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力克群雄的拳击手,甚至会被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人。可是,在具有奥林匹克传统的西方人眼里,他却代表了人类的肉体能力在这一方面所能达到的极限,因而是伟大的,神圣的,非同寻常的。所以,尽管当时的优胜者获得的不是什么价值昂贵的金牌,而只是一个用野橄榄树的枝叶所编成的桂冠,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在古希腊时期,优胜者是神的宠儿,他已达成他的人生目标”④。
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是可以通过一项运动来加以缩短的,这项运动便叫做奥林匹克。于是,凡是能够考验人的感性能力的各个方面,无论危险多大和代价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不仅可以进行危险的赛车、残忍的拳击,乃至容易使身体变得畸形的举重比赛,而且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高山滑雪和几近迷狂的足球比赛。很多人认为,古希腊人之所以举办奥运会,只是为了通过运动而达到健身的目的。这种简单而幼稚的理解无法解释那些使比赛变得危险和残忍的实事:“战车赛跑是在古代奥运会中首先出现的也是主要的使用马参与比赛的项目……这种比赛非常危险,因为大多数战车的建造都不是十分坚固的——通常就是用木头造的,而且总是有很多新手加入进来,这也就增加了比赛的危险性”⑤。“在古代奥运会中最残忍的比赛无疑是格技比赛。虽然现代人都认为古代的奥林匹克项目的本质是平和的,通常获得格技比赛胜利的是具有高素质的运动员,但还是无法掩饰这项运动的残忍。比赛由拳击和摔跤组成,基本上没有严格规则限制,惟一禁止的是挖眼睛或者打眼部的行为。它的形式和拳击、摔跤相同,既不设置分级也不设置回合,参加这样的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说,有时候就像一场灾难”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这种危险而残忍的比赛都已经大大超出了健身的目的,但西方人却有增无减、乐此不疲地进行下去。说到底,奥林匹克已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赛事,而且是一种宗教,一种文化,一种对于人的感性生命力的开发与探究。惟其如此,那些伤痕累累,甚至身体畸形的胜者才显得那样崇高、那样伟大、那样值得模仿,那样受人尊敬。惟其如此,西方意义上的体育活动在超出了锻炼身体的现实需要之后,必然会发展为一种对感性生命的讴歌和对肉体能力的崇拜。进而,奥林匹克运动不仅超出了锻炼身体的世俗目的,而且超出了为国争光的经验范围,它超越了个体,也超越了国家,从而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形而上追求了。
毫无疑问,人的有限性使其永远也达不到神的境界。但人却并不因此而放弃努力,他要通过极限能力的不断扩展而一步一步地与神接近,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中所包含的宗教内涵,也正是人们在运动会上希望不断打破记录的意义所在。尽管这一宗教内涵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种种政治的考量和商业的动机所遮蔽了,但是,我们在1896年现代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圣歌》(Olympic Hymn)中仍可以体会到:“那古代不朽的神灵/代表着庄严伟大的造物者/随着你降临/你的光芒照耀着大地和晴空/也鼓舞着运动会中在竞技场上力争上游的斗士/戴着你所赠永远常绿的枝叶/斗士们的身体更强壮并永远被人尊敬/在深谷、高山、海洋都充满了你的光彩/白色与粉红色的庙堂满壁生辉/你的子民全部集合在你的神庙前/向你膜拜/向你膜拜。”
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不仅构成了古希腊宗教的主题,而且构成了几乎所有宗教的主题。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宗教没有孕育出奥林匹克运动,而唯独希腊宗教导致了这一传统?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尽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也以克服人的有限性而追求神的无限性为指归,但其片面、非理性地追求灵魂而排斥肉体的禁欲主义倾向,使得它们无法从感性的维度上来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从而也就不可能孕育出奥林匹克精神。
与近乎乐观的希腊宗教不同,佛教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宗教。释迦牟尼之所以创立佛教,就是有感于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而生、老、病、死则恰恰是人之有限性的体现。由于佛教徒“觉悟”到人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反而会遭到这些有限性的折磨,产生无尽的欲望,并带来无穷的烦恼,于是便主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弃感性的追求、生命的欲望。在佛教看来,肉身是五蕴的载体、痛苦的根源,是有限之人达到无限境界的障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佛教各派别的修行方式不同,但大都提倡禁欲主义,即克制肉体的欲望、约束感性的行为,并最终进入一种弃绝人生的涅槃境界。因此,这种弃绝生命意志、贬低肉体力量的佛教不可能引发出奥林匹克精神,也不可能关注于体育事业。
同佛教一样,基督教也有着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圣经》认为,人的有限性表现为两种罪恶,一种是“原罪”,一种是“本罪”。原罪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所犯下的罪恶;本罪是每个人今生今世所犯下的罪恶。无论是原罪还是本罪,均来自人的贪欲。而人类要想得救,即获得上帝的宽恕,就必须放弃感性的欲望、肉体的诉求,像耶稣基督那样,将毕生的信仰都奉献给上帝。基督的肉体是有限的,但他的精神却是无限的,在他的感召下,每一个有限存在的肉体要想获得灵魂的拯救,就必须根据宗教的戒律进行一种少私寡欲的修道过程。因此,如果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种启迪民众的宗教实践,那么基督徒的“肉身成道”则是一种皈依上帝的人生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感性的能力和肉体的力量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里,奥林匹克精神只会遭到泯灭,不会获得高扬。
作为与佛教、基督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与人的有限性相比,安拉是伟大的、神圣的、独一无二的。由于安拉的无限性是不能加以形容和比附的,于是,伊斯兰教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认为用任何有限的偶像来形容无限的安拉都是一种亵渎。无限的安拉不仅开天辟地,而且主宰众生。任何人在末日都会受到安拉的审判,并依据其生前的行为来决定其能否进入天堂。进入天堂的人能够免除疾病、痛苦、哀伤、死亡的烦恼,从而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信仰真主的穆斯林必须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进行祈祷、实行斋戒,即克制自己的肉体欲望和感性生命,将全部的身心献给安拉。显然,这种具有禁欲主义色彩的宗教也不可能派生出奥林匹克精神。
但是,或许有人会问: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以“儒道互补”而著称的中国古人大都不信宗教,也没有禁欲主义传统,为什么也没有孕育出奥林匹克精神呢?我们说过,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在动力来自人的肉体能力的有限性和神的感性能力的无限性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而这一矛盾在儒、道两家那里并不突出,即使存在也无须通过体育的行为来加以解决。
毫无疑问,儒家也看到了人的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并企图超越这种有限性,但其强调的是社会性超越。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不同,儒家没有一个绝对无限的宇宙主宰作为其超越的目标,而是将族类生命看成是个人价值的归属。在经验层面上,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主张通过肉体生命的世代延续将有限的个体与无限的族类联系起来,以实现薪火相传、香烟不断的目的。在超验的层面上,儒家讲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讲究“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主张通过积极的社会行为把有限的个体存在和无限的族类生存联系起来,以实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诉求。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派生出奥林匹克精神。与之相反,受其影响,直至今天我们还常常为体育竞赛负载过多的民族意识和族类情感,而无视其人类普遍的价值与意义,这恰恰是需要我们纠正的。
毫无疑问,道家也看到了人的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强调感性生命的意义,但并不主张通过感性生命力的充分伸张来消除这种有限性,从而向无限的神看齐。道家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它们来自于道,复归于道。因而顺其自然即可,不必勉力而为。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因而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主体的感性冲动衰弱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竟坚持:“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种拒绝冒险、回避竞争的态度显然与竞技性很强的体育精神是相排斥的,因而也不可能孕育出奥林匹克精神。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老庄思想中也有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以后的道教,对于以吐纳导引为特征的气功与武术等中国式的健身方式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老子·十六章》),便被视为气功中“意守丹田”的思想根源。又如,“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息之以踵,众人吸之以喉”(《庄子·大宗师》),则被视为健身中“吐纳导引”的早期实践。但是,这种强身健体之术与西方意义上的体育是有重要区别的。
我们知道,与无神论的道家不同,有神论的道教强调人与神之间在感性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并企图运用丹鼎、符录等手段来缩短这一差距,将有限的凡人变成无限的圣人、真人、神人。然而,无论是道教的“内丹”之学,还是“外丹”之术,其目的旨在通过吐纳导引、服食丹药等方式不断打破生命长度上的极限,甚至希望长生不老、羽化升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努力也是要弥合人的肉体能力的有限性和神的感性能力的无限性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差距,但其努力的轨道却与奥林匹克运动完全不同。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不以健康以外的竞争为目的,不去追求某种超乎常态的体能和叹为观止的对抗,因而便不会导致身体机能的片面发展,也不会带来某些不必要的危险和牺牲。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既不构成人对自然的挑战,也不构成人与人的抗衡,因而既弱化了竞争的机制,也弱化了冒险的热情。受其影响,直到今天,我们在足球之类的体育活动中,也很难进入到一种忘我的迷狂状态,这恰恰是需要我们加以反思的。
作为古希腊宗教神学所派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奥林匹克运动不仅随着希腊宗教的确立而崛起,也随着希腊宗教的衰落而中断。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根据大主教布路瓦斯的建议,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随后,狄奥多西借口奥运会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是异教徒的活动,是对基督教的不敬,下令终止了它的召开。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便从此中断了。
与奥林匹克运动通过感性能力的扩张而使人向神看齐的文化路径完全不同,基督教所宣扬的恰恰是要高扬灵魂而贬低肉体,主张“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于是,从事体力劳动而显得肉体强健的人往往被视为心灵卑下的人,认为卑污的肉体会妨碍灵魂的升华。《圣经》称“人是风吹的叶子,枯干的碎秸”;奥古斯丁则主张只有信仰上帝,用禁欲、斋戒、忏悔、出家修行等方法,才能摆脱人世间的罪恶和痛苦,得到上帝的挽救,死后灵魂才可升入天堂。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弃绝一切肉体的欢愉、推行禁欲主义便成了基督教徒最常见的修行方式。美国学者穆尔说:“基督徒的虔诚一开始就带有禁欲倾向。起先,对基督即将到来进行审判的期望,是它的主要推动力。到这种期望幻灭以后,感官与理智、肉体与灵魂的冲突问题,便取代了它的位置。这个问题当时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思想中,使宗教哲学,以及我们不妨称为个人宗教生活的一切,都带上了禁欲色彩。凡是向往在基督徒生活中得到更高成就的人,都多少按照通行方式折磨自己的肉体。”⑦ 基督徒们折磨肉体的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通过严格的斋戒抑制食欲和情欲是最常见的做法。到了公元3~4世纪,开始流行一种类似于印度苦行的禁欲方式,那些修行者们离开城市,隐居到偏僻的旷野中,或者穴居于沙漠中,或者寄身于丛林里,或者吃睡在湿地上,或者干脆在坟墓或枯井中生活。他们或者一连数日不饮不食,或者长年累月终夜不眠。“那些在自我折磨上超过常人的,便被称为‘竞技者’,正如18世纪的英国神学家及哲学家巴特勒主教所说,他们乐于在苦行方面‘创造新记录’。谁听到别人每天吃一磅面包,他立刻把自己的定量降低到五英两和少量的清水”⑧。这俨然是另一种形式的竞技比赛,可惜与奥林匹克运动南辕北辙。从13世纪开始,天主教内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禁欲苦修方式,那就是教徒们在街头排队游行,一边行进,一边用皮鞭猛抽自身,以致皮破血流,遍体鳞伤,意在通过惩治肉体以求灵魂得救,即所谓的“鞭笞派”。这种信仰方式和文化路径的不同,也表现在艺术作品里。在出土的雕塑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诸神的形象都是强壮有力、体态健美的;而中世纪的雕塑和绘画中则只剩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以及同其一样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门徒们。
在这种敌视肉体的文化环境中,不仅奥林匹克运动会遭到了禁止,即使是普通的体能训练活动,也都会受到无情的压制和清剿。教会利用神权,反对一切公共竞技性集会,规定基督徒如果参加竞技比赛和格斗表演,就不准参加“圣餐”仪式;而竞技者和角斗士则必须保证永远放弃这种职业才能成为基督徒。“各王国所特有的体育活动和民间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体育形式遭到严重的打击和阻止。除必要的军事训练和少数统治阶级的消遣活动外,民众从事体育活动者极少”⑨。甚至连洗澡和游泳这样的活动也被迫取消,理由是它们虽然清洁了肉体却玷污了灵魂。而在由基督教会垄断和把持的学校教育中,既没有体育课,也没有任何发展体能的活动,那些擅自从事体育活动的学生则会受到严厉的体罚。可以说竞技和体育活动在中世纪差不多遭到了全盘否定,唯有在骑士教育中保留了一丁点的空间,但那也只是出于军事目的。
就这样,曾经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整整中断了15个世纪!在这里,我们不仅已经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背后的宗教动因,而且也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面前的宗教桎梏。显然,打破这一桎梏,不仅要依靠体育自身的动力,而且要依靠文化乃至宗教发展的动力。这一动力,先是来自文艺复兴运动,后是来自宗教改革运动。
14世纪至16世纪兴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阶级属性上说,是资产阶级的;从思想属性上说,是人道主义的;从文化属性上说,是古典主义的。“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源自意大利文,一般多写作法文。当时的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自中世纪以来却遭到了禁锢和摧残,需要加以“复兴”。事实上,这是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所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的旗帜下所展开的人性复归运动,它要把人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肯定其存在的意义。“人文主义者在研究和整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时,发现了古希腊体育的丰富遗产。例如,荷马史诗中的体育故事、葬礼运动会、雅典的体操学校、运动场、体操馆、泛希腊运动会、斯巴达五项竞技等;古希腊罗马哲人的体育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并得以推崇”⑩。因此,这不仅是文艺的复兴,而且是体育的复兴。第一个表达了文艺复兴时代教育理念的弗吉里奥主张,要通过设立体育、文学、绘画、音乐等课程对青少年进行通才教育,使他们具有“支配的理性”、“顺从的身体”。另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则在其兴办的宫廷学校里开设被称之为“快乐之家”的体育宫,并亲自带领学生骑马、爬山、游泳、击剑,以及从事各种各样的田径运动。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塑造了一个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体魄上都无比强大的巨人,这个巨人上午读书,从事科学研究,下午锻炼,从事体育运动。正像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常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11)。这些巨人在各个向度上不断挑战人类的极限,重新体现了古希腊时代的文化追求和人类理想。
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16世纪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复兴。一方面,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抨击了罗马教廷对信仰的垄断;一方面,这些新教伦理的建设者们否定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针对中世纪教徒们的修道生活,路德认为:“灵魂与肉体不是矛盾的,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上帝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完成在尘世的义务,天职与尽世俗义务是一致的;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12) 因此,他没有像苦修者和“鞭笞派”那样把虐待肉体当作拯救灵魂的手段,而是号召基督教徒们“保持身体健壮”,主张“人们应有高尚和有用的运动练习”,认为参加体育活动“不仅能驱散人的烦恼、苦闷,而且使四肢得以充分发展”(13)。他还要求把体操和音乐定为德国教育的固定课程。在致德国各城市市长及议员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古人已慎重考虑与妥为安排,认为人们应该练习体操,这样才不致使人养成尚浮华、不贞洁、好吃、放纵与赌博的习惯。所以有两种康乐使我最感愉快,那就是音乐与体操,前一种将内心所有的牵挂与忧郁驱除干净,后者使身体产生弹性并能保持健康。”(14)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16世纪就开始有人试图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如依奥汉涅斯·阿克维尔于1516年在巴黎组织的“奥林匹克示范表演”。17世纪早期,罗伯特·多佛在科茨沃尔德创立了“奥林匹克赛会”。到了18世纪,规模壮观的“仿古希腊运动会”在1796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庆典上隆重举行。“在19世纪后期,希腊连续举行了四届泛希腊奥运会。除此之外,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运动会’(1834,1838),法国龙多神学院的‘龙多奥林匹克竞走节’(1832—1925),英国马奇温洛克的‘奥林匹克节’(1849)和‘马奇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加拿大‘蒙特利尔运动会’(1844)等,都是对复兴奥运会有一定影响的尝试”(15)。于是,一项被封杀了千年之久的文化壮举呼之欲出了。
总之,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思想先驱们没有直截了当地呼吁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也没有亲自参与任何与恢复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具体活动,但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却给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清除了文化上的障碍。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有顾拜旦等人日后的成就。在这层意义上,奥林匹克运动背后的宗教动因和文化土壤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并加以思考的。
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在迎接此次盛会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做好各个方面的物质保障,而且要做好各个方面的精神准备,这包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全方位的理解和反思。说到底,这不仅是一项体育的盛会,而且是一项文化的壮举。因此,我们从中所得到的,也不仅是比赛的金牌,还有文化的洗礼。
注释:
①《世界宗教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3页。
②崔乐泉:《奥林匹克运动简明百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页。
③同上书,第21页。
④樊正治:《运动哲学导论》,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4年,第119页。
⑤K.吐依、A.J.维尔:《真实的奥运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⑥同上书,第19页。
⑦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2页。
⑧同上书,第113页。
⑨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⑩谭华:《体育史》,第149页。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12)谭华:《体育史》,第154、151页。
(13)王其慧、李宁:《中外体育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14)杨文清:《源远流长的世界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8~59页。
(15)谭华:《体育史》,第211~212页。
标签:奥林匹克论文; 古希腊论文; 宗教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奥运会项目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体育史论文; 文艺复兴论文; 运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