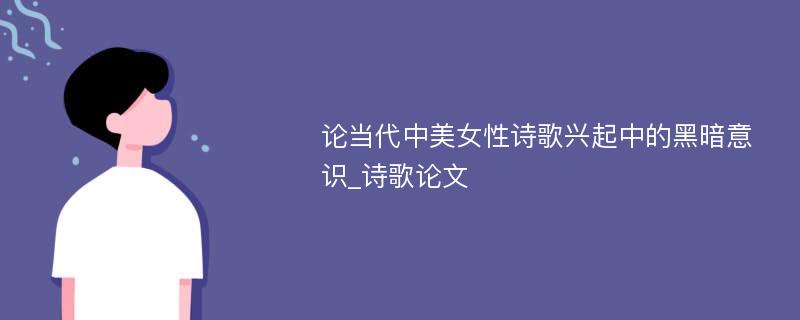
论当代中美女性诗歌兴起时期的黑暗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诗歌论文,当代论文,黑暗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2004)03-0036-04
不管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对女性文学的界定有着怎样的纷争,在中国,人们多数认为它应当具有“女性作者”、“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三个特点。[1]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将中国女性诗歌在当代的兴起界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翟永明,唐亚平等为代表。[2]在美国,它们被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前夕,以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和安·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等为代表。尽管中美女性诗歌的兴起时期因各自文化语境的差异有着先后之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一定的渊源。普拉斯、塞克斯顿的诗作被认为是“代表了一个诗意的潮流,它是女权运动最初阶段的文化特性中的主要方面”。[3](P522)不仅如此,它们还“直接启悟了翟永明等为数不少的‘第三代’女性诗人”。[4](P283)正是由于这种直接影响,以及女性的共同经验,中美女性诗歌在语言、题材、主题、叙事等多重层面上均呈现一定的共性。其中,象乌鸦、蝙蝠、巫女、黑衣服、黑衣人等黑色意象的大量出现,和着对黑夜、黑暗、黑色感觉的渲染,她们在文本中不约而同地凸现一种浓烈的黑暗意识。本文认为这正是女性意识在二十世纪新一轮觉醒的必然表达,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同时又成功地解构了一些男权文学传统的神话,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的意义。
一、黑色意象和黑色感觉交织的黑暗意识
以普拉斯、塞克斯顿为代表的美国女性诗歌中涌现大量的黑色意象,表现包括死亡在内的诗歌主题。如普拉斯在《渡湖》中一连使用了黑湖、黑船、黑纸、黑人、黑树、黑影等六个黑色意象,表达诗中人“黑色的精神”。作为自白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当代美国女性文学的焦点人物,普拉斯在另外一首名为《暗伤》的短诗中反复以“污秽黯淡的部位”、“岩石的洞穴”、“苍蝇”、“(岩)壁”等黑色意象暗示女人的暗伤,或者她的暗伤。丈夫另有所爱,心中苦楚无处诉说,创造的激情和抚养一双年幼儿女的责任永远在冲突,在1963年伦敦少有的一个寒冬,她终于带着那种暗伤悄然离去,在自家煤气炉上得以永久的解脱。在《精灵》中更是以“黑暗”、“突岩”、“巨石”、“黑人眼神”、“黯暗的倒钩”、“坟墓”、“黑醇的血液”、“僵死的手”等一组黑色意象表达里自己对丈夫,乃至父亲下意识的不满和抗议。
而同为自白派主要代表的塞克斯顿诗歌中也不乏同样的例证,如《星夜》中,她运用了“黑发老树”、“死”、“夜那匆促的野兽”、“夜的黑锅”等意象直抒死亡主题;在《太阳》中,更是以与题目极不相称的“苍蝇”、“肮脏的洞穴”、“(苍蝇)身体”、“(苍蝇)翅膀”、“小黑鞋”、“祭司”等意象深化同一主题。
因为中西文化分别重写意/写实的本质差异,中国女性诗歌文本更多渲染黑色感觉,且表现出相当的策略意识。翟永明《女人》组诗序言《黑夜的意识》(1985)被认为是成为“‘黑夜’及其与‘黑色’相关语象”的理论性先导。[4](P283)这种以表达黑夜意识为核心的自觉的策略意识甚至被视为“女性诗学原则”。[5]在《黑夜的意识》中,翟永明这样宣称:“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从一生下来就与黑夜维系着一种神秘的关系,一种从身体到精神都贯串着的包容在感觉之内和感觉之外的隐形语言……”,而黑夜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向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女人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思考和乖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黑夜意识”。[6](P306)此后,“心有灵犀的女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走向‘黑夜’,操起‘黑色’这一共同认可的”图腾[4](P283)
在《女人·世界》中,翟永明以“深奥面孔”、“幻影”、“乌云”、“眼眶”、“纵深的喉咙”、“黄昏”、“原始的岩层”、“黑夜”、“野兽的心情”、“母性贵重而可怕的光芒”、“黑色梦想”等词语直接描绘女人深奥的世界,在《人生在世·黑房间》中更加以乌鸦、黑色房间、猫、老鼠等意象试图呈现女性生存的黑暗。此后,女性诗歌中黑色感觉被渲染到极致,唐亚平《黑色沙漠》组诗就是很好的代表。而林柯干脆以《黑女人》为题,在“黑夜”、“漆黑的目光”、“媒层”、“黑女人”、“黑发”、“黑眼”、“黑裙裾”、“黑液”、“沼泽地”、“墓碑”、“深渊”里再现了作为女人“黑色的液体(眼泪)”。
二、黑暗意识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必然表达
美国知名女性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詹威(Elizabeth Janeway)在扬扬五万余字关于当代美国妇女文学家的论文《妇女文学》中指出:“妇女的共同经历只会消除国别的界限,象西蒙娜·德·波伏瓦、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多丽丝·莱辛这样的欧洲作家,看上去就象是和当代美国妇女文学有着血缘关系似的。”[3](P484)既然如此,加上美国诗人对中国诗人的直接启悟,她们的文本共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黑暗意识就不足为怪了。究其源,这种黑暗意识该是诗人们女性意识在当代新一轮觉醒的结果。
在美国文学中二十世纪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长篇小说《觉醒》(1899)为代表;在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以秋瑾在本世纪初创办的第一份女报《中国女报》为先锋,五·四后的冰心、庐隐、丁玲、萧红等大批女作家的作品代表了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群体的觉醒。当社会历经几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后,敏感的当代文学女性再次感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且达到更高层次。在当代美国,普拉斯的诗歌被誉为“女权运动的试金石”。[3](P484)她和塞克斯顿后期诗作“可以说是从文学上开了七十年代妇女解放声浪的先河”。[7](P54)紧随他们身后的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潮和女权/女性文学批评也随之勃兴。这便足见她们敏感的女性意识了。
在中国,诗人们先是在新时期找回了五·四时期的女性自主意识,舒婷轰动一时并传为经典的《致橡树》可视为代表。但更多更年轻的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第三代”或“新生代”或“后朦胧期”的女诗人们已无法满足于此。她们凭着满腔激情和新时代赋予的气魄大胆阔步走向了更深的层次,在她们的诗歌中勇敢地表达女性隐秘经验、性意识,乃至和西方女权思想高度吻合的话语意识。就在东西两岸的女诗人们将敏锐的目光投向女性自身时,她们痛苦地发现女性的地位在男权制社会中于根本上仍然是黑暗的。人类学家指出,女性在男权文化体系中只是一个失声的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只露出一个月牙形的称之为野地的边缘地带。
她们思考,她们暴怒,她们要呐喊,她们要抗争,但她们该如何表达自己?在使用逻各斯语言的前提下,她们能否清楚地表达自己?她们在黑暗中思考,也在黑暗中找到某种答案:死亡,疯狂和黑夜竟是最接近能表达自我的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宿命的妥协和选择。另一方面,黑色本身的多重语义和黑夜的丰富联想意义也给她们提供一个巨大的弹性空间。而黑色在色彩上既代表凝重、退却,又代表权威的双重特征,与新觉醒的女性意识既要建构又要解构的主观愿望达成宿命的吻合。就这样,位于时代先锋的女诗人们纷纷在文学王国里营造起一片又一片“黑色丛林”,神秘、隐匿、恐惧又极具诱惑力。尽管依然位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但已经绝对不容忽视。
三、 黑暗意识解构男权神话
与此同时,这种黑暗意识的强化和不断渲染也成功地实现了对男权文学传统的解构。一方面,黑色意象在语言横组合轴上的优先权预设了风花雪月一类传统型女性文本的不可能性。很难想象云集的黑色意象能唱出一支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式甜腻的情歌,或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之类的“小女子”情诗。如果黑夜尚可让情人低语,夜莺歌唱,甚至恋人们偷一个羞涩而甜蜜的吻,当“蝙蝠在空中微笑”,周围是“瞎眼的池塘”,情人也真只能“睁着精神病人的浊眼”才算应景。这里的夜晚没有爱情,或者爱情已随“死去的栅栏”而死去,有的只是人和景和大怪诞、大荒谬(翟永明:《女人·边缘》)。
此外,它们还直接颠覆了男权文学传统中的婚姻神话、女性神话和生命神话等。如普拉斯在《申请人》中塑造这样一位婚姻申请人,她非但物化成“橡皮乳房,橡皮胯部”,有一只能“端来茶杯揉走头疼/不管你要它干什么它都干”、“保用保修”的手,穿的竟述是“黑色,有点硬,但挺合身”的衣服,保证“入土时也穿这衣服”。这是对男权制社会中婚姻犹如坟墓,埋葬一切人性的辛辣而最深刻最奇特的控诉。又如塞克斯顿在《她那一类》中精心描绘的一幅女人画,疯女人的画:“紧追着黑风”巫女般“梦想着做坏事”,从夜里走了出去,去了森林“为寄生虫和小精灵准备晚餐”、“总是被人误会”、“宁愿肋骨断裂”绞入“驭手”的车轮,“不会羞于死亡”,也不愿如男权社会要求的那样做一个“屋里的安琪儿”,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再如翟永明在《女人·母亲》中对诞生的抗拒:“多年来我/已记不得今夜的哭声”,因为母亲让“我”生下来,是“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可怕的双胞胎”。这一诗行传递着与张洁那句名言同样的信息: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女人的生命总在女儿/母亲间轮回,每一个像“我”这样的夜里诞生的生命都“因诞生死去”。无独有偶,以“她自己漫长的诗歌实践展开中国的妇女诗学”的学者型诗人郑敏在同时期创作的《心象组诗》中有这样一首:“我多年蜷曲在母体内/让子宫紧紧地,围裹着/一次,剖腹产将我/投掷入世界,它的/刺眼的亮光和/刺耳的噪音中。/我被无数生活的墓碑包围。”在这里,由“母体”、“子宫”和“墓碑”同构的黑暗意识成功地毁灭了男权文学中关于生命何其伟大的神话。不错,“也许郑敏的《心象》组诗的写作动因源于反思‘十年动乱’,但诗歌所获取的却是女性话语的胜利”。[8]早在此前,普拉斯对这样的“生之不足惜”更是清醒得骇人,在《拉扎勒斯女士》中“我”自喻为可以九死的猫,每十年“干”(自杀)一次,因为“死/是一门艺术,像任何事情。/我要干得分外精彩”。
四、 黑暗意识建构女性诗学原则
就在黑暗意识以其特有的冷峻否定男权话语的同时,它们也表现出积极的建构意义。前面提过,翟永明《黑夜的意识》把黑夜意识提升到“女性诗学原则”的层次。因此,她在《女人·世界》中的“我”郑重宣布:“它们(黑色梦想的根)/靠我的血液生长/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在《女人·独白》中,“我”说:“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有人认为,这些女性文本的“黑夜”可诗意地解读为“激情的来源”,或者这些黑色意象“不只是宿命般地成了女性象征性语码,而且是女性自身的保护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9]
尽管这种解读不免笼统,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黑暗意识对于女性、女性诗人的重要性。如普拉斯在《雨天里的黑乌鸦》中写道:“我只知道一只乌鸦/在梳理黑色羽毛时如此闪闪发光/控制我的感觉,拉起/我的眼帘,给予我/短暂的缓解,从完全/无意义的恐惧中解脱。”这里,“我”在“这个疲惫的季节中/顽强煎熬时”因黑色的启悟突然获得一种解脱,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升华,从而使“一个平凡的时刻/骤然变得神圣”。中美诗人不约而同地对黑色和黑夜的关注及深刻认识,使得黑暗意识具有一种解构之外的建构功能。两者的矛盾统一使得所有的黑暗意识顿时更具张力,更具美感。
综上所述,黑暗意识在当代中美早期女性诗歌中的如此彰显是女性意识在当代新一轮觉醒的必然表达,在试图建构女性话语、女性诗学原则的层次上表现积极的意义。这片恐怖、神秘而又不失庄严的黑色丛林在大洋两岸以其丰富的个性和共性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既否定又肯定的张力场,成为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一块醒目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