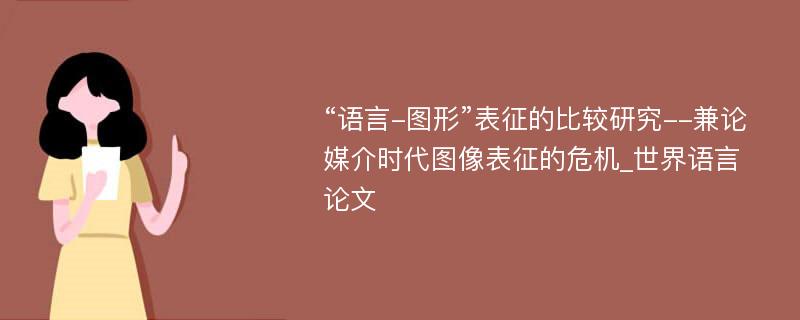
“语—图”表征的比较研究——兼论传媒时代的图像表征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图像论文,危机论文,传媒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3-0067-09
在约翰·费斯克等人看来,表征(representation)指“制造符号以代表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1]在表征系统中,语言的表征和图像的表征对意义生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确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2]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以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为主导的全媒体时期,图像改变了语言独领风骚的地位,与语言势均力敌,呈现出不同于语言的表征特点。视觉文化在满足人们观看欲望的同时,视觉表征的危机也显出端倪。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受到“威胁”的语言符号,是否需要倾心视觉化?在此种情形下,“语—图”表征的比较研究更能激起学界的兴趣。
一、符号能指:淡化与膨胀
任何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图像符号。其中,“能指也是一个关系项,它同所指密不可分,能指是中介物,它具有物质性,它的内质永远是质料性的。”[3]虽然能指是物质性的,但是这种物质性在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上有所区别。语言符号能指的物质性,原本是声音所致,但“在口头语言向文字转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形态的变化,一些信息的成分被过滤了”,[4]比如说话人的语气、节奏、语调、音高等听觉因素。正因为如此,索绪尔才说:“语言的本质跟语言符号的声音性质没有什么关系。”[5]语言中声音信息的减少,它的好处是凸显了语言的一般性或普遍性,不足之处是丧失语言媒介的感性特征,这点从现代诗歌写作对音乐美的呼声中可见一斑。在向文字转变的过程中,语言能指的物质性,还与书写的媒介(墨)有联系,但这些物质性对语言的理解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正如艾伦·戈德曼所说的,“我们并不是通过墨迹来推断词的意义。”[6]
语言能指的物质性减少,形成了语言的概括性特点。“语言的‘万能’能力正归功于其抽象能力,抽象是语言的力量所在。而这也是语言的弱点所在,这种抽象能力阻碍语言以准确的方式表现某些现实,例如空间及时间的直观性。”[7]去掉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性东西,上升到一般层面,语言自然就具有概括性。语言虽然是概括性的,但却又能“开启”丰富的境域。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的使用是为了开启“境域”的需要:“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创构。……创构即是溢流和馈赠。……此真性的和诗构的投射是对那样一个境域的开启,缘在作为历史的(存在)就被投入其中。”[8]这种开启,还需要靠读者的想象力参与来完成,不同于图像艺术的直接呈现。在语言所塑造的指称世界中,“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9]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境域开启。
语言能指摆脱了物质性的依赖,还与能指在语言艺术中的地位有关。能指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所指,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如果意义表达了,就不必在语言能指上做过多的文章。但孔子又说:“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指出了修辞的重要性,这是否有矛盾?再看孔子说这句话的前几句:“《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来这里的“文”是为了“言”更完备,以表达“志”的需要。如果语言修辞脱离了“意义”,缺少意义的语言美就变得无足轻重,成为艺术表现的累赘,南朝浮靡诗风、当代网络文学的“注水”现象就是反面的例子。
为了凸显意义,语言符号运用的最高境界是用最小量的能指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意味,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言语是有限的,为什么却能表现无限的意蕴呢?原因有三,其一是象征、隐喻等手法运用,使得“意”在“言外”成为可能。其二是语言的使用是结合作者自身的体验,“我的言语是‘活的’,因为看来它们没有离开我:它们没有在我之外、在我的气息之外落下可见的远离之中,它们不间断地归属于我,并且无条件地归我所支配。”[10]这种主体的情感色彩与语言联系在一起,自然就融入到艺术当中。其三是语言带有丰富的文化信息,米歇尔说:“词语则是图像的‘另类’,是人为的,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武断地生产的,这种生产通过把非自然的元素引进世界——如时间、意识、历史,并通过利用符号居中的疏远性干涉——而中断了自然存在性。”①语言的约定俗成性与言语个性是相辅相成的,是文化传统与现实当下的有机交融,诚如利奥塔所言:“话语是有厚度的。”[11]
而现代图像能指对物质性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特别是影视创作,它必须借助演员的身体和逼真的场景,能指的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越丰富就越受欢迎。在前视觉时代,文字对视觉压制的现象长期存在,“视觉能力和视觉记忆退化,正是文字长期垄断人类心智活动主要空间带来的副作用之一。”[12]这种压制,导致了图像能指所需要的身体表现能力萎缩,如巴拉兹所说:“艺术家能够通过手势或表情等外形动作来朴实地表现人的心灵。但是,自从印刷术发展成为人们在更遥远的距离外交思想的主要工具以后,人的心灵便更集中地表现为文字,因而就不必再利用身体器官这一更精巧的表现工具。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身体就愈来愈没有表情,愈来愈空虚,日久不用,机能便退化了。”[13]不过,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压制后的视觉释放更为强烈,所以当代社会对视觉的需求是必然,视觉文化的到来有一定的必然性。
图像能指的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需求,是图像艺术的特性所在,“图像表征系统是先天不足的——它不能脱离于‘真实物’和具体物;它缺乏那种适用于普遍性的必要区隔。”[14]很难想象,没有模特,怎能创作出人体艺术?没有演员,电影摄制便无法开工。伯格曾从艺术的表现范围对各类艺术进行了区别:“诗写的是心灵、痛苦、死亡——存在于我们互为主体性的范围中的一切。音乐表现的是被给予的事物背后的世界:不假文字、看不见、自由舒畅。剧场是过往的重演。绘画则与肉体的、可触知的、当下的世界有关。”[15]绘画表现感性可知的世界,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绘画不能用语言来表现,它要用具体可感的媒介来表现。即使是抽象的绘画,也需要呈现颜料的浓淡等质感,它们是绘画重要的审美要素。这种物质性的存在,才导致了绘画的真品与赝品的天壤之别,欣赏原作与欣赏印刷品也是大不相同,因为印刷品削减了图像能指的物质性。
今天的影视艺术对物质性的刻画更为容易,日益发展的科技为此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图像传播媒介中,图画比图形的冗赘性高,图像比画作的冗赘性高,新闻图片比艺术图像冗赘性高,电视图像比电影图像冗赘性高。”[16]这里“冗赘性”与各种艺术能指的物质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递增与技术的进步是成正比的。“电影与电视的出现与普及,无疑重新启动了人类的视觉敏感性,它们能在二维平面上展现四维(空间的三维和时间的一维)形象,从而完整地再现了事物运动着的视觉形象。”[17]现在运用计算机技术,通过图像增强、图像重叠、编码等数字化处理,原来低质量的图像会大大改观,[18]图像这种视觉的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越来越凸显,而不管它是否有助于意义的表现。不过,这种物质性的凸显,一直是电影艺术梦寐以求的。②
美国电影界将1993年的夏天称为“好莱坞数字之夏”,认为真正的数字技术从该年8月的《侏罗纪公园》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电影将3米高的恐龙模型制作为三维图像,展现了人龙交战的精彩故事。[19]2000年,《透明人》上演,影片中巴斯蒂安的隐形,观众不仅能看到外部形状,还可以看到内部的肌肉、骨骼和血管等,[20]让平时不可见的世界视觉化了。
由此可见,不同于语言艺术的能指淡化,在数字技术的协助下,图像艺术能指的丰富性已超出了人类的自然感知,而且这种能指的膨胀还并未结束。从理论上说,世界只能“‘单面地’、连续‘多面地’,但永远不会是‘全面地’被给予”,[21]世界永远不能被视觉全面把握,图像能指的细腻描绘冲动也永远不会停止。
二、表征目的:意义与意图
语言与图像都是一种符号,“符号化的过程,即赋予感知以意义的过程。”[22]对符号意义的探讨,是“语—图”表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语言的意义,是以指称意义为基础,指称意义是指词语所指的对象。北岛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回答》,最后一节是: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其中的“象形文字”,它所指的对象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汉字造字方法“六书”的一种,即与“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并列。但是语言并不拘泥于指称义。指称义比较固定,被格雷姆·特纳称为是“字典式的意义”。[23]如果语言的意义仅限于指称义,文学的阅读只需能识字就行了。事实上,文学阅读没有如此简单,语言的意义会从具体的陈述对象延伸到一般的精神世界。在古希腊时代,意义的生产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智者学派恰好是致力于使语言从指称作用中脱离出来,把它们独立地当作一个体系。……这一种考察为主体超越于客体、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支撑点。”[24]上首诗歌中的“象形文字”,在诗歌当中的运用中超越了具体的指称意义,不再是简单地指向“日”、“月”等具体文字,而是上升为精神层面的仍然散发着活力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具体的指称意义到表达一般的精神世界,何以可能?首先,它必须在一定的语境或文学文本中才能实现,需要与其他语言符号组合才能产生新的意义。其次,更为重要是“符号从一开始就被虚构加工过”,[25]语言意义的建构方与使用者的有意为之分不开。“维特根斯坦建议,首先要区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前者是通过词典编撰者和句法学家的耳朵、眼睛或者他们对于规则的认识而被把握的,但只有那些掌握了语言运用的规则并因此掌握了说话者的意向的人,才能够把握后者。”[26]如果只掌握了语言运用的规则,而不了解说话者的意向,便不能把握作品的精神世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说话者的意向也提升了语言符号的精神层次。说话者的意向,“更多地以使用者的文化经验而不是字典为基础”。[27]这里的文化经验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语言集团精神、民族文化精神等方面内容,这些论述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并不少见。
我们再参照海德格尔的词源研究方法,海德格尔“对‘语言’追本溯源,直至古希腊的‘逻各斯’,把经典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解为‘人是说话的动物’”。[28]海德格尔的这里转换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因为语言摆脱了物质感性,从具体能上升到抽象的一般。我们可以说,“语言的真正本质是包含在其‘意义’中的,这一意义超越于一切感性自然之上,因此语言可以为人的精神独立性提供一个支点。”[29]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上升”、“超越”,并不是说文学中没有语言的感性美,而是感性美与精神意蕴的结合。
当然,语言的意义表达,需要一定的形式创新,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都能有意义。巴拉兹就痛斥“陈词滥调”对意义的戕害,他说:“语言文字并不只是表达我们思想感情的形象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反而主要是一种约束思想感情的形式。陈腔滥调(这是读书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产生的根源即在此。”[30]倒不是陈词滥调没有意义,而是不能产生新的意义并引起读者的审美惊奇。胡适曾经对此也有同感,曾多次撰文陈述“套语”的不足。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有什么危机的话,应该不是缺少意义,而是平庸意义的泛滥,缺少经过作家生命体验的令人震撼的意义。
对于图像符号,从理论上看,它也存在一定的意义,因为“可感的(可听见的或可看见的,等等)现象是被一个主体的活动赋予生命力的,这个主体赋予这些现象以意义,而另一个主体应该同时理解这个主体的意向”。[31]但苏珊·桑塔格对此非常疑惑,虽然“照片填充了我们关于现在和过去的心象中的空白”,让我们能欣赏到令人惊奇的感性美,但“严格说起来,一个人绝不会通过一张照片而理解任何东西”。[32]王安忆也有类似的话语,她说:“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33]的确,通过一张照片或一部影片,我们既不能很好地了解所表现的对象本身,也不能了解其蕴含的意义。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皮尔士看来,符号学的问题主要涉及符号(即索绪尔说的能指)、对象客体、解释项三个方面。其中,客体对象是符号的成因,解释项则是符号的意义。[34]符号的意义主要包括“一符号所表现的观念”和“即可以与一思维对象有关的一种观念”,[35]符号的意义产生离不开符号能指与所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图像的符号能指与其对象客体的距离太小,特别是“所谓‘绝似符号’,包括非常肖似的绘画、照片、录音、摄影,电影、高清电视等。部分‘绝似’符号与对象外形非常接近(例如3D电影),几乎可以完全误认为合一。但是符号与对象并非同时在场,因此它们明显是代替对象的符号”。[36]符号与对象外形非常接近,尤其是数字制作的图像,甚至让人产生可以取代对象的幻觉,让受众沉迷于图像符号而不再关注对象客体,更不去探究符号与其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符号的意义自然会受到削弱。这种情况的造成,源于图像自身的弱点,因为“在图像化表征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就被认定为不是那么任意”。[37]图像能指对外在物质或虚拟物质的依赖,如果又不注重文本中图像符号的精心组合,较少运用蒙太奇、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更容易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图像往往会取消自身的媒介,不再是符号,‘似乎’化作事物本身”,[38]它的意义相对语言符号较少,因为“物‘符号化’(意义生成、增加);反过来的变化,则是‘去符号化’或称‘物化’,让符号载体失去意义,降解为使用物”。[39]越是超真实的图像艺术,它的意义消失就会越多。对此,可以用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来解释,外延越丰富,内涵必然越少。外延,即物执。只有超越物执,才能达到意义。“现象学所悬搁的是感官具有的‘物执’,而达到的是观念意义上的‘纯然之象’。”[40]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这不是正常的图像意识,因为“图像是复杂的……图像意识是个具有多重对象的多重意识的复合体”。[41]“一个完整的图像意识是由三个客体化立义的内在统一来完成的,即图像事物立义、图像客体立义和图像主题立义。”[42]图像意识的发生,需要这三个立义的渗透与交织。但是在当代图像中,我们往往被诱导只需注意或者只看到图像事物,即物理图像或虚拟的物理图像,它是属于图像符号能指的范畴,而不顾及图像主题(对应的实在事物),更产生不了图像客体,即精神图像,像海德格尔在凡·高的《农鞋》中看到的农妇存在世界。既然从图像文本延伸出的意义减少,那么是否只能停留在图像符号能指上?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从图像制作与传播的意图上进行分析,“任何‘存在’从根本上都与境域中的生成、生活、体验或构成不可分离”。[43]图像的产生,离不开所在制作者的生活世界。“图像……提供的是一种最本源的构成场所,在那里人与世界、先天与经验、逻辑与表象相交相遇并相互构成。”[44]对于绘画,“在普林尼看来,绘画历史不能通过它和自然的关系来解释,而要通过它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明。”[45]普林尼重视图像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在今天依然有参考价值。德波的思路也与此相似:“景象不是形象的聚合,而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经由形象所中介的社会关系。”[46]菲斯克也认为:“看制造意义:它因此成了一种进入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将自己嵌入总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一种控制个人的眼下的个别社会关系的手段。”[47]
把图像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便能理解图像制作者与传播者的意图或意识形态倾向,因为“产业与文本、生产与接受的过程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48]当然,图像的意义匮乏,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宣扬,但更多的与当前商业利益相关,通过迎合受众的视觉需求而获得高的利润,形成了图像的当代意识形态,所以,“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徒有其表,而当代伪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源泉的原因。”[49]
当然,文学创作与传播也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从文本生发出来的意义更为丰富。针对当代图像艺术意义贫瘠的情形,它的意图或意识形态性更应该引起受众的关注。只有认识到它的意图或意识形态性,才能揭示所谓超真实的真正伎俩,以应对当前的图像表征危机。
三、艺术形象:虚拟实物显现与想象显现
有个现象很有趣:唐代李白的《静夜思》家喻户晓,成为各个时代传诵的经典,每次阅读都没有让人感到诗作过时。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总感觉到有些不入时,无论是画面色彩,还是人物形象。古老的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被出版发行,但过去的老电影很少能再次回到电影院重演。可以想象,李白的《静夜思》如果是影像文本的话,我们也会感到它过时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如果我们想象它是影像文本,那么井床的质地、颜色、形状,房间的户型、面积、窗户,李白的发型和穿着,会一目了然,尽显观众眼前。李白的这种情感,能够被不同时代的观众认可,因为望月思乡是人之常情。但是李白本人、井床、房屋等形象的视觉呈现,唐代人可能感到很亲切,21世纪的观众则不一定都能认可③,感到很陈旧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它缺少视觉的新奇感。而且这种视觉的虚拟实物显现存在,让观众想象的可能空间减小。“举例来说,当在特洛亚人的命运问题上分成两派的神们终于自己互相殴打的时候,在诗人的作品中这场战争全是不可以眼见的,这就允许读者用想象去扩大那个场面……但是绘画却要采用一个可以眼见的场面……”[50]与莱辛所列举的《荷马史诗》一样,语言文本的《静夜思》,许多东西是不确定的,李白长成什么样,井床、房屋和窗户是什么形状,没有明白写出,读者在阅读时候可以随意想象,一些时代元素就不自觉地加入进去,使古代的语言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当代化,不会有陈旧之感。所以,我们宁愿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也不愿观看老版本的莎剧改编电影,因为电影中的视觉呈现是确定性的,它不仅限制了观众的想象,而且也不一定让各个时代的观众满意。
语言艺术的形象,必须在读者的想象力参与下才能呈现,需要诱使读者进入作品建构的艺术世界之中。明代冯小青就是读了《牡丹亭》后自叹身世而患病夭折,并写下《读牡丹亭绝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④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一则因读《红楼梦》而身亡的故事: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反映了有些读者能进入作品却不能出来。但这是读者本身的文学素养问题,倒不是语言文本本身存在着什么不足。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读者容易进入到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世界中,让自己补充其中的不确定性,进而与作品的主人公合二为一了,并没有切除了现实与艺术的边界,用艺术取代现实,而是沉浸在艺术境界中,如同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
图像形象的实物(虚拟实物)呈现,虽然不足之处在于抑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但却有助于让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下来。本雅明认为,摄影可以利用慢速拍摄、放大细部等技巧让人们领略光的“无意识性”。“面对照相机说话的大自然不同于面对眼睛说话的大自然;这种差异是由于无意识的空间代替了有意识的空间而造成的。我们可以描述出人们如何行走,但只能说出个大概,对迈开腿那一秒里的精确姿势,我们仍分辨不清。然而,摄影可以利用慢速度、放大等技术使上述认知成为可能。通过这些方法,人们认识到了光学的无意识性。”[51]可以看出,由于人眼的视觉能力和时间流逝的限制,只有借助机器,才能让这些不确定性呈现在图像上,当代图像艺术在我们能从视觉上确切了解外在的现实上是功不可没,这一点是语言艺术无法比拟的。
对于图像形象,人们一般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艺术水准高低的标准。对于实际存在的事物,这种真实性比较容易确定,看看是否“酷似”便知。“绘画的‘真实性’的证明,是它‘甚至会欺骗动物,我见过一幅画骗了一条狗,因为画中人酷似它的主人……同样,我还见过一只猴子,和一只画中的猴子做了无数蠢事。’绘画中的‘真实性’由其欺骗动物的能力所证实,这种力量同样可以施之于人类。”[52]这种“酷似”的结果,往往能产生欺骗性。而对于不存在的事物,它的图形化也是可能的。“皮尔斯已经指出:‘像似符号可以不必依靠对象的实在性:其对象可以以纯粹的虚构的存在。’例如麒麟、凤凰的图像,或设计图,符号看起来很生动很‘实在’,对象却不存在,反过来像似符号。”[53]这些形象以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的丰富程度为追求目标,细节越丰富就显得越真实。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让人看起来如剧中的演员一样,像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物,原因即在此。
对图像形象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追求的极致,是让人信以为真,甚至把它们现实化。汪曾祺曾于1963年去洪洞县参观县大堂,那里有苏三跪审的方砖,有“苏三监狱”、苏三井,甚至还有洪洞县的药铺、赵监生毒死沈燕林的砒霜。[54]戏剧的表演逼真性,让人们信以为真,把它从舞台上搬到现实中。不像文学那样,受众沉浸在其中,与形象融为一体,而是把图像艺术形象当成对象化的存在,并与现实存在物并置。鲍德里亚曾说,仿真的符号只进行内部交换,不会与真实相互作用。这只是针对创作的情况,而在传播路途上的艺术品,却不是这样,它取得了与现实物品同等的地位,甚至成为现实生活的参照物。2012年7月20日,在《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的丹佛首映现场,一个袭击者戴着防暴头盔和护目镜,穿着《蝙蝠侠》电影里角色的戏服,站在银幕前不加选择地朝人们开枪。观众开始以为这是影院安排的活动,他们在枪击瞬间甚至都不能分辨是电影中的枪声,还是现实中的枪声。[55]这种枪击案件的产生,除了袭击者的精神障碍之外,与视觉艺术过分对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的追求有很大关系,枪击案疑犯身穿蝙蝠侠电影角色戏服,就是把艺术行为现实化了。
纵然,这也是受众的一种错觉⑤,但是现代社会有力促使这种错觉。影视艺术本身是虚构的,却被电视媒介不当运用,让真实的与虚拟的同时呈现,让新闻与艺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有意识混淆。阿什德指出:“现在有迹象表明娱乐节目正变得更像新闻节目,因为标准的[传播]范式把节目塑造成符号媒介逻辑的样式,而这微妙地使得电视的规则、表述和视点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利用新闻对事件的报道来预告将来要播出的电视剧的那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了吸引人们[对将要播出的节目的关注]的预演或广告。”[56]的确,在新闻中运用电影资料,运用电视剧方式播报新闻,运用新闻的形式制作娱乐节目,才让人们更容易使艺术行为现实化。
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认识艺术的虚拟特征。“现实的影像不是现实,而仅是其影像:我可以坐在一把椅子上,但是,我不能坐在一把椅子的影像上。”[57]1994年的影片《阿甘正传》,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竟然面带微笑地与阿甘握手,阿甘与中国乒乓球选手进行同台竞赛,用的是数字技术。[58]但这仅仅是一个镜头,如果要证明事件的真实性,还必须需要一些文字材料或其他图像资料进行佐证。现实与虚拟艺术不可能分不清,不能像鲍德里亚那样危言耸听,他所说的“海湾战争是一桩发生在天上的媒体事件”,最终成为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⑥
不同于语言文本的主体交融,“意义一旦已经被解释出来,符号的必要性就被取消,就是《庄子》说的‘得意忘象,得鱼忘筌’”。[59]超真实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接受者忘记了这点,而痴迷上了符号能指,忽略了它的意图。而最理想的方式,应该像麦茨所说,把它当做“缺席的在场”来理解:“我必须把被摄对象作为‘缺席’来理解,把它的照片作为‘在场’来理解,把这种‘缺席的在场’作为意义来理解”,[60]并在基础上寻找象征关系,“观影者必须凭借想象关系(将缺席视为在场)开始看片,而以象征关系(通过虚构概念建构缺席/在场的关系)结束看片”,[61]通过“可见之物”了解“不可见之物”。当然,这种方式不仅仅是对受众一方的要求,而且还需要视觉艺术作者的努力:突破视觉媒介对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的束缚,开拓视觉艺术的想象空间。
在当代文化中,语言与图像是两种地位显赫的艺术符号,它们的表征系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由于符号本身对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依赖的程度不同,逐渐形成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淡化和图像符号的能指膨胀,由此造成文学艺术的意义凸显和视觉艺术的意图取代意义。除此之外,还形成了文学形象的想象显现与视觉形象的实物显现或虚拟实物显现,导致文学接受的完全沉浸其中与视觉艺术接受的艺术行为现实化等极端情况。
语言与图像表征的对比研究,不仅仅在于揭示各自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为语言与图像的互文奠定理论基础。正因为语言与图像有着不同的特性,才有可能、有必要进行互文。在互文的过程中,文学艺术可以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获得语言视觉性的审美效果,但是不能为了视觉性效果而放弃对语言本身特性的固守。对于视觉艺术来说,要借鉴文学艺术的特点,突破对物质性或虚拟物质性的媒介束缚,对能指的视觉性追求有所节制,实现意义与意图并重,这样才能解决传媒时代的图像表征危机。
注释:
①引自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云、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索绪尔也有类似的观点:“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比外,语言的符号可以说都是可以捉摸的;文字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里。”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7页。
②早在1933年,雷华电公司制作的《金刚》,就用微缩模型、拟人化妆技术、合成术、叠影技术创造了巨型“金刚”。参见姜静楠:《银屏叙事圈:中国电影》,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③当代人拍摄古装戏,其中的场景和人物,不可能是原汁原味,必须纳入现代元素,才能被观众接受。
④冯小青16岁时被杭州名士冯千秋从扬州买回做小妾,后为其家人所不容,被幽禁。每当夜晚来临,冯小青唯有孤灯一盏,读《牡丹亭》自遣。
⑤W.J.T.米歇尔认为:“‘谬误’不在画家,而在观者:是狗,而不是主人,被主人的错觉欺骗了。猴子可能和画中的猴子干蠢事,但是,要使人像猴子那样,还需要更强大的错觉。”见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⑥“保罗·德曼曾说‘历史知识的基础并非经验的事实而是笔写的文本,哪怕这些文本穿了战争与革命的外衣。’鲍德里亚则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海湾战争是一桩发生在天上的媒体事件。在后现代的感受性中,没有什么比他们两人的话更冒犯人的了。”见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9页。实际上,事实的东西可能经过虚构而变异,但人们还是具备事实还原的能力,“科隆或加利福尼亚州的新纳粹分子也许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这类事情和我持不同的定义。可是历史事实绝不容易抹杀,它岿然不动,毫发无损。”见马克·斯劳卡:《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黄锫坚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