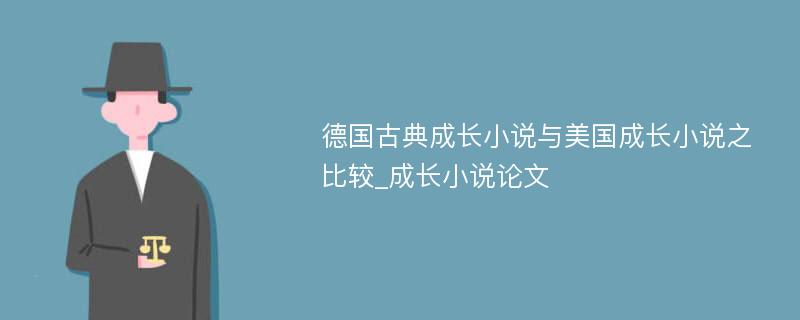
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与美国成长小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美国论文,说与论文,经典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术语同德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一批作家创作的小说紧密相连。[1](P92)它的故乡无疑在德国,而歌德的杰作《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被公认为是这一文学样式的经典之作,可以说它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成长小说的一块试金石。后来,这种小说风靡欧洲,经英国传入美国,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一
成长小说的产生可追溯到德国18世纪70-8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该运动的形成受英法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启蒙思想家强调教育,但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主张依靠反抗来改变社会,其方式是通过抒发个人在社会中的主观感受来揭露社会,表达他们在社会中的体验、经历和感受。特定的社会环境部分地说明了成长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于1795—1796年间首次出版之际,德国被分成了数以百计由统治王朝成员所控制的独立国家。统治阶级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的崛起,感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威胁,认为维护和平和秩序是每个公民的首要职责。18世纪下半叶欧洲德语国家拥有一批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在他们看来,早期教育至关重要,孩子们必须接受有明确教育目的的培训:“他们必须要成为自律的公民和在开明统治者管理下的开明社会中的有用成员。”诚如乔斯特所言,“如果我们寻找例证,说明文学必然植根于社会这样的公理,那么我们也许会想起德国对教育的执著,特别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并[藉此]分析成长小说繁荣的原因。”[2](P101)这是成长小说在德国得以生长的土壤,也决定了它的主要特征。成长小说在美国的继承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其一,美国人自认为是年轻的民族,因此,描述青年、处理青年主题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二,美国人渴望“成熟”而不是“拯救”,因此他们一心想着成长,痴迷于哈克·费恩、霍尔顿·考菲尔德这样的人物。他们把“他尚未失去新鲜感的洞见”、“他尚未耗尽的活力”、“他尚未腐化的天真”理想化了,无意识中他们拒绝原罪的教义。此外,他们把年青人视为美国自己的形象,“粗犷而不受管教”,但蕴藏着成熟和负责的可能性;[3](Pⅶ-ⅷ)其三,成长小说重视经验的教育效果迎合了美国人思想中经验式的“在做中学习”的倾向。[3](P2)这样,青少年的成长在美国文学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同为成长小说,经典成长小说和它在美国的孪生兄弟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诸多共同点。从总体上来说,二者都倾向于描写人物的内心生活,再现个人的成长,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演变的过程,突出成长的方式和原因;小说呈现斑杂的人生和世界,凸显个人和环境的冲突,都对世界持批判的态度;主人公都努力了解这个世界,贪婪地追寻人生的意义,并受益于在这个世界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小说力图通过再现个别人的成长过程来表现带有普遍意义的大人生,等等。[4](P17-18)小说中固有的冲突就在于两个完全相反的理想:年青和成熟;自主和社会化。
但经典成长小说同美国成长小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如《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它的英国现代版《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之间的区别。歌德在前者中感叹:“幸福的青年时节!初次对爱充满希望的时节!”而一个多世纪之后,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后者中却带着他惯常的愤世嫉俗的口吻忧郁地反驳道:“青年是幸福的,这是一种幻觉,是那些失去青春的人的幻觉;可青年人知道他们是悲惨的,他们充满着灌输给他们的不可信的理想,每当他们接触现实时,他们都碰得鼻青眼肿、伤痕累累。”[5](Pⅶ)这是成长小说的范本和它的早期现代版在语气上的巨大差异,而塞林格(J.D.Salinger)的美国现代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给人们的只是对战后青年精神苦闷和心理困境的深刻体味,毫无幸福感可言。这也许正应验了弗莱(Northrop Frye)的断言:“对神话和文体的嘲弄和讽刺性运用将会主宰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的文学。”[6](P3)通过对传统模式的戏仿,甚至颠覆,现当代成长小说(注:本文所使用的“现代成长小说”概念是与德国经典成长小说相对而言的,指的是1955以前的美国成长小说,而“当代成长小说”是指此后出版的美国成长小说。)获得了力量和时代意义。
二
研究成长小说面临的一个棘手但又必要的工作就是既要厘清经典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之间复杂的联系,又要指出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美国成长小说和经典成长小说之间具体有什么不同?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超越并更好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从主题上来看,自主和社会化这对张力在经典和美国成长小说中都存在,但其结果却不同:在前者中它得到了化解,而在后者中却依然存在。例如,德国和英国的成长小说都设法使个人和他周围的世界达成某种调和,而信奉个人的能力和完整的美国人当然不会相信被社会同化的观念。这种不同的结果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说这种小说的变化和发展。正如哈丁(James Hardin)所指出的:“‘大多数成长小说的定义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调和看作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定义全然排除了现代小说,因为现代小说很少表现这种人为的结局,其‘结局是开放的’、不明朗的、相对的。”[6](P6)这种变化代表和体现着历史和文化的两极——传统和现代性。如果说经典成长小说表现了前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那么现当代成长小说则反映了资本主义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工作”在《维廉·麦斯特》中的意象中看出:“所有的农民和手艺人都可望被提升为艺术家,”他们生产“‘和谐的产品’:回归其创造者的产品,因而容许人们对自己活动的全面再占有。”而商人生产商品:“只有在市场交换中才有价值的产品,它们永远脱离了其生产者。”非资本主义的工作,作为一个“封闭的循环”,“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黏合工具,不生产商品,只生产‘和谐产品’、‘联系’。它给个人以家园,强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联系。这种工作总是具体的,它不要求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失去天然情趣的生产者,而针对具体的个人,达到强调个人特性的目的”。[7](P29)这种以“和谐”为特征的工作似乎必然会导致“个人的成长”。相比之下,“严格遵守经济规律,必然漠视个体工人的主观愿望的”资本主义工作将会产生抽象、失去天然情趣和异化的个体。经典“成长小说中的工作使外部和内部、心灵中‘最佳和最隐秘’的部分和生活中‘共有的’的一面之间具有连续性”。[7](P30)因此,“工作可能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形式。第一种——资本主义的工作——使人性退化。它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服务于……‘利润’之神;如此,它背叛的正是工作的本质……。[第二种是]美丽的、使人精神升华的、有助于成长的[工作]。”[7](P31)由此看来,“审美的和人性化的工作”同“工具性的和异化了的工作”之间的关系表明“‘国家的财富’和‘人的审美教育’之间呈反比例关系”。[7](P31)对个人潜能的片面挖掘可能会培育非凡之才,而为了人类的共同目标把所有个人的才能聚焦于一点,则可能会使人如虎添翼,人为地使人超越大自然所赋予的极限,从而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受益,但遭殃的却是个人,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完整而幸福的人”。经典成长小说无意于非凡之才,其目的在于刻画经过“锻造过的”完整而幸福的人。而弥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对个人才能的透支和片面开发以及对普遍目标的追求,必将使个体惨遭其祸,使之分裂、异化。这就是现代成长小说创作主体有意或无意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它的启示意义和审美价值也体现在这里。席勒指出:“只有美能赋予人以社会性格。只有审美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确立了和谐。”[7](P32)
二者的另一共同点是都隐含着一种自我牺牲精神,但旨趣不同:对经典成长小说来说,牺牲的是自我和个性,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化的需要,维持社会稳定和帮助主人公融入社会;而对现代成长小说而言,它意味着个人幸福的牺牲,目的是为了改变社会,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的自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却带来了别样的艺术和社会效果:经典成长小说“鼓励读者远离物质和历史的世界而进入艺术的世界”,“使自己越来越脱离现实主义,其结尾越来越带有强烈的幻想和童话的色彩,”而现代成长小说再现的是“从艺术到历史,从文学到生活的走向”,“让读者回归可能会发生真正政治变化的历史现实中”。[8](P147-148)如果说前者的主人公是幸福的,那么这种“幸福是自由的对立面,是变化的终结。它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和社会之间所有冲突的终结;一切进一步变化的欲望都熄灭了”。[7](P23)它是对束缚的愉快接受。“事实上,只有在故事(历史)和思想(理想)的交叉点上成长小说才会产生具有自身特色的含义,其意义是经由艺术的操纵而又往往得不到解决的张力衍生而来。”[9](P94)美国成长小说体现的就是这种意义。
成长小说都坚持认识论和反映论,既反映客观现实,又反映人的内在本质。但经典成长小说侧重于前者,即更强调反映客观现实,并探讨人和社会如何达到统一,现实主义成分更浓;(注:这是从创作主体的主观愿望上来说的,但实际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美国成长小说侧重于后者,它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重墨描写的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痛苦和绝望。如果把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比作是一个旅程的话,那么,前者从总体上来说走过的是一个愉快的旅程,尽管主人公也会遭遇各种挫折,但这种曲折同最后的喜剧性结局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国成长小说主人公经历的则是一次痛苦的旅程,虽然主人公也会有愉快的经历,甚至有被社会接纳的可能性,但主人公们的精神是痛苦的,他们拒绝被社会同化,要么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要么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不确定性是其特征,因此美国成长小说具有现代主义的性质,甚至包含着后现代性。
在处理个人同社会的矛盾方面,经典成长小说代表着传统理性主义,在表现个人意识时多倾向于同社会、大众的融合性;而现代成长小说则以反传统理性主义为特征,更注重表现个人同社会、大众的背逆性。对自我的执著是个性觉醒的表现,但过度地张扬自我必然与现实脱节,产生异化感、流浪感,带来精神痛苦。人只有抛弃极端的自我,适当地抑制个性,才能融入社会,因为个体的人毕竟要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
经典和美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性格特点、人生际遇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者的主人公渴望了解自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后者的主人公要表现自我,视自我实现为个人幸福的条件。“最显著的差异之一就在于主体同周围社会之间的关系。经典成长小说赞美通过个人内在的独特自我和整个社会中外在的共同自我之间的不断交互作用而获得完整自我。经典成长小说中这种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双重关系,但由于经典成长小说是前进式的,目的在于消解差异,所以这种关系通常是以辩证的方式构建的。”其典型的主题是妥协。“这种妥协也可以被视为尚未同化和流放的终结”,是回归家庭和社会。它标志着分裂主体的结束。[8](P29)最后他们从虚幻的理想中解放出来;而美国崇尚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至上,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行事,竭力表现出个人与众不同,因此,美国成长小说中的主体无法将融入社会作为成熟的最终奖赏。“成为你自己”几乎成了他们不懈追求理想的口号。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明确地感受到来自社会、机构和心理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影响着他们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而这种压力在经典成长小说中却鲜有描述,主人公成长的阻力往往来自他们自身的缺陷。在人生际遇上,经典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能够享受到处于上流社会的资产阶级家庭所提供的教育,并能得到父母的支持,去从事父辈的职业,如维廉的父亲要求他继承父业从商,尽管维廉着眼于更宽广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商业,亦即全面探究人生的意义。而美国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往往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要么被家庭抛弃(如哈克,他根本就是个弃儿,这似乎继承了英国成长小说的传统),要么父母忽视了他们教育子女的义务(如霍尔顿,他除了不断得到父亲要惩罚他的威胁之外,小说中找不到任何父母对其进行人生教育的线索)。这是他们感到苦恼和在生活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思”和“行”在成长小说中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是对智慧的全面概括。通过“思”来检讨“行”,反之亦然。人们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了解自己。“你是谁”不在于你想到了些什么,更多地要看你做了些什么。成长小说就是“当主人公成长到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社会为中心,从而开始形成真正自我时的故事”。[10](P118)人文主义是这类小说的基本态度,它“要求行与思、改变世界的愿望和完全被社会所接纳之间达到一种平衡”。[11](P114)这种思和行的平衡更多地体现的是经典成长小说的特征,而在20世纪的美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思往往多于行,他们似乎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在小说结构和表达方式上,经典成长小说比美国成长小说更忠实于情节、现实,主人公的成长呈明晰的线性发展轨迹,[9](P98)小说的最后一页是一个开端,因为主人公表明自己已为生活作好了准备。正因为如此,许多经典成长小说都有续集,如歌德的《学习时代》之后有《漫游时代》。现代成长小说淡化情节,对人类挚爱的预设提出批评。成长的意义在于过程本身,它为探索的旅程而写,而不是为了旅程所指向的幸福结局,因此它关注经验,而排斥任何结论。例如,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结尾部分,汤姆和哈克费尽周折要释放吉姆,结果读者发现他们要解放的原来是一个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借此过过冒险的瘾,”至少对汤姆来说是这样(第42章)。
“如果经典和现代成长小说之间主要的主题差异之一在于个人和他或她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文本的构建就提供了主要的结构差异。”[8](P29)同经典成长小说线性的时间结构形成对照的是,现代成长小说呈现出“循环结构”(a circular structure),“它通过对隐含在经典成长小说中的起因论和目的论的质疑从两端把结构打开。”“这种结构设计还给主体增加了第二重或双重视角,使主体沉溺于对话或双重状态。这种结构差异进一步突出了经典和现代成长小说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异,其主体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行事者这样的双重主体。”[8](P29-30)与此相关的是叙事视角。经典成长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不仅停留在他……所叙述的事件的外部,而且在事件的顶部。视点来自上部。”[8](P31)现代成长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事,“排除的正是这样一种话语观念,即它对其讨论的主体既能保持客观又能置身于外,”以便叙述者和主人公能呈现自己的体验,这样就能再现“他们所谴责的事物。”[8](P30)这种叙述视角能使读者感同身受,深刻体味到主人公的精神苦闷。
三
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人应该享受充分的自由,体现自身的价值,张扬个性,其尊严应该得到维护。但像许多事物一样,人的际遇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自主的、特里独行的个体存在,具有自由创造价值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他人、社会对自己的束缚、压抑及其所带来的自由异化,这就是人的自由的宿命。而成长小说中带有宗教色彩的悖论是普遍存在的,主人公往往通过“失”而有所“得”;从堕落中得到净化;向这个世界“诀别”而后获得重生;要长大成人必再做一回孩童。[12](P146)在现代成长小说中,人的自由和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坍塌了。有人指出:“我们对青少年时期还没有可靠的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存在的理由在于把心灵分解成相对的‘力量’——而青少年时期和小说却有着相反的任务,即把个人性格相冲突的特征融合、至少是聚合在一起。换言之,因为心理分析总是把目光投射到自我之外——而成长小说则试图构建自我,并且使之成为它本身结构无可争辩的中心。”[7](P10-11)这种观点对于分析经典成长小说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考察的视野显然没有覆及当代成长小说,也没有投射到成长小说在美国的演变——美国成长小说。经典成长小说中的“自我”诚然发挥着它自身独特的重要作用——调节和制约本我和超我,把二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使主人公走向妥协,融入社会,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长小说实现了它对“自我”的构建。但美国成长小说则不然,其主人公在本我的驱动下,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断地追求自由和一些自身难以企及的目标。同时,他又受到超我的左右,实际上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以“道德原则”为准绳,本我时时受到遏制。在现当代社会中,这两股暗流势均力敌,来势异常凶猛,不断地冲撞着自我,使之不堪其负,最终导致自我的崩溃,丧失了它原有的调节功能,使“现实原则”无法得到贯彻。自我的这种分裂状态导致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坍塌,因此美国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和现实达成妥协,更不用说融入社会了。他们往往最终选择逃避,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这也就是美国成长小说在结构上常常表现为开放性的结局的原因之一。
自我中心位置的确立是同社会化的主题相关联的,而社会化的前提就是要按照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行事,和社会达成某种妥协。正是这特别有效的妥协才使自我发挥着它特有的功能。经典成长小说中所描摹的这种“现实”被称之为“常态”(normality)。而“常态并不是被看作一个有意义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一个无标记的实体(unmarked entity)”。它在自我否定中获得意义,即它的意义不在自身,而在自身之外。[7](P11)经典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是通过否定自我、扼杀个性,成为“无标记”的“正常人”从而获得“幸福”。这同美国成长小说不同。美国人向来标榜个人主义至上,信奉个人的权力和完整,因此,同社会化或被社会所同化的理念是不相容的。这种排斥性构成了成长小说的当下魅力。“学习和成长过程的难以表述、以混乱和委琐感代替洞见,知和行、教育圈和其范围之外社会经验的普适性之间的关系等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都是拨动着当代学子心弦的主要问题。”[6](P4)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纠葛、成长过程中洞见的消逝和混沌、委琐感的弥漫是社会现实和人的精神状态在现代成长小说中的反映,这些已构成了当下文化上的一个独特景观,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共鸣。“文化是一种责任,其理想的目标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只有永恒的追求。因为停顿就意味着倒退。文化是一种永远向前的发展,是对知识和完美的追寻,对那些勤奋努力的人来说,它像生活本身一样永无止尽。”[4](P26-27)这种永无止尽的追求迎合了美国人的文化心态,是现代成长小说在美国深入人心的精神土壤。
文学同文化及社会环境是无法隔离开来的。后者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得以产生的基础,而且决定着它的发展方向。“19世纪成长小说主人公的视角明白无误地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这一变化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在主题上,逐渐退隐到人的少年时代;在结构上,转向采用记忆的心理时间记录的形式……;在人物的形象上,由流浪汉变成忏悔者。”[13](P127)这一变化的产生至少有两个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同19世纪逐渐增长的异化感有关;其次是“心理人”的出现,其日益增长的内心和自我意识的负担同社会、经济因素一道促使他同周围环境疏离。19世纪这种将现实逐渐内化或心理化的倾向几乎可以追溯到整个思想领域。在哲学上以黑格尔到尼采的发展为标志;在神学上,从施莱艾尔马赫的基督教新教神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上帝逐渐被剥去神秘的面纱;在小说中,随着上帝般的叙述者的“死亡”,代之而起的是患有神经质的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病态心理投射到书中。在这种背景下,小说家为了忠实地记录现实的日益内化秩序,他们不得不相应地塑造那些敏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物。迈尔斯曾对20世纪的成长小说作过这样的描述:“呈现在现代作家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迈出最后一步,进入完全崩溃、精神错乱的世界,……在那里一切现实都有问题;要么迈出不太激进的一步,把整个小说带到自嘲这个可以拯救的平台——换言之,去创作反成长小说,戏仿这类小说的两个分支,流浪汉小说和忏悔小说。第二种途径在20世纪成长小说中最常见。”[13](P127)在现代成长小说或“反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并没有得到“幸福”,也没有为未来作好切实的准备。福克纳《熊》中的艾萨克放弃了罪恶的祖传家业,但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只是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最后躺在精神病院里,对未来毫无打算,至于未来要做些什么,他认为这是个可笑的问题。同经典成长小说中那些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比,他们仍是孩子,并没有长大成人。
同那些仍未长大的孩子一样,成长小说也在成长过程中。只要人们仍关注成长这一主题,它就只会变化,甚至变异,但永远也不会老,更不会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