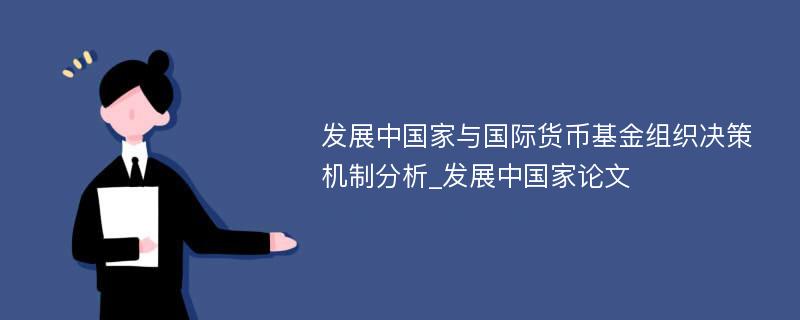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机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货币基金论文,机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近几年的货币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看,货币金融权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武力征服更为严重和深远。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向纵深推进,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除了发展中国家本身脆弱的金融部门这一内部因素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其超强的货币金融力量,控制和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的决策,通过IMF干预、操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走势是重要的外部原因。要使货币金融主权不受或少受干预,金融安全不受或少受威胁,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摆脱在IMF决策中的边缘地位,争取在国际货币金融事务中的平等参与和决策权。因此,研究IMF的决策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控制自己的货币金融主权、保障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IMF决策机制中的不平等
IMF的决策规则有加权投票制、多数表决制和协商一致,这三种决策规则都存在着不平等。
(一)加权投票制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中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1]。由于当时英美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2]。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谈判的结果,每个胁,自身在国际货币事务决策中受到排挤。
自1963年开始,发展中国家在IMF中开始了争取平等参与和决策权的斗争。在1963年基金组织年会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以后的多次年会上,发展中国家反复强调在国际清偿问题上应重视IMF的职能。到6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出参与决策,并得到77国集团和联合国贸发会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的支持。1967年,77国集团第一次部长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该宪章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一开始起就参加有关国际货币改革的讨论(注:See The Charter of Algiers,adopted at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77 on 24October 1967,as reproduced in Peter A.Mutharika,Comp.and ed.op.cit.,Vol.4,2421.)。除在各种场合对发达国家的排斥做法进行抨击并宣示自己的主张和强烈要求外,发展中国家在组织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性措施。在1971年11月举行的第2次77国集团部长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表示:“由一个有限国家集团在基金组织之外寻求做出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有关国际货币制度未来的重大决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注:The Declaration and Principle of the Action Programme of Lima,op.cit.,2435.)。根据代表们的要求,1972年1月24国集团宣布成立,从而标志着IMF中南北集团的划分。
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明确要求主要有两个,一是确认IMF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的权威和职能,二是要求参与决策。经过努力,这两方面的主张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认。首先是10国集团做出反应,表示愿意开放决策程序,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在国际清偿问题讨论后期和随后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SDRs)的讨论中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参与。正如美国一董事在1973年IMF年会上所言:“贸易和货币问题主要在相对封闭的工业国家讨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注:IMF,Summary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Washington DC,1973,57,hereafter as Summary Proceedings,19-.)。在1975年联合国第七届特别联大上美国进一步保证要让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货币事务并享有发言权(注:GAOR 7th Special Session A/PV 2327,1 September 1975,5,para.47.)。在组织建设方面,在24国集团的积极倡导下,基金理事会于1972年通过决议,专门建立了20国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南北双方代表人数相等。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10国集团在IMF中垄断地位的结束。
(二)现阶段要求实质的决策权的努力及成效
有了参与权并不一定享有平等决策权,7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开始在IMF中开展了争取平等决策权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在实权机构的代表人数、投票权的分配、多数表决事项等问题。
早在1970年IMF年会上发展中国家就表达了它们的愿望,印度董事的发言反映了它们的要求:“我们认为,整个管理结构、配额分配和投票权都需要重新和彻底进行审查,必须明确减少经济实力的份量,并反映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注:IMF,Summary Proceeding of the Sixte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Washington DC,1973,57,hereafter as Summary Proceedings,19-.)1972年24国集团成立以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并要求对配额进行调整。1974年,OPEC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在IMF中取得了较多的份额,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它们要求重新确定配额分配的标准,并要求增加基本投票权。由于在改革投票权分配上的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基本投票权至今未进行调整;份额分配方面,它们要求明确份额分配的标准,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能力、提供原材料等因素,但至今没有实现。在表决制度方面,如前所述,目前仍是发达国家占绝对控制权。唯一取得较大成效的是增加在有实权的决策机构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人数。在1972年成立的20国委员会、1974年成立的临时委员会中南北双方席位都相同。尽管席位相同并不表明决策权相同,但“出席会议的代表的人数能弥补国家相对弱小的不足或能提供辅助力量[10]。
三、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可能途径及其困境
以上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IMF决策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要从根本上改革IMF的决策体制,可以有以下思路:
(一)集团投票制
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国际组织的决策应采取一国一票和多数表决制,但这在业务性国际经济组织中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小国获得大大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投票权毫无价值[3](125~126);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根深蒂固的观念也难以改变。在发达国家心目中,此类组织就是股份公司,应当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掌握,如果借款国想实行多数控制,贷款国就会撤回它们的投资。发展中国家想改变投票结构,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对机构认缴的份额,因为投票权与其认缴的份额有关[11]。那么较现实的选择应当是集团投票制。集团投票制萌芽于IMF中,成长于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简称MIGA)中[12]。它的基本思路是:投票权仍然分为基本票和加权票两部分,但两种票的分配结果应使南北两大类集团的投票权基本相同,而不是寻求各国投票权相等。但要实现这一制度,面临着几个基本问题,即增加基本票、两大类集团成员应基本保持不变、集团内部团结一致。目前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存在困难,就增加基本票而言,困难很大;两大类集团成员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
(二)增加基本票
基金组织的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基本投票权却从未改变,如基金的份额由1945年的75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2010亿美元,相应地基本投票权也应增加。基本投票权的调整要求对IMF协定条款进行修订,但IMF协定规定,要修改协定条款需要85%特别多数通过。因此,没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同意,将无济于事。
(三)调整并明确份额分配标准
如前所述,IMF配额分配标准主要是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这种计算方法对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最为有利。因此,在改革时可考虑将人口因素加进去。调整份额分配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份额的增强可能会对IMF的清偿能力造成困难,因为它们认购份额都是以只有很少需求的软币支付的。因此,增加份额也面临较大困难。
四、实现平等参与和决策权的战略对策
国际货币金融事务决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经济实力起着决定作用。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斗争,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发达国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境。发达国家的意愿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左右的,因此,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在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应当逆水行舟,知难而进,积极参与,争取发挥更大的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展中国家应从以下方面去努力:
(一)明确所要达到的目标
平等参与和决策权只是个笼统的概念,它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则需要细化,在IMF决策机制中,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扩大基本票、调整份额分配标准,就要明确基本票要扩大到多少,份额分配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以往发展中国家也曾提出过这类要求,但真正讨论问题时,它们却感到茫然。
(二)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
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抗衡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各国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它们失去了以往的斗志,而且受各自的利益驱动,内部也逐渐失去凝聚力,事实证明,平等参与和决策权的实现靠某个发展中国家“单打独斗”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协调一致。在这方面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它们在根本问题上能够协调,而且协调机制非常完善,这主要包括西方7国协调机制和OECD协调机制。
应当看到,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又重新认识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重要性,而且频繁地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状况,并开始提高对发达国家说话的声音。2000年2月12日~19日第10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为全球各国的发展服务上,会议通过了《行动纲领》和《曼谷宣言》,并呼吁发达国家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要求[13]。77国集团第一次首脑会议于2000年4月开幕,呼吁公平的全球经济,要求WTO不要再向穷国提出如此之多的“过份和代价昂贵的要求”。古巴主席卡斯特罗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讲话时,要求“毁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坚持团结与合作,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14]。
(三)借助外界力量,增强决策的透明度
在货币金融体制的决策中存在各种暗箱操作,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外界监督和约束。为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可将IMF活动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向非政府组织公开[15]。二是在IMF中增加私人组织或非官方组织的代表,增加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和信任度。在这方面,保护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体制革新值得参考: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允许私人发展和环境组织在保护臭氧层的多边基金的执行委员会中有正式的观察员身份,这使得执行委员会的决策有透明度,并使外界对其有信心[3](127)。
(四)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IFM中居于主导和控制地位,与该组织的决策机制关系不是很大,不平衡的决策机制只是一种结果,背后的实质才是它们的“气粗”、“压贫”的真正原因,即“财大”、“富裕”。加权投票制不合理只是一种表现,发达国家当然知道这种机制不合理,可它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不合理。WTO中实行一国一票、多数表决和协商一致,可它们仍然能够在WTO中称王称霸,原因何在?因为它们可以这样做,它们能够这样做。因此,努力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决策机制终究只是一种手段,要想在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决策中举足轻重,根本的途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战后的欧洲和日本曾经满目疮痍,如今已与美国三分天下,靠的是经济实力。因此,靠发达国家的善意、施舍、援助来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