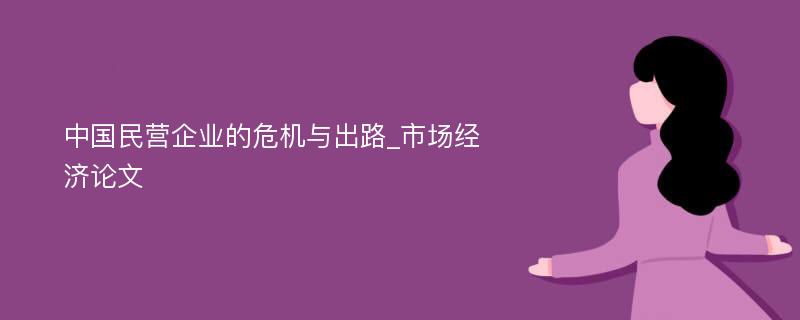
中国民企的危机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企论文,中国论文,出路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想而知,制度创新其实是人心工程,变规则即变人心。除非让人们一起变得更聪明一些,让人们一起认同新的规范,否则制度创新很难成功。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其实在于改变制度中的人的共同信念,正所谓改革制度就是改革人心,变人心即变规则,变规则即变天下。
对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否则制度变革不能取得理想成效的结论,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伟大的亚当·斯密就讲得清清楚楚。他曾用这样优美的论述来做文章的结语:“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执法者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他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均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中国民营企业的变革会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呢,还是苦不堪言的抵牾?显然,仅仅根据正规制度来下断言为时过早。文化是制度的隐件,制度是文化的显件。尽管政府可以寻求从宪法上,从正规制度上明确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支持,对民营企业财富的肯定和保护,但是,社会环境、民众态度与认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此,要理解民营企业的发展处境,展望其发展前景,还必须考察与民营企业生存状态相关的隐性环境,尤其是注意其与正规显性制度变化不同之蛛丝马迹。
企业家变成危险职业暴露民企危机生存状态
2003年,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个不幸的年份,许多企业家死于非命或遭遇困境。在他们的身后,有一个长长的名单:李海仓被害,刘恩谦被杀,乔金岭自杀,周正毅落马,杨斌判刑,胡志标坐牢,刘波“外逃”,仰融落魄美国,艾克拉木神秘“蒸发”、孙大午被“冤”……
让我们从李海仓说起。2003年1月22日,山西钢铁大王李海仓不幸遇害。有人说是一次非正常状态下的非理性的突发事件,其实未必见得,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接下来的一系列同样骇人听闻的富豪丧命事件了:
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家乡温州的自家门口遭歹徒袭击,身中14刀当即身亡。7名嫌疑人随即被抓,其缘起是同乡争市场;
2003年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自己的家中被劫杀。刘恩谦死后坊间出现了3种他杀的版本,结果却不确定;
2003年9月7日,以1.2亿美元的资产,排2002年《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58位,有河南首富之称的上市公司黄河旋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乔金岭突然自杀身亡,自杀原因令人费解。
在2003年这一年当中,企业家意外死亡的名单当中,还有绍兴纺织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的丁遐、包头的李刚等。
以上民营企业家的意外死亡,所遭遇的表面上都是突发的恶性事件,但其背后应该说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越来越多人开始感到,尽管我们的政策和法律越来越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但民营企业家事实上已变成危险职业,民营企业事实上已面临中国创富时代的生存危机。
面对危机状态,民营企业家们难以心安,于是,有了中国资本加速外逃的一幕。据估计,中国每年的资本外逃达400~500亿美元之多,几乎抵消了中国全部的外资引进。其实,中国发展机会这么好,是全世界的亮点,要不是有某些顾虑,这些民营企业家决不会“三十六计走为上”,决不会在事业辉煌的中途自废武功。中国许多富人之所以携资外逃,显然是出自于对生存状态的极端绝望,对危机的极度恐惧,对于中国社会的极度不信任。
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并不仅关乎他们自己,也与全体国民密切相关。因为,在一个社会里,企业家才是财富增长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果企业的状态正常,社会就有很强的生产力;如果企业被搞得七零八落,这个社会生产力便不会得到保护。而企业的领头人便是企业家,如果我们缺少企业家这样的人物,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便会受到巨大的破坏。
中国民营企业家怎么啦?当我们提这个问题时,我们其实也是在询问: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怎么啦?中国怎么啦?中国人怎么啦?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怎么啦?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引人深思的。我们必须关注企业家,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危机状态。
跛足的经济改革: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缺失
民营企业家成为危险职业,民营企业面临险境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的是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的冲突,反映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重大缺陷,反映出整个中国文化在商业发展方面的生存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进步就在于,放弃政治斗争,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实现了社会资源从分配型向生产型、由公平型向效率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进而以对民营企业家的激励为动力,以对外资的引进为动力,以对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创新为动力,迅速增长了财富和国力。
但是,这一改革现在看来,至少存在着三点明显的不足,一是在财富的积累和发展上缺乏完善的游戏规则,二是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三是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建构。
由于缺乏完善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游戏规则和秩序,我们看到,没有规则的游戏,只能在少数人中玩,并游离法律之外,市场变成了江湖。从“首骗首富”牟其中、“明星富豪”刘晓庆、“神秘富豪”仰融、“赌命富豪”杨斌,到“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规则的陷阱搞垮了一大批人。
最明显的是孙大午,由此足以让世人看清“问题制度”是如何将好人变成罪人,将企业家变成“问题富豪”的。孙大午的企业本是一个优良的企业、讲信用企业,他本人也是一个形同苦行僧的富豪,可是竟贷款无门。不愿“同流合污”的孙大午,在企业急需资金的情况下,不得不另寻“出路”,从而成为现行制度下的罪人。被逼无奈的孙大午,留下的是对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以及更多制度的冷思考。
民营企业的生态状态还与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关。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但有一点非常确定,那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大量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分享到足够的繁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即达至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而近两年来这一趋势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对于民众来说,耳闻目睹富人香车宝马美女,升官发财移民,再对照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其剥夺感、耻辱感、不平感定然更胜一筹。
国际上认为,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便随时有断裂和崩溃的可能,这可能是中国富豪被杀的一个社会背景。相比之下,我们过去可能更多地注重了公平,更多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了政府的社会责任,忽视收入分配的调节,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将弱势群体逼入绝境,从而产生出社会贫富对立以及富豪在贫穷的海洋中成为孤岛的险境。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过于注重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的创新,忽视了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建设,过于注重显性制度的推进和建设,忽视了隐性制度的改良和变革,致使改革到一定程度,因缺乏社会道德资源的支撑,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明显。
中国改革奉行的是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会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放在后面,然后在付出代价后不得已再予以弥补。就像是一个由长短不一的木板捆成的木桶,每次总是将最短的板补上,补完后却又发现,总是还有最短的木板。
事实上,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经显示出某种尴尬。一是我们引入市场经济,并且承认人的自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在市场上,人的自利性呼唤出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从毒大米、毒酒、毒辣椒到毒药,从股份公司的做假账到基金黑幕,从官商勾结到民营企业家被竞争对手所杀,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打工妹赖账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员工集体“辞职”,可以说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及。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决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坏的市场经济。
其实,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固然有激励人们不偷懒的好处,但市场并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在交易中出现坑蒙拐骗行为,如果再加上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则“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都会出来,这个市场就可能失效。另外,市场经济还存在着所谓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彼此伤害对方是因为担心对方会伤害自己。仅靠市场本身显然无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效果。
在市场之外的财富层面:20多年前,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心理和文化在当时承认了这句话的合理性。现在,一部分已经富了起来,但是,怎么看待先富起来的人们成了一个难题。总体上,一种疑富和仇富的心态在蔓延。2002年,政府发起“税收风暴”,让富人们心惊肉跳;知识分子则对富人投以怀疑乃至审判的眼光;至于穷人,则用仇恨的白眼看着先富起来的人们。更为要命的是,中国人似乎仍较少明白,富人与穷人共有一个家园,抽刀断水水更流,杀富济贫贫更贫,杀富济贫和爱走极端的文化容易让这个国家的贫富矛盾变得激化。
显然,如何建设市场伦理,如何在经济追求外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社会目标,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手段致富,富起来的人该如何看待和消费其财富,社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富人,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如何,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也都不是市场本身能够告诉我们的,而需要通过一整套的“财富伦理”来予以规范。
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所以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并且能够长治久安。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地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大力建设和弘扬一整套与中国市场经济变革方向一致、能够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效果的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
我们以为,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信仰和道德之上,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突然倒塌,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社会心态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民政治,也不知道仅仅建立在物欲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而朝畸形的方向发展。
“败坏的人心不可能生产出优质产品,也不可能成为财富的保障”。以道德而不是以物欲为取向的市场经济新时代在中国的出现显然为时尚早,因此文化重建的道路也就格外漫长。
有人寄希望通过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成为财富的根本保障。可是,如果社会缺少一种博爱心态,没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就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写在宪法上,又有什么用呢?记得有一位地方长官曾这样对我说:“宪法?别跟我谈什么宪法,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显然,虽有正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发展,有法律和党的大会决议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但是,伦理和民心也许更
为重要,隐性制度将决定着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可能性空间。说到底,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破题,但只有进入文化(道德)重建的层面,才算是进入正题了!
出路:寻求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的同建与和谐
在做出上面的分析后,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危机生态状态的道路应该变得非常清晰,其根本点就在于寻求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的同建与和谐。其内容,又包括三个主要的层面:
一是加快市场经济的变革,完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和秩序,减少问题制度,使好人能够在阳光下赚取利润,而不至于被制度挤扁或被转轨加快后的列车甩下。
二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不再以单一的GDP追求为中心,而是寻求平衡发展,注重收入调节,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运动轨迹呈现倒U型,如果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中国的话,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可能正处于U型的底部。不要指望这种状况会自己从U字的底部爬上来,因为世上本没有免费的午餐。
苏格拉底说过,有选择才有人生,中国目前正面临选择。因为地区差异的加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使社会发展的总体均衡丧失,短期内会降低经济的效率,长期内则会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社会的长远和全面发展。
三就是要大力推进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的建设,要真正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宗教自由,要通过对国外先进文化的引进,对国内优秀文化的继承,创造性地建设出能够与中国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律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让市场经济建立在信仰与道德的坚实基础上,而不是金钱崇拜的基础上。
其中,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是财富的历史问题。我们相信,只有理性和建设性地告别过去,才能真正走向未来。
如果光是追究“问题富豪”,则“问题富豪”会越来越多,反而葬送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前程。如果倡导阳光富豪,并且建设制度环境,则好的富豪越来越多,最终改变富豪的成色。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前途所在,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就是改造中国,就是打造中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