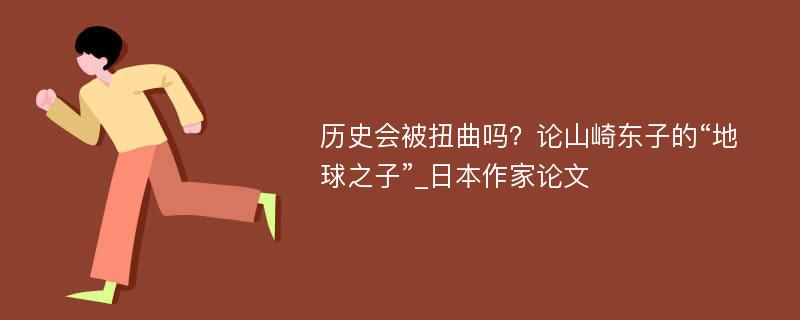
历史岂容歪曲?——评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子论文,大地论文,历史论文,评山崎丰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出版了以描写战后日本留华孤儿为主题的小说《大地之子》。山崎氏为写这部小说,曾在1985年、1986年多次采访我和为养育我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养父。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读到这部小说。直到1997年去日本探望病危的生父时,才从书店里买到此书。读了此书,令我大失所望,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山崎氏不是以对中国人民真正友好的态度和对战争孤儿的深刻同情来写这部小说,而是严重歪曲历史,嘲弄成千上万的战争孤儿。作为一个普通的战争孤儿,面对这种事态,我无法保持沉默。
一
我在接受山崎丰子采访时,还以为她是位有名的进步作家。后来我了解到,山崎氏的名气大半并非来自文学创作的成就,而是因一贯剽窃而出名。去年12月在东京,一位日本友人对我说:“我为日本有山崎丰子这样的骗子而羞耻。”前年,日本筑波大学远藤誉教授向法庭指控她严重剽窃其纪实文学《卡子》的主要内容。这已是她第四次因剽窃、侵权而被起诉。
我很难想象品质这样恶劣的作家能够在自己的小说中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本文着重谈谈《大地之子》对中国社会现实历史和日本留华孤儿生活、思想轨迹的严重歪曲,以正视听。
《大地之子》的基本人物设计,单从形式上看,与我的情况相似:主人公陆一心的养父陆德志也是乡村小学教师;其生父松本耕次和我的生父原谨吾一样,也是长野县信浓开拓团成员;主人公的学历也和我一样,经历了小学、初高中、大学,所不同的,我学的是文科,他学的是工科。
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采用了我和养父提供的若干素材。例如,我年幼时有一次,养父带我到河边钓鱼,我拿了农民在河上设置的捕鱼器具(农民称之为“鱼亮子”)上捕获的鱼,因此受到养父的批评。山崎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进了小说(见该书文春文库版(一),第171 页)。
但是,从《大地之子》全书的内容和主题来看,对这些真实素材的采用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而从全局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山崎对事实的歪曲和随意编造。
山崎氏盗用远藤誉的报告文学《卡子》中的大量素材,在《大地之子》中用相当的篇幅来编造陆德志、陆一心等以围困长春为背景的故事,不可能不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为解脱这种矛盾,甚至不惜丑化日本孤儿的中国养父。例如,在走出“卡子”的途中,为饥饿所迫的陆德志,居然不顾为人师表的教师应有的道德规范,挥舞木棒对骨瘦如柴的路人拦路抢劫!(见该书文春文库版(一),第150页)试想, 即使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即使是为了妻子儿女包括养子,一个教师做出这样的事,也很难说是可以原谅的吧?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在生与死的残酷搏斗中,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自己亲族的生存;而这样一来,在无比艰难的境遇中收养日本无辜的遗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养父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这一类的胡编乱造还都是些小的败笔。更大的败笔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和中日合作的“宝华制铁”的描写。
小说的开篇是以“文化大革命”中主人公陆一心被批斗而登场的。实质的意味是想让读者相信这样一种神话:陆一心只是因为本来是日本人而挨整。这样的神话可能只对仅仅从报刊上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日本人才能发生作用。而这样做不是对广大的日本公众的愚弄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傍着前总书记胡耀邦特许的通行证而在中国大陆走南闯北的山崎氏,居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一窍不通。如果胡耀邦总书记在天有灵,有幸拜读《大地之子》,不是也会大失所望吗?
“文化大革命”虽然曾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因此各界某些人氏,包括学术上的、科学技术上的权威受到冲击,但从实质的意义上说,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陆一心者,按小说的构思,既不属于学术技术权威,当时又不曾进入“党内”,更算不上“当权派”,仅仅因为是日本人就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判刑十五年,流放到宁夏劳改,这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也包括对于像鄙人这样的日本孤儿来说,是真正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文革”那样的混乱、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任何人,包括普通的中国人,也包括外国血统(例如日本血统)的中国籍普通公民,都可能蒙受冤情而遭迫害。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而不具有必然性。从现实性来说,一个居留中国的日本孤儿,特别是在尚未判明其日本的亲族关系的场合,仅仅因为他是日本后裔而挨整,是不大可能的。而从实际的情况来说,在“文革”中受到冷遇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乃至受到迫害的日本孤儿,也不是没有。但问题在于这是不是问题的本质方面,被迫害者究竟是为什么而受迫害。据我所知,在“文革”中受牵连者,不论其是中国血统者抑或是日本血统者,一般而言,不外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和所谓“走资派”有这样那样的牵连;其二,由于造反派分化成对立的派别而有意无意陷入所谓“派性”的矛盾;其三,牵扯某种利害冲突。而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挨整,能说是因为他是日本人而挨整吗?
山崎氏不分析这些具体情况,而笼统地宣布她的主人公只是因为出身于日本血统关系而无故受到那样耸人听闻的迫害,究竟是要给日本的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呢?是不是要以此来加剧日本人对中国的无端仇恨呢?
山崎丰子是出于什么动机来编造这样违背历史逻辑的离奇故事?后来,我在她的《〈大地之子〉和我》一书中,发现了她不打自招的自供词。她承认,她之所以在《大地之子》的第一回《小日本鬼子》中描写“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如何吸引读者的考虑,也就是为了挑起读者的好奇心。她说,除了写“文革”,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见该书第22页)原来,山崎写《大地之子》、根本不是出于对战争孤儿的同情,也不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理解,而是为了挑起日本读者的好奇心。为此,竟不惜歪曲历史来欺骗和愚弄日本的广大公众。这难道就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艺术良心吗?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凡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读一读《大地之子》,都不会不感到,山崎氏并没有也没有想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亿万群众卷进去的动乱。这本身已能说明,这场动乱的爆发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亿万人卷入这场动乱,并非仅仅出于对于领袖的狂热崇拜,从事情的实质来说,群众的造反是出于对日益滋长的党内和社会上阴暗面的强烈不满。问题在于由于“左”的路线长期发展,当时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严重错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很成问题,导致斗争的扩大化,打击面过宽,结果被少数邪恶势力所利用,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很多无辜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也正因此,群众和干部中有不少人是持反对和抵制态度的,明里暗里以各种方式对受迫害的人加以保护的事迹也是不少见的。而像《大地之子》所描写的,北京钢铁公司在“文革”开始不久,就把一个日本血统的一般技术人员揪出来批斗,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人加以抵制。群众和少数造反派头头一起,同仇敌忾,共同向陆一心开火,最后送去劳改。这样的事,我以为即使在当时也是有悖常理的。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有客观如实反映“文革”动乱的诚意,那就应当既毫不客气地暴露它的残酷的一面,也应敢于如实地表现动乱中群众对邪恶势力的抵制,对好人的保护。像“文革”这样的动乱,无疑会使一些人堕落,走向犯罪,成为凶恶残忍的无耻之徒。但是,无论在古今中外,任何动乱中,群众一下子都变成了坏蛋、乌合之众,这样的事也是不曾有的。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即将大学毕业。那时,我作为日本孤儿的出身已不是什么秘密。十年“文革”对我来说也不能说是“好运”,我所热爱的哲学事业中断了十余年,毕业分配、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我的养父也因收养我吃过苦头。但是,从本质上说,我的同班同学的命运也并不比我好,有些人可能还不如我。这十年之中,因我是日本孤儿而受迫害的危险因素,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如此幸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周围的老师、同学、领导、同事们对我的彻底了解和深深同情与理解,即使在他们知道我原来是日本孤儿以后,从内心也没有把我当成异邦后裔来看待。因此,即使有危险因素向我袭来,我也是会受到保护的。对于这种生活的真实,山崎氏贫困的理解力是绝对理解不了的。
二
《大地之子》的另一个巨大的败笔,是编造的松本耕次和松本胜男(陆一心)父子两人在互不相认的情况下,共同参与“建设钢铁公司日中合作项目”的神话。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上海,真可谓新式天方夜谭。
山崎氏为了制造出这种无比神奇的传奇故事,以达到石破天惊的效果,小说中预先埋下了种种“伏笔”:
生父:作为信浓开拓团成员的松本耕次,居然于1938年3 月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而又于1947年3月于东洋制铁八幡工场入社,1978年5月被派往中国上海,出任东洋制铁上海事务所长。
其子:作为与其生父断绝联系四十年的留华孤儿的松本胜男(陆一心),在读过小学、初中、高中后考入大连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钢铁公司(以“首钢”为原型),“文革”后又经工业部这个桥梁,调到上海“宝华制铁”。之后又有周折,最终之结局还是“宝华制铁”。
我知道,在日本这个岛国,二战期间,以所谓“开拓团”的名义移民到中国来的日本人,来自我的故乡长野县的最多,因为在当时,长野县是日本最贫困的地方,穷人最多的地区。在那一批接一批运送到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成员,平均的文化水准是怎样的?能够像松本耕次这样学过“东京高等制铁工业”的人,占信浓开拓团乃至长野县所有的开拓团的比率是多少?
同样的道理,在留华日本孤儿中,像我(或陆一心)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多少,其中所学专业能胜任钢铁冶炼专业的比率又有多少?
中国有句俗话:“无巧不成书。”《大地之子》所设计的这新天方夜谭,“巧”得真是太离奇了。无论是作为残留孤儿的陆一心,抑或是其生父的松本耕次,究竟哪一个能代表事情的本质和主流?他们在上海“宝华制铁”的合作项目中的偶然相遇,究竟能证明什么样的历史真理?究竟能给中日两国人民提供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大地之子》所给予我的整个印象,是南辕北辙。
而在这期间又发生了波折,在陆一心以重工业部成员的身分参与因公赴日出差访问中,又莫名其妙地遭受不白之冤,被发配至内蒙。而这个事件竟然是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下发生的,真是咄咄怪事。在1983年~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的;而当时陆一心因出国访问的被审查的“罪名”是所谓“泄密事件”,二者怎么就可以硬扯在一起呢?
《大地之子》力图把陆一心塑造成居留中国的日本孤儿的代表。然而,由陆一心所体现的战争孤儿的价值实现于何处呢?
小说第九章设计了这样的结局:
在“宝华制铁”公司高炉首次出铁水的一刻,“雷鸣般的掌声和巨大的欢呼声沸腾起来了……体验着最先进的大型高炉开始出铁的中方,极为感激、极度兴奋,以至有人哭泣起来。协力的日方也相互紧紧握手,分享着喜悦。在这一瞬间,中日双方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感、憎恶感消失了”。
在第十章,游览长江三峡的船上,松本耕次和陆一心父子二人又有这样的对话:
松本:“宝华钢铁公司的巨大成功真令人高兴,我也感到自豪。”
一心:“虽然经过了漫长的道路,但我为最终有了同日本一样最先进的钢铁公司而感激。正因为日本方面先生们的协力才有这样的结果。”
然而,为松本、陆一心们感到如此自豪的“宝华制铁”果真使中日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憎恶感烟消云散、一笔勾消了吗?在这种“合作”中,日本方面真的为中国提供了“最先进的”技术吗?
所谓“宝华制铁”的原型就是上海宝山钢铁公司。该公司的产品当时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呢?1997年7月下旬,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有这样的说法:我国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是钢铁生产大国,但不是钢铁生产强国。“因为我们没有一家钢铁工业在国际上排得上号,包括宝钢。宝钢的马口铁只能做饼干罐,茶叶罐,不能做易拉罐,质量还是比不上国外产品。”(参见《经贸导刊》第8期)
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交往中,历来都存在经济交往关系不平等(不平等交易)的问题。而号称“大地之子”的陆一心对这个不争的事实却毫无意识,却把“宝钢”说成是“同日本一样最先进的钢铁公司”而代表中方向日方表示“感激”。中国残留孤儿的应有价值就是如此吗?
不!这是对广大日本留华战争孤儿的亵渎。
成千上万的日本孤儿居留于中国,恐怕是数千年世界史上的极为罕见的历史事件。
这些孤儿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暴行的历史见证,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具有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历史价值和独特历史使命。
侵华战争给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受害最深,牺牲最大的还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最有承受力的民族。中国人民不但承受了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一直承担着战争的后果。这其中就包括为哺育和培育日本留华孤儿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因此,作为留华的日本孤儿,我们所最向往的,是尽我们最大努力,充分利用我们的特殊身分来增进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理解,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造福于子孙后代。我们所最担心的,是忘记那场历史悲剧。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那空前灾难的重演。
然而,《大地之子》所塑造的陆一心这个形象,自诩“这个大地的儿子”,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没有对日本某些当权势力改写教科书(把“侵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义愤,反而要不讲分寸地歌功颂德。这正是《大地之子》的又一不真实之处。
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对于已经返归日本定居的那些孤儿来说,还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仍然留在中国大陆的孤儿来说,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所留下的苦果,还没有吃完。就像日本侵略者半个世纪以前埋下的、至今还未清除的毒气弹等等还在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命一样,一场大规模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也许一个世纪也不能彻底清除。日本战争孤儿对此感受最深。就我来说,我们家七口人在1945年春随开拓团到黑龙江省宝清县。最终有四人陈尸在中国东北。我和生父于1985年才得以重逢,中间隔了整整四十年的空白。这是无法填补的空白,其中不仅有语言障碍,更有两种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背景上的障碍。1985年以后至今,我与生父有四次相逢,每一次都有相见面不能相识的感觉。这其中的痛苦是山崎氏所能理解的吗?我想,那些归国定居的日本孤儿,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其生活中的痛苦也不会次于我,甚至比我更多更重。
在我们的苦还没有吃完的时候,山崎又为我们奉献了《大地之子》这个苦果。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大地之子》及其在日本的走红,无疑是我们进一步透视日本社会的生动教材,我们将从中得到应有的教益。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谢山崎丰子。
三
《大地之子》的“后记”中一再强调,该书的取材,如果没有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对一个日本作家的理解和英断,是不可能的。据说,由于胡总书记的“理解和英断”,本来是“秘密主义、闭锁国家的中国的国家机关及对外国人未开放地区的农村、劳动改造所等”,包括美国司法视察团都被拒绝参观的劳动改善管理所,都得以对山崎氏开放。因而她感到自己是“侥幸”的。
山崎先生真是得天独厚。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又一些困惑就跟着来了:一个外国作家从劳改所等处究竟能得到多少和什么样的关于日本孤儿的有价值的信息?在中国的“劳动改造所”和拒绝美国司法视察团参观的劳动改造管理所中,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日本残留孤儿被“改造”呢?
《大地之子》还编造了“中南海”、“国务院”中的所谓“权力之争”。这又和留华日本孤儿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这无非是吊广大日本读者的胃口,迎合某些日本人的好奇心,乃至欺骗日本公众。
山崎在“后记”中还哀叹道:
“……1989年4月,胡耀邦氏突然逝世, 采访的大门又被牢牢地关闭了。美国朋友说:‘天安门事件以来,大概二十年之内自由主义国家的作家的采访成为不可能了。’我也有同感。 ”(文库版〔四〕, 第339页)山崎氏还说,如果不是胡耀邦前总书记去世, 这离奇的故事还将延伸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现在我们要问:实行这样的写作计划,究竟是尊重历史本身的逻辑,还是以歪曲历史的手法来哗众取宠、谋取私利呢?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根本创作态度,道德和良心问题。
我认为,对于任何国家的作家来说,以为只有依傍某种最高政治权力,才能搜集到对创作有价值的素材,这是很可悲的。试问,在世界文学史上得以名垂青史、具有艺术魅力的名著,有哪一个是依仗某种最高权力而成就的呢?《大地之子》的实例已能证明,一个日本作家,不论其名气有多大,如果对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史,对于留华日本孤儿的生活和思想轨迹没有准确、深刻的把握,即使有了某种最高权力的特许,也不可能真正反映一代日本战争孤儿的命运和价值。在这里所真正需要的,不是多高的权力,而是作家自己的思想境界,写作态度和艺术良心。
作为战争孤儿,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我们还在承受着战争的后果。山崎丰子如果真想如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的疾苦、我们心灵深处的喜怒哀乐,那根本无须依傍什么最高政治权力,“走上层路线”。
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数以千计的战争孤儿中到处都不难找到应该采访的对象,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孤儿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心实意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虚心地体验和聆听他们的心声,而不应像一个“文丐”和“文贼”那样凭着某个大人物所恩赐的特权到处猎奇。在中国,作家和教师一样,被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山崎丰子根本不配作家的光荣称号。她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市侩”,文坛上出卖灵魂的“奸商”。她以玩弄我们战争孤儿的心灵创伤、蹂躏我们的感情为快,以歪曲我们的形象来招摇撞骗,谋取私利,欺骗公众。这无异于往我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是对在艰苦条件下哺育和培育留华日本孤儿的中国人民的污辱,也是对广大的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日本公众的愚弄。
标签:日本作家论文; 山崎丰子论文; 大地之子论文; 文学论文; 山崎论文; 文革论文; 松本论文; 作家论文; 孤儿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