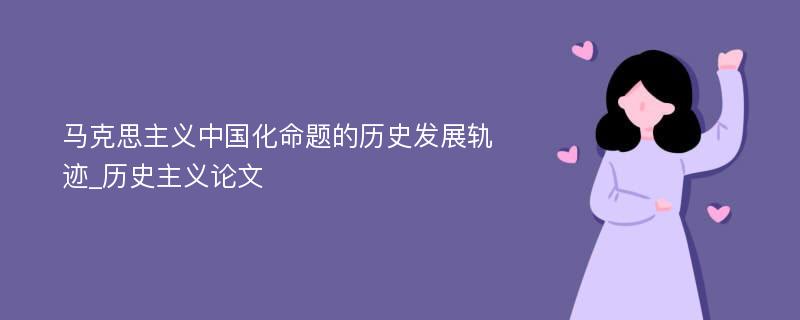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轨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4)02-0010-04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没有什么问题能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具有深远意义和长久魅力。尤其在当今世纪更迭的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更是力图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求得对本党、本民族历史、现状和发展更为深刻的理解。的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贯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始终。正是在实践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适用性”与中国特殊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把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前途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变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备了现实的形态。作者拟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原因作一粗浅的梳理,并求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奋起与抗争的历史。对于具有忧国忧民光荣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为了探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之路,先进的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中国的理论武器,单纯的选择是不够的,拥有了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并不表明就能够正确地使用它。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也就是说,要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能让中国人理解和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客观依据。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看,“中国化”概念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而言的。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在早期中国革命中曾给予中国革命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干预。既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为各国革命提供现实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与俄国处于相同时代,具有较为相似国情的中国自然走上了以俄人为师的道路,即“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走向马克思主义时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而言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现实依据。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意识的对立面所产生的,由于其科学的世界观及其对无产阶级解放道路规律的揭示而成为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来源于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使之民族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那里也不是抽象的教条,他们历来反对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实际和发展过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他们早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曾说过:“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进一步提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这些话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自己理论的谦卑而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必须要变成当地人民能接受的东西,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变成巨大的现实的物质力量,从而更好地指导各国的革命和建设。
在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现代化过程中,俄国工人政党领袖列宁无疑是光辉的典范,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正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工人阶级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在内的本质要求。
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是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这种特殊性反映到中国革命中,也使得中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旧式的农民革命,它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对理论发展有着更特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它自身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必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现实的展开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
1.从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到《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奏。1929年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党的“九大”,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决议中,提出了如何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是告诫党员同志坚持调查研究,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里,毛泽东已经初步涉及了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实际的问题。在次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围绕反对教条主义,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的重要论断,倡导“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先导。之后一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这一思想原则,使中国革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就是这种结合的理论成果,它们代表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大厦的基石。
2.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初表述。1938年10月,中共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报告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已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表述,他指出,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述。具体是相对于抽象而言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中国,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从理论形态来说,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确是一个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抽象概括,他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能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亦即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这些一般性规律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而存在。但是,人类社会生活又具有特定的时空规定性,正是这种时空局限性,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没有能够把一般抽象运用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去,从而形成多样性的具体,而这些抽象性因素如果不与具体国家与民族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就会因其流于空泛而失去理论和实践价值。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42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并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中间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3.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及其曲折过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取得相当广泛的共识。但直到党的“七大”,这一命题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这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3]“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3]刘少奇的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视,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高度,但不久奇怪的是,七大过后不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突然从党的文献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消声匿迹了,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提法已经悄无踪迹。这一变化的出现原因何在呢?
作者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明这种变化。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密切相关,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所谓民族主义嫌疑。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谴责,对一向敏感的毛泽东及中共来说无疑是一发重磅炸弹,中共必须小心谨慎,稍有差错,“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就会被戴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头上。中共做出了反应。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可见,毛泽东和中共对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变化是十分警惕的。关于这个问题,建国后,在1956年9月与南共联盟代表团的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还记忆犹新,他曾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正是缘于这种外部的因素,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毛泽东思想容易被人误解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中共改变了自己的做法。此外,停止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还出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考虑。1948年下半年,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是“曙光在前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这也意味着中共将面临着依靠苏联的帮助,为避免苏联方面发生误解,中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可以从1948年毛泽东对青年团团章中“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修改看出。他说:“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稍后,他在审阅团章草案时,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些话表明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一些考虑,主要是怕引起国际方面和苏联方面的误解。这可以从195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中更明显地看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也正是缘于这种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就没有在毛泽东时代继续使用下去,直到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理论界才重新使用了这一提法并给予高度重视。不过,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着更为广义的内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同步的,这一过程不仅仅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把握理论,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力及非凡的洞察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质的飞跃。
收稿日期:2003-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