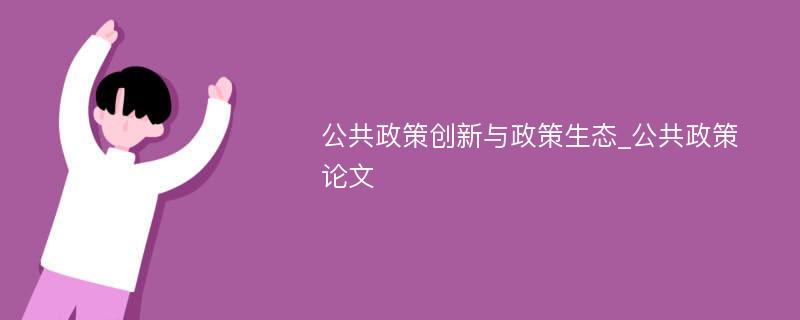
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生态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公共政策创新,即政府以新的理念为指导选择突破传统的政策方案,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公共政策创新是当前政府工作实践的重要内容。政府以新视角看待新情况,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也即公共政策与时俱进,是当代一切责任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自上个世纪以来席卷全世界的政府改革运动的主旋律。公共政策创新也是当前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公共政策创新不仅受制于公共政策生态环境,也必将对政策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力图运用公共政策生态理论对当下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创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公共政策创新:研究现状与范畴
在西方学术界,较早关注公共政策创新主题的是公共政策学家Jack L.Walker,他于1969年就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创新在美国各州的推广》(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的论文,该文在评论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式”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美国各州的公共政策创新及推广。认为在公共政策领域,决策并不都是“渐进的”(incremental),而是存在创新的。(注:Walker,Jack L.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American Politica Sciences Review,Vo163:880-899,1969.)这种观点起初并未引起公共政策研究界的过多关注,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浪潮的冲击,加上政府改革市场化取向愈益显明,公共政策创新在政府施政实践中逐渐形成一道全球性的风景线,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研究才得以全面深入地开展,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在西方国家,政策创新的研究围绕着三个重要的主题。一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政策创新。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广泛渗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政府面临一个全新的技术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给政府的不仅仅是技术便利,也给政府施政提出了很多挑战,比如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如何更快捷地响应民众的呼声等等。这些挑战要求政府改变以往的工作模式,改进工作方法,更新公共服务类别并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比如欧盟的几位学者在《领先者与追随者:欧盟的电子政府、政策创新与政策传导》(Leaders and Followers:E-government,Policy Innovation and Policy Transfer in the European Union)中认为电子政府有降低政策创新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重大潜能,并在比较英国和荷兰两国电子政府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电子政府不仅是降低政策创新交易成本的一个网络,而且会影响政策创新的模式。(注:来自www.hull.ac.uk,Paper to the EUSA Conference,Nashville,Tennessee,27th March 2003.)
二是政府竞争与政策创新。“政府竞争”(competitive governments)概念最早用于欧洲各国对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反映。随着货币与利率差别的日益缩小,欧洲国家一体化日益深化。由于货币政策的一体化,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货币主动权,纷纷采取以税收政策为代表的“政府竞争”措施,鼓励外来投资,吸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纵向和横向竞争。纵向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比如围绕中央确定的货币政策对解决财政矛盾的关键作用,以及中央—地方政权之间存在着围绕税基和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复杂的讨价还价现象等。横向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税制竞争以吸引外部投资等。(注: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一个综述》,《当代财经》2003年12期。)竞争迫使各国政府必须进行政策创新,进而以持续的政策创新实现制度创新,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对地方政府而言,政府竞争主要源自于地方分权,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尤其如此。美国政治学家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在《政府行政的未来:四种模式》中系统地提出了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其中三种模式(“参与式政府”、“灵活反应式政府”和“松绑式政府”)与政府分权有关。(注:[美]盖伊.彼得斯:《政府行政的未来:四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政府权力下放,尤其是财政权力下放,不仅使地方政府具备了创新的空间前提,而且也有了创新的动机。因为伴随着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与政治系统中的激励机制必然会催生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产生压力,压力促使政府创新。可以说,政府创新本身就是一场竞争。
K.Strumpf在《政府分权增长了政策创新吗?》(Does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Policy Innovation?)中回顾了地方分权对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意义,但也认为在接受分权促进地方政府创新观念之前,不能忽略一个学习外部性(learning externality)的问题,即成功的政策创新实验将给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成本很低却很有用处的政策创新信息。他利用一个社会学习模型(social learning model)分析了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下的政策创新。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在性质上比较近似(homogeneous)或者数量比较大,集权体制将引致更多政策创新;如果存有多种可用的政策创新方案,分权将引致更多政策创新。(注:Strumpf,K.Does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Policy Innova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4(2002),207-241.)Christos Kotsgiannist和Robert Schwager在《政治,标准竞争与政策创新》(Political,Yardstick Competit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和《政治的不确定与政策创新》(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Policy Innovation)两篇论文中分析了政策创新与政治激励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政治体系中存在一把“双刃剑”——外部信息,因为一方面外部信息可以提高政治体系的产出,另一方面外部信息又会降低对政策创新的激励。(注:来自www.gwdg,de,19th December,2003.)
三是市场化与政策创新。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集中论述了政府改革和发展的市场化取向。盖伊·彼得斯随后则以“市场化政府”一词来概括这种取向,认为政府应革新传统的体制和运作方式,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借助市场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市场化取向给政府改革和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设计理念,从而引发了政府大量的政策创新实践。K.Ascher在1987年出版了《政治的民营化》(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Contracting Out Public Services),集中探讨了公共服务由私营部门提供的可行性、政策方案设计及绩效评估等问题。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政策创新,但却提出了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创新来改进公共产品的提供。S.Borins1995年出版了《公共部门的创新》(Public Sector Innovation),重点讨论了政府创新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途径。在书中,作者较早地提出了公共政策创新(public policy innovation)的概念。
当代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人物,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Peter deLeon教授1994年在美国《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上发表了《重塑政策科学:面向未来的三个步骤》(注:Peter deLeon,Reinventing the Policy Sciences:Three Steps Back to the Future,Policy Sciences,Vo127:77-95,1994a.)(Reinventing the Policy Sciences:Three Steps Back to the Future)是论述公共政策创新的经典文献。这不仅是缘于Peter deLeon教授在公共政策研究学界的显赫地位,也是因为该文从理论的高度全面地阐述了公共政策学的创新之路。该文在回顾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脉络之后,分析并总结了公共政策学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困境。认为当前的政策科学过于依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日益显现技术导向(technocratic orientation),以及政策问题背景的复杂性,导致政策科学在发展中存在许多不足(shortcomings),比如偏离政策科学最初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特征,偏离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和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的目标。随后指出政策科学要破解这些难题需采取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回顾当前政策科学的范式;发展更具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程序;聚焦实际政策问题。最后,作者认为政策科学将迎来一个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的发展未来。
在公共政策创新的其他方面,小乔治·W.唐斯和劳伦斯·B.莫尔针对政策创新中的“创新”等概念以及影响创新实证研究中的不稳定因素展开了探讨分析,并且界定了四种相互独立的导致不稳定产生的因素;(注:[美]小乔治·W.唐斯和劳伦斯·B.莫尔:《创新研究中的概念问题》,黄晓武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弗吉尼亚·格雷专门研究了政策创新的推广模式,认为政策推广研究有变量研究和过程研究,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并分析了美国为什么有些州首先接受新的观念而其他州却落在后面,从而总结了政策推广中的决定因素和外在条件;(注:[美]弗吉尼亚·格雷:《竞争、效仿与政策创新》,王勇兵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Joseph R.Cerami则试图弥合创新在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组织理论三方面的脱节,认为三者有关创新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互促进。(注:Joseph R.Cerami,Innovation in Policy Analysis,The Innovation Journal,Discussion papers,13/10/04。)
在我国,公共政策创新研究也是围绕三个主题而展开:一是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创新,尤其是企业改革中的政府政策创新。如王东京在提到要提高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推行制度改革,必须“创新”劳动力政策。(注:王东京:《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政策创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4年第11期。)李又才认为政府在国有企业性质的理念、国有企业布局、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决定权、国有企业竞争机制和国有企业服务体系等方面应该“创新”相关公共政策。(注:李又才:《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的作为:政策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3期。)
第二,社会转型期与公共政策创新。如胡宁生认为“公共政策创新是引发和促进中国在社会过渡时期体制转轨的核心战略要件以及具体的操作工具”,(注:胡宁生:《体制转轨与公共政策创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分析了公共政策创新的三个主要影响因子,即利益分化和协调、初始政策设计、规则和组织的变换。张晓峰则认为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创新在价值定位上必须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超越以往各种传统模式和传统理性,以新的政策价值导向把国家带入新的未来。(注:张晓峰:《转型期政策创新的价值定位》,《学术交流》1996年第2期。)另外,施绍祥、李乾贵以及卞苏徽等学者还提到了我国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政府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创新。(注:施绍祥、李乾贵:《论加入WTO与政府政策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卞苏徽:《入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1期。)
第三,关于公共政策创新宏观理论的分析。比如在国内较早论述政策创新的王瑞娟认为政策创新是我国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目标的基本条件,其中观念创新和实事求是是政策创新的重要前提,观念创新决定着政策创新的进程,实事求是决定着政策创新的实践效果。(注:王瑞娟:《论政策创新》,《理论探讨》2001年第5期。)汪永成从理论上描述了提升公共政策创新能力的四个方面,即塑造政策创新的能动主体、营造促进创新的社会环境、构建激励创新的制度结构、突破政策变迁中无效率的路径依赖问题。(注:汪永成:《论中国公共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理论探讨》2002年第1期。)王学杰则从公共政策创新的构成要素出发,分析和论述了公共政策创新应该是科学(合理性)、民主(合法性)和艺术(协调性)三大力量协调平衡的产物。(注:王学杰:《公共政策创新的结构分析》,《南方经济》2003年第12期。)另外,吴春华还分析了政策创新中的规划和传输。(注:吴春华:《政策创新中的政策规划与传输》,《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
综合而言,政策创新是以新的理念为指导对公共政策进行改革与完善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和活动。政策创新具有以下特点:(1)在政府领域内(界定和保护产权,保障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注:钱颖一:《政府与法治》,《比较(第5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4页。)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策创新不只是一种职能,而且是公共管理思维的变迁所形成的新模式。(2)政策创新是一种有价值的政府行为。政策创新的目的不是一般地实现治理的目标和责任,而是发现“创新机会”,获得“创新净收益”。(3)政策创新是有成本的活动。政策创新成本主要由这几部分构成:设计、制定和组织实施新政策的费用;清除既存政策的费用;消除变革阻力的费用;政策创新的机会成本。具体看来,公共政策创新的目的是使公共政策制定更科学,公共政策程序更规范,公共政策目标更精确,公共政策手段更完善,公共政策灵敏度更高,公共政策内容更具体,公共政策效果更明显。
二、公共政策生态:缘起与体系
通过对有关公共政策创新研究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到,中外学者的研究主题有所差异,这源于公共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和运行的。生态环境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外部条件,不仅决定政策问题的性质,也决定政策的生命周期,更决定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取向和行为。因而有学者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公共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P=(E,C),其中P指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E指生态环境(ecology),G指政府(government)。(注:Robert Eyestone.The Threads of Public Policy:A Study in Policy Leadership.Indianapolis,1971,pp18.)公式意指政府做出的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函数。
在行政管理领域,弗雷德·W·里格斯(FredW.Rjggs)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行政生态学,里格斯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科学。(注:转引自:彭文贤:《行政生态学》,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第2页。)但里格斯并未对公共政策的生态进行更为细致的论述。
公共政策的学科奠基人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是最早提出并论述公共政策生态的重要学者。在他与勒纳合著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近期进展》中清楚地阐释了政策科学的三个学科特征:跨学科视角(multidisciplinary)、情境和问题导向的本质(contextual and problem-oriented in nature)、规范性(explicitly normative)。(注: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Lasswell,The Policy Sciences: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8-10.)其中,对于情境性(contextuality(注:对于contextuality,我国学界有很多种译法。比较有代表性是翻译为“情境性”(吴予敏:《论传播与人的反思性》,《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语境性”(陈忠华:《话语序列的符号学含义》,《外语研究》1994年第4期),“场合性”(唐述宗:《语体、语域与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6期),“特殊性”(张清敏:《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等。在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学界,还没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论述或翻译。所以参考各个代表性译法,本文翻译为“情境性”,指问题与环境的相关性。)),拉斯韦尔认为以往的政策研究(或者说是政治决定的研究)往往受限于注意的焦点(the focus of attention)导致对社会情境描述和解释的失败,因此他提出了公共政策情境性的概念,希望能使得相关活动与外在环境产生关联,并建立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内涵。他对情境性的定义是:“一个整体社会过程的认知图(cognitive map),公共政策问题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注:Harold D.Lasswell,The emerging conception of the policy sciences.Policy Sciences,Voll:1-15,1970.)因而,拉斯韦尔所提出的“情境性”其实就是指公共政策生态,是公共政策与其内外环境体系,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定义公共政策生态时,拉斯韦尔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针对政策过程,另一方面是针对政策的知识需要。”(注:Harold D Lasswell,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s,New York:American Elsevier,1971.)因而,他将政策科学定义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策过程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olicy process),另一部分是政策过程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the policy process)。身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政策科学研究者,必须以情境性和问题导向为指导去了解这两方面的知识。Ronald D.Brunner曾经对拉斯韦尔的观点作了一番说明补充,他认为,不同环境下,报偿(pay-off)体系均有所不同,环境的因素也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产生影响,政策科学家应该根据环境、时间、资源的限制判读信息,并且以系统、广博而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注意力的指引。(注:Brunner,R.D.,Book Review:A Milestone in the Policy sciences,Policy Sciences,vol29:45-68,1996.)此外,Peter deLeon也一再阐释情境性的意义和重点,(注:Peter deLeon,Advice and Cont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Sciences,New York:Kussel Sage Foundation,1988.)二者对情境性的说明,无疑是继拉斯韦尔之后清楚论述公共政策情境性的重要文献。
随着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许多政策学家也以自己的视角来分析和诠释公共政策的情境性。比如,托马斯·戴伊(Tomas Dye)建构了由利害关系者(policy stakeholders)、政策环境(policy environment)、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所组成的政策体系(policy system)。认为三个组成因素间是相互关涉并且彼此影响的,而所谓“政策环境”就是围绕政策议题并影响政策议题的特定情境和生态。(注:Tomas 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New Jersey,1975.)再比如,邓恩(Dunn)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政策分析架构:包含了政策问题界定(structuring policy problem)、政策方案预测(forecasting policy alternatives)、政策行动建议(recommending policy actions)、政策结果监测(monitoring policy outcomes)、政策绩效评估(evaluating policy performance)等等,并分别就政策议题环境中的信息复杂性(the complexity of information)提出了重要的分析方法。(注:[美]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许多美国政策研究学者也从实务角度分析和论述公共政策生态。例如Van Horn,Barmer和Gormley,Jr.等三位学者在合著的《政治与公共政策》(Political and Public Policy,1992)一书中就以政治和政策的六个领域来说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决策者、利害关系人、幕僚等群体认知和行动的影响。(注:Van Horn,C.E.,D.C.Baumer & W.T.Gormley,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92.)这六个领域分别是董事会政治(boardroom politics)、首长政治(chief executive politics)、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法庭政治(courtroom politics)、衣帽间政治(cloakroom politics)、起居室政治(livingroom politics),其间运作的复杂性和公众注意的程度均有不同,但都对公共政策的最后成形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Nakamura和Smallwood则从政策环境的概念分析政策体系成败的因素。(注:Nakamura,R.& Smallwood,Politic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New York:St.Martin's,1980.)认为政策环境和政策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因此,作者以政策规划(policy formation)、政策执行(policy implementation)和政策评估(policy evaluation)三个阶段的环境为主,讨论行动者(actor)、领域(arenas)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第一,政策规划阶段。由于此时主要的行动者是立法的(legitimate)决策者包括了总统、国会、官员、州立法者等等,同时受到利益团体、有力的选民等非政府人员的影响。而彼此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体制影响的互动都会促成政策不同面貌的发展。第二,政策执行阶段。在这个阶段,政策执行部门可能受到体制上如委任立法的制约,但其自我认知(如对自我指责的认知、对自我利益的认知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策执行的内容。重要的行动者包括制定者、正式执行者、媒体、游说团或选民团体、消费者和受益者、评估者等等及其所在领域,另外,比如行政组织的结构和规范、沟通网络等相关环境因素都是决定政策执行成败的主要原因。第三,政策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的环境是三阶段环境中最为抽象的,既包括政策规划阶段环境中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阶段环境中的执行者,也包括大量学术团体、公益团体、公民等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所身处的不同情境是政策评估阶段的重要环境因素。
综观从概念体系、理论分析和实务描述等角度关于公共政策生态的论述,可以将公共政策的外部环境因素分为宏观生态因素和微观生态因素两大类。公共政策的宏观生态因素包括经济-资源因素、政治-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经济-资源因素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和最深层的环境;政治-法律因素不仅决定公共政策的性质,而且决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程度;社会-文化因素既决定了公共政策运行的智力条件,也为公共政策的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伦理和心理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直接,甚至国内政治国际化和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象也已初现端倪。公共政策的微观生态环境是指每项具体的公共政策所处的具体的、特定的背景,具有多样性、变动性甚至是突发性特征。
另外,从政策生态系统本身是否均衡的角度,也可以将政策生态区分为常规型政策生态和非常规型政策生态。常规型政策生态表现为社会政治系统中输入端的支持与压力相对均衡,社会制度规范、社会理性相对稳定和有序;非常规型政策生态则较多地表现出支持与压力失衡,并且是压力大于支持,从而出现制度混沌,问题丛生,社会相对无序的状况。在常规政策生态与非常规政策生态之间还存有一种既不属于常规生态,也不属于非常规生态的“过渡性”政策生态,也即转型期(注:“转轨”与“转型”经常混义使用,但也有所区别。所谓“转轨”(transition)一般多指体制的转变、模式的变更;所谓“转型”(transformation)一般侧重包括体制在内的制度以及社会其它方面如观念等的转换。不论转轨还是转型,它们基本上都是制度变换或社会创新的过渡进化形态。关于经济学学者对于“过渡”或“转轨”的理解和论述,可以参见雅诺什·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宇的《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吕炜的《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等。)政策生态。转型期政策生态主要表现为:(1)政治秩序稳定但政治系统不均衡;(2)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不健全;(3)文化价值观存在但缺乏支柱;(4)社会在进步但问题丛生。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洛尔(Yehezkel Dror)曾提出三种公共政策制定类型,即“繁荣时期的政策制定”、“严重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和“巨大灾难形势下的政策制定”,(注: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页。)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政策生态本身是否健全的考察基础上。在常规型政策生态和非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的产生和运行机理都有较大差异。在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因为政治系统相对均衡,政策制定和创新更多地呈现出“维护型”特征;而在非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必须针对众多社会问题做出主动及时有效的回应,因而呈现“回应型”特征。在社会转型期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一方面要起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回应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因而呈现“维护+回应”双重特征。
三、我国政策生态语境下的公共政策创新
在公共政策生态语境下,公共政策创新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进行展开:第一,公共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也即政策创新的变量分析。劳伦斯·B.莫尔是第一个将变量分析应用到公共机构研究中的,随后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学者都采用“变量”研究方法,也就是运用一组独立变量(或因素)借助统计学解释政策创新出现和采纳的频率。比如小乔治·W.唐斯和劳伦斯·B.莫尔就总结了两套有益的变量分析模式:内在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模式和外在决定因素(联邦的激励和专业协会等)模式,并且认为“对政策创新影响最大的因素来自经济变量,其次是政治因素,而社会因素更多的是混合在他们中间”。(注:[美]弗吉尼亚·格雷:《竞争、效仿与政策创新》,王勇兵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但他们只分析了影响政策创新的一般因素,没有系统地梳理出影响政策创新主题的因素。第二,公共政策创新的过程,也即政策创新的过程模型。约翰·金登运用这个分析方法来研究国会议程的确定,纳尔逊·波尔斯比则用它来研究八个国家的政策创新。(注:[美]弗吉尼亚·格雷:《竞争、效仿与政策创新》,王勇兵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但是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做个案研究,很难用通用的变量和变量组成的模型做一般和归纳分析。第三,公共政策创新的内容,即政策创新的主题分析。不同生态下的政府会选择不同的创新主题,但事实上创新主题的选择很能决定不同政府的绩效,所以很有必要在公共政策生态框架下分析公共政策创新的主题。第四,公共政策创新的界限,即政策创新的限度分析。在自然生态下,每种生物的进化都会遭遇生产环境的资源界限;在人类的公共领域,政府创新公共政策更会遭遇许多界限。一旦突破这些界限,公共政策创新带给社会的就不再是公共福利,而是公共悲剧。
社会转型是我国各级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所必须面对的政策生态。这种政策生态不仅关涉我国公共政策形成和运行宏观生态中的经济-资源因素、政治-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而且也影响到每一项公共政策所必须直面的微观生态环境。在社会转型期政策生态下,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机制和分配格局以及政府的角色都已经或即将要发生重大转变,这都迫切需要政府以新的工作思维、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工作手段等应对新的环境,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公共政策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政策生态的独特导致我国政策创新实践与西方国家的政策创新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也必然导致理论研究在视角和体系上有所不同。因而,本文侧重从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两个区别于西方学者的角度对公共政策创新进行阐释。
1.社会转型背景下公共政策创新的主题
处于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的主题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共政策主体创新。如前所述,公共政策是在特定的客观社会环境里产生并运行的,而人民群众始终是客观社会环境里的主体因素,因此,要权变性地处理公共政策与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客观社会环境的矛盾关系,必须遵循和坚持民主原则,创新公共政策主体。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如召开听证会,而且要体现在公共政策的执行、监督和评价等各个环节。也就是盖伊·彼得斯在《政府行政的未来:四种模式》中所阐述的“参与式模式”。该模式认为,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和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拥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所以需要“更大范围的参与”是绝对必要的。在我国的政策生态下,创新政策主体有两层含义:(1)扩大政策主体范围。随着社会不断变迁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新出现的社会主体(如“新经济组织”等),公共政策无法以传统的身份判别方法去涵盖这些主体,因而迫切需要扩大政策主体范围。(2)梳理政策主体体系。社会转型不仅产生了新的政策主体,也导致一些传统的政策主体逐渐被分解,从而致使建立在传统政策主体基础上的主体体系不再符合变化了的生态,也导致公共政策出现许多“不对口”的失灵现象。鉴于此,需要重新梳理政策主体,建立全新的主体体系,比如规范主体名称、主体范围、主体组织状况等。
第二,公共政策内容创新。也就是指公共政策要“到位不越位”。首先,在一般意义上,公共政策产生于政府与市场的“比拼”,经历了从古典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再到现代市场条件下公共政策的变迁之路。在政府改革市场化取向愈来愈显明的今天,政府公共政策在内容上应着重于政府领域(界定和保护产权,保障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及提供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内的公共事务。其他属于市场主体(如企业、民间组织等)领域的大量微观事务就不再适宜用公共政策去规范和调节了,否则就属于公共政策的“越位”现象。另外,社会转型期的政策体系下,急剧变迁的时代引发了许多政府以前没有关注或关注度不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政府运用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和调整,如失业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新问题进入政府传统的常规化政策议程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只有通过创新政府公共政策的内容,才能避免出现公共政策的“缺位”情况。在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持久缺位不仅会导致社会公共问题积重难返,也容易诱发大面积的社会失序,这也就是公共政策在该生态下强调“回应性”的意义所在。
第三,公共政策手段创新。公共政策按其手段特征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具性政策,即常用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第二类是目标性政策,即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政策,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和流动的管理政策、扶贫政策、产业政策等。第三类是制度性政策,指对经济、社会行为或具体制度选择的许可或限制、禁止政策,这类政策对制度创新和深化改革至关重要。在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制度性政策基本完善,政策创新主要是针对工具性政策和目标性政策。但处于社会转型的政策生态下,因为整体系统不够均衡和健全,因而任一方面政策都不能不对社会做出适时有效的回应。对于工具性政策,要以工具理性为指导、以效能为标准进行创新;对于目标性政策,需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以社会公平和利益调控为标准不断完善和创新;对于制度性政策,需要以社会协调发展为指导、以市场健全为标准进行创新。
第四,公共政策程序创新。这也是社会转型生态下特有的创新主题,也应该是社会转型生态下可以率先垂范政策创新的重要领域。常规政策生态下的政策程序相对成熟完善,除非面对新技术或突发性政治事件的冲击,政策程序都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而社会转型生态下,政策程序创新不仅是指公共政策程序(包括制定、传导、执行、调整、终结、监督和反馈评价等过程)要完善,并形成健全的政策运行体系,而且是指公共政策在程序上要公开透明。在社会公共问题丛生,制度规范相对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程序完善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外部生态理性互动保证政府及时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与传统程序进行对接确保社会秩序的维护。近期,我国广州、上海等地先后通过并施行了《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这本身就是创新的公共政策在制度上确保了政府今后在其他政策领域上要不断走向公开、透明。
2.公共政策创新的限度
在政策生态语境下探讨公共政策创新基于这样两个理由:(1)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创新一方面是一种有价值的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有成本的,而创新成本与政策生态的支撑息息相关。在社会转型的政策生态下,政治系统、经济体系、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正经历成长但缺乏规范的制度、健全的体系和稳定的预期。这种转型的政策生态并不能同时支撑和给付所有方面的创新。(2)作为公共权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调整公共利益关系的公共政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认为,“作为一经济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组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些不同之处中,政府有两大显著特性:第一,政府是一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制力。”(注:[美]斯蒂格列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45页。)政府的“公共性”和“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策生态的变迁。如果政策创新没有将政策生态从不均衡引领至均衡,而是将政策生态从一种不均衡引领至另一种不均衡,甚至是更为不健全的不均衡,这种政策创新也就只能是公共悲剧。因而,在大力倡导公共政策创新之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限度和约束。
从社会转型期政策生态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
第一,公共政策创新应以市场为基础。改革就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大政策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市场失灵为政府介入和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与可能,但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政策生态下,一方面是日益发达、成熟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日益扩展的政策效应,二者“相得益彰”。所以处于社会转型生态下的公共政策创新必须以市场划“线”,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为基本着眼点。
或许正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不够健全完善的市场,政府习惯使用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公共政策去取代市场,并且是以“创新”的名义去取代市场。我国某省于2003年9月曾出台《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称要“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从体制、政策、政府职能等方面优化本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注:郝倩:《安徽红头文件“解禁”官员经商》,《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5日。)但在这样一项“新”政策中却赫然写着“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省内开办民营企业,在3年离岗期间,保留原身份不变,并参加正常的工资晋级,基本工资和工资性补贴仍由原单位发放”。这不仅违背了国家有关公务员管理的条例规定和政策,而且势必破坏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就必然出现“权力经济”、“红顶商人”,也就是公共管理通常意义的“裁判参与比赛”。这不仅导致其他市场主体难以公平竞争,也必然破坏市场秩序,也就必然导致市场经济难以发展。
第二,公共政策创新应以法律为准绳。如前述,法律以及由法律所规范建立的政治——法律系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重要生态因素。而且众所周知,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基本治国方略和施政理念。在社会转型的政策生态下,规则建立的速度可以很快,但对规则的认同和自觉遵守却需要较长时间。政府作为特殊的社会主体,不仅应该“独善其身”,模范遵守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维护政治——法律系统的权威,而且应该引导其他社会主体建立对规则和法律的认同与遵守。因而,公共政策创新必须处理好与政治——法律系统的关系。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独特政策生态,而且由于法律所涉及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其条款也只能是原则性的,因而需要某种更为灵活,同时又较为规范的方式来加以弥补或调节众多的社会公共问题,这就为公共政策的产生提出了需求,奠定了基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解决了政府在某些无法可依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又能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变动和某些社会冲突中,大大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相机抉择能力,适时化解那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障碍。但是法律需要政策作为补充,并不意味着政策可以违背法律,更不意味着政策可以替代法律。
但在我国一些实践工作部门中的所谓“政策创新”却是以破坏法律的权威为代价的。比如,2002年江西弋阳县政府的13号文件中关于各级政府机关对赣东北贸易市场的促销规定,(注:《红头文件,强制搬迁》,www.cctv.com,央视经济半小时,2004年7月13日。)以及2003年湖南嘉禾县的“嘉办字[2003]136号文”中关于“四包两停”的规定,都是不以法律为准绳的政策实例。这种破坏政治——法律系统的所谓政策“创新”实际上是政策“倒退”,退回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阶段,也是退回到“无法无天”的状况。对于这种所谓的“政策创新”,不仅不能给予在创新意义的收益激励,而且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
第三,公共政策创新应以政策体系均衡健全为指向。公共政策创新应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否则,政策创新就很容易落入政绩工程、运动式折腾的陷阱。从总体上看,政府各方面的公共政策构成一个公共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在纵向上包括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横向上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等。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能够实现自我维持和功能整合,从而超越各单项政策的简单组合。当前的公共政策创新,往往是选择一两个领域或一两个内容进行突破创新。这样的确是符合政策创新的“试点——成熟——推广”的创新推广模式。但是,这种“单项冒进”的政策创新方法往往会导致政策体系不配套,甚至破坏原有相对健全政策体系从而引发更严重社会公共问题。公共政策体系均衡中有一个重要公式:100%×100%=100%,其含义是指各单项政策都相对健全,从而形成的政策体系也必然会有相当完善的功效。公共政策体系均衡中也有另一个重要公式:50%×50%=25%,其含义是指不够完善的单项政策相互组合会使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在社会转型的政策生态下,政策体系下的许多政策都亟待完善,但选择哪一领域的政策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创新效果却有很大差异。比如,广州、上海等地选择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策创新的突破口;而河南郑州市在2003年8月选择“户籍新政”作为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注:《郑州难以承受人口激增压力,部分户籍新政策叫停》,《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5日。)前者在实施后带动了国内许多城市学习和模仿,而后者在实施中却遭遇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公共资源稀缺的瓶颈,一年之后不得不宣布“暂停”。因而,在现实的政策生态下,政策创新的选择应以政策体系是否均衡健全为重要指南,或者选择与原有政策体系关联度不高的政策领域;或者整体推进关联度较高的几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