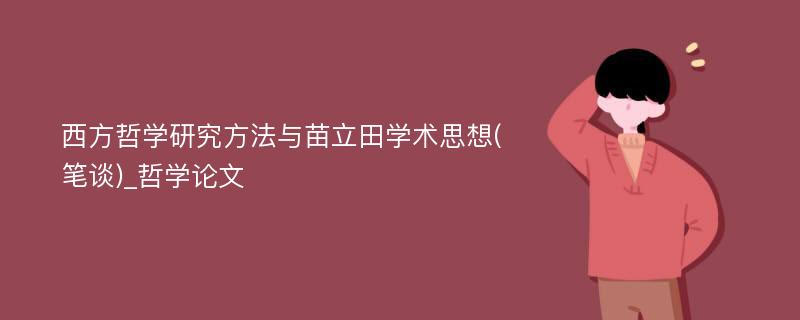
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与苗力田学术思想(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史论关系的三种模式
综观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实,史与论之间的联系大致有三种模式。为简练起见,我们不妨 把这三种模式分别概括为“以论带史”、“就史论史”和“论从史出”。
黑格尔被誉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创始人”。形容词“科学的”在这里指用哲学理论来指导 和概括史料的研究方法。虽然很少有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科学的,但他按照自己的哲学理 论来写哲学史的方法却被人们普遍认作是研究哲学史的科学方法。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并不是第一部哲学史。早在1655年,吉尔基荷姆的雷登(GeirgeHorn of Leyden)用拉丁文 写了《哲学史研究:哲学的起源、继承和派别》一书,托马斯·斯坦雷(Thomas Stanley)用 英文写了《哲学史》一书,系统的哲学史著作才宣告问世。此后,雅可比·布鲁克尔(Jacob Brucker)所写的五卷本的《批判性哲学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于1742年至1 7 67年在莱比锡出版。黑格尔虽然批评这部书包含着“一连串错误的观念”,“抽象地把真理 和错误两极化”,但他却从这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用他的 逻辑范畴来整理和概括哲学史的材料,达到了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的统一,堪称“以论带史” 模式的典范。
中国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国哲学界的方法、风格和模式的影响。长期 以来,我们接受的是从苏联传入的“以论带史”的模式。据说,这是惟一正确的模式,属于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确实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不少东西,但马克思是否 也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否也要坚持黑格尔的“以论带史”的模式 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讨的。更何况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本身有不少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之 处。事实证明,把这种模式凝固僵化,当做惟一正确的方法,不利于哲学史的研究。我们过 去甚至把“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结果把西方哲学史研究作为马列经典著作的注 脚。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国哲学史工作者从一开始就批判了苏联日丹诺夫提出的哲 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定义,实际上摆脱了“以论带史”的模式,逐 步转向了“就史论史”的模式。西方哲学史领域出现的这种类似范式转换的变化,在很大程 度上应归于老一代学者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条件的限制,老一辈西方哲学研究 者,如洪谦、王太庆、陈修斋等先生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哲学经典的翻译工作。他们主持 翻译的五卷本《西方哲学原著选辑》、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以及《现代西方资产 阶级哲学资料》,可以说哺育了我国一代哲学教师和研究者。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哲学研究 者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学风,以“就史论史”的态度,忠实于原著,忠实于事实,力图 恢复西方哲学的原貌。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苗力田先生,应该高度评价他对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贡献。苗 先生在教学中“原汁原味”地向学生讲解西方哲学的精髓,形成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 。他所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我国哲学翻译的标志性成果。
“就史论史”的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向把哲学史研究引向深入细致,“就史论史”模式的 一项突出成果是勘定版本,翻译注释,编辑资料,特别注重文字功夫,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 的“小学”。但是,“就史论史”并不是不要理论,更不是没有理论。事实上,史和论的界 限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能够严格区分开来。即使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研究也无形中受 到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理论背景的影响,绝对地“就史论史”是办不到的。比如,英国 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受到的分析哲学的训练,所使用的语言分析的方法,他们专注于对话若干 段落的逻辑结构,重建论证的步骤,形成了独特的分析学派;而受欧陆哲学传统影响的欧洲 哲学史家也有不同的“就史论史”的职业习惯,他们重视整体结构,认为一篇对话就是一出 戏剧,对话的结构是关键,论证只是插曲,重要的是要像理解剧情那样去品味对话的意义, 形成了独特的戏剧学派。分析学派与戏剧学派的争论充分说明:“就史论史”的模式摆脱不 了哲学理论的影响。“就史论史”与“以论带史”的分歧不是根本的分歧,而是程度上的不 同。关键的问题不是“哲学史要不要接受哲学理论的影响”,而是“理论用何种方式影响哲 学史”。
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成果问世,继续提倡“就史论史”的模式。我国 应该有一批穷经皓首的专家,他们中每一个人也许只精通一个哲学家,甚至一部哲学经典。 但是,这样的人越多,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水平也就越高,从而使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 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陈康先生提出要让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外国人以不懂中文为憾。这一理 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功底,让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逾越语言文字的障碍,成为西方哲学 研究的典范。
有人说,90年代中国学术时尚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这可以看做是对“以论带史” 的学术时尚的一种批评。其实,真正的学问家何尝不是思想家,哲学史研究到广博精深的程 度,自然会出新思想。中国的政治家和读书人都喜欢以史为鉴,从过去认识现在,预知将来 。这种思路与我们要提倡的“论从史出”的治学模式是一致的。我希望,我们这支西方哲学 史研究的队伍沿着这条道路,踏实苦干,涌现出一批思想家、理论家。
哲学研究的方法与哲学的“孝”
我想从哲学的“孝”的角度谈谈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涉及如何对待和尊重学术前辈 、学术传统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学术伦理问题。在哲学上,“孝”从来就不只是狭窄地局限于 家庭血缘关系上。哲学意义上的“孝”其实与西方哲学有直接的关系。苏格拉底认为,孝乃 是一种公正,体现在人对神的服务之中。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真正的对神的孝便是做哲学, 不断反思、揭示人类的局限性,不断自我批判,在对自身无知程度的探讨中扩展知识。正是 在这种对神尽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成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可以说,作 为西方哲学灵魂的反思批判精神,正是苏格拉底的——也是西方哲学上的——“孝”。在中 国哲学中,“孝”是儒家所倡导的一中心美德。可儒学所讲的“孝”,不只限于对父母的供 奉赡养,丧葬祭祀。《中庸》曰:“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而孔夫子把他 自己的哲学方法归结为“述而不作”。把这两个“述”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孔夫子的哲学活 动也被他自己看做是一种“孝”的活动。他修订整理“六经”正是为了继文武周公之志,述 中华文化之道。
初看起来,孔夫子的“孝”比较尊重传统,追求连续性;而苏格拉底的“孝”则重批判和 反思。可是孔夫子的“继人之志,述人之事”首先要求思考什么是先人之志,先人之事,而 且“述”也并非简单描述,而是彰显其精义。因此,“述而不作”其实照样强调创造性,强 调超越与发展。另一方面,苏格拉底也不是为了诘难而诘难。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的问答 法是为了改进人的灵魂,引导人到更正确的方向,从而促进人类智慧的进步,增进人类的幸 福 。由此看来,孔夫子之“孝”与苏格拉底之“孝”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容互补的。作为后 学,我想我们既应该有孔夫子的“孝”的精神,继承苗先生之志,也应该有苏格拉底式的“ 孝”的精神,尽力服务于先生未竟之事业。
多年以前,苗先生看到日本有数部亚里士多德著作集日文版,而我泱泱文明古国却没有一 部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中文版,便矢志进行这一工程,以“不让日本在东亚专美”(苗先生项 目申请报告语)。经过多年努力,《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终于在先生去世前问世,成为 中 国第一部西方哲学家的译文全集。我们继承先生之志就应该发扬先生这种力求让中国的古希 腊哲学研究及其他西方哲学研究昂然屹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的雄心和抱负。值得欣慰的是 ,在先生这种雄心和抱负的带动下,其他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的中文编译工作也正在 积极进行中。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苗先生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 》无疑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性贡献的。
苗先生的代表性成就是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的中文译本。就如同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 历经两千年而不衰一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也是一个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在西方有 长达千年历史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与带定冠词的“哲学家”是同义的。因此,研究亚里士多德 即是研究哲学本身,而翻译乃是这一研究的内在部分。20世纪初,W.D.罗斯在牛津这一具有 千年古典研究学养的学府召集当时英国最有成就的一批亚里士多德专家耗44年时光(1908—1
952年)译成《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译本》。即便如此,罗斯主编的本子在七八十年代仍遭 到了广泛的修订。1984年普林斯顿出版了由乔纳森·巴恩斯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 修订译本》。而巴恩斯在前言中指出,他主持的这一修订也是阶段性的,有待进一步完善。 最近一二十年英语世界出版了多种亚里士多德单本著作的译本。而且光是翻译已经不够,鉴 于亚里士多德著作原文的难懂,现在大多数译本都带有详细的注释,且注释常常是原文的数 倍。牛津的克罗林顿出版社更进一步组织了一套《亚里士多德译丛》,选择亚里士多德单本 著作中的一章或数章进行译注,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四、五、六卷译注》(C.柯文 ,1971;1992年第2版),《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七、八卷译注》(D.波士多克,199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十三、十四卷译注》(J.安那斯,1976),《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一、二卷译注》(W.查尔顿,1970),等等。不难看出,与西方相比,《亚里士多德全集》 中文译本的面世是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确实只是第一步。我们应该不断加深对亚里士多德 的研究,促进对原文的理解,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忠实、更确切地以中文表达出来。
应该说,亚里士多德自己所遵循的哲学方法可以说正是一种把苏格拉底式的“孝”与孔夫 子式的“孝”相结合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富有批判精神的。他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 批判,其激烈程度尤为罕见。在一定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正是在对柏拉图哲学 的困难的揭示和批判中发展出来的。他自己对这种批判精神做了如下阐述:“作这类谈论是 非常艰难的,因为相(或‘理念’)是由我们自己的朋友引入的。尽管如此,如果驳倒那些我 们最亲近的人是维持真理所需要的,那么我们最好这样去做,而且,尤其是作为哲学家这样 做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既爱真理,也爱朋友。但孝敬要求我们尊重真理甚于尊重朋友。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6章1096a13-17)亚里士多德这一精神被中世纪哲学家们概括 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自己则把这一精神看做是“孝”这一美德的要求和体现。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和所有他之前的探求智慧的人又都抱有真诚的尊敬。这种 尊敬的基础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坚信所有的爱智者都对真理的发现具有贡献。亚里士多德研究 哲学的经典方法是“拯救现象法”。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一章讨论意志薄弱的问 题时,亚里士多德把这一方法概括如下:“如同研究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先列举各种现 象,在考察了它们之中所有的困难之后进一步去证明关于这些情感的种种观念的真理性。如 果可能的话,证明所有的观念都是对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需证明极大多数人的观念和 最有权威性的人的观念是对的。如果我们既能解决疑难,又可保留这些观念,那么我们 便充分地解决了问题。”(1145 b1-7)在希腊文中,“现象”指显现出来之物,故不仅是指 经 验材料,也包括人们说出来、写出来的种种观点和意见。亚里士多德“拯救现象法”中的“ 现象”主要是指后者。亚里士多德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方法,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他总是先 搜集前人和同辈人有关问题的种种论述(即现象),进而分析这些论述的彼此冲突之处,并通 过对冲突的考察揭示真理的困难所在。在这样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一种结论,这一 结论解决了现有各现象间的冲突,同时又显示了这些现象都含有一些真理成分,它们是对问 题的片面的部分的解决,而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则是这些真理成分的有机结合。
搜集材料,指出他人之不足,大约是做学问最基本的一步。亚里士多德以罗列现象为出发 点,则是因为他确信真理就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中,而他自己的任务则是要把每种现象所隐含 的真理成分抽出来加以阐发、整理。这是因为每个人在追求真理时都会有所发现,又都各有 局限。如果把大家的努力累积起来,人类离真理便愈近。亚里士多德说:“对真理的研究一 方面很难;在另一方面又很容易。这一观点可由以下事实作证:一方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 地 把握真理;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失败,每个人都会对事物的本性说出一些真理来 。作为个人,每个人或许对真理的获知贡献甚少,但大家联合起来却可以汇集相当数量的真 理成分。”(《形而上学》第二卷,913a28-b5)
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对前人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这与儒学的“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对于亚里士多德 来说,对前人的尊重与对前人的批判的考察是一体的两面。他一方面确信前人的观点中有智 慧需要去“述”,另一方面也深知这些观点也有其局限性。“拯救现象法”正是通过揭示前 人观点中的不足而“拯救”其中真理的智慧。因而,苏格拉底式的批判保证了孔夫子式的“ 述”的有意义性。即使是对柏拉图的批判,其宗旨亦是要明白柏拉图的学术在哪些方面是对 的,在哪些方面是不合适的。例如著名的“分离”问题,柏拉图把普遍看做是分离于个体而 独立存在的本体。亚里士多德对此批评说:“分离问题是与关相所提出的一切困难之源泉。 ”(《形而上学》第十三卷九章,1086b5)可这不是指普遍本体自身的分离是错的,而是指柏 拉图所认定的分离方式是错的。亚里士多德清楚地区分了这一点。他说:“那些认为相(理 念)存在的人把它们分离开来,这在这一方面是对的,如果相是本体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又 是错的,因为他们说相是多上之一。”(《形而上学》第七卷16章,1040b28-30)基于这样的 分析,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分离”说的同时,却又把“分离”列为评判他自己哲学中 第一本体的标准之一。“本体最主要的是分离的,是这一个”(《形而上学》第七卷3章,10 29a 28)。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评判最系统、最激烈,正是因为他认定柏拉图的哲学中有 最多的东西可以学习,可以“述”。
人们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普遍印象是哲学系统层出不穷,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而对中 国哲学的一个普遍印象是自孔孟老庄之后,“江河日下”。于是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把学问的 做法分成两种,一是“我注六经”,一是“六经注我”。而且,“我注六经”基本上是贬义 ,受人鄙弃。不少人都声称其学问是“六经注我”式的,欲弃掷前人,自立体系。这种风气 最让人困惑的地方是,孔夫子“述而不作”的态度是“我注六经”的始作俑者,可他却是中 国哲学的不二宗师;声称要“六经注我”者甚众,可至今只见“六经”不见“我”。事实上 ,西方哲学看似不断翻新,可骨子里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怀特海直截了当地说: “关于欧洲哲学传统的最可靠的概括是,它是由一连串柏拉图的脚注组成的。”(《过程与 实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9年版,第63页)这话如加上亚里士多德或许更为确切。但 这话与孔夫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我想再引用一段以严谨著称的分析哲学大家彼特·斯特劳逊的话来见证西方哲学的承继性 :“形而上学有一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因此在描述形而上学中不可能再有新的真理被发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描述形而上学的任务已经完成或能被一劳永逸地完成。它不断地一再被重新 描述,虽然没有新的真理可被发现,旧的真理却可以被再发现。因为描述形而上学的基本主 题虽然不变,批判性与分析性的哲学术语却不断变化,永恒的关系是由不永恒的术语来描述 的。这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气氛和每个哲学家的个性化思维方式。一个哲学家必须以他自己的 当代术语去重新思考前人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前人。而情况总是这样,如康德、亚里 士多德这样的伟大哲学家较之于别人更能使这种再思考的努力获得报偿。”(《个体物》伦 敦,1959,10-11)斯特劳逊在这里说明了西方哲学只是在“述”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经 典。在他看来,“述”就是一个哲学家出于时代及个体特性去对传统的永恒问题做出批判性 的再思考。这里弥漫的是一种把孔夫子的“孝”与苏格拉底的“孝”相结合的精神。或许怀 特海、斯特劳逊这样的哲人对声称“六经注我”者是崇拜对象。从这些哲人们自己的论述中 我们看到,他们真诚地认为只是在重新阐发前人的智慧。或许正是由于他们对传统的由衷的 孝敬,才使得他们可以走得这样远。
研究与教学、为学与为人的双统一
在哲学史上自经验论和唯理论开始就对科学研究方法论进行自觉的探讨,特别是笛卡尔、 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专门区分了“发现的方法”和“教导的方法”。发现的方法是研究的方法 ,或曰科学发现的逻辑,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科技创新、研究和开发的方法。教导的方法或教 学的方法,也就是把已有的科学发现成果传授给他人,教给他人。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中有 人认为,发现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教导的方法是综合的方法;也有人认为,发现的方法是 归纳的方法,教导的方法是演绎的方法。有些哲学史家评论,哲学家们昭示给世人的方法往 往是教导的方法,而他们自己所用的发现的方法则是秘不示人的。例如有人就说,笛卡尔通 常被人们当做演绎法的典范,而实际上他的科学成果都是通过分析方法得到的。总而言之, 在他们看来,研究的方法和教学的方法是不同的。
然而,在我看来,苗力田先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是统一的。苗先生对西方 哲学的研究重在对于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的追根溯源,考察一个范畴、概念在希腊原文中的词 根和本义是什么,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嬗递,现今人们对它们有何种理解。通过这种 考察,来体悟和阐发出哲学的含义和基本道理,评论现今各种理解的理论得失。哲学的研究 就是语言的分析,这一点在苗先生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对哲学就是这样去研究的,也是 这样去教学的。教学就是把自己研究的体悟告诉学生,教学是研究过程的再现或重演。其实 ,苗先生的研究过程就是他自己的学习过程,他的教学就是引导他的学生们像他那样重学一 遍,追述一遍自己的心路历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每逢得意之处,喜不自禁,因为这种教学 就是重温一遍发现过程的欢娱。在与大家分享发现成果的过程中,又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 条理和明晰。因此,教学的过程和研究的过程是不可能分开的,甚至教学也成为他的研究成 果本身。这也是苗先生一生如此重视教学、甚至把它奉为神圣的重要原因。
苗先生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统一起来。在苗先生看 来,哲学不只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常说,“哲学”(Philosophy)不是一个名 词,而是一个动词。哲学不是把现成的真理告诉世人,“爱智慧”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 一种不懈的追求。因而,他选择了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研究西方哲学是他一生惟一的追求和全部内容,或者说他把研究西方哲学看做是他生活的 全部或人生的宿命,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只有这样来看,我们才能理解苗先生 的许多行为,如50年代初他瘫痪在床、甚至不能翻身时,在床上学会了俄语;“文化大革命 ”期间坐着小马扎在广场上参加批斗会时,手中拿着小本子学习拉丁文;七十多岁时,还早 上六点多钟起床在阳台上背希腊文词根;八十多岁时,在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 之后,又要着手翻译《康德全集》,等等。
苗先生是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他的哲学观和研究方法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 德认为哲学是为了知而求知,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如名誉、地位、利 益为目的。同样,在苗先生看来,不要问学哲学是为了什么目的,干什么用,学哲学不是为 了 干什么,也没有用。因为爱智慧,是为了求知而求知,求得知之后干什么?再求知。所以, 不应该把学习和研究哲学看做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一种职业,或升官发财的一种途径。那样 ,哲学就不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就会屈从于外在的目的。凡是有功利目的的学问就不再是哲 学,而是科学和技术。
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是一切事物包括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至善”自身是无目的 的,它是自在自为的,不再追求什么。人类的幸福和“至善”就在于符合德性的活动。而“ 理智之德”就在于对真理的静观和沉思,即爱智慧的哲学活动。哲学能给人最大的愉悦,而 追求智慧的哲学家则是最幸福的人。因此,苗先生一生淡薄名利,以苦为乐,见到名利就让 ,从不向组织提要求,讲条件,在组织上要给他加工资时,他建议将工资加给孩子多、最困 难的同志;学校要给他分大一些的房子,他建议把房子分给家庭人口多的同志;他受到了不 公正的待遇,从不提起,别人问起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笑了之。
苗先生将研究与教学、为学与为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践履的。苗先生是 平凡的,而他的人格却是很伟大的。
“多读、多想、少写”及其他
苗力田先生治学50余载,有一条著名的原则,即“多读、多想、少写”,不仅为他自己所 奉行,而且也是他指导学生的“家训”。在流传中,这条原则被多加渲染,“多读、多想” 往往被人忽略,“少写”却被突出出来,甚至有“苗先生不准学生在50岁之前发表文章”之 说。是故,重新诠释这条原则,仍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凡治思想史者,皆以他人的思想为对象。认识对象,是研究对象的前提。斯人已逝,其思 想多以著作的方式传世。故而多读书、尤其是多读原著,是研究思想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毛 泽 东称吃别人嚼过的梨子没味道,认为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是就研究社会现实而言的。 而对治思想史者来说,思想家的原著也就是自己的“现实”,读书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只有从原著出发,才能得出真实的见解。苗先生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所 谓材料,也就是哲学论证的过程。一个哲学家做出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 观点如何被论证。研究者一定要把别人的哲学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理清楚。而要弄清楚哲学观 点的论证过程,就必须通读原著。苗先生对读原著的要求近乎苛刻。原著必须是地地道道的 “原”著,是“原”文“原”著,原汁原味。语言是思想的家园。只有熟悉思想家自己使用 的语言,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思想家的思想。苗先生始终坚持治西方哲学必须置外文于首位, 其中实在包含着为西方哲学研究固本培元的深意。译本尚且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更遑论经 过他人咀嚼的二手材料了。近些年来,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支配下,一些人往往喜欢走捷 径。坊间曾流传一些西方哲学史著作,动辄数十万言,却无一处引证哲学家的“原”著,注 释中甚至到处都是“转引自”,这固然比肆意抄袭者多了一份诚真,但这类著作的价值却是 令人不敢恭维的。
研究就是思想。故而仅仅“多读”还不够,还要“多想”,要带着思想去读。一部好书, 读起来令人兴味无穷,爱不释手,但要研究,却要学会掩卷而思。苦读带给我们的只是知识 ,善思才能给予我们智慧。但思想史的“思”与其他科学研究的“思”不同,思想史以思想 为研究对象,说白了也就是思考思想。因此,这里的“思”就具有了双重的含义。它要求研 究者不仅对思想家的思想有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沿着思想家的思路去思想。相 比之下,前者是研究的目的,而后者则是研究的前提。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 移情原则”,即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苗先生也主张哲学史研究要有历史感 。一方面要把哲学家的思想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从发展的角度把握其思想的内容和价值;另 一方面要深刻体验哲学家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学会与哲学家一道思考。 苗先生认为,研究哲学史最重要的不是给哲学家贴上标签,而是弄清楚历史上的哲学家究 竟是怎样思维的,究竟说了些什么。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做到“人我分清”,即把研究者的“ 思”与被研究者的“思”分清,不能借着被研究者的观点大讲自己的观点,更不能没弄明白 就随意杜撰,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编织被研究者的思想。
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多读、多想”,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要“ 少写”,更何况苗先生主张要更多地让哲学家自己说话。与其写一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 专著,不如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过来,让亚里士多德自己来讲述他的哲学。翻译是外国 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研究者不仅要能够用原文读懂外国哲学家的著作,而且还要善于用 自己的母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作为一名翻译家,苗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 这是他数十年翻译工作的总结:一要“确切”,即要忠实地、完整地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 。二要“简洁”,即在翻译时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意去铺陈。三要“清通可读 ”,即要能为现代读者准确无误地把握。四要有“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一定 要考虑到它的词源学渊源和思想家使用时的特殊语境,不可仅仅从其现代词义出发简单翻译 。在一些重要术语的翻译上,苗先生常常殚思竭虑,反复推敲,力求准确再现西方哲学家的 原意,有时为一个词的翻译改动多次。用苗先生自己的话说,发现一个词的准确译法,其喜 悦程度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即便是撰写研究著作,苗先生也主张尽量让哲学家自 己说话,让材料说话,材料组织好了就是一篇好文章,研究者甚至用不着说什么话。
当然,“少写”并不是“不写”。哲学史的研究毕竟不是纯粹的自娱。如果说读和想是研 究的前提的话,写则是研究的结晶。惟其如此,下笔就更要慎重。凡论著必须持之有据,言 之有物,反复琢磨,三易其稿。对于那些没有弄懂材料就大讲特讲一通不着边际的套话,对 于那些为稻梁谋而生硬地炮制出来的所谓专著,苗先生历来是非常反感的。
“多读、多想、少写”的治学原则,看似简单,不啻是老生常谈,然而要真正做到又谈何 容易。它既是一种治学的态度,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戒绝浮躁,淡泊名利, 甘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它说明了思想史研究的特征,要求研究者实事求 是,厚积薄发,在大量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在苦苦思索的漫长过程中,在真正理解历史上的 哲学家的前提下,写出真正的传世之作。在人们屡屡呼吁端正学风的今天,倡导“多读、多 想、少写”的治学原则,仍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意义。
苗力田教授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方法
苗力田教授是我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一位里程碑式的名家。据有的专家考证,早在公元七 世纪唐朝时,中国人已通过佛经间接知道了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明朝末年通过利玛窦来华和 徐光启、李之藻翻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论天》,希腊哲学首次进入中国,但当时 影响很有限。中国学术界真正开始较多介绍和研究希腊哲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严群先 生在翻译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培养希腊哲学研究人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陈康先生尤其做出 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果是很突出的,国际上研究希腊哲学的 专家很重视他的研究著作和独到之见。陈先生还在国内培养了我们现在称为老一代的希腊哲 学专家,如苗力田、汪子嵩、王太庆等先生,使得我国40年代虽历经战乱,希腊哲学的教学 与研究仍得以薪火不断。苗力田教授是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将陈康先生的事业 继承并发展的传人。他培育了许多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中青年人才,使希腊哲学研究后继有人 。他们有的已活跃在国际学术界,或在国外任教与研究,使中国学者的希腊哲学研究也走向 世界。近十几年来国内希腊哲学的研究比较热烈,也由于苗力田先生等孜孜育人,国内有了 比过去壮大的研究希腊哲学的中青年力量。他晚年以巨大的魄力与毅力,主持翻译了《亚里 士多德全集》,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基本建设,对我国今后深化研究希腊哲学将会产生深远 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发展史方面,苗力田教授承前启后, 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后人永将怀念他。
苗力田教授很重视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多方加以采用。首先是“我注六经”的 方法,就是首要地要钻研原著,吃透希腊哲学思想的本义,从中引出自己的解释和见解来。 他认为这是希腊哲学翻译与研究的最基本的扎实方法,并且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身体力行的。 西方20世纪研究希腊哲学的大家,从策勒、伯奈特、康福特、罗斯、泰勒到格思里等人,都 是用这种方法不断深化对希腊哲学原著的研究,使英国、美国、德国成为希腊哲学研究的重 镇。“六经注我”的研究方法则是指当代有些哲学流派的大家,非常重视用自己的哲学学说 研究希腊哲学,并将这种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哲学学说作为有机构成部分,如尼采和海德格 尔 对早期希腊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苗力田教授对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是关注 的。
20世纪西方新创的研究希腊哲学的总体性方法主要有三种,苗力田教授也都重视或采用。 一是德国耶格尔的发生学的方法,即强调要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本人的哲学思想有 个演变过程。陈康先生最早将这种方法引进中国,他自己用这种方法研究希腊哲学,取得了 独创性成就。苗力田教授得老师真传,很重视用这种方法治学。二是分析学派的方法,兴起 在20世纪中叶,欧文、巴恩斯等人抨击发生学方法,而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细密研究希腊哲学 范畴的意义。这种方法对考察奠定西方科学理性传统的希腊哲学,确实也是很有价值的。苗 力田教授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做细致的范畴意义的剖析,也可以说是采用这种 分析方法。三是解释学的方法,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等人建立哲学解释学后,在西 方盛行的研究人文学科包括希腊哲学的方法,强调联系语境对文本的意义或意义演变做出理 解与说明。记得1985年我较早在国内发表文章述评解释学时,苗力田教授看了就很敏感,和 我专门谈话,认为这种方法对古希腊哲学研究也是值得重视和采用的。
总之,在希腊哲学研究方法方面,苗先生不是固执一种,而是主张就具体研究内容,博采 众长,综合运用,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特色,获得我们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柏拉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哲学史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