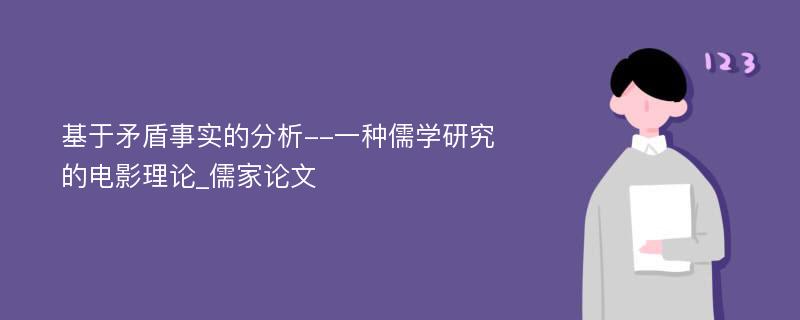
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儒学研究之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矛盾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11)04-0015-07
儒学研究已成为“显学”。此时检讨其研究方法无疑是必要的。本文试以从分析矛盾的事实出发,改进当下儒学研究的方法,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入。这一意图的明确形成,源自著名的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的论文《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①因此,先从陈康的论文谈起。
一、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从陈康的论文谈起
陈康这篇论文收在《陈康:论希腊哲学》,为这本论文集的最后一篇,也是唯一一篇讨论中国哲学的文章。它最初发表于1955年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第10卷第10期。当时台湾当局竭力复兴孔孟之道,试图以此救治日益沉沦的社会道德。如陈康所指出:“关于违反道德的行为一事实,人将它们归罪于现在人的不读经书。我曾听见过一位先生慨叹地讲:如若多数人皆读过‘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两句书,我们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状况”;但上述的“指责和感叹皆是出于情感。由情感可以产生出第一流的诗词来,然而不能产生出对于事实中肯的解说”。这些指责和感叹之所以只是出于情感,在于发出这些指责和感叹的先生“他们忘记,违背经义的行为在历史上无时没有,即在终日读经的时代也未尝稍缺,甚而违背经义活动的人即是读经的人。因此事实决非如此简单,只须读经,问题即可解决”。为了进行不是出于情感的“平心静气的分析”,首先要面对两个显著矛盾的事实:一方面儒家学说以关注人的道德行为作为“主要课题”,“两千余年来,儒者朝朝暮暮讲说仁义道德”;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注重道德行为,然而未尝得到应得的结果”。
陈康由此入手分析儒学,显然比仅仅阐释儒学说了些什么更为深入。事实上,他确是从中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他指出,理性、苦乐情绪、宗教情绪这“三种力量决定行为,使之合乎道德”;然而苦与乐具有相对性,因此苦乐情绪对于行为的决定性“飘浮不定”,作为遵守行为规则的心理“基础太薄弱,不可预期,不可信赖”,而理性和宗教情绪则具有“绝对力量决定人的行为”;按说“儒家所订立的行为规则原是学说的结论,它们是理性的产品。理性的产品本身可以为人的行为绝对遵守”,然而儒家“恐它们不能产生绝对的效果,于是要求人对它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可非议”,“要求人以对待神的诫命的态度对待学说的结论”,把“学说的结论教条化”了,这样“理性无所应用,它至多只能作些敷陈经义的工作”;但是,“学说终是学说,决非教条”,一旦“学说教条化了,它和人的内心可有的唯一的坚强联系,和理性的联系被割断了”,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它失去了为人绝对遵守的机会”,因为“它在人的内心里没有可靠的着落,即使人在口中人云亦云地背诵它”。这个观点对当今的儒学研究很有借鉴意义。当今儒学研究的重头戏是聚焦其现代价值,很多论著以为儒家经书可以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表现出把儒学奉若神明、不可非议的浓厚的教条化倾向;殊不知,这样反而可能使得儒学因失去规范人们行为的“坚实不摇”的理性基础而无法落实其现代价值,如陈康所指出的那样。
陈康在分析上述两个显著矛盾的事实时,至少揭示出其中蕴含着这样三方面的矛盾的事实:第一,“一方面是一部十三经,另一方面是违背经义的行为”,即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第二,儒学注重道德行为,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多数人并非道德君子,另一方面“社会上仍有些合乎道德的行为”,如杨震辞金,即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第三,儒家把“精力耗尽在四维八德的讲论中”,对此的一种评价是,这造就了“现在多方面称道的中国人本主义”,另一种评价是,这使得中国陷入“纯粹科学和它的产品一无所有”的“悲惨的境地”,即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本文依次从上述三方面的矛盾事实对儒学研究发表一些意见。
二、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分析:两种传统的区分
陈康揭示了十三经所说的与人们实际所做的相背离,分析这样的事实,对于儒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儒学文本的论述是否等于实际的儒学传统。现在用以揭示和阐释儒学传统的通常方法,是引证、排列儒家典籍上的种种论述,由此得出结论,儒学有怎样的传统。这固然是认知儒学传统的重要途径。但是,从陈康揭示的事实来说,由此得来的儒学传统其实只能说是“文本”上的传统,并不能等同于实际存在的传统。因而需要进一步分析文本传统为何不能等同于实际传统。
首先,前者是被倡导的,后者是被接受的;而被倡导的东西,在实际中有被接受的,也有不被接受的。只有在实际中被接受了,才能成为存在于社会中的传统。由此看来,儒学的某些传统只是属于在文本上倡导的,它们并没有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实际的传统。这一点鲁迅曾辛辣而冷峻地作了揭示:“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1](P507)比如,先秦儒家都讲重义轻利,其宣传对象主要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国君们看来没有接受如此的教化,要不然就不会有春秋战国无义战这一说了。这意味着重义轻利并不是先秦实际存在的传统。以后的儒学文本一再申述重义轻利,理学甚至将其提升到理欲之辩的高度,要求“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因为事实上它没有被普遍接受。所以,重义轻利只是文本上的儒学传统。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在考察重义轻利的儒学传统的现代价值时,探讨它为何不能在古代成为实际的传统或许要比探讨它在今天有哪些价值更有意义。
其次,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而抽象的观念一旦转化为具体的存在,其形态必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就是说,当文本上观念形态的儒学传统成为实际存在于人们行为中的传统时,后者所呈现的情形是很不一致的。比如,“内圣外王”的儒学传统实际存在于古代社会不同阶层时,情形各异。对于皇帝来说,“内圣外王”大体上是由“王”而“圣”,其逻辑是只有圣人宜于作王,既然已是“王”,那必然“圣明”。所以几乎每一个皇帝都以“圣王”自居。对于儒生士人而言,一般以“内圣外王”为抱负。这表现为或是以做帝王之师为己任,用“内圣外王”来塑造帝王,如程颐任“崇政殿说书”,便说“得以讲学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尧、舜、禹、文、武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②;或是实现立言、立德、立功之“三不朽”,如王阳明就是典范,康熙时有人赞曰:“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精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2](P1620-1621)而在农民那里,“内圣外王”主要转化为渴求“圣明天子”和圣王并举的好官替他们做主。儒学传统在实际中的多样性,是其价值不同侧面的反映。因此,我们关注儒学的现代价值,在方法论上应当考虑其原本存在的这种多样性。
再次,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文本上的儒学传统是以概念、范畴、命题来表达的,这些概念、范畴、命题有其相对确定的涵义;而实际的儒学传统则处于活生生的变动之中,它为了应对实际社会的变化,在原有概念、范畴、命题的名号下与时俱进,在变动中既保持着传统的一贯,又使得传统绵延不绝而产生新的生命力。讨论儒学的现代价值,这在方法论上是特别需要提出的。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实际产生影响力的儒学,基本上不是静滞在文本中的东西,而是经过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淘洗,其内涵整合了异质文化尤其是西学,在动态的自我更新中获得了与现代价值的相匹配性。比如,现在常常讲的“天人合一”,继承了天人和谐的传统,但原先“天人感应”、“天命论”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色彩在近代以来一直遭到批评,已经被消解了,并且融进了来自西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对科学主义的现代反思。再比如,我们今天把奔“小康”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最初一步,这果然表现了儒学“大同”传统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无疑是建立在近代以来把“大同”作了现代性解释或社会主义理解(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之上的,而这种解释和理解是以进化论或唯物史观为根据,否定了原先《礼记·礼运》里把“大同”看作是返回三代的复古主义。上述两例,无非是要说明: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在实际中的流变,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蜕变,是讨论儒学传统现代价值的重要基础。因为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讲,近代中国是刚刚逝去的“昨天”,蜕变于那时的儒学传统是对“今天”的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
将儒学文本传统和实际传统相区分,并非否认这两者的联系。事实上,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正是因为其文本的很多传统比较有效地转化于实际之中。然而,儒学文本的传统往往带有理想色彩,和实际是有距离的,因而区分这两种传统,对于儒学研究方法论来说,还关联着一个常常不为人注意的问题:文本传统是如何落实于实际的?其实陈寅恪早就揭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儒学之“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3](P6-7);“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而“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汉承秦制,“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4](P440)。明了儒学的文本传统在古代怎样依托制度(法典)而成为实际的传统,是实现儒学现代价值的题中之义。余英时曾说:“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将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5](P267)这个难题不解决,所有关于儒学现代价值的讨论,只是纸上谈兵的空话;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借鉴历史的经验显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目前阐发儒学现代价值的论著中,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三、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分析:理论内在的两面
陈康说儒学的“主要课题”是人的道德行为,意味着成就君子这样的理想人格,是儒学在理论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其造成的结果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即真君子和伪君子同在。如果不回避这样的事实,那么在儒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显然需要分析同一学说为何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当然和不同主体对同一学说的认识以及贯彻的不尽相同有关,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其原因在于儒学理论内在的两面性。就是说,只有揭示这样的两面性,才能有效地解释同一学说产生正负结果的事实。这里试以《论语》的君子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论语首末二章义》认为,《论语》首末章都论述君子,意味着君子论贯串于《论语》的始终。孔子要求君子表里如一、言行如一。所谓“君子坦荡荡”、“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表明孔子强调君子人格的真诚性,而对虚假的伪君子则不齿。但是,在儒学的熏陶下,之所以孕育出真假君子同在的结果,这与孔子君子论具有两面性是分不开的。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6](《雍也》)孔子对君子规约于礼,其理论内涵有着循规蹈矩和勉强克己的两面性。
孔子以礼制约君子,并对僭礼的行为深恶痛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6](《八佾》)意在强调君子必须循规蹈矩,即完全合乎礼之规定。这意味着孔子认识到人格的确立必须遵循作为社会规范的礼。正是有见于此,孔子把“立于礼”作为成人之道的必经阶段[6](《泰伯》)。个体作为人格的承担者,在刚降临世间时,只具有自然的本能,只有经过社会化的过程,才能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人,而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就是对于社会规范的认同。就此而言,人格确立是以个体认同社会规范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要求君子对于礼必须循规蹈矩,由此表现为恪守礼义的真君子。
礼对个体的行为方式有着颇为繁复的规定。为了不违背这些规定,孔子便相应地对君子的言谈举止等提出了十分精细的要求。例如《泰伯》记载:“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从容貌、脸色以及说话的言辞和声调等方面规定了君子应当做到不粗暴无礼。这虽是曾子所言,但应该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因为即使是穿衣戴帽之类,孔子也不厌其烦地作出规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有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齐,必有明衣,布。”[6](《乡党》)这一长段话通篇是讲君子在什么场合、什么季节,穿什么样的何种颜色的衣服、戴什么质地的帽子、佩带什么样的饰物等才是合乎礼的。《论语》中类似的记载还有相当的篇幅。孔子进行这些近乎琐碎的教诲,是为了确保君子的表现时时事事合乎礼之规矩。当然,循规蹈矩还意味着承担礼所规定的责任,因而真君子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具有社会中坚力量的担当。每个个体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占有某种位置,这种位置就是所谓的社会角色。例如,君臣父子都是特定的社会角色。礼的种种规定虽然繁复,但其功能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使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其所处的社会角色相一致。因此,对君子约之以礼,也就是要求其按礼的规定承担好某种社会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6](《宪问》)君子以礼来规范自己的外在行为,就是使之与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社会角色)相吻合,由此显示出对社会的责任。具体的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大约有两个方面:家族方面和社会方面。关于前一方面,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6](《泰伯》)君子如果能按照礼的规定来履行家族内部关系中的社会角色(笃于亲),那么整个社会就仁德勃兴。关于后一方面的社会角色,大致可分为入仕和在野两类。孔子认为入仕的君子应当像子产那样,成为君主的忠臣和百姓的清官: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6](《公冶长》)。在野为民的君子,孔子认为不仅要修己,还要教化百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颜渊》)。由上述可见,君子无论是承担哪一方面的社会角色,都体现出社会中坚的责任担当。因此,曾子认为君子在社稷危难之际具有力挽狂澜的责任:“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6](《泰伯》)
君子对礼的循规蹈矩,以“知礼”、“学礼”为基础。从《论语》的记载里,可以看到“知礼”、“学礼”贯穿于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中。礼由学而知,以博学于文作为约之以礼的前提,③意味着循规蹈矩是出于理性的自觉,即对礼的规矩应当充分认识其意义,从而就能做到“好礼”[6](《子路》),即自觉地予以遵循,而不会僭越。不过,孔子的循礼而行的理性自觉与出于意志自由的自愿是分离的,这在其君子论表现为勉强克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并进一步将其规定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颜渊》),要求自我把一切言行举止全部纳入礼的规定之中,意味着礼成了人为的非出于自愿的强制性的绝对命令。孔子的老友原壤坐相放肆,“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在孔子看来是完全无视礼义规矩的小人,因而怒斥他“老而不死,是为贼”,用手杖叩其胫[6](《宪问》)。可见,孔子对于种种僭礼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正是希望礼成为具有强制性的规矩。他的“正名”论,就是主张按照礼的名分强行匡正与此不符的现实之“言”和“事”,认为这是君子必须认真做到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6](《子路》)。同为儒家的荀子对孔子这样的克己循礼颇有微辞,《荀子·宥坐》记载了孔子称言行逾越常规、“强足以反是独立”的少正卯为“小人之桀雄”而予以诛杀的传说。荀子还指出:“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孟子之妻仅因坐姿不雅,就被孟子视为无礼,予以驱逐,荀子认为这是把自我强行纳入礼之规矩,并不足取,因为“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正是有见于此,他特别突出意志的自主性,“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7](《解蔽》)。如果违背主体意愿强行克己复礼,那么循礼而行就会蜕变为虚伪的矫饰。因为不是出于自愿,就没有真诚性可言,由此勉强而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表面与礼契合而实际与此背离的伪君子。自愿与自然在排斥强制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因此,主张自然原则的先秦道家对于儒学礼义由人为强制而导致的伪饰提出了很多批评。《老子》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礼由人制订出来,但没能得到大家的响应,于是只能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去强拽别人,于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忠信淡薄意味着礼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因此《庄子·知北游》在解释老子这段话时说:“礼相伪也。”《庄子·盗跖》指斥孔子讲究礼义,是“矫言伪行”的“巧伪人”,矛头所向正是礼义“强反其情性”、“不能说其志意”的强制性;并指出孔子的“正名”,实际上是“君子殉名”即牺牲自己真实本性的异化:“变其情,易其性,则异也”,由此礼所看重的五伦不能不成了“儒者伪辞”。此后理学借用道家原意为自然之理的“天理”来阐释勉强克己之礼,“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试图淡化其强制性的弊端。
以上是以孔子君子论的两面性,来说明如果正视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结果具有正负两面的事实,那么分析其理论内涵的两面性,在方法论上是必不可少的。罗素在叙述西方哲学史时说道:“有两件事必须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完全的最后的真理。”[8](P67)然而,在眼下众多研究儒学的论著中,罗素要求牢记的方法基本消失了。
四、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分析:传统现代的互补
陈康指出对于儒学存在着两种相反评价:一是认为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不适应,一是认为儒学人文主义有现代价值。应当说这两种评价共存是“五四”以来的事实,但它们往往是此起彼落。从“五四”到1980年代末,前一种评价占据主导地位,即对“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遵从之价值”作了否定性的回答[9](P81)。从1990年代开始到现在,后一种评价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标志是现代新儒家的话语成了儒学研究的引领者和规范者。因此上世纪末涌现的很多儒学研究的论著,对于“五四”以来的前一种评价或简单地扣以“激进主义”的帽子而不屑,或予以回避而不置可否。如果我们既正视前一种评价对于近代中国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具有正面作用的事实,也正视后一种评价对于推动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作用的事实,那么就儒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则有个基础性的问题必须回答:既然肯定批判儒学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必要的,那么仍在继续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今天,儒学何以有了正面的价值呢?
这需要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曙光升起于近代的启蒙运动。启蒙的重要涵义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传统性成了每个旧秩序批评者无所不在的敌人”[10](P8)。中国近代以来对于儒学的批判,深重地打上了西方启蒙运动的这种影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涂尔干、齐美尔,开始走出启蒙运动将现代与传统对立二分的框架[11](P30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迪南德·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即Gemeinschaft(共同体或公社)和Gesellschaft(社会),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是前者的主要纽带,“这种Gemeinschaft的典范是家庭”,而契约、交换和计算关系则在后者中通行,“这些关系源自个人决定和自身利益”;“在这里,人人都得靠自身,人人都是孤立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紧张”。他指出传统的共同体关系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趋于解体,“欧洲社会已经从Gemeinschaft关系转向了以协议和契约为基础的Gesellschaft关系了”,这样的转向有其积极作用。因为尽管“一个以Gemeinschaft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常常令我们感到‘温暖’、‘亲密’,且以‘私人关系’为特征。然而,这些前现代的特征,常常会伴随着广泛的腐败、裙带关系以及法规的根本缺陷”。但是Gesellschaft关系导致“竞争和利己主义变得越来越强势”,因而尽管通过契约、规章把彼此异己的个人组织起来,但这只是一种“机械的团结”,而不是Gemeinschaf关系所建立的情感真挚和融洽的“有机的团结”。滕尼斯认为将这两者结合是可能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试图将Gemeinschaf关系和安全机制引入Gesellschaf 的努力(社会政治、福利国家等)”。④这些观点包含的洞见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明对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具有互补性,理想的文明形态应是两者的互补。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述关于传统与现代具有互补性的思想,成为后现代思潮里的重要一脉。希尔斯的《论传统》是其中的代表作。希尔斯在该书中指出,兴起于西方并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破坏着“实质性传统”。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发展’理想要求人们与传统的观察方式和行事方式决裂”。希尔斯肯定源于启蒙运动的西方现代文明“也属于我们文明的宝贵成就。它把奴隶和农奴改造成了公民;它解放了人类的想象和理智能力;它使人类有可能得以实现美好的生活”,但其代价是“实质性传统被许多人肆意破坏或抛弃,这导致了许多为良好秩序和个人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的丧失,同时也造成了普遍蔓延的社会混乱”[10](P384-385)。然而,在现代化凯歌行进中,“实质性传统还继续存在,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仍未绝灭的习惯和迷信的表现,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天生就需要它们,缺少了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于是“它们退到了社会中更为隐蔽的部分,但它们会通过复兴和融合而一再重新出现,而且现在依然如此”。所以,在他看来在理想的文明形态中,“传统应该被当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就是“将某些启蒙传统与启蒙运动后继人试图加以抛弃的某些传统结合起来”[10](P440-441)。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何以在现代化进程中由负面价值转为正面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础,更深刻地论证了现代与传统的互补性。他们以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指出取代现代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的理想文明形态将是现代与传统的互补。1861年梅因出版了《古代法》,它由分析家庭父权入手,提出了著名的观点:“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滕尼斯用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来描述欧洲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显然是受到了梅因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意到了梅因的观点,指出:“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因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流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12](P75-76)不过,《共产党宣言》同时指出,这一进步也造成了新的不和谐,即建立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种种对立和紧张,这些对立和紧张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异化。因此,只有消灭这样的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才能形成和谐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表现了由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螺旋式上升,由于这个运动过程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因此资本主义之后的文明形态就应当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现代资本主义这两种文明形态的互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有句名言:“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13](P109)此中有一以往被忽略的涵义:当资本主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即由其基本矛盾产生的很多弊端得到较为充分暴露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传统是宝贵的,并应当在后资本主义文明中重新再现。⑤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马克思把古希腊文明与现代文明作比较,把前者比喻为人的纯真童年,然后说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13](P114)马克思还在比较古希腊和现代资本主义时,指出前者的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后者,但是“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高尚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因此,“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鄙俗的”[14](P486-487)。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是对上述古代的高尚传统在更高阶段上的复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关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称它“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12](P443),这表现为该书结尾时写道:在“以财富为唯一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之后,“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以肯定的态度摘录这段话,后者还同样以这段话作为结尾。⑥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些“再现”、“复活”,都蕴含着将前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这两种文明互补的意味,而这正是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运动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以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作为儒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就能认识到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负面价值转为正面价值,体现了传统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逐渐显示出与现代互补的历史辩证法。因此,儒学研究既不是简单地否定激进主义,也不必曲意回护儒学前现代性的某些传统(如轻视妇女、亲亲互隐等)。
注释:
①参见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以下陈康的引文同此,不再注明。
②《二程全书·伊川文集》卷二,《在辞免表》。
③颜渊说孔子对其的教育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
④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第531-5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对于滕尼斯思想的叙述,均出自该书和于海的《西方社会思想史》有关章节。
⑤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不少思想家把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归咎于传统的丧失,其实是对马克思此一涵义的某种证明。
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97-39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1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1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