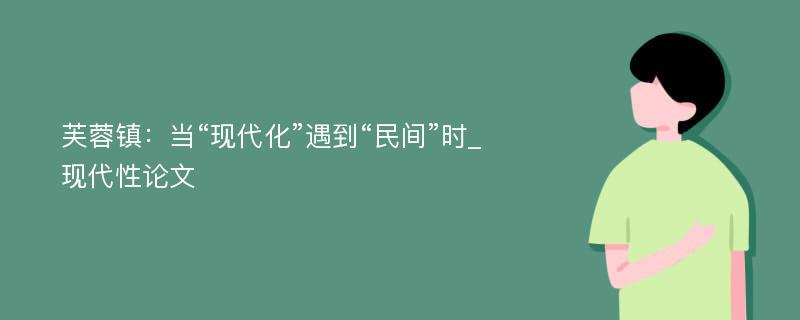
《芙蓉镇》:当“现代性”遭遇“民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芙蓉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兴衰“芙蓉镇”
1981年《当代》第1期,《芙蓉镇》发表,次年,该作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芙蓉镇》仍然是一部不错的小说,虽然只有薄薄十五万字,但在五届二十二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它丝毫不显得寒酸。
经历了文革极左文学“高大全”然而“生冷硬”美学风格的长期窒息,经历了文革后“伤痕文学”泛情然而粗糙的直白宣泄,《芙蓉镇》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中含喜、哭中作乐的整体美学品格,和它展开时充满浓郁湘南气息的民俗画卷让人耳目一新!主题上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要求,艺术上充分显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芙蓉镇》的大受欢迎顺理成章。
1986年,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问世,当年即连获国内“金鸡”、“百花”大奖和捷克、德国、法国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至此,《芙蓉镇》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但此后,当人们提起《芙蓉镇》时,谈论的往往是谢晋和他执导的影片,而不是小说《芙蓉镇》和他的作者古华了。进入九十年代,这部曾轰动一时得到文学界公认的好小说如同《李自成》、《将军吟》、《黄河东流去》等其他获茅盾奖的作品一样,已经基本没有新读者了。这与另外一部获奖小说《平凡的世界》恰形成鲜明对比——《平凡的世界》艺术上朴实无华,却获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上述两部作品命运的反差并不是什么难解释的问题。从表层内容看,《芙蓉镇》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政治批判剧”,有鲜明的时效性,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读者群的更新,它自然会失去轰动效应;从深层母题看,《芙蓉镇》重述的是“好人蒙冤”母题,这个文革年代的“公共体验”对新时期以后的大多数人来说,却难以引起太多共鸣;而从艺术上看,《芙蓉镇》是一部典型的文人小说,它不追求一个紧凑的环环相扣的故事,而力图通过对一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时代变迁。它与同时出现的汪曾祺的诗化民俗小说一样,文笔平和冲淡、节奏悠闲从容。这样的艺术风格,对于市场大潮中忙于消费文化快餐的新一代读者来说显得过于古典。而反观《平凡的世界》,尽管出场人物不少,但核心就是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故事线索非常明确。更重要的是,孙家两兄弟的故事暗合了“个人奋斗”“向上爬”的“灰姑娘”母题和爱情上的“青蛙王子与公主”母题,在今天这个鼓励个人奋斗,社会上到处都是挣扎着、奋斗着、渴望好命运的“灰姑娘”的时代,《平凡的世界》的久盛不衰,难道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么?
二、民间:“现代性”隐蔽的对立面
《芙蓉镇》当年的成功大抵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二是它语言上的地方特色,而当它被改编为电影时,一方面出于导演的个人理解,一方面也由于电影这种艺术样式与文学的不同,前者得到了强化,后者——它在语言上的魅力却无法得到体现。而当《芙蓉镇》的价值仅仅体现为政治批判意义时,一旦改革开放的“向前看”取代反思批判的“向后看”成为时代主旋律,它自然就淡出了历史舞台。《芙蓉镇》可谓“兴在政治批判,衰也在政治批判”。
但是,《芙蓉镇》是否真的已丧失了与当代社会的对话能力,只能作为新古董列身于中国文学博物馆?它的价值是否真的只是时效性的政治批判?重读《芙蓉镇》,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突破以往把《芙蓉镇》只视为政治批判剧的思维限制,应当把它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来理解——这个话语空间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广阔层面的“现代性”研究话语,而一旦如此,这部“过时”的小说立刻就获得了崭新的当代意义:事实上,《芙蓉镇》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性”试图对“民间”进行“同质化”改造,但最终失败的故事。它是一个现代性的寓言!
最近十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现代性话语置换阶级分析话语。这种置换当然不是出于一种话语时髦,而是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无庸置疑,作为资本主义最彻底的批判者,当人们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时,马克思主义就表现为现代性的批判者。但是,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模式,由于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也就是说由于“反思”和“自我批判”这个现代性题中之义的存在,现代性事实上存在多元形态,其中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之所以这样说,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基础上的“宏大叙事”,它在许多理论预设和思维方式上都是属于现代性的。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史,就是一个从“前现代”不断获取“现代性”而走向“现代”的过程,一个某种特定的现代性方案在中国扩张、实验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克服对象、作为“现代性”对立面而存在的始终是中华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性”。在中国,整个20世纪的时代主题,都可以被约化为“现代性”对“地方性”的统治、驾驭、改造和同化。这个主题,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曾经“表现”和“被表述”为:党对群众的教育、改造和领导,先进的革命理论对自发反抗情绪的驾驭等。
人们习惯用“地方性”、“民族性”、“中华性”来指称“现代性”的摩擦面,但事实上,上述“能指”都未能抵达问题的核心。因为在国家制度、生产方式层面上,“现代性”的形式实现并非难事,“地方性”、“民族性”很容易让位于“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制度。真正顽强地对现代性的同质化之路构成掣肘的是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民间”,因为民间是“传统”、“自性”——在某些人那里被称为“惰性”真正的栖身地,“现代性”的扩张事实上是对这种“民间”的占有和改造。《芙蓉镇》所表现的正是外来的现代性方案侵入象征民间社会的古镇,打破民间社会的平衡,但最终又恢复平衡的原型故事。“平衡——打破平衡——重归平衡”,这是一个原型结构,它让人想起四季轮回、日月圆缺、投石池水等最普遍的自然现象。
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范式的整体方案,它对民间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改造无从分析,事实上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一是“伦理关系”,一是“话语体系”。两种生活范式的差异最深层地体现在人际关系这一伦理层面,而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层面——从鲁迅笔下阿Q的“柿油党”(自由党)到张炜《九月寓言》中的“革命拣鸡儿”(革命阶级),两种生活范式的冲突和纠葛总会在语言层面留下痕迹。在《芙蓉镇》中,就始终存在两套伦理标准——一套是“素朴的民间伦理”,一套是现代的“阶级伦理”,同时也始终存在两套话语——一套是“官话”,一套是“方言”。现代性与民间之间的较量就体现为两者之间的纠葛。
三、李国香与王秋赦:失败的现代性方案
如果我们把芙蓉镇上米豆腐摊摊主“芙蓉姐子”胡玉音看成民间性的象征,李国香则无疑是现代性的符号。她出场的身份是“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是个“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的“外来干部”,她的出场动作是——“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立眉横眼地把戴了块‘牛眼睛’(手表——笔者注)的手伸了过去:‘老乡,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而当众人纷纷打圆场时,她“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李国香一亮相就作为“他者”站在了芙蓉镇这个民间社会之外,她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现代标示”确立的。而这个现代性的载体,当她还仅仅是一个饮食店的经理时,就自觉地以改造芙蓉镇为己任了。
一年以后,当李国香重返芙蓉镇,她的身份明确为政治化的“县委社教工作组组长”。所谓“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是发生在1963年到1966年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在城市以“新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在农村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中心,目的是要“挖掉所谓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不变色”。这场运动本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统一民间思想的运动,是一次现代性的扩张垄断过程。
以政治身份出现的李国香,其权威性首先体现为一套“神圣话语”。小说多次强调李国香的口音是“一口和悦清晰的本地官话”,她讲话的内容则是“一口一个马列主义,一口一个阶级斗争,‘四清’‘四不清’。讲三两个钟头,水都不消喝一口,咳都不会咳一声,就象是从一所专门背诵革命词句的高等学府里训练出来的”。她工作的方式是“注重搞串联,摸情况,先分左、中、右,对全镇干部、居民‘政治排队’,确定运动依靠谁,团结谁,教育争取谁,孤立打击谁”。而工作的目的,则是“依靠贫雇农,打击地富反坏右,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李国香所做的实质上是用现代阶级关系替代芙蓉镇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民间伦理。
经过李国香的改造,古老的芙蓉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那个生机勃勃、温情脉脉、和谐的民间社会没了,代之以“现代”然而“紧张”的“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这种改变体现在伦理层面,是“人和人的关系政治化”了:
“镇上制定了‘治安保卫制度’,来客登记,外出请假,晚上基干民兵查夜。并在街头、街中、街尾三处,设有三个‘检举揭发箱’,任何人都可以朝里边投入检举揭发材料,街坊邻居互相揭发可以不署名,并保护揭发人,……确立了检举揭发制度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每天天一落黑,家家铺面都及早关上大门,上床睡觉,节省灯油,全镇肃静。就是大白天,街坊邻居们也不再互相串门,免得祸从口出,被人检举,惹出是非倒霉。原先街坊们喜欢互赠吃食,讲究人缘、人情,如今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只好互相竖起了觉悟的耳朵,睁大了雪亮的眼睛,警惕着左邻右舍的风吹草动,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再者,如今镇上阶级阵线分明。经过无数次背靠背、面对面的大会、中会、小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排队,大家都懂得了:雇农的地位优于贫农,贫农的地位优于下中农,下中农的地位优于中农,中农的地位优于富裕中农,依此类推,三等九级。街坊邻居吵嘴,都要先估量一下对方的阶级高下,自己的成分优劣。”
芙蓉镇的“现代化”,其民间伦理关系的政治化,反映在话语层面,一是街上出现了大量政治标语;什么“兴无灭资”、“农业学大寨”、“保卫‘四清’成果”、“革命
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当然最革命的还是李国香在工作队驻地吊脚楼的对联“千万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永远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谈话中,现代性的政治
话语也替代了朴素的民间语言,连小孩子也在用这样的语言抱怨着:“唉,背霉!生在一
个富裕中农家里,一开口人家就讲我爷老倌搞资本主义,想向地主富农看齐”,“唉,
我爷老倌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这回参军就准有我哥的份”,“你晓得?贫下中农里头也
还有蛮多差别呢,政治历史清不清白,社会关系掺没掺杂,五服三代经不经得起查”…
看上去芙蓉镇已经被李国香们所改造,古镇已经“现代化”了,然而,现代了的芙蓉镇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而是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非和谐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李国香式的居高临下、试图通过压制消灭的方式全盘改造民间性的方案是失败的。当然这结论也早已成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李国香现代性方案的失败从另一角度反映在王秋赦身上。如果说胡玉音是民间性的正向标志,王秋赦就是民间性的负面符号,是民间劣根性的体现。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的是一种民间性的正向现代性彻底臣服靠拢的取向。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李国香的紧跟献媚,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对现代性话语的迷恋上。王秋赦与李国香的第一次交流,就使用了“现代政治语言”,他追问李国香这次运动“是不是象土地改革时那样”,“要不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他评价税务所长使用的话语是“官僚地主出身,对贫下中农有仇恨”,评价黎满庚“立场不稳,重用坏分子秦书田写这刷那,当五类分子小头目”。而他最风光的事情是从北方取经,取来了“三忠于”、“四无限”整整一套仪式,和一套完全不同于本土语言的“神圣话语”:
“王秋赦接着做开了示范的姿态、动作,但见他立正站好,挺胸抬头,双目平视,看着远方,左手下垂,右手则手臂半屈,握着红宝书紧贴在左胸心口上,然后侧身四十五度,斜对着光辉形象,嘴里朗诵道:
‘首先,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王秋赦在向群众传授这套仪式之后,他“豪情澎湃,激动万分,喉咙嘶哑,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无比高大,无比自豪,无比有力量,他就象个千年修炼、一朝得道的圣徒,沉湎在自己的无与伦比的幸福、喜悦里”。王秋赦的上述迷狂状态,是民间性对现代性彻底臣服的表示。但是芙蓉镇的吊脚楼最终倒了,彻底臣服于现代政治的王秋赦最终疯了,这就事实上宣告了民间性向现代性臣服之路的不通。
作为王秋赦的补充,黎满庚的行为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间性向现代性屈服的一面——事实上在古华的小说初稿里,王秋赦这个人物是不存在的,他的行为都由黎满庚来承担。起初,当入党(现代性的召唤)还是娶胡玉音(民间性的召唤)摆在黎满庚面前时,他并没有明确选择前者,尽管最终也没有选择后者,但毕竟有一刻“山里人纯朴的伦理观占了上风”,他庄严承诺“玉音妹妹……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但是,面对更为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妻子的威逼,他却“跟原先的那个黎满庚告别”了,交出胡玉音让他藏的钱款,出卖了自己最心爱的人。黎满庚面对谷燕山的指责,辩称“在党组织面前,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怕被开除党籍呀!妈呀,我要跟着党,做党员……”,这虽然有自我推托的成分,但也基本是那个年代的普遍事实。因此黎满庚的屈服就不仅仅是道德的亏欠,更是一种现代性的迷信。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李国香与王秋赦有过一段龊龊的结合,这意味着蛮横的现代性与恶劣的民间性之间有可能结成某种联盟,这种联盟的结果是芙蓉镇因此变成异化的世界。这样世界当然并不仅仅存在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今天仍然充斥着贫困、战争、腐败、专制、屠杀的拉美世界不也是如此么?从这个角度,《芙蓉镇》就显示了它普遍的当代意义。
四、谷燕山和秦书田:另一种现代性方案
与李国香体现的失败的现代性不同,在谷燕山和秦书田身上则预示着现代性与民间性成功结合的可能。这种可能不是通过现代性对民间性的改造,相反,它通过前者向后者的靠拢来实现。
谷燕山是一位南下干部,标准的公家人,在严肃场合,例如庆祝胡玉音新房落成的酒席上,他常常讲一口纯正的北方话。然而谷燕山之能被小镇人接纳成为“全镇人的老谷”,不是因为他有一口北方腔,而恰恰是这口北方腔必须“入乡随俗”,“改成镇上人人听得懂的本地‘官话’,“跟人打招呼,也不喊‘老乡’而喊‘老俵’”。
与李国香张口现代性话语不同,谷燕山即便谈政治也是:“小老俵,你闻出点
什么腥气来了么?”“唉,只要不生出别的事来就好……常常是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
”,他使用了典型的民间语言。不仅在话语上他尽力民间化、本土化,行为上也遵循民
间伦理规范——芙蓉镇上半大的男伢妹娃,多半都认了他做“亲爷”,而他为街坊评理
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矛盾激化,事态闹大”,这些做法都与李国香形
成鲜明对比。即便文革期间,“不铁硬了心肠,昧了天良,就做不得人”(黎满庚语)时
,他依然恪守民间道德,为秦书田和胡玉音证婚,在胡玉音生孩子危险之时伸出援手。
谷燕山对胡玉音没来由的关照,他的去势与胡玉音的长期不孕,他以胡玉音爱人的身份出现在医院,以及胡玉音给孩子取名“谷军”,这些都暗示了两个人之间的性联系。但是谷燕山并没有实质性地与胡玉音结合,这个关键性的情节是富有寓意的,它可以理解为谷燕山的现代性虽然真诚地向民间性靠拢,但却并没有找到实质性结合的通道。这条结合的通道是由秦书田找到的。
作为小镇上唯一的知识分子,无疑秦书田也是现代性的载体之一,但与谷燕山比较,秦书田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他出生于本土,另一方面他对民间文化表现出了痴迷般的热爱。秦书田曾大张旗鼓地率领县剧团到民间采风,独出心裁地把胡玉音的婚礼办成了民间歌舞《喜歌堂》的现场表演会,并从此与《喜歌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因为编演风俗歌舞剧《女歌堂》而获奖,也因此而获咎;他晚上睡不着时哼唱《喜歌堂》,在胡玉音的病床前,也以此来安慰和倾诉;他与胡玉音幸福时哼唱《喜歌堂》,痛苦时也哼唱。民间文艺《喜歌堂》成了秦书田与胡玉音结合的纽带。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关注民间文化在沟通现代性与民间性的重要作用。胡玉音对秦书田的接纳可以看成民间性对现代性的的接纳,但秦书田对民间文化的接纳,即现代性对民间性的接纳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作为民间性的载体,胡玉音娇好的面容、丰满的身体、美妙的歌喉、泼辣的性格,充分显示了民间的魅力。她强大的性吸引力,与李国香在同一问题上的处处碰壁,可以视为民间性在与现代性较量中的天然优势。但是优势不等于强势,面对咄咄逼人的李国香,胡玉音仍然表现出了柔弱的一面,随时面临被舍弃扼杀的危险,曾经与胡玉音热烈相爱的黎满庚不是就做出了自己的取舍么?然而值得玩味的是,知识分子秦书田自始至终都是胡玉音价值的发现者和保留者——胡玉音结婚时,她民歌演唱的才能就在秦书田的安排下得到发挥;而当丈夫黎桂桂自杀,众人皆如瘟神般躲避,胡玉音一个人在坟地里精神恍惚呼天抢地时,又是秦书田亲近并保护了她;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秦书田处处保护着胡玉音,以至在布置批判会场时细心地不在胡玉音的名字上打叉。秦书田与胡玉音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可以被解读为知识精英与民间的关系,即民间的魅力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发现,也只有知识精英才能保护。当然在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状态除了知识精英与民间最终结合外,这种结合还必须得到政治精英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在秦书田与胡玉音的秘密结婚仪式上,谷燕山恰当地出现并担当了证婚人的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想大于形象”是一切优秀作品的“通病”,这就意味着,一部优秀作品,它的意义往往会溢出其表层故事,作为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芙蓉镇》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我们上述对《芙蓉镇》的解读主观比附的色彩过重,但是在“革命话语”失效,并因此殃及那些曾为“革命话语”垂青的作品,它们面临被打包放进文学博物馆之际,我们的上述尝试就不是一次无谓的文字浪费。事实上,一件事物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往往由它所放置的语境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