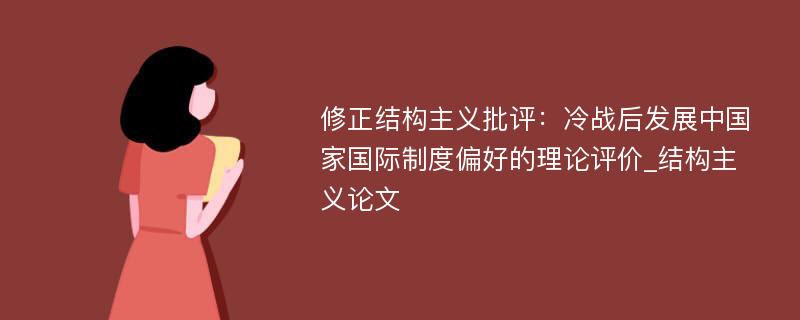
修正结构主义批判——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际制度偏好的理论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战后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习惯于认为,现存的国际制度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建立起来的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结构特点决定了它们与自由规范的国际制度是不相容的,因 而倾向于采取拒绝加入或反对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南北关系研究领域里的修正结构主义 理论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看法,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制度偏好假定为物质性和内生性, 忽视了其先验性和外生性的一面。本文从修正结构主义的基本命题入手,在理论和经验 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制度偏好与行为方式。
一、基本命题
研究南北关系主要有三种主流理论:自由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理 论。(注:Joan Edelman Spero,Jeffrey A.Hart: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fifth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p.149— 156.)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现存的国际体系结构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好的 框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在于其国内经济政策导致了市场缺陷,土地、劳动力和资 金等资源的低效利用和社会政治的僵化。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市场导向的国内经济政策 ,然后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贸易、对外投资和国际援助来促进经济发展。(注:参见
Walt W.Rostow,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Harry G.Johnson,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New York:Praeger,1967.)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位,国际市场 处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只是有利于发达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从不发达国家中榨取经济财富,其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民众 的更加贫穷。因此,处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扭曲的 和部分的,唯一合适的发展战略就是革命性地摧毁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然后用国际社会 主义体系取代它。(注:参见Samir Amin,Unequal Development: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 6;Fernando H.Cardoso and Enzo Falett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由发 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结构使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况和依附地位长久化,无规则的国际 贸易和资本运动深化了国际不平等,只有从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对国际体系进行改良 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四种政策变化, 即进口替代工业化、扩大南北贸易和投资、地区一体化和人口控制。结构主义理论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虽然都强调国际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作用,但两者在如何对待国际体 系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认为只需要对国际体系结构进行改良就可以了,而后者却坚持 认为必须摧毁现行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用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取代它。(注:参见W.
Arthur Lewis,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Joha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No.8,1971.)
结构主义有传统结构主义和修正结构主义之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国际政 治看成是国家间的“零和”冲突,认为制度只是权力组合下的一个小小的变体,缺乏自 主性,而后者则强调制度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政治权力在制度创建中的重要性。以斯 蒂芬·D·克莱斯勒为代表的修正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在 国际上和国内的脆弱性而倾向于支持和建立权威导向分配的国际制度。克莱斯勒从这个 基本命题出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这种国际战略和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市场原则 和规范之间的“非相合性”,由此得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是冲突性的 结论。(注:修正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 D.Krasner),他在 Structural Conflic: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中系统地提出了南北关系研究中的修正结构主 义理论。克莱斯勒关于南北关系及其制度性分析的著作和文章有:“North-South
Economic Relations:The Quests for Economic Well-Being and Political Autonomy ”,in Kenneth Oye,Robert Lieber,and Donald Rothchild,ed.,The Eagle
Entangled(New York:Longman,1979);“Transform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What the Third World Wants and Wh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No.25(March 1981);“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Spring,1982);“Third World
Vulnerabilities and Global Negoti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9(1983);“The United Nations and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in T.T.Gati,ed.,The US,the UN,and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Chang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
修正结构主义提出这个命题的基本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国内方面的“脆弱性 ”使它们难以应付外部体系的冲击。具体说来,在国际经济体系结构中,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规模小,发展程度较低,除了极少数国家有望对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国际环境施加广 泛的影响外,它们都处于极度不利的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巨大脆弱性是促 使它们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制度的最大动力。从国内结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政治体系僵化导致政 权能力有限和政策选择手段匮乏;税收结构决定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际经济的波动;意识形态和个人领导因素。发展中国家国际国内方面的脆弱使得它们无 力去影响和控制外部体系,虽然市场导向的制度能给它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全球经 济的波动会威胁到它们的国内稳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退出国际 体系,要么改变国际游戏规则。
二、理论批评
从理论层面看,修正结构主义主要采用的是结构分析方法,它充分利用了国际权力和 国际制度两个概念,认为一国的行为是由其相对权力大小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结 构和国内结构两个方面都处于脆弱状态,国际体系结构的权力分配严重失衡,这使它们 在面临外部压力的冲击时显得非常虚弱。为了维护国内政治完整和对外部环境有更大的 控制力,它们的国家政策选择是倾向于支持或建立权威导向分配的国际制度。而国际制 度的结构性特征却是自由主义原则,强调的是市场导向分配制度,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南北方国家在制度偏好上出现根本性分歧。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能 力来影响和改变既有的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又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迎合发展中国家 的需求,由此,南北方国家关系注定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并且在长久的未来不可能改 变。
这就是修正结构主义用以支撑上述命题的基本逻辑,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权力特征。 这套逻辑涉及到三个关键的国际关系要素,即国际制度特征、国家偏好和政策选择,它 们是修正结构主义理论用来分析国家行为的关键理论环节。我们有必要对这三者逐一进 行探讨,以便发现修正结构主义上述命题的理论薄弱之处。
修正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即现存的国际制度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 北方发达国家根据自由主义规范和原则创建的,它们反映了北方国家的偏好和利益。这 些制度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是相冲突的,即“非相合性”(incongruence), 由此决定了南北方国家在制度偏好上出现根本性的分歧。这是一种静态的现实主义结构 观,强调的是权力性因素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制度中的其它重要因素,如制度的合作 性激励因素和规范化效应。虽然克莱斯勒也强调制度的自主性,但他是从“权力分配格 局与制度特征的不一致”(注:克莱斯勒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 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来规范它。而且,他坚持的制度 自主性含义更多的是指制度的继续维持和制度本身的偏好,而不是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 响。国际制度的自主性不仅仅包括权力的内容,它还包括合作和规范化;国际制度的规 范和原则也不只是被动的存在,它会通过内化的进程使南北方国家的偏好和行为都发生 改变。正如玛莎·费丽莫所说的那样:“规范是共同拥有的、社会的,它们不仅仅是主 体的,而且还是主体间的。”(注: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 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对于国家偏好的认识,修正结构主义没有跳出传统理论的窠臼,从物质权力的角度出 发,认为国家偏好是既定的,它来源于国家的客观条件和物质特征。发展中国家对权威 导向分配国际制度的偏好来源于其国际和国内的物质结构特征,即脆弱性。修正结构主 义又从国际权力分配结构的角度进一步认为,南北方国家在偏好上的根本分歧是构成其 基础的国家权力能力差异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国家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并不植根 于国内需求和国内条件,也不完全局限于物质状况。由于国家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 ,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国家常常采取“模仿”的理性选择战略,彼此之间互相学习。 这种学习的动力来自国内,但学习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来自国家外部环境,因为国家是“ 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而不仅仅是自主的行为体,国家所处的社会体系限定了国家偏 好。但是,国际体系结构不一定是物质的,它也可以是社会的,即社会建构的规范、原 则、规则和共同信仰等。这些社会建构因果变量塑造了国家的偏好,从而使偏好内生化 。“偏好受到社会规范、文化上的决定性角色与规则和历史上的偶然话语的强烈影响, 并且常常由它们所构成。”(注: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第19—2 0页。)
修正结构主义不但强调制度内国家物质权力的主导作用,而且认为国际权力分配状况 决定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国际权力分配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处于极度弱势地位的发展 中国家为了维护国内政治完整和应对外部体系的压力,不得不选择反对自由主义原则和 规范,支持和试图建立权威导向国际制度。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是增加物质资源的流动和 创造一个预见性更强、更加稳定的外部环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国际行为, 是因为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是国家间的权力和能力分配。(注: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o.36,Spring,1982.)
修正结构主义强调国际权力分配状况与国家政策选择之间的联系,但是并没有推断出 两者之间明确的因果利益联系。这是一种简单的论断,即认为地区外部环境和结构,决 定了地区内部行为者的选择偏好。阿瑟·斯坦(Arthur Stein)认为,除了权力分配这样 的结构性因素外,“其他一些结构性因素,如知识的性质和技术的性质,也决定了行为 者的选择偏好和对制度的预期”,“国家的内部特征也是其行为选择的基础”。(注: 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 1年版,第48、49页。)
就国家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而言,作为有限理性行为体的国家,其政策选择并不是仅 仅依据其所处的权力地位,它还受到国家对自我利益的界定、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国际 规范和原则的禁制以及国内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基欧汉就认为,决策者在实践中 远非受外部环境的决定,而是均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注:罗伯特·基欧汉著, 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35页。)我国学者苏长和从国内结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角度提出:“在对国际制度 的遵守和承诺问题上,民主国家的信誉并不见得一定就很好,而那些中央集权国家的信 誉也不一定就很差。”(注: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 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8页。)即便从权力本身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权力 分配中的劣势地位也并不一定导致其反对自由主义规范,从而使南北方国家的合作总是 充满“紧张和冲突”。除了前面提及的制度的规范化效应外,国家自身的“学习”能力 、制度的互惠机制以及被基欧汉称为的“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t)(注: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第148页。)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国家的政策选择。
三、经验分析
如果说修正结构主义的命题存在许多理论漏洞的话,那么它据此推导出的结论在经验 上就很难站得住脚。令修正结构主义者难堪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不但 没有退出国际体系,反而以惊人的速度参与各种国际制度,包括所谓的“市场导向分配 ”国际制度。而且,它们在国际制度内基本上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 是挑战自由规范与原则。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股参与国际社会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对各种国际组 织的积极参与。从1960年到1993年,印度参加的政府间组织数量从41个增加到61个,年 均递增仅为0.6个,而从1993年至2000年,印度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增加了240个 ,年均递增数高达34个。(注:印度在1960、1993和2000年参与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数量 分别为391、1467和3416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参与程度远远高于之前的30多年。参 见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93/94(Vol.2),Munchen,London,Paris:K.G.Saur,pp.1704—1707;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0—2001(Vol.2),Munchen,Germany:K.G.Saur,2000,pp.1479—1480.)新中国从成立 到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孤立”的国家。(注: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Introduction:China Joins the World”,in
Elizabeth Economy,Michel Oksenberg eds.,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pp.3—6.)自20世纪8 0年代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在绝对数量和参与程度两方面都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 ,至2000年,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数量已经达到了2593个, 其中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从1993年的47个上升为2000年的282个,年均递增数为3 3.6个。(注: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1977年的21个增加到 2000年的282个,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数量变化更是惊人,从1977年的51个增加到200 0年的2311个。从参与程度上看,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根据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与 其国内发展程度之间的比例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在1977年参与程度过低,实际参与国 际组织数量(21个)低于预期数量(37个),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际参与国际 组织数量(51个)高于预期数量(45个),属于参与程度过高(over—involved)了。以上数 据来源分别参见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0—2001(Vol.2),p.1480;Samuel S.Kim,“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in Elizabeth Economy,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p.46;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 期,第5—6页。)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也 基本上呈现出类似的快速递增模式,个别国家已经基本上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参与国 际组织的水平。(注:从1993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增长率平均为500 —600%,和发达国家基本上相同;从数量上看,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尼日利 亚、埃及在2000年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分别是301、310、299、303、260、353 ,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分别是3416、3564、3107、3043、1786、2066,日本和美国的参与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数量分别是325、406和3954、5521。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93/94(Vol.2),pp.1704 —1707;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0—2001(vol.2),pp.1479—14 80.)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大为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 兴趣和积极性并不低于发达国家。
虽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程度增高并不能说明它们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方式如何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愿意进入各种基本上按照北方国家倡导的规范和 原则建立的国际组织。与修正结构主义的分析相矛盾的是,发展中国家并非只选择参与 权威导向分配的国际制度,而是更愿意参加市场导向的自由性质国际制度。例如,WTO 成员由1980年的80个增加到1999年的134个,而其中增加的成员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注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转引自 谈世中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发展中国家是近年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最多的国家群体,它们积极支持有效的 多边收支平衡体系。(注:Peter M.Keller,“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Creation of an Enabling Environment”,in Gianni Vaggi,From the Debt
Crisi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155.)又 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出现收支不平衡和发生外币兑 换危机,往往对外资的流入和流出加以适当的限制或控制。然而,在国际金融自由化的 巨大压力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放了它们的金融体系,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相继解除了对金融机构从事国际活动进行控制的规定”。(注:
Stephan Haggard and Sylvia Maxfie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o .50(1),Winter 1996,p.35.)不少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开始积极参与《 多边投资协议》(MAI)的谈判活动,而不是一概排斥和反对。
在有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甚至拒绝和排斥权威导向分配的国际制度。核不扩散是修 正结构主义者提到的权威导向分配制度之一。在这个领域里,市场导向的贸易制度从来 就没有运用过,南北国家对核不扩散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认同比其他国际安排更高,而 且它们基于本国利益也都反对核扩散。然而,有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核不扩散制度 的权威导向性而积极参与,例如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因为印度认为这是一 种“歧视性”的国际核秩序,加入进去后会“被剥夺核选择的自由”。(注:斯蒂芬· 科亨著,刘满贵等译:《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 3页。)
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不同的,基本 上经历了一个从拒绝、排斥到参与、融入的转换过程。例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 由于申请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遭到拒绝而扮演了“体系的反对者”的角色;70年 代以及80年代早期,中国充当了“体系的改革者”的角色;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 国支持许多本质上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现状的制度,属于“体系的维护者”。(注 :Samuel S.Kim,“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in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p.45—6.)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基本行为方式不再是挑战既有 的国际规则,而是合作性地维护它们。(注:江忆恩:“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 外的视角”,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50—351页。)有学者在研究了中国在主要的多边经 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内的行为活动后得出结论,认 为中国“并未打算推翻现有国际体系的规范”(注: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 伯特·罗斯主编,黎晓蕾、袁征译:《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 版社2001年版,第269—270页。)。这与南北关系研究中的修正结构主义的分析和推论 是大相径庭的。
要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方式,首先必须明确决定国际组织内的国家合 作行为是国家特征还是国际组织的类别和性质。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是,在国际组织 内外,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趋于合作,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内处于更加不利 的地位,没有太多的资源来控制国际事务,更倾向于挑战现状。然而,有学者对35个国 家十年间进行的11665个对外政策事件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判断国家在国际组织内的 合作行为的要素不是国家特征,而是国际组织的类别和性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组织内的合作程度是基本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内比在国际组织外更趋于 合作;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低级政治类的国际组织内更趋于合作,而大的发展 中国家在地区性的、高级政治类的国际组织内更趋于合作。(注:James M.McCormick,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in Paul F.Diehl ed.,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atterns and Insights,Chicago,Illinois:Dorsey Press,1989,pp.83—98.)
至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内进行合作的原因,当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就中国 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在解释中国遵守国际制度行为的原因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江忆恩 提出了五个基本假设,即规范认同、物质报酬、物质惩罚、社会报酬和社会惩罚。(注 :关于这五个假设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江忆恩:“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外的视角 ”,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第351—7 页。)塞缪尔·金从“学习”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中国在冷战后的行为变化是属于 “适应—工具性学习”(adaptive/instrumental learning),而非“认知—规范性学习 ”(cognitive/normative learning)。(注:Samuel S.Kim,“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in 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p.80.)王逸舟则认为 中国行为的这种变化更多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变化”和“中国对国 际组织的需求的变化”。(注: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外交》,2002年第11期,第50页。)
四、建立综合性的理论框架
要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偏好和行为方式及其变化原因,仅仅依据修正结构主 义的物质权力理论是不够的。在我们的理论视野内,需要将重要的体系新特征、单位结 构变化以及国际制度的特定功能等要素包括进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动机和特点已经不能仅仅从物质权力 角度去判断。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以有效确保国内 经济的增长、稳定和安全。(注:Ngaire Woods,“The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 Ngaire Woods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London:Macmillan Press,2000,pp.202—205.)它们确实希望对国际机制进行权力控制 ,以尽可能地促进本国发展,但同时它们也坚定地相信,有效而稳定的国际机制对于其 国内发展是根本必需的。(注:Craig N.Murphy,“What the Third World Wants: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deology”,in Paul F.Diehl ed.,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atterns and Insights,p.237.)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结构变化、经济相 互依存的体系特征和国际制度的社会化功能已经逐步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制度偏好 和行为方式。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联合不再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即便在冷战时 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联合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注:参见Samuel S.Kim,“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i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in 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3rd ed.),p.129.)) ,冷战时期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组织力量也不复存在。相反,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严 重的分化和多样性,经济利益正日益成为它们的优先追求目标。发展中国家把更多的注 意力转向了国内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经济目的性占了主导地位。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 使它们意识到参与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始寻求在国际经济和贸易制度内实现 利益最大化。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已经逐渐渗透到其国家内部,新的利益部门随之出现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经济制度)方面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与动力,兴 趣也在不断增大。
除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变化外,国际政治中的经济相互依存特征在改变发展中国家对 国际制度的偏好和行为方面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更深 地融入经济相互依存体系中,而且与发达国家水平型(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 依存相比,它们是垂直型(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注:Mark J.Gasiorowski, “The Structure of Third Worl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o.39(2),Spring 1985,pp.331—342.)这不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 的外部压力,而且会给它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内外政策带来不小的威胁和挑战。发展中国 家要解决这些关乎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从外部的国际体系中去寻找办法,而不 是回到以往的封闭状态中去。经济相互依存导致国家认知的转换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 领导人观念的变化上。依附理论的主要发明者、巴西前总统亨里克·卡多佐曾经谴责国 际制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但后来他认识到,国际制度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 必要保证。(注: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 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70页。)现任巴西总统卢拉上任伊始,就 积极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表示,中 国必须融入国际体系,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观念的改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相互依存带来最为重要的影 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危机控制能力在不断减弱。它们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如果采取内 向型措施,只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以金融自由化制度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表 明,从1985年到1990年,发展中国家采取金融自由化的措施从22项增加到49项,远远超 过控制性措施的数量。(注:Stephan Haggard and Sylvia Maxfie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o.50(1),Winter 1996,p.37.)这其中的原因是,当发生 金融危机时,发展中国家必须维持或加大金融开放度,以便向投资者发出积极的信号, 明确表明政府的财政和金融立场,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在对外直接投资(FDI)领 域里,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仅仅依靠地区一体化和合作来取代有效的国内经济政策调整, 它们必须坚持包括取消投资限制等在内的市场开放原则和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投资框架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投资危机。(注:Jamuna P.Agarwal,Andrea Gubitz,Peter
Nunnenkamp,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ubingen:Mohr,
1991,pp.126—132.)经济相互依存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内政策调整,它们对国际制度 的偏好与行为方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以尽可能地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各种资源来保障与 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相互依存的机制化表现是国际组织,它对国家的社会化(socializing)功能不能被忽视 。国际组织可以促使国家间发生互动,并施予一定的压力,帮助规范国家行为,是国家 发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和重要推动器。(注:Jeffrey T.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http:/ /www.arena.uio.no/presetation/Checkel.htm)经验证明,国家的社会化是一种实在的 社会进程,例如欧洲巴尔干地区国家对欧盟和北约制度的接受和内化。(注:Emilian R .Kavalski,“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the Balkans”,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No.4,Summer 2003.)国际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环境(
social environment)是通过劝说和社会影响等微观进程来促使国家逐渐认同和接受现 有的国际规范与准则的。(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1)4 5,pp.487-515.)发展中国家在最初参与国际制度时主要是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之类的战 略估算,但在进入国际制度之后,其认知角色会发生变化,逐渐接受规范式劝说,并在 一定程度上内化国际规范。例如,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后相继出台新的国内法,设立新 的机构,以实现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开始对国家利益进行重新界定,在许多重大问题 上采取了灵活的可协商态度。(注:Ann Kent,“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 ion: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lobal Governance,No.8,2002,pp .343—36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采 取有效合作的立场,而不是要么反对既有的国际自由规范和原则,要么退出国际体系。 修正结构主义在分析和判断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方面表现出巨大的贫乏和滞后,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提出基本命题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将近30 年的时间了,其时效性毫无疑问会大打折扣。
从理论层面看,修正结构主义单单坚持从现实主义物质权力观去考察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制度内的行为,采取了一种静态的结构观,忽视了这么几个重要的因素,即制度本身 会促进国家间合作和对国家产生规范化效应;国家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具有一 定的学习能力,其偏好会受到国际社会结构中的规范与原则等的限定;影响国家政策选 择的不只是外部和内部环境中的权力因素,还有自我利益再界定、决策者的认知、机制 的限制能力等重要因素。克莱斯勒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依然坚持国际制度研究中 权力定位方法的重要性,强调要将国家行为与权力直接联系起来。(注:大卫·A·鲍德 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234—249页。)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 他的这种权力偏执观还是没有改变。(注:参见Stephen D.Krasner,“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and Steven Topik,eds.,
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Routledge,1999.)
从经验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内部不但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而 且将国内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经济相互依存所造成的压力迫使它们只有学会融入国 际体系,接受自由规范和原则,才能增强危机处理能力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国际组织的 社会化功能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利于促进它们逐渐接受和内化国际规范和原 则,从而改变对国际制度的偏好和选择。
其实,还存在许多其它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传统”观点,如认为参与国 际组织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和对其国内外政策造成巨大限制等。实际上,国际 组织虽然会影响成员国的对外政策或者对它们的某些国内政策形成冲击,但并不会直接 干预到它们的国内决策过程,也没有对其国家主权形成重大的限制。国际组织只是限制 国家对外事务的绝对自由,而不会改变国家的核心主权原则。(注:Magdalena M.
Martin Martinez,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Hague:Kluwer.Law International,1996,p.215.)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21世纪的发展 中国家与国际制度(或者更广泛层面上的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 和细致的研究与分析。
建构主义只是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国家的社会化意义,而从微观进程考察国家社会化的 理论文献不多。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是根据纯粹的利益计算来改变对国际制度的偏好和行 为,而是实现了对国际规范的内化,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它们改变国际制度偏好和行为 不是适应性而是习得性的。实际上,这即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是不大可能如此泾渭 分明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内的接触,特别是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多边 环境和综合性的理论评估框架中的互动和交流,确实可以促使它们逐步认同与接受国际 规范与准则,这对于它们的国际制度偏好和行为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