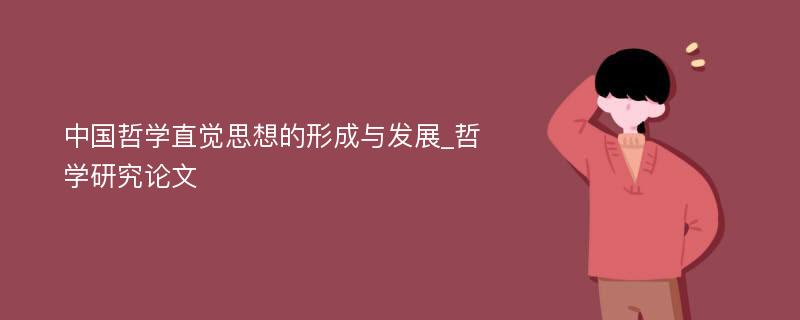
中国哲学直觉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直觉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4-0033-06
直觉是无须借助于概念、判断、分析、推理等逻辑思维活动而直接把握对象本质的一种非逻辑的思维形式,是人重要的创新之源。与偏重逻辑思维的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更注重非逻辑的直觉思维,因而蕴藏有丰富的直觉思想资料。本文试图对中国的直觉思想作一简略勾勒,以取其精华,以期引起哲学界同人的关注,从而有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
一、“直觉”概念的引进
“直觉”一词是对intuition、intuit、inspration等英语的汉语翻译。在西方,虽然对直觉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洛克、柏格森等哲学家以及从欧几里德、阿基米得到牛顿、彭加勒、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共识:直觉是无须凭借概念、推理等逻辑思维而直接把握对象本质的思维形式,直觉所获得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最可靠的。
中国古代并无“直觉”一词。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时将intuition译为“元知”。书中有这样的译文:“人之得是知也,有二道焉:有径而知者,有纡而知者。径而知者,谓之元知,谓之觉性;纡而知者,谓之推知,谓之证悟。故元知为智慧之本始,一切知识,皆由此推。”“推知可妄,故名学言之;元知无妄,故名学不言。”[1](P5)穆勒是经验论者,推崇归纳,但也因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认为逻辑推理的前提——“知识的本原”(即元知)是由直觉得来的、无须证明的、不妄的。严复在英国留学时,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还没有对直觉引起特别的关注和讨论,严复对元知(直觉)的了解不多,也无其他评论。
在近现代,梁启超是一位积极介绍西学的思想家。他在1901年12月1日《清议报》上发表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一文,介绍和述说西方的灵感(直觉)学说,但他用的是音译。他对灵感作了这样的描述:“突如其来,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为我,无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烟士披里纯’之来也如风,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云,人不能攫之,虽然,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诚而已。更详言之,则损弃百事,而专注于一目的,忠纯专一,终身以事之也。”[2](P69、71)梁启超不是从认识论上阐述灵感,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上讲灵感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他认为,历史上千古英雄豪杰“惊天地泣鬼神之事”,皆为“烟士披里纯”之鼓动。不过从他的论述中可显现,灵感(直觉)有以下特点:一是突然发生;二是时间很短,一刹那间;三是长期专注一事,至诚尽心,具有价值含义。他把西方的INSPIRATION与中国古代的至诚相联,但未涉及现今学术界所认为的中国哲学中的直觉思想。
将“intuition”译为“直觉”的是日本学者。王国维认为,此译语未必精确,不过,人既造之,我沿用之也无不可。但王国维很少用“直觉”,而主要用“直观”。他在介绍叔本华、尼采哲学时涉及了他们的直觉思想。他看到了直觉的创新意义,并认为:“概念者,仅为知识之记忆传达之用,不能由此而得出新知识。真正之新知识,必不可不由直观之知识。”[3](P300)但他并未将直觉与中国哲学思想相关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东邻日本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开始关注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李大钊参考和吸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思想,赞同当时盛行的“西方文明主动,东方文明主静”的观点。他用简洁、对应的“一为…,一为…;”的句式来列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十五个方面的不同,其中说到:“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4](P557-558)。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虽然把“西方重理智,中国任直觉”作为建构自己思想的重要支柱,但并未对中国哲学中的直觉思想作过系统的梳理。
由此看来,“直觉”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引入中国思想界,并和中国古代哲学发生沟通、交融的。中国学术界也由此开始对古代哲学中的直觉思想进行发掘和研究。
二、道家直觉论
中国古代首倡直觉思想的是道家。道家创始人老子哲学的中心范畴、最高范畴是道。他认为,道无形相,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不可言说,非一般的感觉、名言所能认识。如何认识玄之又玄的道?他认为要通过“观”:“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5](第1章)。如何观道?老子对认识的主体提出了要求。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5](第16章)怎样做到“致虚极,守静笃”?他提出“涤除玄览(鉴)”[5](第10章),就是要把主体的私欲、杂念、成见都去掉,犹如把鉴(镜子)上的尘污清洗掉。
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和“涤除玄览”并非是要认识主体的头脑绝对空虚、清静,而只是要求抛弃成见和杂念,专心精思。为此,他提出了“抱一”的原则。但是,如何理解“抱一”?历来注家的解释不一。笔者以为,《管子》的《心术》和《内业》提供了对“抱一”的最好注解。《管子·心术下》说:“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6](P1354)其意是说,在认识事物时,要专心思索,思之不得,又重思之,在思索不通时忽然间想通了,这看起来似乎是鬼神的作用,其实是专心思索的结果,是执一的结果。笔者认为,这里的“执一”就是专一深思。“鬼神教之”,这实际上是指在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受阻时发生的突然而来的直觉。古人不理解这种飞跃、中断,故而说“鬼神教之”。上述论述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直觉的最早的具体说明。这些思想与《老子》的虚极、静笃、抱一是相通的,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直觉思想。庄子也认为,道是无形无相的,不可闻,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言,不可传,因此不是通过感觉、思虑所能认识的。《庄子·知北游》专门讨论如何认识道,其中说到:“齐(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庄子还主张“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7](《大宗师》)。庄子未继承老子重视思索的“抱一”思想,他排斥思虑(“无思无虑”),提倡通过心斋而虚静的方式达到道。
魏晋玄学继承和发展了老庄的直觉思维。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在本体论上倡言了“贵无”,在认识论上主张“体无”。他认为,世界的本体为无,无形无相,不可言说,只能以体悟的方式去把握、体会。王弼提出的体认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到宋朝,“体认”成为认识世界本体的一种方式。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象、言、意的关系做了阐述,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象莫若言。”“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8]从现代观点看,言(概念)在思维过程中有两重性,既是思维的工具,有达意、存意的一面,又有妨碍创新和不能尽意的一面,片面执言,可能以言害意。但王弼的“得意”在忽视了“得意”后“意”本身还须用言来表达、论证和传达,在言与意的关系上,这种直觉思想忽视了对直觉结论的逻辑表达和证明,有碍于逻辑思维及形式逻辑的发展。
老庄的直觉思想在隋唐道教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重玄宗是道教中以“重玄”思想注解老子《道德经》而闻名于世的一个学派。它的重要代表人物成玄英认为,“道以虚通为义”,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虑,“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理穷恍惚。”[9](第1卷)重玄宗另一位重要人物李荣也认为,玄之又玄的道,是虚寂的,无形无象,不可言说,“无劳言教,悟至理”,“得意忘言,悟理遗教,言者不知。”他认为,认识道的真髓在于,“体道忘言”、“悟理遗教”[10](《老子注》)。唐代道教影响最大者是茅山宗代表人物司马承祯,他在所著《坐忘论》中对道教修炼方法作了系统论述,其中对直觉也多有涉及。
道教哲学虽然有“静则生慧”的说法,但总的来看,其提倡直觉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世界的本体和规律,而是为了达到万物一体、道通为一的心理体验和神秘的精神境界。道教哲学的虚静偏离了老子的“抱一”的专心深思的思想,变成了一种纯道德修养理论。
三、佛教哲学直觉论
中国哲学中对直觉有专门篇章阐述的是佛教哲学。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逐渐中国本土化。佛教哲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吸取了道家的直觉思想,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直觉思想。方立天的《佛教哲学要义》中,对佛教哲学的直觉思维有精到详尽的阐述,这里只讲具有代表性的僧肇、竺道生、慧能三人的直觉思想。
僧肇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重要佛教哲学家。他由老庄的道家哲学转向佛教哲学,他的思想亦是当时玄学和佛学的结合。他认为,世界万物“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亦即虽有非真有,虽无非真无,“有无称异,其致一也”。因此,不必执著非有非无,有无皆不真,不真即空,世界本身是“万物之自虚”,这就是不真空论。关于如何得道,他在《不真空论》的最后说了这样两句话:“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这是说,道并非远不可及,身边的事事物物都有道;要成为圣人也不远,只要去“体”就可得道。他的《般若无知论》则是专论认识论的,是对“体之即神”的展开,体现了他的直觉论。“般若”为古印度佛教的专用名词的音译,指能洞察真理的最高智慧。僧肇认为,般若所认知的对象,是“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是“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如何认识?他吸取道家思想,提出:“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监(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他强调的是圣人无知无虑,虚静玄鉴,因而“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这就是所谓的“知即无知,无知即知”,“般若无知而无不知”。可见,僧肇的直觉论虽然引用了不少佛教经典,但骨子却里是道家的排斥言象的“玄监(鉴)”思想。
竺道生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即便是一阐提(断绝一切善根者),也有佛性,也可成佛。对于如何修行成佛,当时流行的是须经过一定阶段的渐悟说,而竺道生则倡导顿悟说。他提出:“夫象以尽意,得意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息言。…若忘筌取魚,始可与言道矣。”在此基础上,他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11](P256)这清楚表明,竺道生的顿悟说与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有密切关系。慧达在《肇论疏》中简述了竺道生的顿悟说:“第一竺道生法师大顿悟云,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见解名悟,闻解名信。信解非真,悟发信谢,理数自然,如果就(熟)自零。悟不自生,必藉信渐,用信伏惑,悟以断结。”竺道生认为,真理玄妙,不可分,只能通过顿悟的方式才能获得。由顿悟得到的是“见解”,是真理;由传闻得到的是“信解”,不是真理。顿悟发生,信解就失去作用,这是自然之数,犹如果子熟了就会自然掉下。竺道生首创顿悟说,但他并不否认信解(渐悟),而是认为顿悟必须借助于信解。
禅宗六祖慧能进一步阐发了顿悟说。他认为,万法尽在自心,要识得万法,得到真如本性,只须自识本心,明心见性。他强调主体内心修养,自我觉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即佛。”[12](《般若品第二》)。如何才能明心见性,一悟成佛?慧能认为,佛性、真如人人有,只是为尘世的欲望迷,为了自识本心,只须排除一切杂念。因此,他说:“此法门立无念为宗。”[12](《定慧品第四》)慧能提倡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靠自己成佛,反对烦琐的修行,提倡顿悟成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变革。从哲学上讲,他高扬了主体能动性、人性平等和直觉论。与道教的直觉论一样,佛教禅宗的顿悟说也是一种获得精神解脱的伦理直觉,而非认知客观真理的直觉。佛教顿悟说对宋明哲学有重要影响。
四、儒家直觉论
儒家认识论注重学思、知行,《大学》讲“格物致知”,《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很长时期内,儒家的这些思想是与道家、佛家的直觉思想相对立的。孟子以后的儒家哲学,很少有论及直觉的。到了宋明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家融合的新趋势。新儒家吸取佛、道的直觉论,提出了“体悟”和“豁然贯通”的直觉形式。
程朱理学讲得最多的直觉形式是“豁然贯通”。程颐认为:“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如何通过具体的物认识一般的理?他在解释“格物致知”时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13](卷18)在程颐的语录中,“脱然贯通”、“豁然有悟”等类似说法甚多,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直觉的典型说法,也是对中国佛教哲学顿悟思想的扬弃。
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脱然贯通”思想。朱熹在这方面的经典表述是他对“格物致知”所作的解释,其中说到,在即物穷理时,“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4]他认为,要做到豁然贯通,需要积累。他说:“如穷格工夫,亦须铢寸积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15](卷9)朱熹的这些思想是对认识过程的一种总结,豁然贯通是建立在格物致知基础上的,是对感性材料长期思索的飞跃。朱熹对张载的“体认”也有发挥。他认为,“体认”、“体物”之体“体”,与“体、用”之体不同。“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如格物、致知之义。”有人问:“体物”“是将自家这身入那事物里面去体认否?”朱熹回答:“然。犹云‘体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是这样的‘体’。”[15](卷9)他用“格物致知”来释义“体认”,强调“置心在物中”。朱熹的“置心在物中”与20世纪初法国直觉哲学家柏格森的“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的说法相契合,其真正的含义是指认识主体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认识之中,以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
中国内地学术界普遍认为,程朱理学的直觉论是向外的,重格物致知;陆王心学的直觉论是向内的,重明心见性。陆象山发挥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首创心学。在认识论上,他继承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他批评朱熹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支离事业”,终将“沉浮”;而自己的“切己自反”是“易简工夫”,终成“久大”。受佛、道的影响,他主张静坐直觉。《象山先生语录》记载静坐直觉一事:“他日待坐,无所问。先生(陆象山)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即陆的学生自称——引者注)因此无事,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瑩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曰:‘此理已显。’”学生又说,往日,他读张南轩(栻)的《洙泗言仁》,“考察之,终不知仁,今始解矣。”[16]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一部分儒家学者受到当时佛、道静坐直觉论的影响。
宋明心学的集大者王阳明更是推崇内向直觉。王阳明在本体论上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主张“致良知”。他对“格物致知”做了新的解释:“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17](《答顾东桥书》)从伦理学上看,他是典型的直觉道德论者。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人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17](《传习录上》)王阳明推崇向内直觉,自然是由他的本体论决定的,同时,这也与他曾亲历体会直觉有密切关系。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三十七岁时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黜到偏远荒凉的贵州龙场。在龙场,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一静;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王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些文字是对一个哲学家的根本哲学观念产生的直觉过程的完整记述,其中有:(1)直觉发生之前的主体状态:“日夜端居澄默,以求一静”,“久之,胸中洒洒”。(2)直觉发生之时的主体状态:“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3)直觉的结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也”。(4)直觉发生之后的主体工作:对直觉的结论及时进行逻辑论证,“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在西方,自然科学家通过直觉思维而作出科学发现过程的记载甚多,但未见有哲学家对哲学观念的直觉思维的记录。《王阳明年谱》的这一“始悟格物致知”的生动、具体、完整的记载,是研究直觉思维的十分珍贵、十分经典的史料,值得重视。
笔者认为,道家、佛家的直觉排斥名言,悟理遗教,而宋明新儒家则力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他们的直觉思想要高于道家、佛家,其中有些观点与现代直觉论相契合。
五、现代中国直觉论
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心学和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受到王夫之等哲学家的批判,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认识论中重直觉的思潮消退。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学的大规模输入,尤其是柏格森哲学的传播,中国古代直觉论与西方直觉思想逐渐交融,形成现代中国的直觉论。
梁漱溟是这一时期“第一个倡导直觉最有力量的人”[18](P175)。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用柏格森的直觉哲学来读解孔子,把孔子说成任直觉而反理智,把直觉理解为一种意味精神、体验,一种反功利的人生态度。他指出,感觉(现量)、理智(比量)、直觉(非量)是构成知识的三种不可缺的成分。这就打破了西方哲学的感性、理性二元认知结构,有其理论的价值。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中国哲学重直觉,这有其合理之处;但他认为世界未来的走向是任直觉,这是为他的尊孔论所作的主观主义论证,并不可取。
梁漱溟的直觉论对熊十力有重要影响。熊十力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智与性智两部分。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本体显现的万象,所凭借的是理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本体,所凭借的是性智。西方哲学重理智,靠思辨;中国哲学重性智,靠证会、体认、修养。理智、思辨讲分析,不能获得世界本体,对世界本体的把握只能靠中国的体认、修养。他所创立的新唯识论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体认、修养,证会本体,给人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对理智与性智的分析并不全面,但他主张中西哲学交融的观点则是可取的。熊十力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对体认、修养的意义阐扬最力的一位哲学家,但他只是把对本体的体认归结为德性修养,即王阳明的“即工夫即本体”,而对如何体认、修养,则无更多论述。
受熊十力的影响,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中国哲学中的“体认”与西方的“直觉”是“同义的名词”。他在《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中,首次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直觉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认为,老子、庄子的“体道”,荀子、《周易》以及邵雍、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体物或穷理”,孟子及陆九渊、王阳明的“尽心”,都是直觉法。他着力挖掘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直觉思想资料,但他对直觉的本质未作明确界定,因而如他后来所说,把一些不属直觉范畴的资料当成了直觉。他也未论及中国佛教哲学的直觉思想。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对直觉作出最有价值阐述的哲学家是新心学的提倡者贺麟。1942年,贺麟在综合中西哲学直觉论的基础上,对直觉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宋儒中,无论朱(熹)、陆(象山)两派,其思想方法均系我们了解的直觉法。他对梁漱溟把直觉仅仅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方法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他认为:“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所谓直觉是一种经验,广义言之,生活的态度,神契的经验,灵感的启示,知识方面的当下顿悟或触机,均包括在内。所谓直觉是一种方法,意思是谓直觉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功能或技术。”他进而对直觉的这两方面的特点、价值做了扼要说明。他批评否认直觉、把直觉视为反理性反理智的错误观点,全面论述了直觉方法与抽象理智方法的关系。他指出,直觉法“仍须以训练学养之酎熟与否为准”,直觉的结果,犹如实验的结果一样,不一定都正确。“直觉的方法是不断在改进中,积理愈多,学识愈增进,涵养愈酎熟,而方法愈随之逐渐愈为完善。”他把直觉方法区分为先理智的与后理智的二类。“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其全体,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此先理智之直觉也。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凭直觉的助力,以窥其全体,洞见其内蕴的意义,此是后理智之直觉也。”贺麟的这种区分是形式上的,但它说出了直觉与理智的关系。事实上,任何直觉的发生都是在实践、实验、生活的基础上对认知对象思之、重又思之而发生的,它不是凭空洞见对象的本质和全体,而是以理性的逻辑思维为前提;直觉发生后,理智还要对直觉的结果进行逻辑的分析、证明和实验的检验。贺麟指出:“无一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及矛盾思辨的。同时亦无一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他又说:“形式的分析与推理、矛盾思辨法、直觉三者实为任何哲学家所不可缺一,但各人之偏重略有不同罢了。”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不仅哲学家是这样,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发明家同样都是这样,因为人的思维包含知性思维(形式逻辑)、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等多种形式。贺麟反复强调,直觉不是反理智、反理性的方法,真正的哲学的直觉方法,“须兼有先天的天才与后天的训练,须积理多,学识富,涵养醇,方可逐渐使成完善的方法或艺术。”[18](P179-183)他认为,直觉方法的种类甚多,大致有“向内反省”与“向外透视”两大类,宋儒陆象山代表前者,朱熹代表后者。
受罗素等人的反柏格森直觉论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一部分哲学家、科学家简单地把直觉与理性对立起来,把直觉论视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而加以批判。在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中,玄学派主张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派中多数人对此则持批判态度。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却承认直觉。他在批判《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指出,梁漱溟并不了解直觉,梁漱溟所讲的直觉与柏格森的直觉不一样。杨明斋并不否定直觉这种认识形式,他把直觉视为中国哲学的悟性。他说:“直觉这种东西似中国所说的那种‘悟性’的作用。中国常说‘恍然大悟’,开博思说他是‘顿悟的结论’。这话有理。他既是‘悟性’的作用,那么感觉以后非经过想象、记忆、经验等的时间。”他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应该感觉为先,理智次之,而直觉为最后。”他不赞成梁漱溟所说的孔子、儒家任直觉的观点。他说:“总起来说,儒家用理智比较用直觉多得多。”他强调理智的作用,认为直觉离不开理智,直觉随理智发达而发达。他说:“理智发达高明的民族,他的直觉就随着增高。譬如,不研究哲学的人,他的直觉怎能够像柏格森那样悟到宇宙万物之进化是有新的分子增加!不研究数学的民族,怎能够如爱因斯坦氏那样悟到相对(论)的原理。”[19](P54-74)杨明斋在1924年就有这些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20世纪30-7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直觉基本持否定的批判态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提出思维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对灵感(顿悟)的研究。他认为,思维科学体系的基础学科包括抽象(逻辑)思维学、形象(直感)思维学、灵感(顿悟)思维学[19](P20)。经钱学森等人的大力提倡,当代中国诸多学者从思维科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对直觉(灵感)作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奉硕成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直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思维科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在直觉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未能予以吸取和概括。
从当代直觉思维论来看,中国哲学中以下的思想值得我们吸取和发挥:①直觉是一种不借助于名言的非逻辑的具有创新性的思维形式;②直觉是在思之思之、重又思之“不通”时的一种特殊的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形式;③直觉的结论仍须有逻辑的表达和论证;④直觉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纯思维(如逻辑思维),而是包含有与认知对象达到物我一体的价值取向;⑤直觉既有利于对世界本体的哲学把握,也有利于对具体事物的科学认识;⑥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思维形式,等等。
[收稿日期]2008-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