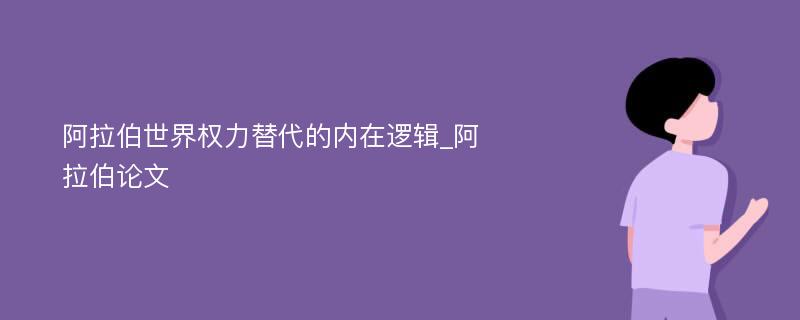
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逻辑论文,权力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丛林法则”
对局外人来说,阿拉伯政治宛如雾里看花,充满了神秘性和非理性。2011年的中东动荡,使外界进一步领略到阿拉伯政治的独特性。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问题上,阿拉伯政治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权力更替的“丛林法则”。“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夺取或失去权力是通过非常激烈、而非温和的方式完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导人获取权力基本靠暴力手段,而且也是用“枪杆子保政权”,权力更替仍要通过革命、政变等暴力方式完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曾掀起政权更替潮:1952年埃及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8年伊拉克卡塞姆推翻了费萨尔王朝;1969年利比亚卡扎菲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等。无论是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还是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也门的萨利赫,都是军人出身,军队支持成为领导人获得权力的基本保障。而当权者一旦掌握权力,往往贪权恋栈。“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①在阿拉伯世界,终身执政乃至家族世袭现象十分普遍。截至2011年中东剧变时,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已连续执政23年,埃及穆巴拉克超过30年,也门萨利赫在位33年,利比亚卡扎菲更是执政长达42年。在正常情况下,唯有自然死亡,才能终结一个总统的政治统治。②
这些当权者都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因此中东的权力更替只能通过军事政变、民众革命、外来入侵等暴力方式完成。在历史上,苏丹的尼迈里自1969年军事政变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85年被新的政变推翻;突尼斯的布尔吉巴自1956年该国独立就担任总统,此后3次连任,并在1975年当选“终身总统”,直到1987年因政变辞职,由本·阿里继任,而后者同样长期执政,直到2011年被赶下台。在伊拉克,自1958年卡塞姆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后的10年间,各派为争夺最高统治权激烈较量,曾发生过大大小小十几次政变、未遂政变及武装起义,直到1968年阿里夫政权被推翻,贝克尔领导的复兴党当政。而萨达姆又在1979年强行从贝克尔手中夺权,直至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推翻。
当前中东的权力更替,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突尼斯、埃及领导人都是直到众叛亲离、局势无法收拾时才黯然下台。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领导人为维系权力,不惜鱼死网破,动用“铁血手段”:卡扎菲出动雇佣军镇压民众抗议,使和平示威迅速演变为流血冲突,并招来英法持续空袭,国内转瞬间战火纷飞。叙利亚政府自2011年3月爆发抗议后,同样动用军队镇压,迄今已造成上千人死亡。也门从2011年1月15日就出现民众抗议,但萨利赫软磨硬顶,死活不肯让出总统宝座,还三次拒签海合会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使也门成为“中东波”中动荡时间最长的国家。反对派最终还是靠“枪杆子说话”,6月3日炮击总统府,才迫使萨利赫负伤外逃。即便如此,萨利赫仍屡次扬言将很快回来。
阿拉伯领导人在权力更替问题上表现出的超常执迷和不惜血本,远远超出了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范围。这种现象委实值得思考。
二、阿拉伯政治运行的三大内在逻辑
中东政治更替暴力色彩十足,固然与权力本身的稀缺性有关,但更是阿拉伯政治特定的“游戏规则”使然。阿拉伯政治的运行,主要遵循三大政治传统。首先是宗派主义传统。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部族、族裔、教派等传统因素迄今仍是维系民众间关系的主要纽带。③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使宗派主义在阿拉伯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④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种传统观念的形成,与贝都因人特定的生存环境有关。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部族,主要受到两个压倒性事实的支配:第一,由于水和放牧资源有限,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得不像狼一样,准备靠牺牲其他部落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既是猎人,同时又是被捕食的猎物。⑤第二,在沙漠里,当部族之间为了生存而采取掠夺行为时,由于没有外部调解者和仲裁机构,求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其他的人们知道,假若他们在任何方面侵犯了你,你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⑥。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关系必须在其他一切义务之前受到尊重。“个人一旦与家庭、部落、教派等断绝关系,将根本无法生存。而现代国家不仅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取代传统群体认同的替代物,而且统治者也经常将这种关系作为镇压和迫害的依据。因此,个人的道德感仅限于小群体范围,而不是更大范围的社会。”⑦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进程,因此未能把部族整合为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从而使这种部族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国家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实际是民族主义掩盖之下的部族主义的复活。”⑧这种基于部族结构形成的宗派主义,习惯性地将外部世界划分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两大范畴,并由此奉行两套完全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部族内部(即“熟人社会”里),对同族人是无止境、无条件的忠贞,认为“本氏族或本部落自成单元,能独立生存,至高无上”。与此同时,对部族之外的世界(即“陌生人社会”)则毫无同情,“把其他一切氏族或部落当做自己合法的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⑨
宗教主义/部族主义传统,使阿拉伯人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展,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阿拉伯人有句俗语:“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及我的表亲反对陌生人。”⑩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根据血缘、地域来确定情感亲疏的特性。很显然,这种部族主义对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缺乏足够信任。例如在部族传统根深蒂固的也门,尽管也门人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及反对外族入侵的斗争,形成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意识,但仍难以接受“主权国家”概念,特别是在部落和边远地区。对他们来说,政府仅仅是那些掌握权力并用其损害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同义语。部落成员既不相信政府的意图,也不关心政府的决策。(11)
在正常状态下,只有当国民的认同对象聚集于主权国家本身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实现国家与民众力量的有机融合。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淡漠,以及对其他部族、教派缺乏信任感,使这些国家很难形成正常的政治更替机制,并容易导致领导人政治行为短期化。尤其是在那些包含多个部族和教派、高度异质化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黎巴嫩等),这种宗派/部族主义对政治生活的负面效应尤为明显。一方面,它容易导致家族政治、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同心圆式”的宗派主义传统,决定了当权者在分配权力和财富时,总是优先照顾本部族或教派的利益,“提拔主要基于部落和家庭血缘,军队中最重要的职位总是被那些与领导人有血缘关系或个人亲密关系的人所占据”(12)。如伊拉克国内主要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教派/民族,萨达姆统治主要倚重占人口20%的逊尼派,特别是其提特里克家乡的人;叙利亚境内的居民14%信奉基督教,85%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徒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阿萨德家族来自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约占全国人口的11.5%),该国政府、军队、情报等要害位置基本由阿拉维派把持。利比亚境内有上百个部落,其中主要的部落有四个:麦格拉、阿里·祖瓦亚、瓦法拉、卡达法。卡扎菲的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位于东部、人口最多的瓦法拉部落则长期被冷落。也门约有200个大部落,主要分为四大部落联盟:哈希德、贝克尔、哈卡和穆兹哈。萨利赫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总统,正是因为他来自也门势力最强的哈希德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动员10万人以上的武装力量)。同时,这种“同心圆式”的政治思维,还导致家族政治和裙带风盛行。如也门总统萨利赫任人唯亲,其侄子阿马尔是负责国家安全的副指挥官;另一个侄子雅赫亚担任中央安全部队兼反恐部门司令;第三个侄子塔里克是总统卫队指挥官;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也门空军司令。萨利赫还试图让其儿子艾哈迈德继任总统,并大力提拔那些拥护他儿子继位的领导人。卡扎菲虽号称“人民领袖”,自身也算廉洁,但在权力、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上,仍难摆脱“家族政治”的窠臼。据报道,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长子穆罕默德掌控通讯部门;次子赛义夫(被视为卡扎菲的继承人)负责“卡扎菲发展基金会”;三子萨阿迪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希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六子哈米斯担任精锐的第32旅旅长。
另一方面,这种“同心圆式”的政治思维容易导致当权者对其他部族/教派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因而在镇压其他部族/教派的反抗时毫不留情。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外部世界就是“陌生人的世界”,因此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阿拉伯世界曾流传一个“火鸡的故事”:有位贝都因老人发现火鸡被偷了,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称“现在处于极大危险之中”,孩子们不以为然。后来,老人的骆驼被偷了;再后来,马也被偷了;到最后连女儿也被强奸。老人这时对儿子们说:“这都是由于火鸡引起的。当他们看到拿走我的火鸡而无人过问时,我们就丢失了一切。”(13)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阿拉伯人形成有仇必报、不容欺凌的特性,认为如果对外族示弱,很快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既得利益。体现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就是当权者对反对派倾向于采取高压手段,而不是坐下来平等协商。在这些人的思维中,“如果不镇压反对派,人们就会认为他很虚弱,并将失去尊重”(14)。
这种部族式对立和暴力化倾向,可以很好地解释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议,在这些国家为何会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当年萨达姆对北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残酷镇压南部什叶派穆斯林起义;阿萨德政权在1982年2月镇压哈马城“穆斯林兄弟会”的反抗时,竟然用大炮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上万人被杀。而在2011年的中东动荡中,叙利亚和利比亚政府也是动用军队镇压民众抗议。从根本上说,这些当权者并没有把反对派看做是本国公民,而是视为打他们“主意”的“陌生人”和外族人。
与之相对应,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从心底里同样没把当权者视为自己的领导人。如面对北约持续空袭利比亚,该国反对派非但没有谴责西方,反而高呼“萨科齐万岁”。在他们眼里,卡扎菲不是本族人。西方武力干涉实际是在帮助他们推翻“异族统治”。而在目前,尽管卡扎菲已“众叛亲离”,但仍能抗衡至今,原因就在于得到本部族支持。换言之,这些国家在本质上仍是“部族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反观那些部族政治色彩不明显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当权者与抗议民众间的对抗就不那么血腥,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尽管也想保住政权,但始终未敢对民众进行残酷镇压。
阿拉伯世界的第二个政治传统是集权主义传统。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并未充分经历类似西方的工业文明洗礼,多数地方仍沿袭传统生产方式。这种传统生产关系的地方性特征,决定了各个体间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形容的马铃薯一样,它们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但却彼此隔绝。对他们的生存来说,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为重要。这种传统性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也是传统式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5)
总体看,落后的生产方式铸就了一种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政治文化,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由于缺乏自尊,阿拉伯人始终在追寻英雄或克里斯马型领导人。这种领导人能够自我表达,并能纠正所有错误。他自视为大家庭的家长,其演讲时喜欢使用诸如我‘亲爱的人民’、‘亲爱的孩子们’等词汇。这种风格很适合等级制模式和威权式家庭的氛围。”(16)在阿拉伯语中,sha'b和sha'bi(人民),不像英语中的citizen(公民)那样,没有单数,只是一个集体名词。(17)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中,这些统治者个人“能够以其个人的创造力、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18)。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作为对阿拉伯人政治文化塑造影响最大的宗教信仰,其教义中同样隐含着一种威权主义倾向。伊斯兰教义始终强调共性,反对个性;强调权威,以建立社会共同体为最高目标。而国家是最高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一般而言,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基本理念是“主权在民”,而从伊斯兰教义的角度看,唯有真主才是最高权威。由此导致的逻辑结果就是:反抗国家不仅仅被视为是不服从行为,而且还违反真主的意志。(19)
在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双重作用下,阿拉伯国家的权力安排基本都是威权政治式的。通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演变,尽管各国起初政体差异甚大,但最后基本都殊途同归,走上高度威权化的道路:总统主导的国家,最后往往演变为“老板国家”;军队主导的国家,最终往往演变为“安全国家”;而政党主导的国家,一般最后会变成党国体制。(20)
这种威权统治就像一种“新家长制”。在最好情况下,它孕育出一种“仁慈的家长统治”,即当统治者自认为已充分掌握权力、得到民众拥戴后,喜欢扮演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家长”角色。远者如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近者如二战后的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阿拉法特等,他们在本国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并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力。尽管这种统治以个人面目出现,但被多数人接受和欢迎。彭树智先生曾指出:纳赛尔政府是独裁的权力主义政府,但是“革命领袖的形象,使政府的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他是以‘总统’而不是以‘铁腕人物’进行统治的”。(21)而在最坏情况下,即当执政者感觉缺乏足够民意支持时,就开始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出现了“暴君式家长统治”(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不管哪种情况,当权者显然更倾向于维持秩序,而普通民众似乎也乐意接受“有人管束”的生活。阿拉伯人有句谚语:“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乱好。”(22)
相比之下,阿拉伯政治文化中显然缺乏平等意识和公民意识,因此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在他们的政治概念中,平等协商或政治妥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多元主义意味着国家生存面临危机……对话是争论的开始,而争论又是内战或分裂的开始。”(23)曾与阿拉伯人生活战斗多年的劳伦斯曾这样分析阿拉伯人的性格:“他们是一个只认原色的民族,或者说他们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民族。”(24)体现在国家权力问题上,就是将权力视为垄断性的、不可分割的资源,基本没有中间道路和调和余地。
信任和平等是建立正常权力更替机制的基本前提。“民主制度取决于对反对派将接受民主程序规则的信任。如果你将政治权力交给你的反对派,你必须视他们为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不会监禁或处死你,而是可以被信赖为在法律范围内统治,而且一旦你所在的一方赢得下次选举,他们将会让出权力。”(25)因此,如何看待政治对手,是否愿意分享权力,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化的前景和发展方向。阿拉伯国家“赢者全得,输者全失”的权力观,使得当权者一旦放弃权力,就意味着可能失去现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也门的萨利赫、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人,宁肯拼得鱼死网破也不肯放弃权力,实际就是担心一旦失去权力,将被反对派“秋后算账”。
阿拉伯世界的第三个政治传统是现代国家意识。阿拉伯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历史非常短暂。此前,阿拉伯民族的发展是帝国史,早期是阿拉伯帝国,后来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人未能如愿建立由所有阿拉伯人组成的统一国家,阿拉伯世界被划分为英法西意等国的势力范围,并以“委任统治”形式被分割为若干小国,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是“人造国家”。如伊拉克就是由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省拼组而成,连国名都是英国人起的。由此使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意识较世界其他地方更为薄弱。“尽管建立西式国家已经几十年,但国家观念,连同由此衍生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在阿拉伯世界依然非常陌生。”(26)
但对当权者来说,强化国家意识,对巩固权力、增强执政合法性至关重要。有人曾将执政者合法性来源归为三类:来自个人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以及来自结构的。其中来自结构的合法性最为可靠持久。一个政府越是制度化,执政合法性就越强。(27)这里的制度化,首先就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体系。对阿拉伯当权者来说,建立“议会”、“政党”、“宪法”、“总统”等体现现代国家特征的东西,可极大增强自身执政合法性,尤其可以理直气壮对境内其他部族、族裔、教派进行有效管辖。
由此不难理解,尽管阿拉伯现行国家体系是由殖民者强加的,对多数阿拉伯人来说,是“一只不合脚的鞋子”(28),但各国当权者还是沿着这种人为划分的疆域巩固自身权力。当权者自己尽管部族意识浓厚,却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号召民众摆脱部族观念束缚,强化国民意识。(29)这些做法包括:通过对古老神话、英雄人物、辉煌历史的有意提炼,寻找联系全体民众的共同纽带,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通过强调内部一致性(如发展目标、大众福利、历史文化共性等)和对外排他性(强调自身经历和命运独特性),强化国内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感”;借助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来培育全民共识,把外在、后天的“国族”,变成民众内在、先赋的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经过多年培育,阿拉伯人的国家意识日渐强化,这无疑有助于增强当政者以“总统”身份进行有效统治的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国族建构过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中东民众仍把他们的信任置于那些他们十分熟悉、能够分享他们相似利益、目标和特征的环境中:如亲戚、邻居、宗教、朋友,以及作为族裔、宗教和语言团体的一员。而作为外部强加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民族国家”仍然不能像中东的亲缘性和庇护性的系统所宣称的那样,获得同样或同等程度的支持、忠诚和合法性。(30)尤其是当权者仍将部族、族裔、教派差异作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标准,很大程度抵消了国族整合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阿拉伯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在统治(rule),而不是治理(govern)。那些能够在中东政治舞台叱咤风云,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中东枭雄”,不管是昔日的萨达姆、阿萨德,还是现在的萨利赫、卡扎菲,几乎总是同时具备三副面孔,不停地在三者间来回跳动。他们有时扮演部落酋长,有时扮演独裁者,有时扮演现代总统。他们的真正天赋,就在于“他们能在他们地区的所有三个政治传统中来回活动的出色能力。他们毫不费力地在一瞬间从部落酋长变成独裁者,再变成现代的总统”(31)。换言之,中东“强人政治”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正是因为其最适应中东的政治土壤。
三、阿拉伯变革能否超越“潜规则”?
当前,阿拉伯世界风云激荡,维系多年的现行统治模式岌岌可危,政治转型在所难免。中东政治更替本身就是个“翻烙饼”过程。20世纪20年代,该地区曾实行议会民主制;50-60年代,这批民主政体却纷纷被阿拉伯民族主义/威权政体取代。而今该地区又进入新一轮政治调整期,开始由强人/集权政治重新转向文官/分权政治。很多人相信这种转型将使阿拉伯国家的前景更加光明,但实则不那么简单。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其推行多党民主之前已具备若干前提:如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谁上台都不会影响经济;经济足够发达,有资本进行内耗;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精英阶层获得掌控国家的能力等。(32)而多数阿拉伯国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事实上,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没有充分经历过工业化洗礼,国家建构未完成,致使宗派主义、威权主义等诸多“潜规则”至今仍在发挥很大作用。尤其在也门、叙利亚、利比亚这样独立建国史较短、部族势力和意识依然强大的国家,这些“潜规则”与通行的“显规则”一道,主导和支配着当地政治运转。而无视这种事实,贸然推行旨在分权制衡的多党选举,很可能使政治竞争沿着各部落/教派的界限展开,并导致国家内聚力下降,族际对抗意识抬头,给国家统一带来巨大隐患。过早来临的民主化,就像无福消受的奢侈品,只会使这些国家陷入纷争状态,导致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
在这方面,伊拉克民主化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试图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样板”,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伊拉克就能实现繁荣稳定,因此其一上来就打碎了伊拉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建立西式民主制。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这种建立在教派、种族版图瓜分政治权力基础上的“分裂型民主”,使政府陷入孱弱无力、议而不决状态。伊拉克百废待兴,本来亟须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以力挽狂澜,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却催生了一个与动荡局势极不相称的“弱势政府”。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很难恢复原先的地区强国地位。
当前,很多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部族、教派意识强烈的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都正面临类似伊拉克那样的“马赛克式”权力分布前景。也门目前已形成萨利赫、反对派、部族力量、恐怖势力冲突交织的复杂局面。“萨利赫式”强人政治的终结,很可能使国家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向“弱政府—弱社会”,形成群龙无首、群雄割据的“准无政府状态”,出现类似“索马里化”的前景。有媒体认为,“这个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可能迎来糟糕的未来,甚至比萨利赫33年独裁统治下的生活更为糟糕”。利比亚同样如此。利比亚由三块原来相对独立的地区合并而成,包括西北部的的黎波里、东部的昔兰尼卡,以及西南部的费赞地区。卡扎菲虽然号称“政治强人”,其绝对控制区实际仅限于西部。部落构成了利比亚的基本社会单位,并具有很大影响力。2011年2月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目前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卡扎菲的斗争,很大程度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即使利比亚示威者取得成功,将卡扎菲赶下台,也很难实现民主化。
从深层看,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不在政体,而是该政权依靠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虽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刀握在谁手里一样。中东现行模式弊端丛生,实际是掌权者阶级的属性出了大问题,因此政治变革的关键,应是进行阶级革命。相比之下,政体改革属于次要问题。事实上,“强人政治”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盛行,当权者也青睐中央集权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政体可以有效发挥功能”(33),解决中东种种棘手问题。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由集权走向分权,国家面临的沉疴将不治而愈,这种做法不过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它只会使这些国家由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中东近百年政治变革的历史也已充分证明,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理论指导,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最终变成一场空欢喜。
注释:
①Barry Rubin,"Pan-Arab Nationalism:The Ideological Dream as Compelling Force",Edited by Jehuda Reinharz and George.L.Mosse,The Impact of Western Nationalism,London,Newbury Park,Calif.1992,p.184.
②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econd Edition),Rautledge,2000,p.37.
③Edited by Deborah J.Gerner,Lynne,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Riener Publishers,2000,p.267.
④[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9页。
⑤[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⑥[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87页。
⑦Nazih.N.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lisher,London and New York,1995,p.166.
⑧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 State,ST.Martin Press,Inc.,1997,p.65.
⑨[美]希提:《阿拉伯通史》,第30页。
⑩[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88页。
(11)Elham M.Manea,"Yemen,the tribe and the state",Jun.25 2007,http://www.al-bab.com/yemen/soc/maneal.htm.(上网时间:2011年7月5日)
(12)Risa Brooks,Political-Military Rel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Arab Regimes,Oxford Univ.Press,1998,p.107.
(13)[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88-89页。
(14)Nazih.N.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p.322.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16)Nazih.N.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p.166.
(17)Nazih.N.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p.204.
(18)王京烈:《动荡中东的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19)Hisham Sharabi,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D.Van Nostrand Company Inc.1966,pp.16-17.
(20)Nazih.N.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p.203.
(21)彭树智:《纳赛尔与阿拉伯世界》,载《学术界》,1988年,第5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23)Barry Rubin,"Pan-Arab Nationalism:the Ideological Dream as Compelling Force",Edited by Jehuda Reinharz and George.L.Mosse,The Impact of Western Nationalism,p.184.
(24)[英]T.E.劳伦斯著,温飚、黄中军等译:《智慧七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9页。
(25)[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转引自[美]马克·E·沃伦著,吴辉译:《民主与信任》,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26)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s: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83.
(27)Michael C.Hudson,Arab Politics: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8-23.
(28)Edited by Deborah J.Gerner,Lynne,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p.97.
(29)事实上,不仅是阿拉伯国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都需要不懈地进行国族整合。
(30)Laurie King-Irani,Kinship,"Class and Ethnicity",Edited by Deborah J.Gerner,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p.268.
(3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102-103页。
(32)张维为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33)Nazih.N.Ayabi,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p.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