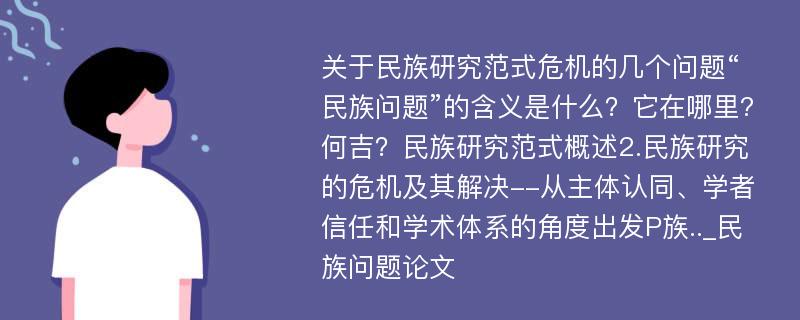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若干议题——1.“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民族研究范式概议——2.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3.族群范式与边疆范式——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民族论文,危机论文,边疆论文,族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 ——民族研究范式概议 周明甫 周明甫,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 民族研究必然涉及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现代社会纷繁复杂,从整体的视角观察,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的运行层面:一是实践层面。它围绕着生存和发展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面向自然、社会、人类的全部活动,包括诸如社会生活、具体劳作等内容。二是机制层面。它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安全有序而由制度安排、法律法规、组织机构、行为规范等构成的社会运行的机制层面。三是学术理论层面。这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体,形似一棵大树:实践层面如同枝叶;若要枝繁叶茂、开花结果,须有机制层面“干”的支撑和保障;同时,还需要学术理论“根”的供养。民族研究范式即民族研究“根”的生长方式,属于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范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论,研究范式可理解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针对某个领域、某种现象或某个研究对象,由核心概念、核心理论以及收集、归纳相关材料的表述体系、诠释体系等所形成的、带有不同研究者价值取向的、为相关研究群体所约定俗成为规范的某类研究理论方法之总和。据此,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和积累进程,围绕“民族”这一对象,存在着三种研究范式,即社会研究范式、民族问题研究范式、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研究范式。 1.社会研究范式 人类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首先会遇到“不一样的他者”。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方式的多样以及交往程度的加深,人们会感到“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而不一样的特征又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相对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历经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他者”的关注和知识的累加,逐渐积聚为民众和研究者的集体记忆并扩散传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研究范式。该范式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具有民众性、持续性和知识性。论证这一点虽然耗费笔墨,但其依据随处可见。如世界性宗教的经典中,探险家、旅行者的记述中,我国几千年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神话传说、口头文学的创作中以及社会生活的实践中等,都承载着难以数计的知识和材料。社会研究范式是民族研究范式中最基础的层面,过去存在,今后还会继续存在,其研究成果丰厚而充满智慧,有待我们进一步梳理、归纳、挖掘和借鉴。 2.民族问题研究范式 该范式的基本关注是民族的“问题何来”“问题何在”“如何面对”“怎么治理”。或可以说,当人类社会出现国家早期形态的时候,民族问题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古代国家在疆域开拓中,武力征服成为“如何面对”的首选实现方式。殖民主义时期,面对殖民地,殖民者要对派往殖民地的官员开设包括民族学课程在内的学习训练,如1864年的荷兰、1905年的南非联邦、1908年的英属埃及等。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历代王朝就已经懂得利用相关民族的习俗和制度进行间接统治,如因俗而治、和亲、朝贡体系等。共产主义思潮兴起后,见诸文献的有1913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48~1962年间李维汉(时任统战部部长和中央民委主任)的《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以及我国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最近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的讲话等。通过仔细梳理可以发现,民族问题研究理论方法的主要特征是:“民族”作为一个客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必须从现实出发妥善面对;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纲领、国家建构、社会治理、群体关系中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对象。或者说,该研究范式是从社会总问题的视角来关注和研究民族问题,隐含着“民族问题即是一类与民族的特性因素相关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民族问题研究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建设、社会治理和民族发展。 3.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研究范式 19世纪中叶,社会文化人类学及民族学学科在欧美诞生并相继传遍世界各地。一百多年来,形成了不同学派和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伴随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新的研究视角,又不断涌现出新的学派和学术理论。总体上看,该学科是一个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确切地说,是一个关注人类及其文化整体的学科,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方法是区别其他学科的明显特征。该范式从客观的社会成员的实际生活出发,实证式地探寻、认识人类的发展,并以文化这个覆盖人类全部活动过程和成果的核心概念展开研究为之特色。由于人类、社会、民族都与文化共生、互生、变化,且又都与自然环境相关联,使得这个学科包罗万象,彰显出学科旺盛的生命力。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的当代民族研究工作者,如何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刻不容缓。目前,尽管上述研究范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有着我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的实践积淀,也包含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多视角研究,但是,面对一个时期以来涉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民族和社会问题,民族研究范式仍然存在某些危机,解决民族研究范式转换问题迫在眉睫。 这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民族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习俗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回避不了“族群”“土著”“原住民”“少数人”这些概念。但感觉现在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尚不完整。究竟什么是“民族问题”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似乎民族问题很多很大;另一方面,又有学者提出“民族文化无问题”“民族无问题”“民族非问题化”。在我看来,“民族”是一个客体的概念,它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体,怎么会是“问题”呢?比如我们说这是桌子、这是凳子,能说这是问题吗?这是基本概念,是原身份,它没有“问题”。然而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以后可以建议在“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不要叫“民族问题”研究了,叫“民族领域研究”行不行?或者就叫“民族研究”。1992年,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出了一个概念:民族问题是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民族发展的问题。照理说,民族的发展本身不是问题,我唱歌也好、跳舞也好、用什么文字也好,都不是问题。实际上,想表达的是:民族问题是在民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中涉及民族特征、民族的身份认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叫民族问题。这是一些学者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视角。然而,这样概括民族问题也有不足,也不全面。像原生论、建构论等这些“论”,都很难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加以概括。不过,无论什么是民族、民族问题,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矛盾的。翻开历史书卷会看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的民族政策和做法,确实是从实际出发走出来的一条道路。 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我想至少有这么几点:一是尊重历史、尊重少数民族。把五千年历史和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加上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梳理之后,可见中国特色及其民族研究就是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少数民族。二是坚持平等,注重协商。多民族社会进展到国家这个层面的时候,涉及最高权力的集约问题。国家以平等的原则,注重各民族协商的方式,形成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三是坚持统一团结,提倡各民族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和谐发展。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世界从帝国时期进入现代国家,唯有中国是这么走过来的,罗马帝国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其他帝国也好,都不是我们这么走的。五千年中各民族的悲欢离合是不容漠视的,凝聚在五千年历史中的中华文明是不容中断的。四是承认差距,包容多样。这样才能推进共同繁荣进步。五是推进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以此推进解决民族的问题。这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从来强调的是两个发展:一个是民族发展,一个是民族地区发展。然而什么是民族发展?标志是什么?指标体系是什么?到今天几乎还没有人去做这项工作。另外,把民族地区的发展看成一般区域的发展,也是不正确的。民族的发展,绝不可以把民族去掉。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少数民族发展有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我们几乎还没有找到办法来解决文化保护和发展等问题。这些其实都涉及民族研究的范式。 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蕴含着学术上的重大变革,直接影响学术规范的进一步完善,间接影响“民族问题研究范式”的走势,并会波及“社会研究范式”的变迁,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而言关系重大。我们的学科舶来国外,如继续简单沿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现象,已经难以走下去了。对国外理论的学习和借用绝不能或缺,然而也不能以中国的事实简单地去印证西方的理论。我们的民族研究关心民间而忽视国家;注重材料的收集、知识的积累,不太关注问题的追问;历史性的研究偏多,现实性的研究偏少。当然,我们无意去否定前辈和诸多学者的贡献,只是就现今的总体研究状况而言,不能不令人叹息。“统治者觉得我们没有用,劳动人民觉得我们没有用,我们对社会贡献太少”。前辈们当年对学科的如此感慨迫人深思!究其原因,其一受制于西方理论的影响,其二受到当年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三也是学科的曲折发展进程使然。 中华文明延绵五千余年,在数千年的文字历史中凝聚着浩瀚的研究社会、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料。我们需要发掘、研究、整理先人的概念、理论、方法和智慧,结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和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现实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中探寻、求证、思考,去回答“民族”的文化本质和民族的未来发展,逐渐完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核心概念、核心理论、描述体系、解释体系和研究方法,树立人类发展下的学术价值取向,建设具有中国本土智慧的研究群体,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范式。 ·议题之二· 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 ——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 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如果说民族研究到了“最危机的时刻”,难免会招致危言耸听的诟病或不屑一顾的讥讽。仅从学科的存续和学者的生存来说,离危机尚远;但从学科认同和社会信任的角度来看,危机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断蔓延。 危机首先来自民族研究的学者内部,即学者的学科认同危机。“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反观中国民族研究危机的形成过程,此言不虚,民族学内部对自身认识的不足或错误导致学科存在合法性危机。随着思想禁锢的逐渐打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讨论。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一批质疑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文章。进入本世纪后,“族群”(ethnic group)、“国族”(nation)等理论被引入,学者们把ethnic group、nation、nationality等西文词语与“民族”概念相比较,“民族”“族群”和“国族”三者关系的讨论一时间成为学术热点,其中对能否用“族群”取代“民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争论并无结果,但国内最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用“族群”取代“民族”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其反对者也无意识中受其左右,一些机构的英文名称将“民族”译为“ethnicgroup”。与此同时,西方的族群建构理论和运用该理论研究中国民族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反思中国民族识别的成果开始出现,其中不乏质疑其科学性与批判其随意性的观点。由此,民族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模糊不清,民族研究的支点开始动摇甚至坍塌,民族研究或民族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遭遇挑战。于是,具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人类学成为救命稻草,委身于人类学或攀附人类学成为时尚,不仅原来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纷纷改换门庭,给自己贴上人类学家的标签,而且变成组织行为——研究机构开始更名换姓,学术团体把人类学的标签贴到更显眼的位置,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学者牵头发起向社会学一级学科争夺人类学归属的“争夺战”。个中缘由大家羞于启齿,但却心知肚明:民族研究的自信和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出现危机! 其次,危机来自社会信任,即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和民族地区的干部、关注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公众失去了对民族研究者的信任。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冲突骤然增多且趋于复杂化,甚至在一些地区频发暴力恐怖事件。以民族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主要在做什么呢?第一种是延续注释经典和文件的意识形态化研究路径,用一百年前以欧洲民族问题为基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解释中国当下的民族,或论述各种文件的经典理论基础等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第二种是热衷于引进西方概念和阐发宏大的理论,其论著新术语频出,因新颖、深奥和前沿而吸引了一批青年学人趋之若鹜;第三种是绕过关涉当前各民族生存发展和民族问题解决的论题,沉迷于无关宏旨的文化细节的调查研究;第四种是接受有关领导或政府机构委托完成研究课题,出于在有限时间完成有限任务的需要,常常未经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便草率地做出判断或结论,不时出现研究者的民族团结和谐判断的话音未落就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的情况。尊重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前提,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开展研究本来无可厚非,更无责难的理由和必要,然而整个群体或学科对于当前中国民族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迫切需要讨论与解决的重要问题几乎都不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做令人信服的有效回应,对于民族工作者及广大公众来说,就等于民族研究群体和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失语、妄语和呓语。这样的学科怎么能够博得社会的信任和尊敬? 最后,危机源于体制问题。一方面,目前新闻出版中的一些规定设置阻碍了民族研究呈现真情况与讨论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空间不断扩大,中央高层和公众都想听到真话,希望获得真知灼见,但许多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官员奉行的原则是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不出事,视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等为“险学”而避之唯恐不及,针对民族宗教研究设置特别审查关卡,致使许多调查真实资料和讨论真问题的论著胎死腹中,或最有价值部分被删节后才获准出版。如此必定引导民族研究者们放弃认真调查、研究真问题的学术路径,转向无需深入调查和探究就能完成成果的道路。另一方面,学术资源的配置模式制约了民族研究的进展。掌握重要学术机构权力者,无论是否认真做学问和有无真学问都被当作“名家”,无论他们的科研项目论证做得怎样,评委们都得给他们面子,于是这些根本没有精力做调查研究的“名家”们的项目应接不暇,经费不知道怎么花,垄断了学术资源,最终找几个学生编出一堆文字敷衍了事。加之“985”与非“985”、“211”与非“211”、部属院校与地方院校、行业内与行业外等区隔与分层,致使许多踏踏实实做田野、认认真真做研究的人没有资源做事或因资源有限而难以做成事。 那么,如何破解民族研究的危机呢? 首先是重构“民族”概念,寻回被拆迁的“家园”。反思是学术进步的必要路径,解构既有学术范畴和理论范式能够细化与深化学者及其他群体的认知,促进学术创新,并往往会产生“棒喝”般振聋发聩的效果,然而,反思与解构的最终目标不是毁弃而是建设。从民族学学科来说,研究对象“民族”为其位居首位的核心概念,“民族”概念的被解构意味着学科合法性遭受质疑,学者们学术研究的“家园”被“强拆”或被宣判为“危房”,其结果是让学者们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因此,重构“民族”概念、重建学科的合法性和学者的学科认同,是中国民族研究的当务之急。从当前国内外情势来看,各种含义和各种类型的“民族”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矛盾甚至冲突频繁发生,关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社会稳定、民众安全,迫切需要有专门的学科进行调查研究并做出有效地回应与解释,不能因为西方没有这样的学科而放弃这个学科,不能因为谋求所谓学术的“国际接轨”而弃之如敝帚,因此,重构“民族”概念、重建学科的合法性和学者的学科认同,也是社会科学回应与解释社会生活的社会责任。 “民族”概念如何重构呢?需要对解构者的解构方式进行解构。解构者对“民族”的解构路径有二:一是从中文“民族”与西文的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中文的“民族”与西方的相关语词不相对应,故中文的“民族”存在问题,必须取消或更改。马林诺夫斯基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费孝通先生也提出过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省”问题,指出因语言的文化语境相异,不同语言的言语或语词之间一一对应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以西文为标准清理中文则是一种语言暴力!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辩驳,另撰文详细评论,仅对西方学者用nation和ethnic group两个概念指称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略做几句简单的评议。 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的西方学者的nation定义是:那些具有自治要求,已被政治疆界化或正在追求政治疆界化的族群。“具有自治要求”和“正在追求政治疆界化”如何确认?其主语是谁?如何判定?因此这一定义是一个缺乏任何客观标准而可以任意使用的模糊概念。但翻阅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民族的论著则会发现,他们大都用nation指称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而且用ethnic group指称其他少数民族,其根据是什么?但用意大家心知肚明。二是从“民族”所指的多义性切入,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不同,故“少数民族”之“民族”应该改用“族群”。略有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语言的许多语词的所指或既有广义也有狭义,或既可指称整体也可指称部分,或既有泛指也可特指,具体所指为何则视其语境而定,并不妨碍沟通交流。有学者指出,具有中国之外国家国籍的华人也称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也并非nation。因此,以“民族”所指具有多义性为由要求将“少数民族”之“民族”改为“族群”的论说,依据也是不充分的。反思与解构“民族”的专家们恰恰忽略了或有意回避了辨析概念或语词最应该应用的方法——语用学(pragmatics),即通过语境解释言语行为,走出语义学的二价(“X的意思是Y”)的局限,通过语用学的三价(“通过X,S的意思是Y”)方法理解与解释话语的意义。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理解,“民族”的多义性并不构成使用与交流的障碍,在具体语境中其意义是清晰明确而可以准确理解的。广义的或泛指的“民族”就是“民”(“人”)和“族”(“群”)两个语素的组合意义,所指为与文化相关的人群,囊括了国民或国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中国56个民族(minzu)、中华民族之民族;狭义的或专指的“民族”,既可指国民或国族(nation),也可指族群(ethnic group),也可指中国56个民族中的任一民族,还可指中国少数民族;特指的“民族”(minzu),就是指中国民族识别所确定的56个民族。“民族”具体所指为何义,语境会提供选择与判定。以上各种“民族”都是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民族学以广义的“民族”为研究对象。民族是一种包含着心理经验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子虚乌有的主观幻象,以之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具有无可争辩的存在合法性。 其次是确立“求真务实”学风,探索与运用一切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有关民族的社会事实并做出有效解释的研究方法。理论的译介与辨析是必要的,然而,在国内外民族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当下,前人未曾经历与解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坚持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求真务实”学风,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急剧变化之中的民族及其相关的社会事实,以求做出系统、深入、有效地回应与解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常性和系统化的田野调查应当成为从事民族研究学者的生活常态和发表言说的必备前提。不仅如此,还需要发扬费老的“闯”的精神,探索与运用一切能够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地获取民族及其关涉的社会事实的方法,如量化研究、统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挖掘、社会实验等,超越小型社区研究、族别研究和文化撰写的模式,以适应各民族之间、各地域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间的关联比以往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并做出系统而可靠的解释,切实担负起大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 再次,厘清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重建民族研究者的学科认同。国内学界存在着或隐或显的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思考方式。在民族研究领域,有人以民族学在西方现在的学科设置中已经消失或并入人类学为由否定民族学存在的合法性或贬损民族学的价值。我认为此说无法成立,一是西方没有而中国有的事儿俯拾即是,西方没有并不能决定中国不能有;二是西方没有民族学或民族学已经消失并非事实,不是有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这么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吗?美国除了American anthropologist之外,不是还有American ethnologist吗?即使民族学在西方学科体系中已被取消或自然消亡,中国保留它仍然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学科是否有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是否需要和能否生产出有效的知识或思想,而不是西方有无。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社会事实本身都是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并不存在孤立的所谓政治、经济、艺术事项。从学术演化的过程来看,人类早期并无学科划分,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等和中国的孔丘、老聃、庄周、墨翟等上古中西哲人都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现代的学科体系始建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科分类乃为了处理日益增长的知识而做的学术分工,是建构的产物。民族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事实,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因而民族学必定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相互关联与交错,需要借鉴与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其中,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与研究以文化为纽带结成的人群即广义民族的民族学之间的相通性、相似性最强,研究领域和理论方法交叉、交错、共享最多,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必然会涉及族群、民族、国族等与文化相关的人群,民族学研究族群、民族、国族等与文化相关的人群必定会关注其社会文化,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民族学与人类学是完全重叠、彼此替代和同一个学科,犹如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之间存在许多遗传的和文化的相似性,但他们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民族学与人类学在研究旨意和研究重点上存在着细微但不能忽略的差异,前者聚焦于族群、民族、国族等人群,也就是说,以与文化相关的人群为研究焦点,以解释其形成演变、族性特征、关系模式、相互转化为重点,知识生产的目的是认知相关文化群体与妥善解决群体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冲突,后者聚焦于人类的社会文化,即使涉及相关人群,人群只是其边界,仍以其社会文化为研究焦点,旨在解释人类的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前者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即主体——人群为中心,后者以人群所创造与传承的社会文化为中心。因此,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并立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之间不是同一关系和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不能也不应互相取代。后者不必由于自身在西方属于主流而妄自尊大与贬低甚至否定前者,也不必因为尚未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而怨天尤人;前者也不要因此而妄自菲薄或盲目攀附,更不要借此而阻碍后者成为一级学科的努力或策动将其纳入自己的一级学科囊中。作为在当今学科体系中规模小、受重视程度低、话语权弱但彼此关联密切的两个学科,民族学与人类学“各美其美”、相互合作与支持,才能“美美与共”、做好做大、为人类贡献有益的知识和思想。 最后,吁求相关管理部门转变理念,敞开讨论与研究民族、宗教的大门,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恐民”只会导致“民恐”。真相不大白于天下,谣言便大行其道。给更多完整、真实、规范的民族调查公开面世,社会对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合理诉求及其满足程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就可能获得较为全面、真切地认知与理解,决策者就可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或完善政策措施。不同研究者对于民族形势、民族关系等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但未必准确、全面,盲人摸象的情况在所难免,因此,只听一家之言、独尊一人之见,难免造成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错误,如果被决策者采纳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只有建立起通畅的言论通道、良好的沟通秩序、平等的对话程序、共同协商的机制,才能获得关于民族的相对完整、确切地理解与判断,也才有可能制定妥善、合理、有效的决策,最终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 ·议题之三· 族群范式与边疆范式 ——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 范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近些年来,学术界有关族群和民族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部分体现了学者们对国家政治的关怀。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or poly-ethnic country),多面临国内的种族、族群纷争。这就使人类学的民族研究也带有政治色彩,但是,民族研究中政治学倾向的归类未必有助于学术的繁荣。归类(categorization)形成新的范畴(category),大量的范畴构成我们的认知系统,类别会对事情的认识继而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强烈的影响,因而与范式联系在一起。按照库恩(Thomas Ku-hn)的说法,一旦范式形成,就会对其他不符合范式的做法与课题有所排斥。①在这个意义上,范式不啻为一种类别。因此,谈范式的转换,还不如说是谈避免形成某种范式。这里试就我国学界民族研究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成为某种范式——简要进行讨论。笔者认为,一些基本概念或者类别如果不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予以思考,相关的学术研究将难以避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窠臼。这对于学术创新甚至现实政治关怀都没有好处。 1.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宗族范式”谈起 “宗族范式”(the lineage paradigm)是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来的,②指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两本宗族研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和方法论,它在人类学汉族社会研究领域(sinological anthropology)成为一时之选——围绕着宗族问题——产生了大批的著作。华琛把这一现象称为宗族范式。范式的形成当然是现代科学程序中对积累的要求所致,但它却可能导致学界中人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忽略甚至排斥其他可能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库恩的眼里,构成范式的既定范畴最终会桎梏人们的创新、发现与发明。华琛写该文章的用意也在于希望人类学中国研究能有所突破,发现其他新的研究课题,否则学术永远无法进步。 那么,在当前我们的研究的领域里还有哪些范畴或者范式可能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民族研究在我国学界形成一定的规模自然与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关。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族识别之后,民族研究渐成气候。不仅如此,学术界也出现了民族形成以及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是什么的讨论。近几十年日益密集的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交流又带来了新的范式,这就是族群理论范式。在民族研究领域还有一个历久不衰的范式,我称之为“边疆范式”。该范式起于民国年间却延续至今,在这个领域里地位稳固,它所带来的问题却少有人考虑。人们早已不假思索地把边疆与民族并置,二者已然不可分割,如影随行。 2.族群范式 族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课题与一些美国人类学家在东南亚国家进行研究有关。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将这一课题的缘起归功于一些英国人类学家在非洲的研究,主要原因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所致。社会科学最初由一些学者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而来,要求在研究上得提及前人的贡献,尤其是在相关主题上其他人的贡献。对于学科的积累来说这当然很重要,但也就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导致了范式的形成。英国学者原先并没有用族群或者族群关系之类用语,而是用政治人类学上青睐的术语,如“部落主义”(tribalism)之类。当时,曼彻斯特学派独领风骚。这一学派的学者完全秉承了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注重于社会关系。他们之所以关注到族群性问题与“二战”以后殖民地解体有关。早在战争开始之前,随着种植园和铜矿在非洲殖民地如赞比亚、罗德西亚这些地方的创办和开发,导致了大量分属不同本土政治单元(部落)的民众前来赚取硬通货。许多原先从未见过面的人开始有了接触。注意到这点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的非洲社会,当地人多生活在“熟人社会”里,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在这样一个陌生人成堆的环境里,他们怎么能对从未见过面的人委以信任?操同样的语言于是成为他们寻求同族人的坐标,这些人往往来自同一个部落,于是根据部落从属性来聚合成为了非洲民众在新的环境里建立自己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 随着美国学者研究族群性日益增加,学界出现了两种取向,即原生论(或称根基论)和情境论/工具论的另一种表示方式。前者以美国学者居多,后者则以英国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居多。其原因在于,美国人类学家的中心关怀是文化,因此多有贴近被研究主体以洞察其内心世界的取向;英国研究族群性问题的人类学家则从政治人类学脱胎而来,他们习惯于关怀人们的决策和社会行为过程,而且“社会”一直是这部分人论著中的关键词,实际上也是他们的核心关怀。这点,在注重社会关系的巴特(F.Barth)的著名论文中表达得很明显。③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则由于所关心的对象常常扩大到跨区域或者整个国家的层面,因此,族群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当然像是某种政治诉求的工具。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反映的是研究者不同的取向与学术关怀。 族群性研究的上述两种取向在国内的相应研究领域内发展成为族群范式,所有的族群研究基本都围绕着这两种取向展开。同时,由于民族分类当中的民族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思考似乎都与这一范式存在着理论上的紧张,于是又有了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的同与异,或者何者在中国语境里更为适用的研究投入。鉴于民族识别之后的大量著述都想当然地将“民族”视为一种线性发展轨道上的整体性存在,因此,纠缠于民族和族群之内涵与外延,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式,却也对原先的“民族范式”提出了挑战,因而在学术界具有积极意义。 3.边疆范式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上述族群范式不太妨碍发现新课题,因为它们都只是局限在特定的理论讨论语境里。另一类范式则不一样,它们会极大地束缚人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从而引导人们在思考方式上走向另外一个理论上或者实践意义上的死胡同,因为这类范式已然成为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在内的不少人考虑民族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笔者所称的“边疆模式”。 “边疆范式”可以溯源到民国年间。民国诞生之后,建构民族国家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件要事便是对于主权归属的强调与肯定,这在前现代国家里是阙如的。前现代国家——如帝国——从核心到边缘的漫长地带中,权力的光谱呈现为一种斑驳陆离的状况。国家权力随着版图向四周蔓延有着趋弱的状态。在版图内的许多区域,国家权力甚至无法顾及,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正是这种国家中央权力的不在场,使得帝制国家版图内在人口构成上和文化异质性上得以延续。因而,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对于自己版图如何大概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帝国的边疆实际上是与邻近的其他政治单元共享之地,是一个谁都可以自由往来的区域空间。长城的存在证明了边疆的存在可以没有特定的主权归属。一旦游牧群体遇到年景不顺便可能侵入农业区域,长城就是为了遏制游牧部落入侵而建。所谓的“边塞”也是如此,它们并不是为主权而设,而是为了戍卫中心区域。现代国家就不同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一个差别,就是前者有的是边疆(frontier),后者有的是边界(border)。④在欧洲的历史上,民族国家形式在威斯特法尼亚条约缔结后被广泛接受。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建国的过程当中,都试图确定主权范围,都力求使国家的边界与文化或者民族(nation)的边界重叠,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很形象地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将松软的社会边际夯实。⑤由于对主权的关怀,“边疆”遂在民国年间成为重要语汇,见之于许多国家表述和民族建构论述当中。国民政府甚至有边政建设委员会这类机构,专门研究边疆治理。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在称之为“边疆”的广袤区域内,对边疆的关怀自然也就与少数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于是,少数民族遂被称为“边民”——甚至那些生活在内地的少数民族民众也被叫“边民”。从发现于福建的解放初年的一些材料来看,“边民”在政府文件里泛指所有被认为非主流人群。畲民被叫做“边民”,生活在水面上的疍民也是“边民”。⑥因此,在民国边政研究和其他涉及少数民族研究的论述中,“边疆”是因应“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化政治议程,昭示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生活其间者一概不分族裔地称为“边民”,似“有意地”忽视不同族群的存在,本质上是消解族群文化多样性。 边疆于是成为与“民族”并置的重要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二者几乎可以在认知上相互取代,人们一想起边疆,少数民族立刻进入脑际;一想起少数民族,边疆就成为烘托的背景。此外,有边疆就有中心与边缘,两者的对峙于是可以通过边疆与内陆之间这种外围与中心的关系得以表达。边疆同时也象征着主权,这样就会影响到主流社会人士在考虑少数民族时多了一些想法。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这些知识产品在叙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多有关于边疆的描写与强调,而且社会历史调查的结果都对少数民族所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于是,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落后的文化以及其他相关描写往往与边疆的条件结合起来,更是加强了人们把少数民族与边疆、与落后相联系。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给予少数民族一种另类刻板印象。由于边疆有主权的象征意涵,而主权对我国政府而言是重中之重,边疆也因之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上的特殊类别。 如同因应国家治理之需而划分的民族类别,边疆也是一种封闭的类别。它仿佛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中国的“边疆”与美国的“边疆”(frontier)有着不同的命运。美国的边疆是为人迹罕至的与文明对垒的“蛮荒”之地,它随着文明的进程日渐缩小并最终消失,它不象征着主权。美国人类学家对美国边疆史无视北美印第安人的存在感到不满,提出了边疆也是“文化接触区域”(cultural contact zoon)。⑦随着欧洲和其他大洲的移民遍布了整个美国国土,尽管印第安文化在欧洲裔移民移动扩张的过程大为削弱,但对他们的敌视却也随着边疆的消失而消失。由于边疆在中国的语境里又象征着主权,当这样的象征植入人们的认知系统之后,产生的观念便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取向。例如,在政策制定时,决策者会更多地考虑到主权的因素,从而可能在民族地区的治理上会遇到一些难处。 4.讨论与结论 几十年来,边疆与民族(严格而言是少数民族)之并置并由此而生产的大量著述足见边疆范式之影响。虽然边疆范式在民族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也影响了人们的认知,而这样的认知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实践,如此认知影响下的实践,从长远的观点看,却未必总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上产生积极的后果。因此,对这样的范式应予反思,从它的限制中解套。今天有些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已然成为紧身衣,束缚了学术的思考,而视文化为有边界的整体,这么一种传统人类学文化观今天是否依然有效?这已经成为问题。⑧“边疆”就是这样一种紧身衣。 边疆作为一种类别与“民族”这样一种人口分类有何关系值得思考。我国政府由于国家制度建设的需要,于1953年开启了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对人口进行了分类。关于人口统计和分类的现代性意义,福柯(Michel Foucault)、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安德森等人多有论述,并都将之视为现代政府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⑨我国的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为了让各民族分享权力,以及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意味着在人口分类中有了如安德森所谓的“封闭的系列”(bound serialities)。这一系列中的类别都是限制性的,而且本质上具有冲突性。这些类别造就了族群政治的工具,个体只能从属于一定的类别。因此,封闭系列里的类别虽然不少,但被它们遮蔽或者消解的多样性远超过类别的数目。由于封闭性系列的存在,任何个人只能是“1”或者“0”。这是从“法定身份”上而言的。换言之,如果这些分类与政府的决策有关,那么,各种资源配置原则上也是根据是否为“1”来进行。其实,在“1”之内还有多样性,还有差异,而忽视差异和碎片的“1”也是一种便于政府操作的简单化,而简单化所带来的复杂后果与纠结,正是斯科特(James Scott)所力图揭示的。斯各特认为,为了方便治理,国家采取的做法往往是理性化和标准化,这实质上是一种简单化,它忽视了内部差异,要求一致性,从而导致问题频仍。国家机器无法成功地表现它所描绘的社会的真实活动,也无法了解这些民众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表现的仅仅是官方观察家们感兴趣的一些来自这些社会的片断。⑩ 正如56个民族的构成无法真实地反映我国的族群与文化多样性,边疆的建构也可以在观念上遮蔽地方和族群多样性。边疆既然象征主权,对边疆聚居的少数民族民众就可能有所提防,这就不利于民众的互信,国家的政策就会摇摆于优惠与控制之间。而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国家的首要工作应是民生,即他所言之处理“人与物”(men and things)之间的关系,主权不应是现代国家的首要关注。(11)如果接受福柯的这一观点,我国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不是完全的治理,而是带有管控性质的治理。而对于学界而言,边疆范式的存在会导致学者在治学和研究上形成某种路径依赖。事实证明,这一范式导致了大量研究聚焦于强调“边疆”的重要性,国家主义的取向贯穿于字里行间。有些研究把“边疆”视为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仓储,在话语间仿佛边缘与中心的对峙有助于多样性繁荣。总而言之,边疆已然成为紧身衣,束缚了学者的视野和思考。它与民族的56个类别一样,无视甚至排斥任何碎片性的非整体性存在,给我们带来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民族研究范式的转换亟待摆脱这样的学术范式。 注释: ①参见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962]。 ②参见James L.Watson,Anthropological Overview: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cent Group,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Watson,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274~292。 ③参见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Boston:Little,Brown & Co.,1969,pp.9~38。 ④参见Anthony Giddens,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London:Polity,1989。 ⑤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65~69;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Overseas Chinese and Idea of China,1900~1911,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eds.,Undergroun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⑥参见范可:《“边疆”与民族——略论民族区域自治的治理逻辑》,《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32~43页。 ⑦参见Robert Redfield,M.Herskovits and R.Linton,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38,1936,pp.149~152。 ⑧参见Paul Rabinow,George E.Marcus,James D.Faubion and Tobias Rees,Designs for an Anthropology of Contemporar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⑨参见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1976,New York:Picador,2003,pp.239~264; Partha Chatterjee,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3~26;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London:Verso,1991[1983],pp.163~170; 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Nationalism,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London:Verso,1998,p.29。 ⑩参见James C.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98,p.3。 (11)参见Michel Foucault,Governmentality,Michel Foucault,James D.Faubion,ed.,Power,New York:The New Press,2000,pp.208~222。标签:民族问题论文; 民族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民族研究论文; 范式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