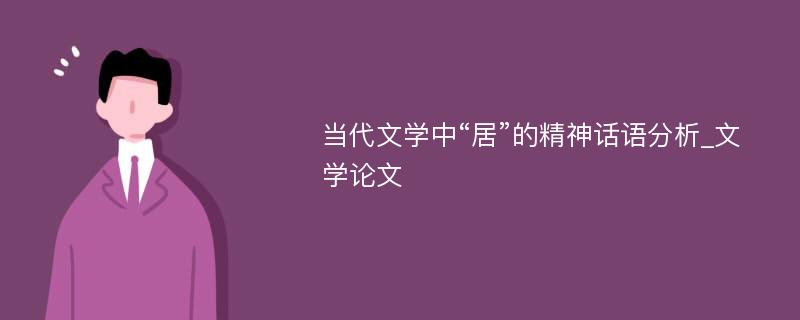
当代文学中关于“居住”的精神性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3—0070—05
西方建筑哲学认为,建筑于人,就是它为人提供了一个“存在的空间”(Existential Space),或者说是一个“存在的立足点”(Existential Foothold)。而中国古老建筑哲学也与之殊途同归,《黄帝内经》曰:“宅者,人之本。”作为人类衣食住行基本生存要素之一,“房子”(建筑)始终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房子”的功能可以被分为基本的和第二位的两种功能,第二位的功能指的就是指示意义和暗示意义的功能。建筑师要通过第二位意义表达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种世界观和特定的精神特质。例如德国18世纪的农舍,清楚地表明了其基本的和第二位的功能,给住在里面的人强烈的家的感觉。① 艾可作为一名十足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建议“建筑师应该把基本功能设计得富于变化,以便给第二位功能留下更开放的空间”。②“房子”的这两种功能——为人遮风避雨、容身居住与心灵的安居之所——始终是一体的。
人同建筑除了具有实用的居住关系外,还存在着一层更加休戚相关的感情关系与精神关系。黑格尔把建筑的起源归结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缘故,而不只是为了纯粹的使用功能。他认为精神家园是圣洁的,是“把大众灵魂联系到一起的东西”。建筑主要是一种象征,表明它隐约感觉到的掌管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神的力量。③ 而更为具有深刻意义的是,海德格尔提出了人类的“安居”问题。他说,“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处呢?通过建筑。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④ 正因为人“诗的创造”同样是一种让心灵得以安居的“建筑”,一种精神乌托邦的诗意建筑,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建筑物之间便产生了默契与共振,作家们笔下关于“房子”的叙事和诗意构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精神上的象征和隐喻意义。
获得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剧本的标题即为《房间》,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中,称作者“强行进入压迫的封闭房间”,指国家权力的扩张逼得个人蛰居在狭窄封闭的空间里,那些来自房间之外的威胁,剧中的戏剧冲突,来自于人与他人所组成的“黑暗”社会之间,“房间”既是避世者的“壳”,也是作家品特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人际关系准则的伦理学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哲学观点,在品特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因此,我们看到这部作品表面缺乏逻辑性的语言对话中所阐释的哲学思想。《房间》成为一个极富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文学文本。
与西方几百年来的精神世界探索的历史和思想传统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的“形而上”精神追求显得相当薄弱和匮乏,普遍缺乏对人类生存/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中国20世纪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站在一个缺乏哲学背景而更多的是政治的和实用的背景的舞台上,自身不能不受到三种明显的局限,即:文学泛政治化进而形成了政治性的基本规约的局限;经验美学的局限,个人创作圈子狭小的局限。”⑤ 在当代文学中,关于“房子”的精神性话语与写实性物质话语相比处于弱势,但我们也看到从新时期初期的探索性戏剧,到新潮小说先锋派文学的实验性写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作家们毕竟在通过创作,孜孜不倦地将思考引向一种更深的、更为本质的层面,其精神探索始终在延续。
20世纪80年代初马中骏等编剧的《屋外有热流》⑥、四幕喜剧话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以及90年代黄蓓佳的小说《玫瑰房间》⑦,都采用了超现实的象征手法表达一种人生哲理、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具有鲜明的象征寓意。毕淑敏在散文《精神的三间小屋》中,罗列出人类的精神空间所至少需要的“三间小屋”,分别用以盛放“爱和恨”、“事业”以及“我们自身”。对“房子”与“人”之间所具有的多重联系的思考及其精神性话语表达,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有所呈现,例如张承志、迟子建以及鲁羊为代表的众多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作品,以及大量以写实为旨归的“非虚构作品”等。
迟子建对房屋有着理性的思考:“房屋不仅是人的休息之所,也是人类表达感情的场所。……房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人类表达自己精神气息的一种象征。”⑧ 除了在小说《旧时代的磨房》中探究过人类的两大基本主题——食与性(“磨房”成了人类最为本能的食与性贪婪需求无法遏制所造成的悲剧性结局的象征)⑨ 之外,她的散文中还多次写到故乡黑龙江漠河一带的木刻愣民居,与自然相和谐的“非同寻常的美感”。⑩ 她对那些无比钟情于抒写和描绘房屋的作家和画家充满敬意。
基于作家本身对“房屋”的理性认识,我们则可以比较清楚地解读迟子建的作品《零作坊》中那些对“零作坊”的描写和粗俗生活表像之下所要表达的诗意梦想。《零作坊》这个极富艺术气息的标题让人对文本的阅读自然产生出一种“高雅”的期待,然而小说开头的第一章就赫然亮出了“屠宰”、“马灯”、“嚎叫的猪”等显得粗俗而野蛮的词语,这不能不令满怀期待的读者扑了个空。然而故事就这样有滋有味地讲下去了,屠宰场不合法的生活就这样自然地铺展开来,带着原始的、粗俗的、浑浊的血腥气息,屠宰台沾满了污血和猪毛、苍蝇满天飞,注水的猪肉、成堆的猪下水……这个私屠滥宰的生猪屠宰场给人的感觉充满了肮脏和罪恶,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和非法的屠宰出卖过程一起构成了小说的现实场景,尽管其中充满了屠夫式的满足和快活,但给读者造成的是视觉和想象的厌恶和反感。那么,在这样一个毫无诗意的甚至是与诗意完全相悖的地点,为何能够成为以“诗意化”写作著称的女作家迟子建所要描述的“居所”?
虽然翁史美是个精明干练、开朗大度的杀猪场女老板,但她性情中始终有着与她农村出身不相符的温柔高雅浪漫气质,正是这些性格中无法摆脱的因素,使她在结婚生子之后还毅然爱上了城里来度假的纪行舟,并抛家别子跟随他进城,然而那场婚外恋以她被伤害而告终。制陶艺人孟十一留下的陶器碎片和雕花廊柱再次唤起了翁史美心中的爱恋,尽管这种爱那么虚幻,但却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同样,这群粗俗不堪的屠夫们也并没有失去质朴真实的人性和对生活的幻想,为爱情而成为植物人的鲁大鹏、爱拍照和写诗的年轻人杨生情,屠夫们相互之间的朴素感情,都成为小说中浪漫诗意的亮点。最终屠宰场的生意无法继续下去,杨生情给翁史美寄来了20多种花种,希望她把屠宰场改造成一个花房——或许这才是“零作坊”应有的身份和气息,翁史美似乎也是与“花房”这种住居相和谐的女性。我们无法知道她是否愿意接纳这包花种,对她来说,将屠宰场改为花房,不幸的、缺乏诗意的生活就此可以结束了吗?迟子建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将小说的结尾提升为一个对人的生存目的进行思考的哲学命题。
“空间”一词古义是“已清理好的,适于定居的地方”。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让人居住的地方和暂时的栖身之地也有很大区别。他是在区分“安居”和“栖息”这两个概念,是真正定居下来还是找一个暂时的栖息地。“建筑”的真正含义是“定居”,反过来,“定居”的意思是“存在、建造”,所以,“定居”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人和空间的关系就是定居关系,这是经过严密思考并传颂下来的。”(11)
郁达夫的散文《住所的话》(12) 描述过对于个人住所的想象,具有20世纪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住居的时代特色。虽然不同时代的房子会有质地样式的区别,但它必定是一种理想生活的载体。正如巴舍拉德(Bachelard)所说的,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深藏有这样一所梦一般的房子,常常在梦中萦绕,从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真实的过去的影子。梦想有这样一所理想的房子实际上是在期望一种更和谐的生活,也就是真正实现心灵的“安居”。(13)
张承志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黄泥小屋》,在当代文坛上引发过不小的震动,其原因就在于作家关于人的精神与心灵寻找“安居”之所的思考,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新探索。“黄泥小屋”既是苏尕三和尕妹妹二人苦苦追寻的具体归宿,又是寄托贫苦农民生活幻想的一种象征。一代代勤劳、善良的农民默默忍受着屈辱和饥饿,各自怀揣着渺茫的希望,寻找那座可以“护住自己心里那块怕人糟辱的地方”——“主给我预备的泥屋子”。伊斯兰教信仰崇拜成了精神血源的强大纽带,成为一个民族全部的希望所在。“黄泥小屋”作为一种象征已在当今文学评论中具有它独特的魔力,成为贫瘠状态下一种精神向往的代名词。
在当代文学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于对理想精神家园的向往,在物质意义上的“屋”还是个难题时,作家们理智地走出物质现实的烦恼,寻找精神的、理想的家园,实现真正的“安居”始终是作家们所要表达的终极目的。宋唯唯的“非虚构作品”《当青柚子落在你的头顶》(14),则探究了人的“故乡”和城市“安居”之间的关系。她相信我们的灵魂必有出发点和终结点,人都需要一个“故乡”,它意味着真正的安居的“家”,对于城市中的房子,作者这样写道:
……我在都市生活中居住的房子,我永远只能称呼它为寓所,而不是家。我的房子是在这北方的城市,一幢高楼里的某一层,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它的地板是低一层人家的穹顶,它的天花板以上则生息着陌生的日子。楼梯上相遇的是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语种的人们,唯一的姿态是擦肩而过。我的寓所从来只放置着简单的家具,使用的书本和农物。它只能用来生活,寄放我们的躯体和年轻时候的一些生活。我们注定彼此互为客栈与过客。……而在这人山人海当中,我从不能安之若素地生活,我害怕的东西是那么多,屋子里错综复杂的管道,电,煤气,水,大门以及门外的敲门声。
作者所表达的无根的漂泊感,害怕在城市中迷失自我的恐惧感,使她时时要用一种“回返”的姿态面向故乡,而不甘心在“半空中”——这既是城市居住的普遍现实景况又是作者心灵无根的所指——某一间房子里静默地度过一生而没有丝毫的声响和变化。作者以诗意的语言,叙述了人类生存中一个恒常的主题:寻找与回归。
关于“安居”思考的另一面就是作家对于无法安居的焦虑表达。鲁羊的小说《在北京奔跑》没有一贯的双重叙事,也没有一贯缓慢而悠长的情绪梳理,整个小说被一种“奔跑”简单地占用了。鲁羊还有一篇小说《出去》,这篇小说以“我们怎样才能把屋子改造得可以居住呢”开题,“屋子”在新生代作家的意识中是“无法居住”的意思,因而在《出去》中主人公马余有着一种近乎强迫症式的“出走”、“出去”、“离开”的感觉和冲动,然而出去之后又能到哪儿呢?事实上他最终的结局只能通过酩酊大醉而“从自己出去”。他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是连自己的世界都找不到,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定居之所,在这个世界“尚未定居”并将永远地处于“奔跑”之中。
徐星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中,也写到了人们在世界上寻找精神之所的过程,“出门、回家、出门、回家,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节奏,一种生存方式。”(15) 两个可以被称作堂吉诃德式理想主义的流浪汉,希望可以在世界某地寻找到生活的真谛。“多年来我就这么胆怯懦弱地张望四周,想找到那一小块悲哀的、传奇似的地方,哪怕那只是一小块地方,仅够我用来跪下祈祷,因为我根本说不清我找那块地方干什么。于是我就心怀鬼胎地在这片巨大的、悲哀的土地上乱转,这是抽象意义上的理解,具体说也许就是因为我根本不敢面对面问问自己——你到底是谁?”(16) 对那“一小块地方”——用以“安居”的空间寻找是一个充满艰难的未知过程,寻找的结果依然是虚无与绝望。
除了对无法定居的焦虑和虚无情绪的书写之外,也有作家在面对艰难生存状况的同时,对自身的“安居”诉求进行冷静理智的反思,从更为深层的哲学角度俯瞰现实。柳宗宣的散文《我住过的房子》(17) 有着沉重而飞扬的哲思和神妙直指内心的文字表达,仅从朴素的题目当中你便会感到一种思想的力量。
作者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他还是一个思想者。或许“诗”与“思”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们都是能够超越物质现实而抵达神性殿堂的途径。作者在书写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不同房子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仅仅只是童年、青年时期的成长与追求,不仅仅是自愿过着的漂泊动荡、居无定所的生活历程,我们透过诗人诗意化的笔墨文字和蒙着一层轻纱的回忆,看到的是关于自然、生命、诗意栖居的思索。经过了乡村校园的教书生活,到郊区租赁民宅的过渡,直到拥有了一幢楼房的顶层,作者进入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他总想走出隔墙,到外面的世界寻求自己的理想。“一个人在窗前张望窗外,发现自己身体在室内在此地,精神却行走在异地在远方。”于是,39岁的他拖着漂泊的旅行箱开始了“北漂”生活。不同地方的居住赋予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的体验,他既想在城市里享受都市文明,又渴望拥有在田园里获得的自然的抚慰。
“住地”在作者心中的记忆是和他热爱的写作分不开的,“只有留下文字的生活才是让人难忘的”,留下文字的地方似乎也留存下生命的一部分,刻下了活着的痕迹。回到旧地,他感受到的是时间的无情和勇敢选择的正确性,对于过去的房子“我”已经成了陌生人,旧居给人的空洞感让“我”觉察到在此地灵魂的缺失。作者把“房子”当作建立内部世界的一个根基,就像荣格那样,开始面对他的“第二人格”及其内部世界。外部工作和内部愿望同步进行,当整个城市面临突发疾病的巨大灾难之时,除了要关怀更广阔天地里的生命之外,作者通过精神性话语的写作和坚定的信仰来战胜内心的恐惧,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诗意的栖居”。
所谓“以人为本”的建筑,营构人性的建筑空间,其核心都是追求“自在”和“家”的心境。谁能诗意地栖居于广袤的土地上?那就是能够使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得到真正“安居”的人吧!
收稿日期:2006—01—06
注释:
① 尽管农舍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怀旧之情,但时代发展了,人们已学会要求有更多的自由、更开放的空间。
② ④(11)(13) [美]卡斯藤·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9—91,138,150—151,194页。
③ Christian Norberg-Schulz,Intentions in Architecture (Cambridge:MIT Press,1965),p111,See also pp112—114.
⑤ 杨匡汉:《倾向与启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山花》2004年第11期。
⑥ 《剧作》1980年第6期。
⑦ 黄蓓佳:《玫瑰房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⑧⑩ 迟子建:《房屋杂谈》,见《清水洗尘》,中国文联出版社(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2001年版,第306,309页。
⑨ 迟子建:《你一直对温柔妥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2) 《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
(14) 《大家》2004年第1期。
(15)(16) 徐星:《剩下的都属于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1,42—43页。
(17) 《大家》2004年第5期。也许“散文”这个概念已经不太适合新时代文体发展现状,《大家》杂志将思想含量较高的散文命名为“非虚构作品”。
